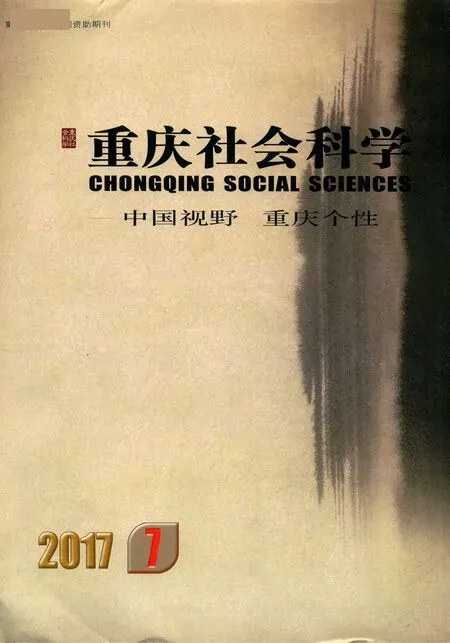社會系統理論視角的農村社區管理*
陳 強 林杭鋒
社會系統理論視角的農村社區管理*
陳 強 林杭鋒
加強農村社區管理是現階段我國社會管理的重要課題。文章回顧了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及其特征,并對農村社區管理進行了再思考。從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農村社區顯然是客觀的,在封閉的同時又具有開放性;在強調自主性的同時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在推進農村社區管理過程中,必須將農村社區當作一個客觀存在的系統并予重視,在推動農村社區系統內部管理主體和管理機制的自我成長,也要為農村社區管理建立具有張力的、良好的外部環境,并通過有效的引導,實現系統內外要素的充分互動,從而實現農村社區的“善治”。
盧曼 社會系統 農村社區管理完善
農村社區既是社會的有機構成,也是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丁元竹認為 “社區應該是指可以滿足居住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基本需要的居住區。”[1]費孝通先生把農村社區描述成一種“禮治秩序,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及熟人社會;無為政治,基層社會結構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構成的網絡。”[2]詹成付等人認為,“農村社區是農村基層管理與服務的基本單元,是聚居在城鎮以外的一定地域范圍內的、具有一定互動關系和共同文化維系力的人口群體和社會組織,是農民長期居住、生產和生活的社會區域共同體。”①陳圣龍:《農村社區組織管理體制研究——基于對60個 “全國農村社區建設實驗全覆蓋示范單位”的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劉長明認為,農村社區“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主的,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以農民為居住主體的,具有文化的同根性,習俗的相近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①劉長民:《山東省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與發展研究——基于對德州市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考察》,中國海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可見,關于農村社區的定義尚未形成一致,但人們都認同其就是一種基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自然規律而形成的,包含了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產、生活設施,有一定的成員認同感,是一個融合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多種功能在內的社會系統。一般來說,作為社會的構成,農村社區通過自身的生產與活動以及與其他系統的交換,來維持自身的發展,并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變遷,因此,有必要加強農村社區的管理。
農村社區管理實際上就是社區管理的一種形態。而何為社區管理,目前學界并沒有形成共識。王金榮(2012)把我國社區管理的概念分為四種類型:從歷史的角度來講,社區管理是不斷演變的;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講,社區管理就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公益性的目的而對社區進行的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的過程;從管理的目的來講,社區管理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這一目標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公共性;從管理的角度來講,社區管理依托社區中的各類主體廣泛參與,它要求不同的主體在這一過程中“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張興杰把社區管理定義為“在社區范圍內,由社區內的基層政權組織、企事業單位和社區群眾為維護社區整體利益、推進社區全方位發展而對社區的各項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的自我管理。”[3]汪大海等人則認為,社區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導下,社區職能部門、社區單位、社區居民對社區的各項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進行的自我管理。”[4]在實踐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農民的需求模式、需求內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雖然黨和政府通過完善村民自治、村務公開等諸多措施完善農村社區的管理,并最終形成了政府主導,企業主導,民間組織,政府、社區互助,政府、社區、社會互助等五種類型得農村社區管理體制[5]。然而,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經濟社會轉型的加速,最終引發了農村社會內部結構的變遷,這又進一步導致了現有農村社區結構與傳統社區管理體制之間的摩擦,使得農村社區管理面臨嚴峻的挑戰。于是進一步推進農村社區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已經成為我國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那么,在這一過程中,如何理解和認識農村社區?又如何重構農村社區管理機制?這顯然亟待我們探討。我們以為,作為觀察和理解現代性的一種理論,盧曼②盧曼,也譯為魯曼,全名為尼古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是德國社會理論學家,也是當代社會系統理論的創始人。的社會系統理論顯然給我們解答這些問題提供了很好的話語和視角,這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
一、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及其核心要點
在構建主義理論的影響下,盧曼重新修正了社會現象的觀察方法,并建立了“系統自身的觀察理論”,即“二階觀察”理論,對社會諸功能系統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觀察與探索。1971年,《社會的理論或社會技術——系統研究提供了什么?》文集出版,該書記錄了盧曼與哈貝馬斯關于社會理論或技術等方面的爭論,也對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1984年,奠定了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的基礎《社會諸系統》的問世,標志著社會系統理論的形成,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一)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回顧
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體系十分龐大,在社會學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一理論是建立在對現代社會全方位分析基礎上的產物,對于認識、解讀現代社會及推動現代社會的治理具有重要意義。在我國,許多學者對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及其實踐應用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一些學者如丁東紅、肖文明、高宣揚都比較系統地研究了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肖文明認為,“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為我們觀察和理解現代性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理論話語和視角。”[6]高宣揚則認為,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運用獨特的視角,揭示了社會的復雜分化情況。而從實踐應用上看,吳澤勇(2004)、翟小波(2007)、泮偉江(2014)等人利用該理論對法律方面的議題進行了研究,葛星(2012)利用該理論對媒體、媒介進行研究,劉力鋼 (2004)利用該理論對企業管理,楊麗茹(2009)和吳立保(2010)分別利用該理論對教育、大學生工作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是,既有文獻幾乎沒有運用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對社區治理的問題,從這一理論研究農村社區管理問題的成果更是幾近空白。實際上,作為一種社會構成,農村社區具有典型的系統的特征,在對農村社區進行管理的改革與創新的過程中,顯然需要我們在全局的角度對其進行思考。因此,利用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研究我國農村社區管理問題,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
(二)社會系統理論的主要觀點
1.社會系統是客觀存在的
理論與經驗都證明,社會系統是客觀存在的。這種“系統”,不僅是社會學上的一個分析概念,也是一種現實經驗的存在。按照盧曼的說法,人類的生活與活動,導致了系統的出現,“一方面正是人類社會的特征,決定了社會的系統性;另一方面又是人類觀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模式,決定了系統的普遍性……社會始終是作為社會系統而存在的。”[7]事實上,系統不僅普遍存在,并且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思考與生活。這就要求我們在看待任何一類事物的時候,應當將其視為社會系統并用系統的分析方法研究這一事物。
2.強調系統與環境、封閉與開放的關系
一般系統論十分強調整體和局部的關系。然而,盧曼的社會系統論獨樹一幟,更強調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這種從整體與部分到系統與環境的轉變,也促成了社會系統理論范式的第二次轉變。盧曼認為,“系統理論是以‘系統和環境的差異的統一體’為出發點的。環境對于這樣的差異結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契機,因此對于系統來說,環境具有不輸于系統本身的重要性。”[8]也就是說,系統與環境兩者之間,同等重要且相互依存。當然,這種同等重要且相互依存的關系,并不代表著系統與環境之間完全開放,他們之間也存在一種界線:這種界線就是基于封閉性的開放性。盧曼認為,系統首先是封閉的,只有封閉,系統才能進行自我組織、調整、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而后才能對環境開放;只有開放,系統才能得到更新與發展,否則,系統與環境之間的依存,也就無從談起。
3.社會是一個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系統
盧曼用“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替代了一般系統論中的“輸入—輸出”系統。“自我指涉系統通過將其與環境不斷區分開來的過程不斷指涉自身,而這一過程也構成了功能分化的過程……強調了諸系統的自主性和它們之間的差異。”[9]而根據盧曼的自我再制系統理論,“功能系統只能自我調控,無法由外部加以調控,而且一個系統正常操作的前提是,其它的系統亦能正常操作,履行其各自的功能。”[10]事實上,個體正是憑借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運作,實現其主體性,從而也區別于其他系統。“在這一過程中,主體性是不受制于外部環境或其它系統的。外部因素或其它系統的作用只限于提示一些可能的自我確認方式,只有當個體或系統接受了這些提示,并將其納入自我再生運作中時,這些外在的影響力才有意義。”[11]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中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強調了內因在事務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差異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差異性的存在,世界的豐富多彩才得以實現,而這也造就了不同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形式多樣的聯系。
二、作為社會系統的農村社區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村民生產與生活的共同體的農村社區,實際上是客觀存在的。借助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視角對“農村社區”的內涵進行再解讀,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充分地把握農村社區這一系統的內在特征及其與外部之間的聯系,從而正確地認識和解讀農村社區。
(一)農村社區:客觀存在的社會系統
聚落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人類生存的需要。農村社區則是人類最早的聚落。雖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城市成為人類社會的主要“聚落”,非農產業生產成為人類主要的生產活動,其在人類生產與生活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與之相反,農業生產愈加顯得輕微,比如,世界銀行的相關資料顯示,2014年美國的農業生產總值僅占全美GDP的1.45%,同年我國農業生產總值也僅占9.16%。但作為承載著農業生產功能的農村社區,其本身不會輕易消失,比如,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已經實現了工業化,但是農村依然分布廣泛,歐美國家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的現象;我國雖然已經成為工業大國,但是,農村、農業與農民依舊在我國社會發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實際上,“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無可回避的問題,也是我國民族復興偉大事業成敗的關鍵。201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而要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對農村社區這一承載著農業生產、生活在內的多種功能的社會系統進行系統的,科學的“再造”,從而建立一種完善的管理機制,助力農村社區的發展。
(二)作為系統的農村社區的兩個面向:封閉與開放
作為社會系統的農村社區在“系統—環境”的框架下通過“封閉—開放”的機制來維持系統的運作。所謂封閉,是指系統具有不容其他系統介入并篡改“編碼”的自主性。農村社區作為一個社會系統,明顯具有這種封閉性: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農村社區有固定的成員,有特定的文化,生產、活動方式,管理風格和權力運作模式,這也是其成為農村社區以及區別于其他系統的重要因素。也正是這種封閉性,使其能夠在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外部環境中,保持自身的特點,維持自身的秩序,形成自己的特色。當然,它又具有開放性,肖文明認為,“封閉性并不意味著系統是遺世獨立的,相反它與環境中的其他社會系統有密切的關聯,存在一種所謂的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關系,系統是開放的系統,它開放地承受著其他系統對它的刺激和影響,但這種開放關系并不同于傳統的輸入與輸出模式,后面的這種模式更強化的是系統間的相互依賴。”[12]實際上,農村社區這一系統承受著外部環境的各種“刺激和影響”,并與其他系統緊密聯系,比如自然環境系統、生產資料市場系統、銷售市場系統發生變化的時候,農村社區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就需要進行調整,如果社會政策發生了變化,比如國家提出要推進農村社區建設,那么,農村社區中的權力結構和管理方式就可能發生變化。所以,在推進農村社區管理過程中,就應該注意從內、外兩個角度思考問題。
(三)作為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的系統農村社區:自主性與多樣性
系統通過自我指涉和自我再制,以此形成和維護系統的自主性或者自我特質。雖然外部環境可以通過“溝通”的方式,影響系統邊界的內部要素,但如前所述,這些因素必須得到內部要素的接受并進入自我再制的環節,才能發揮其作用,這也導致了農村社區的多樣性。比如,同樣一個地區的農村社區,雖然有同樣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和制度安排,但是,每個社區的“個性”卻不盡相同:民風淳樸或民風彪悍;以傳統農業生產經營為生或以外出務農務工為生;社區管理民主或管理獨斷等。可見,外部環境的相似性并不否認社區的獨立自主和多樣性。究其原因,正是由于系統內部要素的不同及其對外部因素的“主導”:對外部環境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最終形成了農村社區的差異化與多樣性。這就要求我們,在對農村社區進行管理的時候,應該“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應當把每個農村社區當作是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個體,承認其差異性,并通過民主、科學的途徑與農村社區內部的要素有效“溝通”,獲得系統內部的認可和接受,從而影響農村社區的變遷過程。
三、社會系統理論對農村社區管理的啟示
從社會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農村社區作為一個系統,顯然具有社會系統的特征。其是客觀的,在封閉的同時,又具有開放性;在講究自主性的同時,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征。因此,我們在推進農村社區管理過程中,必須注重從系統的角度理解和觀察這一系統,并運用系統的思維與方法重構農村社區管理機制。
(一)重視農村社區管理:從邊緣到重心
黨和國家十分重視農村社區的管理工作。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把農村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但是,由于農村社區地理區位的局限以及在趕超戰略①張雙娜(2006)認為,趕超戰略是指發展中國家高度動員有限的資源,依靠工業化實現經濟增長的戰略。新中國建立之后,在國內外壓力下,為了盡快擺脫貧苦落后,實現四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我國實施趕超戰略(參見張雙娜發表于2006年第1期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學報》的《我國趕超戰略的代價分析》)。的影響下,我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向來以城市建設、GDP、經濟發展為導向,而輕視農村社區建設與管理,以致于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社會的演進過程同時也就是農村社區建設的邊緣化、真空化的過程。”[13]然而,從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來看,農村社區是客觀存在的,從我國社會發展來看,農村社區的發展是我國現代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此,正視農村社區的客觀存在性,構建一個主體多元,功能齊全完善,發展健康有序的現代化的農村社區,應當說,是推進我國現代化發展,實現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到地方管理層面上,都應當重視農村社區的管理,將重心回歸到社會建設上來。
(二)轉變農村社區溝通方式:從單向溝通到互動溝通
按照盧曼的觀點,內因是系統變遷的關鍵,外部要素只能透過“環境”,與內部要素適當地溝通,才能影響內因并發揮作用。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農村社區管理的過程中,必須從單向溝通轉變為互動溝通。單向溝通速度快,但是其不足也十分明顯:“單向溝通中的意見傳達者因得不到反饋,無法了解對方是否真正收到信息,而收受者因無機會核對其所接受的資料的正確性,內心有一種不安和挫折感,容易產生抗拒心理。”[14]所以,在推進農村社區的管理過程中,必須轉變溝通的方式,通過有效互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從而增進了解,形成共識,最終實現對內部要素的有效影響。這就要求我們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首先要尊重村民在農村社區治理中的主體地位。村民是農村社區的主體,也是農村社區管理的客體,因此,必須認真傾聽村民的訴求,并創造條件,完善制度,鼓勵和支持村民對本社區治理的參與。其次要在平等的基礎上,以合理而有效的程序制度為保障,推進農村社區的協商治理,從而通過充分而有效的辯論、討論等方式,實現對話雙方的有效溝通,最終達成共識,以獲得村民的理解和認可,獲得村民對社區管理的服從與支持。
(三)完善農村社區內部治理:從不成熟到成熟
農村社區內部的有效治理,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制度,多少方法,也不在于為農村社區管理提供了多少資金,而在于農村社區治理機制的成熟與完善。因此,加強農村社區管理,應當使社區的內部治理從“不成熟”走向“成熟”。②這里借用了克利斯·阿吉利斯的 “不成熟—成熟”理論,他認為人的個性發展,是一個不成熟到成熟的連續的發展過程(參見畢蛟發表于1998年第2期《管理現代化》的《阿吉里斯與“不成熟—成熟理論”》一文),社區治理機制的發展,也是一個從不完善到完善,不成熟到成熟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一要在堅持和完善農村社區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地位的條件下,優化農村社區的治理結構,不斷完善社區中的非政府組織(如村委會等)的建設,提高其獨立性和權威性,強化其在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完善農村社區的治理制度。要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一步完善村務決策、執行與監督機制,強化村務公開,進一步暢通村民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規范社區治理各個主體的權力和責任,推進社區的有效治理。三是要提高村民對社區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治理參與能力。社區是社區的成員的共同空間。沒有社區成員的認同和參與的社區治理,是不成熟的治理。這就要求在強化對社區成員的引導和教育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根據地方特色和實際情況,創造條件、創新機制、完善制度,從而理順居民與自治組織的關系,提高居民參加社區建設,參與決策過程,監督執行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優化農村社區管理的外部環境:從“標準化”到多樣化
管理追求效率、經濟。在管理的范式下,管理主體受工具理性影響,通過權力、資源和制度對管理的客體進行控制,從而尋求以更少的“消耗”實現某種目的。應當承認,工具理性在現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所具有的非人格化特征、效率優先邏輯,追求形式合理性,對于管理的現代化、合理化,政治生活的規范化以及權威的合法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具理性所具有的過度理性、工具化、精細化與計算化的特征,導致我們在推進社區管理的時候,習慣于“統一”“標準”“一刀切”,用一種思維去分析不同的系統,一種制度去管理不同的客體,用一種手段去處理不同的事情,這種“標準化”的外部管理環境,對于多樣化的社區說,顯然是不夠的,也無法適應多樣化的農村社區的需求。因此,面對存在差異化和多樣性的農村社區,政府應當從工具理性轉向 “價值理性”,承認農村社區的差異化和多樣性,充分認可和尊重不同社區的現狀、文化、風俗和利益訴求,并據此設計不同的管理形式、管理方式形成不同的管理風格,從而為農村社區管理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五)改變農村社區管理的手段:從控制到引導
國家基于實現一定的秩序的目的而對社會進行控制。然而,控制卻存在一種失靈悖論。張康之認為,“近代以來的情況顯示,政府往往試圖通過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去提供社會秩序,然而,卻經常性的陷入社會失序的境地……所以,一個控制導向的政府并不能真正贏得其治下的社會安定,即使有著強大的暴力機構做后盾。”[15]因此,在對農村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政府應當通過引導而非控制的方式,從而獲得農村社區這一系統內部不同主體的認同和接受。這首先需要政府一方面做到“簡政放權”,還權于社會,避免對社會系統的過度干預和控制,推動市民社會的發展,提高社會的自我管理與自我成長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切實的從具體的行政事務過程中抽離出來,從“劃槳”到“掌舵”,實現對社會的價值的有效引導。其次,在推動農村社區管理的過程中,要站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上,通過制度的頂層設計,為農村社區治理制定“元”戰略,提供戰略方向的引導和規劃,具體到農村社區治理來說,就是要在制定農村社區治理“元”政策的基礎上,繼續鼓勵和支持社區自治,通過農村社區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與自我服務實現社區的成長。
四、結論與思考
不能否認,農村社區管理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的研究及其應用也頗多。但從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管理,則顯得較為稀少。因此,從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考察農村社區管理問題,確有其理論意義,也為我們完善農村社區管理提供了新視角: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在推進社區管理的時候,更側重從外部的角度來為社區管理提供不同的驅動,而忽視了作為社會系統的農村社區其所擁有的自主性。然而,從社會系統理論的角度來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系統,農村社區通過封閉性維持自身的特征,通過開放性與外部環境進行交流,外部環境只能通過“溝通”的方式,獲得系統的認可和接受。所以,在重構農村社區管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以“社會系統”的觀點與方法,審視、反思農村社區及其管理:重視農村社區的管理,認識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加強其管理的必要性,必須注重農村社區管理的多樣性、靈活性,注重引導與溝通,注重內部要素的成長與發展。
應當承認,在社會系統理論視角之下的農村社區管理的具體方法,還有待進一步思考和論證。盧曼本人也認為,社會系統理論本身并不是一種“單純的觀點上的”分析工具,所以本文的觀點只是基于觀察而得到的思考,其并不能直接操作,但這并不能否認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的獨特價值,也不能否定其對我們重構農村社區管理的啟發。顯然,推動農村社區管理創新,實現農村社區管理的“善治”,需要我們“擺正”立場,也需要我們借助該理論,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農村社區管理機制。
[1]丁元竹:《社區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9頁
[2]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22~23 頁
[3]張興杰:《社區管理》,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5頁
[4]汪大海等:《社區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 9頁
[5]李增元 田玉律:《農村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創新》,《重慶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第29~34頁
[6][9][12]肖文明:《觀察現代性——盧曼社會系統理論的新視野》,《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5期,第 57~69 頁
[7]高宣揚:《魯曼社會系統理論與現代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頁
[8]葛星:《N·盧曼社會系統理論視野下的傳播、媒介概念和大眾媒體》,《新聞大學》2012年第3期,第7頁
[10]張嘉尹:《國家理論——系統理論的觀點》,《淡江大學法政學報》1985年第5期,第87~107頁
[11]丁東紅:《盧曼和他的社會系統理論》,《世界哲學》2005年第 9期,第 34~38頁
[13]殷翔:《農村社區的邊緣化及其重建的路徑依賴》,《社科縱橫》2004年第8期,第69頁
[14]陳莉:《管理中的有效溝通》,《企業文明》2001年第6期,第16頁
[15]張康之:《公共行政的行動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40~241頁
(責任編輯:張曉月)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Chen Qiang Lin Hangfeng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management of our country.The article reviews the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 and reconsiders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The paper argues that rural communities are a typical social system,which is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It has its closeness and meanwhile it has its openness,which shows its autonomy as well as diversity.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the rural community must be regarded as an objective system and must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the internal governan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the favorable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should be built for the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guidance should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let these inner elements interact fully and finally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Luhmann,social system,the perfect of rural community management
三亞學院法學與社會學學院 海南三亞 572022
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2016年度規劃課題“三亞行政區劃調整過程中的農村社區管理問題研究”(批準號:HNSK(ZC)16-3);海南省教育廳2015年度規劃課題“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研究——以三亞為例”(批準號:Hnky201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