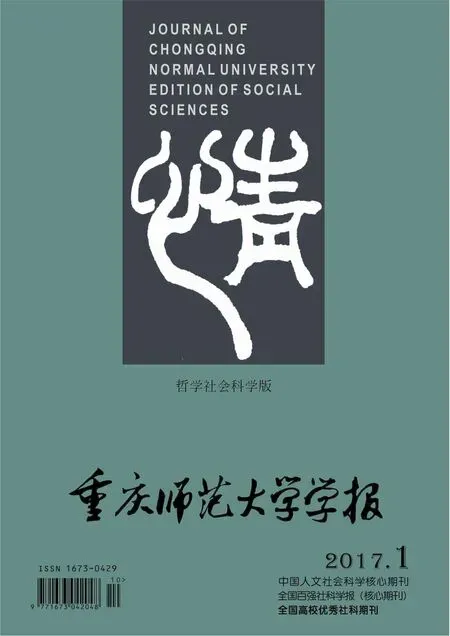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董澤芳教授教育社會學思想中的特質
胡 春 光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長沙 410205)
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董澤芳教授教育社會學思想中的特質
胡 春 光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 教育科學學院,長沙 410205)
董澤芳教授是我國教育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對我國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縱觀先生的教育社會學思想,其鮮明的特質就是“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先生倡導及踐行的創新取向的本土化,從研究方向上說,是走向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究;從研究內容上說,是指向教育社會問題的本土化研究。先生秉持“創新取向的本土化”,使先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呈現出強大的理論與實踐生命力,為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從“西化”走向“化西”樹立了研究典范。
董澤芳;創新取向;本土化;特質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學作為資產階級偽科學被打入“冷宮”,教育社會學與社會學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也進入了長達30年的停滯期。改革開放后,科學的春天來臨,教育社會學才開始重新獲得了生存與發展的權利。董澤芳教授是我國教育社會學學科恢復重建期的先驅,先生長期擔任中國教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對我國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恢復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先生從1984年開始從事教育社會學的教學研究工作,經過七年的學術積累和實地研究,先生于1990年完成專著《教育社會學》[1]。該書出版之后,立即被全國許多師范院校選作教材,多次印刷再版,并獲得了中南地區優秀圖書二等獎,湖北省優秀教材一等獎等榮譽,成為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經典之作。其后先生陸續發表《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新論》《關于社會轉型期教育社會學使命的思考》《從二元對立到多元綜合——教育社會學方法論的歷史演變》《我國大陸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與演變(1979-2005)》等系列論文,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理論和研究框架。先生在多年潛心研究的基礎上,于2009年出版了新編本《教育社會學》,此書突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理論體系建構,注重了對教育社會學學科基礎問題的探討,加強了對重大教育社會問題的研究,是我國教育社會學人在新世紀對教育社會學進行本土化研究的一個典范。縱觀董澤芳教授的教育社會學思想,其鮮明的特質就是“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正如先生所言:“為了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必須加強教育社會學中國化的研究”[2]19,“追求本土化特色,既是尋求民族文化認同、擺脫‘學術殖民’陰影的要求,也是獲取學術獨立地位、實現學術社會價值的要求。”[3]
一、創新本土化:走向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究
“本土化”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基本上是與第三世界“現代化”的過程息息相關。眾所周知,十六世紀西歐發展出現代性原則,隨著西方先進國家在全球政治版圖中優勢地位的確立,這些現代化原則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姿態強壓在其他非西方社會中。這些原先以具有傳統的非西方文明乃自愿或被迫卷入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中,此時現代性的普遍原則就會與原先本土的傳統生活世界產生極大的捍格與張力,這些捍格與張力就是非西方社會產生本土化運動或訴求的基本歷史處境,關于本土化的論述是深植于現代性的視野中的(不管是贊成現代性還是反對現代性),本土化正是對現代性的回應。
教育社會學作為興起于西方的一門學科,當其在我國本土生根茁壯,必然也會遇到上述所言之捍格與張力。我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一直處于忙于吸收西方研究成果,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發展模式,似乎已經忘記將我們自己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社會實際情況反映在研究活動中。在缺乏自我肯定與自我信心的情況下,長期過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動的結果,就是使我們的教育社會學研究缺乏個性和特征,不少研究淪為西方理論的解讀及行為科學的注腳(如常常引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伯恩斯坦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等來研究中國的教育問題等),這樣的研究對西方社會的理論也許有所啟發,或者成為西方理論的特例,即使研究有所貢獻,卻也只是貢獻于西方理論的驗證與否。引用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結果,不僅讓我們成為觀察實驗的受試者,其結果也在強化西方對我們的認識論,證明著西方理論的普適性,這不只是讓西方取得文化解釋的發言權,同時我們也患上了“學術失語癥”。如果我們妄想通過這樣的研究來認識我們自己的教育問題,不但失之于片面甚至于會造成扭曲。如果中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要避免成為西方學術界眼中的“人類學櫥窗”,身為研究者更應理解問題是會隨著國情文化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這需要我們勇敢地對西方理論作出修正與批判并與之對話,“增強同國際教育社會學界對話的能力”[3],建立我們研究自身的主體性,而不是滿足于擔任學術的“貿易商”和“代理商”的角色。遺憾的是,我們從來不曾見到有過研究顯示,運用西方的社會學理論在研究中國教育社會問題時會發生謬誤,進而推論出這樣的西方社會學理論不適于中國。在我國教育研究上,只要是西方有新的理論出現,國內馬上就有學術販子引進,只要誰引進占得先機,誰就有可能在學術地位上占有一席之地。董澤芳教授正是有這樣的學術反省、思考和憂心,才鮮明地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要特別重視教育社會學的本土化問題。”本土化的問題,不應該“只是”在本土作經驗研究的問題,中國過去教育社會學許多所謂的“本土化研究”,大多還是直接用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實證的方法)來探究中國本土的教育問題,研究者對于這些理論和方法背后所隱藏的西方人的世界觀與身心狀態,不是毫不反省的接受,就是有意加以忽略。對此先生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教育社會學是在一種特殊的國情和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建構的,我國社會與教育發展所面臨的形勢,所選擇的道路都具有特殊性,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各種新的教育社會問題,很難用過去的理論框架來解釋,更難用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說明。”[2]20先生這段話告訴我們,本土化研究不能夠不反省所使用的理論、方法、概念架構,甚至是界定問題意識的出發點;本土化研究必須要注意到社會的特殊性,要掌握這個社會中個人的世界觀、身心狀態以及行事邏輯,而不是一味的以華麗的概念、漂亮的理論套用在本土的教育現象上來解釋。教育社會學發端且成熟于西方,合理移植與學習借鑒其理論與方法是必要的,但各國的教育社會問題的性質、原因與解決方法不盡相同,歷史表明,一切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本國的國情才會有生命力。因此,引進吸收國外教育社會學理論與方法不能盲目復制和照搬,必須與本土化過程相結合[4]。
先生抱著“建設具有中國特色教育社會學”的堅定信念,不僅強調要進行中國教育社會學的本土化創新研究,還一直主張中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要特別注重“中國特色”的打造,走“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之路”。先生認為:“‘中國特色’比‘本土化’內涵更豐富。‘中國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幾點:在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上,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觀點與我國當前的教育社會改革實踐相結合;在學科發展的方向上,要把立足國情與面向世界、關注現實與開展傳統相結合;在學科發展的內容上,要充分考慮中國社會與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復雜性,把統一性與多樣性、民族性與國際性結合起來。提倡‘中國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過程的片面性與狹隘性。”[3]先生進一步說道:“在強調‘中國化’研究的同時,要防止將眼光只盯在‘適應于中國國情’上的片面化傾向,而應同時面向世界,繼續有重點地翻譯、介紹和評價外國的研究成果,反思國外的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適用性,盡可能從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的教育社會問題,增強同國際教育社會學界對話的能力。”[2]19總之,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究只有立足中國國情,從研究我國當前各種最緊迫的教育社會問題入手,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融合百家之說,博采眾國之長;在不脫離世界總趨勢的情況下,講“中國特色”,才會有出路[4]。
教育社會學的“本土化研究”可以從三種不同的取向來理解。第一種取向是“意識形態取向的本土化”。這種取向將本土化視為對文化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立場的選擇,基本上這是屬于一種政治運動或社會文化運動層次的本土化,例如所謂的全盤西化派、文化保守派、自由主義等。第二種取向是“實證取向的本土化”。這種本土化取向與第一種不同,它不關注是否應對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立場進行選擇,而是把重心放在我們是否能更真切地理解本土社會的真實情況,基本上這是屬于一種學術層次的本土化反省。本土化在這里被視為對本土社會進行經驗研究的一種實證研究,也即本土化是一個真切且如實地理解本土社會實際的歷程,在研究過程中可以大量運用西方社會人文科學的概念工具來理解本土社會,當西方學術工具不足時,也可使用本土文化的概念來發展本土化的經驗理論,但是最終仍需遵循西方科學實證主義的方法原則。第三種取向可稱之為“批判取向的本土化”。這種取向將本土化視為對西方現代性原則進行深層反思、解構及批判,并謀求另外的可能出路。第三種取向十分關注西方現代理論與本土生活世界之間的鴻溝與縫隙,以及兩者背后不同的意識形態預設與不同的身心狀態,它常常以對西方科學與學科體系之反省為本土化研究的起點,所以充滿了批判的性格。因此,批判取向的本土化,重點也不在于研究者要采取何種價值立場,而在于對西方學術中所內涵的各種現代性原則進行檢視與反思,尤其是對這些學科知識霸權中所隱藏的權力宰制關系進行揭露與批判,例如對西方學術體系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客觀普遍主義以及東方主義等的批判。批判取向的本土化除了對西方現代性及學術體系進行毫不妥協的批判外,也試圖在現代性的邊界上,尋求各種新的可能性與出路。先生倡導和踐行的本土化研究其實就是以上述第三種“批判取向”的本土化研究為基礎,生發出一種獨特的本土化的進路或態度,筆者將其稱之為“創新取向的本土化”。此種取向的本土化極具反思性功能,它以顛覆西方知識為中心,過去固態科學理性所形塑的種種夸稱具有普遍真理性的思想、認知和知識體系為己任。作為一種理性的心智活動,本土化是運用本土所累積、形塑文化認知的歷史經驗,以擺脫、修飾或超越西方知識體系幾近全盤壟斷的狀況,并進而樹立、實踐具有獨特性的理解和詮釋風格,乃至知識體系理想正當化的過程。正如先生所說:“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觀點為指導,從研究現實的各種教育社會問題出發,按照各種問題自身形成、發展與解決的邏輯順序,進行深人地實證性研究,理清其脈絡,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規律,探索其解決對策,逐步積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資料,并注意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在此基礎上才能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與知識體系,才能將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國現實的土壤,才有可能生發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理論。”[3]
先生不同意第一種取向將本土化視為一種西化、反西化或其它意識形態的立場選擇,因為真實的情況遠比簡單的立場選定復雜得多。身處全球化時代中,無論如何,我們早已經走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沒有哪個文明社會在此趨勢下可以將自己置于現代化的大門之外,現代化對我們而言,早已不是一種“異己”的東西,它早已是我們的制度、思維方式與身心狀態的一部分了。“社會現代化作為有目的、有計劃的社會變遷活動,離不開對原有社會基礎的認真思考,它是在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下進行的,各國現代化的起點不同,內外環境不同,其方向、內容、道路也有區別,因此很難形成統一模式。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將普遍的現代化特征與本國的歷史條件與文化傳統有機結合的產物,我國的社會現代化絕非‘西方化’或‘歐洲化’”[2]134-135先生也不同意第二種取向的本土化研究,也就是以“實證主義”貼近本土的真實為滿足。因為此種“樸素經驗主義”心態下的真實不過只是在西方現代學術概念工具下的真實,仍是不自覺地帶著西方有色眼鏡下的本土經驗,這種經驗的獲得,勢必以篩選或忽略許多本土人特有的身心狀態之經驗為代價,也可能對于此種經驗背后西方學術夾雜的特定心態或預設毫無知悉,尤其當這些特定心態或預設常常偽裝成具有普世價值時,就如西方學者建構出的“東方學”。雖然“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唯科學主義’傾向和注重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等特點,對于提高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科學水平和學科威信是有意義的,但它把社會現象完全等同于自然現象,過分強調經驗的作用,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和價值選擇的意義,又容易使教育社會學實證研究陷入偏頗的困境”[4]。因此,忽略了本土人的主體性和價值選擇性的實證主義傾向,不但把科學方法與邏輯獨裁教條地供奉起來,而且根本窄化了人類社會所具有的最可貴的特性,這個特性就是,因為生活環境的不一樣,人們的所想、所感、所視、所為常常也是不一樣的。第三種批判性取向的本土化意涵與視野非常深廣,它超越了第一種取向簡單的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價值判斷和選擇,也不像第二種取向那樣,只是在“本土”進行驗證研究,外表樸素的經驗主義卻可能導致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盲目跟從。先生在“批判取向”本土化的基礎上踐行出中國特色的“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這種研究取向是對于中國教育社會學自身當下研究處境不間斷地反省檢視、批判與創造,不僅是在加深批判意識的可能性,更針對中國的國情走轉化的教育實踐行動。因此,先生的本土化就是不斷“創新”、“活化”,這是一種朝向未來可能性的重建與創造。在這個意義上,先生的創新性本土化可以視為一種態度:找尋“出口”的態度,找尋一個我們面對西方學術霸權重建中國特色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出口。
“創新取向的本土化”使先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呈現出強大的理論與實踐生命力,為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從“西化”走向“化西”樹立了研究典范。所謂“化西”,就是我們應把西方現代性及其學術文化之精髓在當下歷史情境中,徹底吸收、同化與轉化,使其與中國實踐情況相結合(在這里要徹底檢視西方現代性原則的根本預設),并且以此作為學術研究進一步的資源或基礎。當然,先生強調的“中國特色”也不是主張中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從此就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建立起唯我獨尊的學術中心主義,關起門來作純粹的“本土化”研究,如此的鴕鳥心態也實在不必,不要忘了正是西方的學術思潮,才帶給我們重新建構學術主體性反省的契機,只是我們在引進西方學術理論和方法時,也應深植創造性的轉化過程,避免成為西方理論的“客觀性”對象。正是堅持這種創新性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先生才建立起獨創性的中國教育社會學的“本土化知識”,例如先生對教育社會學學科基本問題的探討就讓我們對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有了全新的認識。在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上,先生認為可從三個層面上來揭示:從目的論層面上是探討教育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及協調發展的規律;從認識論層面上是研究教育社會現象;從選擇論層面上應重點研究教育社會問題。研究對象的這三個層面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探尋教育與社會互動機制及協調發展規律是研究的最終目的;考察教育社會現象是探尋機制與規律的必要前提;突出對教育社會問題的研究是深化對教育社會現象的認識、探尋機制、揭示規律的有效途徑。因此,先生將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通過對教育社會現象,尤其是對教育社會問題的研究來揭示教育與社會互動的機制及協調發展的規律。這樣,既能將教育社會學同其他學科區分開來,體現其獨特的學科功能,又能充分反映時代發展對學科的迫切要求,同時有利于促進學科自身的建設與發展。[5]在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上,先生主張從三個層面來把握:從教育社會學與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關系看,教育社會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從教育社會學與教育學及社會學的關系看,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中介學科;從教育社會學與教育學科群的關系講,教育社會學是一門中層學科。[2]38-39明確其邊緣學科的性質有利于教育社會學在廣泛吸納諸多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學的理論滋養的前提下,既能主動劃清與教育學、社會學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界線,形成自己的獨特的學科地位,又能在不斷借鑒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拓展新的研究領域;明確其中介學科的性質,有利于加強不同專業出身的研究者之間的合作。樹立其學科意識,有利于在研究目的上把學術使命與社會使命相互結合,在研究內容上將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這樣,不僅可以防止西方教育社會學界那種人為紛爭,而且可以克服研究中的純思辨與純實證的兩種傾向。在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上,先生強調要從二元對立走向多元綜合[4]。受社會學方法論的影響,傳統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在方法論上一直存在著自然科學取向與人文科學取向、規范性研究與證驗性研究、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和諧論取向與沖突論取向、演繹性模式與解釋性模式、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二元對立。教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這種分裂和對立,嚴重影響了教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先生摒棄非此即彼的簡單、線性思維方式,以多元綜合的思維方式構建了一個縱橫交錯的方法論體系:在縱向維度上包括哲學方法論、系統科學方法論、專門科學方法論和具體學科方法論四個層次;在橫向維度上包括時間、空間和學科三個視角,具體說既要實現三個“相通”,又要做到七個“結合”。三個“相通”,一是選擇性地吸收國外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實現中西融通;二是批判性繼承中國傳統的教育社會學方法論,實現古今貫通;三是創造性地移植相關學科研究的方法論,實現科際會通。七個“結合”,一是自然科學取向與人文科學取向的結合;二是規范性研究與證驗性研究的結合;三是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四是和諧論取向與沖突論取向的結合;五是演繹性模式與解釋性模式的結合;六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結合;七是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結合。在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取向上,先生提出要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教育社會學研究是一種物理研究,即為探明事物自身客觀規律而展開的研究。這一取向決定了教育社會學研究必須奉行事實判斷,其價值取向是研究過程的客觀性與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其次,教育社會學研究同時也是一種事理研究,亦即為探明事物具有的意義和價值而展開的研究,也就是通過研究既要說明事物是什么,又要解釋為什么,還要講出如何做。因此,事理研究既是價值研究,也是應用研究,其價值取向是研究結果的合理性與指導實踐的有效性;再次,教育社會學研究還是一種共理研究。因為物理研究所關注的事實同事理研究所關注的意義是不可分割的,事實負載著意義,而意義來自于事實,二者并不相悖。[2]38-39所以教育社會學研究實質上是一種“物事共理”研究。同時因為教育社會現象是古今中外都共同存在的現象,所以教育社會學研究也是一種“古今共理”和“中外共理”研究。共理研究的價值取向是科學與人文的并重,實然與應然的統一,傳統與現代的交融,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契合。
先生倡導并踐行的“創新取向本土化”研究,是走向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研究。此種取向的本土化研究在理論產生與實踐應用上有兩條路線:其一為內部本土化,指的是關鍵性本土概念、方法與理論的淬煉、編碼、系統化與應用的歷程;其二為外部本土化,“面向世界,繼續有重點地翻譯、介紹和評價外國的研究成果,反思國外的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適用性,盡可能從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的教育社會問題”[2]20,最終達成理論上和方法上的適用性轉化。換言之,本土化研究中所采用的材質,有來自本土內部和本土外部,前者是從本土情境中重振本土知識與文化,或者從本土根基上有所創新,如先生一直強調要“尤其注重從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2]前言;后者則是吸收外來要素加以融入,形塑本土新的內涵與風貌。總之,本土化不是用他人的理論與方法在本土進行“驗證化”,也不是搞狹隘的“在地化”,拒斥一切變化與外來特質的純粹復古化。本土化要保持蓬勃的生命力與更大的發展空間,就必須有源頭活水,也必須要不斷適應外在環境變遷納入創新新元素,而且每種本土化都各有其殊異性與獨特性。
二、走向實踐化:指向教育社會問題的本土化研究
先生認為,“教育社會學應致力于為教育決策與教育改革的實踐服務,這既是社會轉型時代的強烈呼喚,也是學科自身發展的迫切要求。”[3]研究即實踐。實踐是人類嘗試去克服限制,致力于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建立一個相互轉換的過程,并且通過實踐來生產新的結構關系。因此,先生在長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中一直秉持學術使命與社會使命并重,先生說:“我們研究教育社會學自不應坐而論道,而應該同時承擔起學術使命與社會使命,對一些問題既要有理論分析,以揭示規律,解釋事實,又要有對策研究,以參與實踐,為現實的改革服務。”[2] 前言在先生看來,研究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追求價值中立的知識,而是追求一種“解放的實踐知識”,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不再只是抱著一種客觀超然的立場,也不再只是追求對現狀的了解而已,而是抱著一種承諾與涉入的態度,通過走向實踐的研究,主動提供改變現狀的策略,喚醒被研究者的批判意識,擺脫受支配的情形,協助被研究者提高自我組織和轉換的能力。
長期以來,我們把“邏輯的事物”當成“事物的邏輯”,認為只要理論對了,事情就解決了。于是乎許多教育學者(包括教育社會學者)習慣于在書齋閉門造車,崇尚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學術研究方式,熱衷于“跑馬占地式”地建立“新說”“新學科”“新體系”。要么他們把自己架在高空,遠距張望所觀察的對象,使教育理論遠離了鮮活的生活世界;要么把其它理論作為自身理論合法性的依據,忽視了教育理論發展自身的邏輯和實踐基礎。這般將理論的邏輯置于實踐的邏輯之上,抹煞了實踐的獨特性,同時又造成了許多理論上的無謂難題。教育社會學研究需要將具體的經驗研究和敏銳深刻的理論建構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結合成為一個整體,使之具有鮮明的風格,如此理論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真實空間。真正的創造不僅僅是理論觀點或思維與眾不同,而是能在實踐中產生實效。“完全和解決現實問題沒有關系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是得不到發展的”[2]27。當然,我們并不是一概否定學理研究和體系探索的價值,“在學科恢復重建初期有必要注重體系構建,但從教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及本土性、時代性特征來看,忽視實踐問題研究則可能有失偏頗”[6],中國的教育學理論發展更需要現實問題取向,更需要在日常實踐的基礎上構建體系,教育學(包括教育社會學)只有凸顯出實踐特性才能彰顯出它獨特的學科地位。總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我們需要從整體化上來構想,實踐是從一個理論點到另一個理論點的“驛站”的總和,而理論是兩種實踐之間的“驛站”,任何沒有碰過壁的理論都是不可能發展的,而實踐就是用來鑿穿這堵墻壁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頭腦里的一百元不等于口袋里的一百元。因此,先生的教育社會學研究一直致力于加強對中國重大教育社會現實問題的實踐研究,先生說:誠然,這些問題都相當復雜,一時確難以認識清楚,有些提法可能也不夠準確,但與其回避不講,不如面對現實、客觀反映,提出一些看法,引導和激發其他研究者(學生)自己去思考[2] 前言。
中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熱衷于“批評式研究”,這種研究往往充斥著慷慨激昂的陳詞,華麗動聽的辭藻,激情浪漫的關懷,對現代教育問題的討伐之聲不絕于耳,好像自己就是教育真理的最大代表者,教育責任的最大擔當者,但熱鬧的教育批評中卻對教育實踐的轉進之道無動于衷。批評式研究依靠感性主義的誘惑和夸夸其談的情緒來贏得學術市場的贊譽,其實在很多情況下,它只是生命壓抑下的一種生理沖動,是對現代教育體制僵化、考試霸權主義、工具理性工業、生活程式化等的一種反抗,用韋伯的經典名言就是,力比多造反邏各斯。教育社會學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格,讓我們對教育問題必須保持批評的態度,批評的實質是為了改造實踐,呵護生命,塑造人性。可是,“批評式研究”并不關注教育實踐,或者說他們往往是一種抒情式的“修辭學”研究,把熱情消耗在否定和哀怨上,現實的教育及其實踐都以負面和畸形的形象出現在批評式研究的戰斗檄文中,它目空一切的否定、批評一切現實教育,導致批評式研究是一部沒有結局的小說,是一種沒有教育研究責任擔當的虛無主義,除了睥睨萬物而又有些老生常談的“否定”外,批評式研究基本沒有自己的研究信仰,變成教育實踐的馬路放火者和夸大其詞的混亂制造者。在無所擔當的虛無主義自由中,批評式研究缺乏深刻、嚴肅的對教育問題和生命本身的思考,陶醉在淺嘗輒止的自我恣意的片語中。
針對上述問題,先生反思了我國近年來包括教育社會學在內的整個教育科學的發展,認為在理論研究為教育實踐服務的問題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教育科學研究不是發號施令,研究者也不是行政官員,科學研究的結果不是得出必然的結論,而是陳述客觀事實;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教育科研應服務于實踐,為教育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和前瞻性的“預測”,是教育研究的真正價值之一。兩種觀點的分歧在于對教育研究最終價值的認定,以及對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所在認識不同:前者認為教育研究的最終價值在于求真,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是認識世界;后者認為教育研究的最終價值在于求用,理論工作者的責任是在認識世界的同時,還要參與改造世界。先生總結后認為,要正確認識教育科學研究中“求真”與“求用”的關系,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二者結合才能獲得教育研究的最大價值。此外,先生還特別強調,要重視由理論成果向實踐應用的轉化環節的研究。[4]理論研究的成果再先進也不能直接應用于教育改革的實踐,必須對中介環節進行細致的研究。如新的教育公平理論是一種以承認多樣性為前提的公平論,要應用這一理論來指導教育分流制度的改革,就必須首先研究新的教育公平理論對教育分流的各環節,如招生環節、錄取環節、分校環節、分班環節、教學環節、學籍管理環節等產生怎樣的影響,進而研究各個環節應該采取怎樣的改革措施,還需要研究各種措施需要的相應的保障條件及機制等等。這些轉化環節的研究對理論服務于實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但這些研究又往往因不被看作是科研成果而不受重視,不少人也不愿去做。這也是我國教育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社會學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產生的一門學科,教育社會學研究必須秉承社會學研究的傳統,從普遍性中走出來,進入到教育社會現象的實踐中去,以發現這些特殊現象的性質。就像看一座山,遠看觀得的外部輪廓未必就是“廬山真面目”,我們必須曾在此山之中,勘踏過它的草徑,漱飲過它的溪流,撫摸過它的石和樹,必須曾生活在那里,才能從外形看到實質。看,如果是跳出來看,只是一種回憶,唯曾在者才能識得山之真面目。對于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來說,先生認為只有那些對教育與社會互動、對教育與社會協調發展產生重大正負效應的教育社會問題,才是教育社會學的重點研究對象,“所謂教育社會問題,是指教育系統在自主且適應社會系統的運行中,出現的與社會大系統或其他子系統之間不協調而引起的種種矛盾與沖突現象”[2]19。只有對我們自身的教育社會問題一個一個地進行具體的、實實在在的研究,并作出真正有說服力的社會學解釋,才能體現出這門學科的終極價值。“教育社會學的問世就同工業革命引起的歐洲社會急劇轉型、教育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也正是對這些教育社會問題的研究,使各國教育社會學找到了自己的學科生長點。”[3]因此,中國的教育社會學研究如果不研究自身的教育社會問題,不用自己的學科之眼去看待自身的教育社會問題,那么中國的教育社會學至多仍不過是西方教育社會學的印跡,我們的學人還是善盡一種“土著報道人”的角色。因此,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需要在對各種教育社會事實、行動實踐、文本話語、理念價值反思批判、整合優化的過程和基礎上,立足于教育日常生活,能動、敏銳地揭示、評價、把握和預測教育社會環境、教育社會成員生存情境的不斷變遷帶來的問題、挑戰和機遇,真實反映所有教育社會成員相互依存協作和競爭制約的共生共榮的生命天性和生態規則,坦誠面對教育社會成員個體和群體更好生存、發展和享受的客觀需要和能動追求,動態考察學校場域中個人、群體的實踐行動和互動的過程和方式,冷靜面對教育社會個體和群體生命擠壓、個性對峙、生存緊張、理念沖突等行為越軌、制度廢弛、組織沖突、結構失調和功能紊亂的現象,科學揭示教育社會變態、扭曲和病變的憂患、機理和原因及提出相應調適、治理和康復的對策舉措。具體來說,先生認為,應該從以下三個層次來把握教育社會問題[3]:宏觀層次講有社會結構轉型與教育制度的調適問題、教育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與教育的社會功能重構問題、教育與社會沖突的加劇與教育的整合機制問題;從中觀層次講主要是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社會分化而引發的一系列新的教育社會問題,如區域分化與教育失衡問題、社會轉型與學校組織的沖突整合問題;從微觀層次講主要有社會行為無序與教育行為失范問題、教育時空拓展與師生關系變化問題、學校內外環境變化與教師角色沖突問題等。[7]
中國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各種教育社會問題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特點,很難用以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更難用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說明。因此,日益強烈的問題意識對揭示這些問題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學規律,對促進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社會學發展,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如先生所言:“教育社會學要立足于問題研究,著眼于學科發展,致力于實踐服務。”[3]亦即,教育社會學研究需要一種走向教育實踐的智慧,這種實踐智慧不僅僅是一種機械技巧,更是一種視野想象的指向中國教育社會問題的創新取向的本土化研究。
[1] 董澤芳.教育社會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2] 董澤芳.教育社會學(修訂本)[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 董澤芳.關于社會轉型期教育社會學使命的思考[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2, (2).
[4] 董澤芳,胡春光.從二元對立到多元綜合:教育社會學方法論的歷史演變[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6).
[5] 董澤芳,黃學文.教育社會學研究對象新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3).
[6] 董澤芳,張國強.我國大陸教育社會研究的特點與演變(1979-2005)——基于對教育社會學重建以來概論性著作的文本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7,(7).
[7] 蘇有.“過猶不急”對“新公共管理”的借鑒必須適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5,(2).
[責任編輯:朱丕智]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Innovative Orientation: a Study on Traits of Professor Dong Zefang’s Ideology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Hu Chungua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Professor Dong Zefang,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holars in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discipline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in China. With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ation, the most distinctive trait of Professor Dong’s thinking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s his loc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innovation orientation, whose research direction is aimed at emphas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focusing on the typical issues, related to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China. Not only advocating but also living up to by himself in person, what Professor Dong has insisted make his ideology quite vivid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ing way and naturally become a typical model for china’s researches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a dewesternization way.
Dong Zefang; innovative orientation; localization; traits
2016-08-15
胡春光(1976-),男,湖南第一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教育學博士,主要從事教育社會學研究。
IG40
A
1673—0429(2017)01—008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