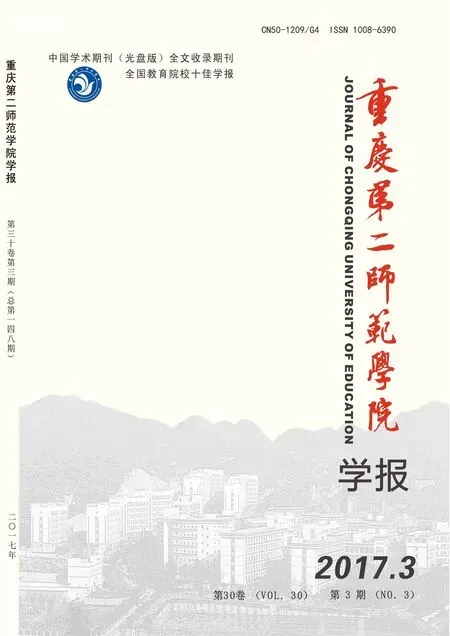歷史名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信仰問題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學術思考之三
趙心憲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重慶 400067)
歷史名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信仰問題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學術思考之三
趙心憲
(重慶第二師范學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慶市文史研究館,重慶 400067)
從《新新游記》殘本中,可以發現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有關《圣經》的基本觀念及其“見證基督”的巨大熱情,而其臨終遺囑有關十字架的特別安排,更是其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認同的體現。如果剝離其基督信仰,劉子如就不是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了。劉子如人生價值的實現,離不開其基督新教信仰實踐的達成,而其對國家的高度認同,更體現了當下兩種價值關系中信仰問題的研究不可忽視的學術意義。
歷史名人;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價值取向;信仰
一、問題的提出
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1924年環游世界,歷史文獻顯示,這是一個虔誠的中國基督徒環球“全程證道”之旅。先看幾條歷史文獻:
1.1939年1月1日,《前線旬刊》第13期《大時代——戰地服務記》載:“十年前(即1924年——引者)曾一度游歷歐美各國,宣傳基督博愛精神,備受各邦人士歡迎。”[1]2.1998年4月20日,定居加拿大溫哥華的臺灣運康公司董事長葛家瑗和夫人,為劉子如生平事跡撰寫近3000字的評語,其中涉及劉子如游歷歐美時的證道演講。葛家瑗夫婦認為,劉子如對《圣經》的認識很深,境界很高,在國外學校、教堂宣揚福音,“令會眾感動立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更上電臺證道、演說,有專人翻譯”,還不忘考察國外的現代化建設與“都市景觀”,“既愛上帝又愛國”[1]P377,讓人非常敬佩。3.《綦江縣私立青山孤兒院史話》記載:劉子如1924年應英屬加拿大教會邀請,出席聯合布道團百年紀念大會并主持開幕式;應英國基督教美以美會邀請,出席紐約召開的董事會并應邀發表演講,“近一年自費環球考察,每到一地必發表演講。在渥太華等地受到了貴賓級的隆重歡迎,為國爭了光”[1]37。
可見,劉子如1924年環球之行的目的,應與英屬加拿大教會、英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邀請分不開。劉子如充分利用這次難得的出國機會,借教會聯系的方便安排落實到有關國家的宗教考察計劃,并加上相應的國情了解與順道的旅游,讓這次環球旅行體現出濃厚的宗教色彩。筆者細讀《新新游記》(以下簡稱《游記》)殘本[1]294-341,對此印象頗深。這些歷史文獻主要從兩個方面反映了劉子如環球游歷中自覺的基督徒身份認同。
一方面,即臺灣運康公司董事長葛家瑗和夫人記敘的“演講證道、宣揚福音”。這是《游記》重點記錄的內容之一,共計24次,遠超有關國家旅游景點(不到5次),考察與教會有關的商業、慈善、教育、醫療機構(不到10次),工農業(不到5次)等的記錄次數。《游記》殘本所記加拿大境內的游歷活動,即可見證其“演講證道”的特點。如,卷三第十章第九則:“午前先在意大利人會堂演講,繼至一堂謳詩后,到大會堂禮拜,以‘馬可福音’十四章四節為題目。午后亦先至中華青年學生會演說……后至美以美會、青年會演說……余以‘約翰第一書’四章之愛字為主,鼓勵……歸入正軌也。”再如,卷三第十章第二十三則:“本日演講三次。午前在大堂主講,聽者七百余人。午后行青年禮拜,聽者八百余人。夜間亦在大堂主講,聽者千余人。每次講畢,輒有多少人士等候握手……”再如,卷三第十章第三十一則:“余住加拿大境內二十余日,遍歷各城演說,常聞人云:較一干西人返國之報告尤佳。各埠報紙每日均載有子如演說之事。在火車站,在碼頭,在街市所(遇)人士之友人,無不向余握手也。”這些記錄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劉子如《游記》記錄了演講《圣經》教義見證的基本內容,如第十章第九則:“以‘馬可福音’十四章四節為題目”,“‘約翰第一書’四章之愛字為主”等;也有記錄話題具體內容的,如“余略論本身自歷明證,兼毛宅三、段青云之信道史”(同上第三十則)。其次,記錄現場聽眾的大概人數,熱情程度等,說明自己《圣經》見證的實際效果。第三,記錄媒體及輿論綜合評價個人見證的主要觀點與社會反響。
另一方面,現存文獻信度較高的《劉子如毀家助善實錄》(1934年1月12日出版)收錄的《劉子如自述》一文,直接袒露了一位虔誠基督徒助善動力來源的心路歷程,及其宗教慈善事業的全部經濟賬目。個人信教、經商與慈善關聯均有具體表白[1]251-254。查閱《劉子如毀家助善實錄》[1]251-277提供的相關信息,劉子如成為商業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的社會影響,與其信奉基督新教的信仰實踐[2]息息相關:1896年劉子如結婚一年后“入教歸主”,成為基督新教“倫敦會教友”;1898年起經營卜內門洋堿業務等多種商業活動均告失敗,后轉代銷縫紉機業務并在1901年任美商勝家公司縫紉機四川總經理;1913年兼任江西南昌、九江勝家公司經理,開始將商業盈利按照基督新教倫理回報社會,創辦重慶孤兒院等慈善機構;1921年創辦中華基督教重慶青年會,“自傳”基督教義,遵循基督新教教旨“愛教進而自覺愛國”,“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就下了決心,哪年打日本,就去參加”[1]412,表現了鮮明的國家認同價值取向。不難看出,劉子如在個人商業經營步步成功的同時,加大回報社會力度,舉辦重慶孤兒院等慈善事業,在西南教區名聲日隆。直到1924年,應英屬加拿大教會邀請,出席聯合布道團百年紀念大會,再應英國基督教美以美會邀請,出席紐約董事會并應邀發表演講,成為20世紀20年代初福音派基督新教的全球知名人物。《劉子如自述》還以個人成為基督徒的經歷為線索,重點開列按照基督教義開展社會慈善事業的“實洋”賬單,也是其個人基督徒身份認同信仰實踐的最有力證明。
值得注意的是,劉子如的國家認同不僅體現在其《游記》關注國家現代化的具體行動與內心表白方面,而且表現在抗戰初期的愛國舉動上。其時,劉子如以自己的社會聲望組建重慶戰地服務團,擱置個人參與的商業活動以及家庭事務,帶團到前線勞軍三年。有媒體評價說:“對于這樣一個家境富裕、生活安逸且年近七十歲的老人,出此舉動,不免有些難解。然而事實上這位‘老當益壯’的英雄……一年多當中,領導著重慶戰地服務團男女青年數十人,由重慶出發沿長江贛浙皖諸省……擔起了民族求存的責任。”[1]411-412由此可見,歷史名人的身份認同及其國家認同,存在兩種價值取向(即身份認同價值取向與國家認同價值取向)的關聯認識關系,它深刻影響著歷史名人信仰的實際表現,成為當代中國歷史名人研究的難題之一,很有普遍性。這就是本文提出的,在地域名人文化研究中,作為“歷史名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信仰問題”的基本含義。譬如,重慶抗戰時期的歷史名人,超越其社會地位、經濟實力、階級屬性、政治面貌與文化影響等的愛國行動,是其國家認同的社會行為,但其階級屬性與政治面貌等身份認同的信仰選擇,我們可能難以得出正面的肯定性文化評價。回避這個問題的學理探討,不利于中華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因為身份認同的價值取向,是個人核心價值觀的信仰展示,往往會跨越時代、社會的局限,頑強地體現在個體生命歷程的最后階段。具體到劉子如而言,文獻有這樣的記載:盡管劉子如晚年身體每況愈下,但臨終囑咐字字清楚,要求一定要在其墳塋上放置十字架[1]485。這表明劉子如平生視其基督信仰高過一切,基督信仰成為其終極價值取向,也是他事業成功之后,一切社會行為的精神動力之一。筆者認同戚功的觀點[3],如果避談劉子如的基督信仰問題,那么評價其現代化思想、愛國精神、商業頭腦、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慈善事業、抗戰熱情以及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當下意義等,就難以說清楚。因為一個剝離了基督信仰的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愛國者與實業巨商的劉子如,就不是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了。劉子如人生價值的實現,離不開其個人信仰實踐的不斷激勵,而其國家認同價值取向表現的高昂愛國熱情,則體現了對兩種價值取向關系的認識在當下的巨大學術意義。
二、《圣經》觀念、“見證基督”與十字架:劉子如基督徒身份認同的三個要點
如前所述,劉子如《游記》殘本對環球之行“演講證道、宣揚福音”的有關記載中,《圣經》是劉子如“見證基督”的基本依據,更是他作為一位基督徒身份認同的重要特征之一。
除了《游記》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第九則日記之外,劉子如提及“《圣經》見證”的還有某卷第八章“英京之汗漫游”第七則:“至衛斯理總會堂聽講,系論‘哥林多前書’第二章屬靈之事。”所記當是在教堂聽講《圣經》。而《游記》直接出現“見證”一詞的有兩處——卷三第十章第三十則:“十四號晨,在大堂見證,聽者千有余人。午后課書禮拜三處,每處千余人。”“課書”即主講《圣經》,到了三個講經處,聽者都很多。《游記》卷三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第五則:“夜,年會請各地代表于大學校晚餐,由余見證,大得感動。”間接提到“見證”一詞的也有兩處——《游記》卷三第十章第二則:“請余備講自歷明證。”《游記》卷三第十三章第十則:在浸禮會講道“因余非傳道之人而能為主做證,故使彼輩受感匪淺”。其中的“自歷明證”與“為主做證”,與“見證《圣經》”內涵相同。
劉子如以“非傳道之人而能為主做證”,對《圣經》的崇拜、熟悉、認知、理解與個人實實在在的信仰體驗是基礎。劉子如早年在重慶市渝中區木牌坊倫敦會福音堂聆聽《圣經》,成為其信奉福音派基督新教的開始,奠定了其身份認同的基礎。基督福音派堅信,信仰及其實踐的最高與最終權威只能“源于《圣經》”,上帝之道的《圣經》,是“最高與最終”的規范或原則。這樣,福音派認同的信仰權威在《圣經》之中,《圣經》權威的性質成為信徒關注的中心。當基督徒們對《圣經》的理解出現爭議的時候,上訴的“最高法庭”在哪里呢?依據神學家詹姆斯·帕克的論斷,權威仍然“來自于上帝的啟示,上帝對現在的人所說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他通過耶穌基督而對世界所說所做的一切,而《圣經》就是對上帝所說所做的權威性見證。”[4]
上述話語的內在邏輯似乎是這樣的:《圣經》是上帝之道,當然是完全真實可信的,由此成為信徒思想與生活的最終權威。《圣經》內蘊的教誨,就是上帝對教會與信徒言說的“道”,要明白了解“上帝的意思”,人們就必須求助于《圣經》中“書寫的道”,個人的領悟與體驗自然成為其中的關鍵。因為由上帝“默示而來的《圣經》,是完全而明白的神啟的記錄、解釋和見證”[4]。這樣,福音派神學當然將《圣經》視為發現宇宙之“道”的終極所在,相信它才是永久保存救贖福音的“神授文獻”,是判斷基督徒信仰實踐的最高權威。
有意思的是,劉子如《游記》有兩則記錄似乎暗合研究者上述對《圣經》權威的論斷。一則即第八章“英京之汗漫游”第七則:“至衛斯理總會堂聽講,系論‘哥林多前書’第二章屬靈之事。”一則即卷三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第四則:“大雨未出,特記多能(倫)多基督教發軔之歷史……更憶余父母所奉之瑤池教(指佛教——引者)純系詐欺取財之法門。”“余今入基督之門,始悉大道不分中外”,斷然放棄佛門而認信福音派基督,這與劉子如的信仰實踐過程息息相關。“屬靈之事”與基督徒“靈性生活”相關聯,劉子如對福音派新教的信仰實踐深有體會[5]。他19歲時為了個人的前途,孑然一身“負氣出走”至重慶主城區。正當他舉目無親,饑餓難耐,命懸一線之時,蒙臨江門下紅廟當家和尚收留,天天與廟內菩薩抬頭不見低頭見,卻一點感覺都沒有。這與劉子如在家里目睹父親執著于佛像崇拜卻沒有得到佛道感應的經歷有關。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劉子如皈依福音派基督新教成為“倫敦會教友”四年,一心信奉《圣經》教旨,雖然經受生意場上的一連串失敗,卻能陣腳不亂,在耶穌基督信仰實踐的引導下“三十而立”,此后商業經營一帆風順。故“‘哥林多前書’第二章屬靈之事”,有劉子如自身“證道”的“屬靈”經驗,當然倍感親切。
可以說,“以《圣經》為中心”見證基督的記錄,在劉子如《游記》殘本中處處可見。劉子如近一年的環球之旅,從一位福音派基督新教信徒所為而言,就是“以《圣經》為中心”環球見證基督的信仰實踐。因此,有關記錄雖然簡短,卻往往直接道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布道”“靈性”對《圣經》教義的認知、理解與體驗。劉子如在有關文字表述中,對見證基督信仰實踐的現場效果與心情記錄很多,如《游記》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中的幾則。第二則:“午后,赴課書禮拜堂歡迎會,請余備講自歷明證,由彭普樂、唐醫生二君移譯英語,大受歡迎,爭行握手禮者,不計其數”。第十六則:“入堂禮拜。沿街見各商店門前首懸余肖像下注明,今日在何堂演講,甚至通衢繁區亦懸余放大之像,注明如前。余于晨間在少年禮拜堂演講,有三百余兒童入聽……其間向余握手言歡者指不勝屈”。第二十四則:“夜在大堂主講。未講之先,有四百余人同余握手,親愛至極。受感者云:余愿盡忠至死也。”
福音派基督徒傾心見證基督,“布道”“靈性”“事工”的相關信仰實踐,體現特定的神學內涵。簡而言之,見證基督的“見證”,即“為福音真理所做的見證”。福音派信徒認為,他們是牢記耶穌“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教誨的信徒,因此堅信“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福音派宣教主要關注普通信徒,認為傳播福音不僅僅是專職教牧人員的工作,也是每一位信徒的神圣使命。這種“將一切信徒皆為祭司”的觀念,可以將福音傳播推向極致。而有關福音真理的見證,還被神學家視為“靈性成長”的主要手段與方式,“它為個人的靈性狀態提供了一種公開的指標式標志。福音派信徒極為樂于同他人分享福音信仰的現象,甚至成為福音派限定自我身份的一個重要特征”[4]。《游記》卷三第十三章第十則云:“因余非傳道之人而能為主做證,故使彼輩受感匪淺。”可以認為是上述神學闡釋的最好例證。
如果說,1924年環球見證基督福音,讓劉子如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認同感得到極大增強,成為1925年子如先生“毀家助善”——為重慶社會公益事業獻出全部私人財產的直接原因,證實其福音基督新教信仰實踐“實質性”開啟的話,那么他的臨終遺言有關十字架的囑托,則有力證明了其福音派身份認同信仰實踐的事實存在。至于為何選擇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作為基督信仰的象征和標志,福音派新教神學的論斷有三:其一,“上帝的愛與正義的終極啟示”;其二,“對惡的決定性的勝利”;其三,基督徒“得救的根基”“犧牲的最高榜樣”“奉獻的最有力感召”。筆者認為,有關話語的內在邏輯如下:人原來與神關系和諧,因為人的罪過而與造物主疏遠,甚至整個人性完全墮落。上帝通過十字架的“神秘作為”,標明神對世人可能“重新悅納”。由于上帝的“圣愛”,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世人救贖,人得以重新站到上帝面前,在“信仰與愛”的侍奉中與上帝和好。十字架為上帝的子民開啟了一條唯一的現實的自由通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彰顯“神愛世人”的核心內涵,確立起基督在信徒崇拜與宗教生活中的“中心性”。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最終成為“福音派神學與靈性生活中的核心意象和觀念,它遍及信徒之宗教信仰與實踐的一切方面與領域”[4]。
劉子如不是神學理論家,而是福音派基督新教的信仰實踐者。選擇十字架作為自己身份認同象征符號的價值取向,可見他對福音派基督信仰所達到的認識境界,這也自然留下福音派基督教在華傳播史上有關時代影響的痕跡。據史料記載,福音派基督新教在重慶的傳教活動始于1888年,劉子如在1896年“入教歸主”。1901年至1920年,是福音派教會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其在華傳教事業出現前所未有的興旺。據教會統計資料,1920年各差會在四川開辟的教堂總數僅次于廣東、江蘇,教徒人數超3萬人,四川地區的外國傳教士總數已位列江蘇、直隸、廣東之后,“1920年成為基督教在四川地區的發展巔峰”[6]。值得注意的是,這20年也正是劉子如個人事業發展的巔峰時期。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福音派新教在四川的傳播出現了問題,并很快走入低谷,而正處于個人事業峰值階段的劉子如,卻十分渴望基督信仰的見證機會。1924年他能成為中國西南教區數萬信徒的唯一代表,應加拿大教會邀請,出席世界聯合布道團百年紀念大會,又應英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邀請,出席在紐約召開的董事會并發表演講,可見其在世界福音派基督新教界的代表性。
三、身份認同概念內涵的辨析及其與國家認同價值取向關聯的信仰問題
進入21世紀后,國內學界關于身份認同、國家認同等的“認同研究”不斷深入,成果頗豐。本文限于篇幅,難以對相關學術成果進行全面梳理,僅就有關“身份認同”概念的兩種代表性觀點加以比較,提出歷史名人文化研究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關聯的信仰問題。
《身份認同與身份建構研究評析》一文立足于社會學的“身份/認同概念的發展”角度,從解析“身份”與“認同”概念的特定內涵開始,追蹤“認同”概念研究20年的發展軌跡,對身份/認同概念的社會學意義提出了研究者的學術論斷。“身份”,當下已經成為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概念,與“類別”“角色”等概念相關聯,主要用于揭示社會個體與社會的關系。有關身份的理論研究目標,似乎集中于身份認同研究與社會認同理論等方面。英語“identity”,有本身、本體、身份即“我是誰”和“相同性、一致性”有關事物認知兩個方面的含義。認知“我群一致性”必然伴隨“他群差異性”。因而,“對身份的研究,也就是對個人與社會、個人與集體關系的研究”[7]。追蹤社會學領域中影響身份/認同研究的五條理論脈絡(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論、G.H.米德和符號互動論、舒茨和知識社會學、涂爾干和結構功能主義、馬克思和批判理論),可見學術界關于身份/認同研究不同階段的進展。20世紀60年代是身份/認同研究發展的“關鍵時期”,種種社會運動的不斷涌現,促使相關研究擴展到非常寬廣的領域;至20世紀70年代,身份/認同研究“更多應用于經濟研究”,同時“逐漸理論化”。這樣,學術界幾十年努力探討身份/認同的內涵發展,認同從“心理分析的技術術語”,轉型為“社會學研究的綜合概念”。認同從個人心理描述,到個人與社會、集體的關系認知,表明身份/建構的過程特點,也就是說,身份認同并非一成不變。所以,認同研究應該置于“時代的情境”之中,兼顧歷史文化的影響與當下具體社會結構情境的制約;認同離不開與他者關系的建構,關系的變化必然帶來認同的變化;個人認同多重,身份認同多重,多重身份管理成為個體身份認同的重要任務。總之,身份“多重認同是分層次的,在不同情境下會側重不同的認同”[7]。
《上海大學生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及成因分析》一文將社會學的身份/認同理論,應用于宗教社會學具體案例分析的項目操作,對上述內涵復雜的身份/認同概念作了簡化,因為研究目標的清楚確認,其內涵的核心認同要點得到明確認定。關于“身份認同的含義”問題,研究者先從應用的術語詞組說起,重點探討身份認同英語詞源的本義,最后落實到漢語成語的對應理解,這個思路有利于解決理論應用問題的討論。
認同問題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如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性別認同等[8]。據筆者了解,近年來涉及的認同熱點問題,還有國家認同、社會認同、族群認同等。因為認同一詞在日常生活用語的普遍應用,一些學者常常不加學術界定直接應用于問題研究,每每造成歧義。但只要按照學術規則,明確認同研究實際對應的研究對象,認同問題具體確認,諸如基督徒身份認同、劉子如國家認同的基督徒身份問題,認同研究就不會像一些文獻資料那樣給人似是而非的感覺了。據相關資料,“認同”一詞是外來語,譯自英文單詞“identity”,現代漢語同時譯為“身份”和“自我同一性”。1989年版上海譯文出版社《英漢大詞典》中的“identity”詞條有如下釋義:名詞。1.身份;本身;本體。2.同一人;同一物。3.同一(性);相同;一致。4.個性;特性[9]1601。筆者認為,“identity”詞條釋義有兩層含義:同一性與獨特性,表現為相同時間跨度中一致性及其連續性。“認同”一詞之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相似與差別的實質關系。相似與差別就是認同的兩個不同的認知方面。一個人經歷前后的同一性與一個群體之間存在的相似性,同時也構成與他人的差別。當“identity”用于突出時間不同,就譯為“身份”;為了表明同一性的存在,就譯為“認同”。因為是一個概念,它不是詞義分裂的存在,所以也變通譯為“身份/認同”的組合詞,以兼顧“identity”內涵的個體和群體意義。當然也有持不同意見者,認為“identity”譯為“認同”比“身份”動態意義更顯豁,英文的原意在后現代立場上保留更清楚。因為“從后現代來看,身份本身變得既不確定,多樣且流動,正需要一個‘認同的過程’去爭取。身份來自認同而認同的結果也就是身份的確定或獲得,成語‘驗明正身’即有此意”[8]。例如,劉子如1924年的環球見證基督,一年之中在10多個國家的20多個城市見證演講70余次,可以認為就是他作為基督信徒造成世界影響“認同的過程”之一。
因為對認同問題的實際考察與相應學科知識的應用限制分不開,不同學科中“identity”一詞的譯法也就不一樣。例如,心理學譯為“自我同一性”,哲學譯為“自我認同”,社會學和文化學則譯為“身份認同”。不同譯法所側重的意義有所區別,但“身份”和“認同”兩個義項始終包含其中。對于歷史名人的文化研究而言,通常運用“身份認同”相關的社會學、文化學學術研究成果。例如,劉子如基督徒身份認同問題,探討的是劉子如對其基督徒角色合法性的確認,人們的有關共識以及影響的社會關系。因此,劉子如基督徒身份認同的判斷,應符合個體基督徒身份認同的以下三個“判斷標準”:
第一,個體能明確自己所屬群體。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身份認同是指個人對自己角色的一種自我確認,它是個人系列個性的統一,是一個人區別于另一個人的整體標識,他是個人依據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0]58劉子如的基督徒身份認同,其臨終前有關葬式十字架的要求應該最有說服力,這是劉子如 “我是誰?”——“我是基督徒”的最后確認。
第二,個體能明確自身在群體中的角色地位及其承擔的責任、義務和權利。這是因為身份認同是借助于身份系統功能實現的,是社會成員的類別區分。不同類別角色被賦予不同的權利、責任及義務,由此形成群體公共生活的“支配與服從”的社會秩序。《劉子如自述》就是劉子如作為一位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明確其在群體中的角色和地位、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及其應具有的權利。對于這樣的基督徒身份自我認同的范本,這里沒必要重復展開分析了。
第三,個體對群體價值的認同。上述兩個判斷標準,更多考慮的是身份認同的外在表現,而第三個標準則有關身份認同的內在價值。社會心理學認為,群體本身有四個特點,即“角色、地位、規范、凝聚力”。群體規范的認可以及凝聚力的產生,都必須有“價值觀的支撐”[8]。毋庸置疑,身份認同的第三個“判斷標準”非常重要。就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研究的文獻資料而言,符合身份認同“外在表現”判斷標準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方面的資料相對多一些,《劉子如研究與史料選集》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而除了《游記》殘本、《劉子如自述》之外,有關劉子如基督徒身份認同內在價值的史料卻幾乎沒有,這是非常遺憾的。
抗戰爆發初期,劉子如自發組團前往浙皖前線勞軍三年,成為他愛國情懷的集中表現,得到國民政府的褒獎,這與他的基督信仰有關聯嗎?劉子如所表現出來的抗戰激情,就是他踐行國家認同的證明。有學者指出,定義國家認同這個社會文化現象研究的專屬概念,實際上有兩種表述方式:第一是看“誰認同”,以描述心理過程去定義,明確所屬國及其心理認識活動的經歷。一個人對國家產生認同與熱愛是漸進的過程,最后表現出對國家的“忠誠、支持和依賴”。第二是看“認同什么”,主要包括所認同國家的“歷史發展、文化傳承、國家主權”等核心內容。概而言之,“國家認同是一個人或群體確認自己屬于哪個國家之后形成的一種對其認可與接受,與愛國主義相聯系的情感”[11]。學術界一般將國家認同劃分為文化性與政治性兩種情感類型:“文化性”國家認同,是對國家的“主流傳統文化、信念”等方面的認可程度;“政治性”國家認同,則是對國家“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認可接受程度[12]。我們知道,政治學研究首次引入國家認同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第三次民族主義革命后,那時國家認同的政治學意義逐漸得到展示。現代國家非常重視國家認同公民意識的教育。從學理上而言,一個人出生即具有所屬國家的公民身份,這是“國家認同的前提”,在這個人隨后的人生經歷中,國家公民意識產生,并逐漸形成對所屬國家“歷史、文化、主權及信仰”等的認同。一般而言,一個人確認了自己的歸屬國,國家認同感會隨著“分享”其所屬國的文化傳統而產生,而且“認可與服從”所屬國法律、制度、領導人等國家的“權威要素”,產生依附于所屬國的歸屬感以及效忠心理和行為。一個公民將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自愿歸屬于所屬國家的時候,就有特定的“鄉情”依戀。在國家遭受外來侵略的時候,就會自覺扛起武器保衛國家。國家認同政治教育重要性的上述分析表明,國家的存在與發展,“需要依靠這種國家認同的公民意識”[11]。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信仰實際上成為劉子如國家認同自覺表現的指南。信仰基督教對“自我的肯定”,這讓劉子如的自我意識得到自覺建構。筆者認同基督教文化影響研究者的論斷,即基督教信仰確證“個體存在的價值和獨特性”,強調責任感和群體歸屬,對于公民身份認同的形塑不僅僅具有外在性意義,而肯定自我的存在與價值,在現代中國早期意義非凡,因為這可能促使公民個體真正“從內心產生對身份的自我認同”[8]。總之,一個人自我認同自覺達成的經歷,應有一個三階段(層次)進步的完整過程:個體經歷“群體認同”,再到“社會認同”,最后才可能真正抵達“自我認同”。而“個體存在的價值和獨特性”沒有得到確證,作為現代社會發展基石的公民就不會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子如基督信仰的身份認同,成就了其國家認同。
綜上所述,國內福音派基督信仰的社會實證研究的學術成果值得我們重視,即一個人如果篤信基督,他最關心的將是自己與所屬群體與上帝的關系。如此執著的關注,會成為這個人及其所屬群體生活經歷中“最重要的坐標系”,最終成為其“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所在”。毋庸置疑,劉子如的信仰經歷就是最好的說明。從主觀上來看,基督徒因為對上帝馴服形成其“優良品性”;而這種優良品性在客觀上卻“表現為對社會的馴服”,甚至對國家的忠誠。這樣,“基督徒通過與神建立良好關系,從而實現了與人、與社會建立良好關系”[8]117的歷史名人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信仰問題,的確值得深入探討。
[1]重慶歷史名人館編.劉子如研究與史料選集(下)[C].內部資料.
[2]趙心憲.劉子如的基督教信仰——重慶歷史名人《劉子如自述》文本解讀與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2):313-319.
[3]戚功.關于倡導子如精神的五點建議[G]∥重慶歷史名人館編.劉子如研究與史料選集(上).內部資料.
[4]董江陽.現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7.
[5]劉子如.劉子如自述[M]∥重慶歷史名人館編.劉子如研究與史料選集(下).內部資料.
[6]劉稚旖.簡論近代西方基督教在四川地區的傳播[J].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60-62.
[7]王瑩.身份認同與身份建構研究評析[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50-53.
[8]華樺.上海大學生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及成因分析[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
[9]英漢大詞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10]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11]陳光軍.論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及二者的關系[J].廣東開放大學學報,2015(2):52-56.
[12]馬得勇.國家認同、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外近期實證研究綜述[J].世界民族,2012(3):8-16.
[責任編輯 文 川]
2016-12-09
國家人文社科基金項目“武陵地區傳統聚落保護與民族文化傳承研究”(12CM2038)
趙心憲(1948— ),男,重慶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巴渝文化名人。
G112
A
1008-6390(2017)03-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