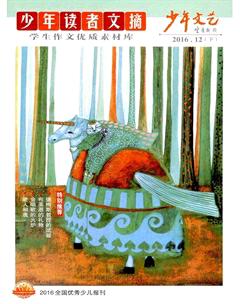狂亂的一刻
愛德華?D?霍克
雨已停了,但八月夜里的空氣仍然濕熱。李歐波穿著睡衣站在窗邊,默默咒罵他那臺吵得要命,卻又只會送出暖風的窗型冷氣機。在鎮的另一頭正發生著一場火災。他聽著遙遠的警笛,試著要確定它的位置,他猜是米爾路上那家購物市場中的某家商店。
他慶幸自己不是消防隊員。
好一陣子他注視著云底映照的火光,把城市的彼端涂成橘紅色。電話響時,他正轉身要回到床上。
“我是李歐波。”
“組長,你最好來這里看看。”是佛來契的聲音,有點太大聲。
“什么事?是那火災嗎?”
“韓克剛才在隊辦公室內發了瘋,開槍打了四個人。”
“我馬上來。情況控制住了嗎?”
“組長,我開槍打了他。沒其他的法子。”
“好,我十分鐘內到。”
五分鐘不到李歐波就著裝完畢,坐進了他的車。一般來說,從他住的大廈到總部車程要十五分鐘,但在清晨三點時,路上沒有多少車。他把有磁性的閃光燈插在車頂,開關打開,一路時速五十五英里地開進市區。
在古舊的總部建筑物前,滿街都是汽車和救護車。他認出幾個想沖過臨時警戒線的記者。其中一個認出他,喊著:“組長,發生了什么事?”但李歐波沒理他。目前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韓克是局里工作了九年的老將。除了例行的巡邏勤務外,從事過各種秘密的任務。雖然他不曾隸屬李歐波的重案組,李歐波對他卻并不陌生。
“讓開!”一個身著白外套的擔架員叫著,李歐波讓到一邊。擔架上的人就是韓克,他似乎已失去知覺。李歐波匆忙上到二樓,佛來契巡佐正站在隊部的中央,檢視損壞的情況。一張椅子四腳朝天,地板及一面墻上有血跡。警方的攝影師正在拍攝一具身著制服的身軀,但李歐波看不到究竟是誰。
他表情嚴肅地問:“死了幾個?”
佛來契抬頭看了一下,好像有些吃驚,李歐波竟然這么快就到了。“一個。躺在那兒的班特利。我們認為他挨了第一槍。”
從二十年前李歐波自紐約來到他成長的都市,加入警方以來,他就認識班特利警官。班特利當時就已在隊里。現在他只差一年就退休了。
“韓克還射了誰?”
“一個不知姓名的男性犯人和兩個帶他來的警探——史威尼和葛羅斯。他們傷勢不重,但那犯人挨了兩槍。在我阻止他時,他已把他警槍里的子彈都用完了。”
“韓克還活著嗎?”
“奄奄一息。他們四個都在醫院。”
李歐波走過去,注視著下方班特利的身體,心情壞得要命。
“你最好把整件事,從頭開始告訴我。”警察局長不久就會來,李歐波希望手邊有些答案。
“組長,我們所知不多。我在我的辦公室里。一切相當平靜,班特利在他桌子那兒打著一篇逮捕報告。兩點半過后沒多久,史威尼和葛羅斯帶著那個人犯進來,然后韓克就進來了。”
“他穿著制服嗎?”
“不,便服。我不認為他在執勤。我聽到他們講話,但沒有注意聽。山姆剛得到一篇關于購物市場那兒的‘皇冠超級購物店失火的報告,正跟他們談這件事。當韓克把槍從他的夾克內掏出并開火時,我正好從玻璃隔間往外看。我一時真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山姆撞到墻,倒了下去。韓克繼續開槍射殺其他人,大伙都在尖叫。我從我的辦公室跑出去,拔出手槍。史威尼和葛羅斯這時都已倒在地上,還有他們的人犯——我沒數一共開了幾槍。韓克轉過身來,把槍口指向我——組長,我只好射他!他的槍彈已經空了,但我不知道。”佛來契的聲音顫抖著。
“你沒有選擇的余地,”李歐波說道,用手按著佛來契的肩膀。“我也會這么做。”
“我昨晚才和他喝過咖啡——”
有人來了。是局長和某個地方法院檢察官辦公室的人。李歐波沒有什么答案可以給他們。在短暫的寒暄后,他說他正要去醫院。
局長說:“報紙會把它寫得很可怕。”
“事情的確是很可怕。”
“一個理智的人怎會那樣亂來?他有嗑藥嗎?”
李歐波回答道:“我會去查。”
局長郁郁地看著地板上和墻上的血。它似乎比班特利的尸體更令他心情沉重。
李歐波下樓去開他的車。到醫院不過是一小段路。他到達時,四個人都還在急診室。他找到一位名叫萊斯的醫生,他和一位實習醫生正在治療史威尼。史威尼似乎是四個傷患中傷勢最輕的。
當醫生暫時從一間有帷幕的小房間出來時,李歐波問:“我可以跟他講話嗎?”
“等我們把傷口縫好就可以。他很幸運——子彈穿過他大腿的肌肉部位。”
“其他人怎么樣了?”
醫生查了下病歷表。“韓克情況不好。我們正準備給他動手術。至于葛羅斯警官,他腹部有個傷口,但我想他可以撐過去。那女人則還沒清醒——”
“什么女人?”
“我也不曉得。不知道是誰?一個女的穿了男人的衣服。”
“她是和其他人一起被帶進來的嗎?從總局嗎?”
“沒錯。起先我們不知她是個女的。她很年輕,我猜不到三十歲。”
他道聲歉,又回到小房間內。李歐波踱著步。或許史威尼多少能解釋一下這個瘋狂的事件。他真的期待這樣。
幾分鐘后醫生出來了,并且向李歐波做個手勢。“你可以和他談五分鐘,別超過。他失了不少血,還很虛弱。”
李歐波點點頭,撥開白色帷幕,走了進去。“嗨,史威尼,”他說,“覺得怎樣?”
史威尼勉強歪著嘴笑。“我會活下去。其他人怎樣?”
“就我所知,葛羅斯不會有問題。班特利死了。”
“老天!”
“很遺憾必須在這種情況下跟你講這些。”
“韓克呢?在他從下方打中我的腿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佛來契開槍打中他的胸部。他們現在正送他進手術房。”
“他究竟為何要這么做?”
李歐波嘆口氣。“我還希望你能告訴我呢!”
“我們剛帶人犯進來。山姆正在一張桌子后,談論某地的一場火災。韓克突然不知從哪冒出來,從他夾克內的槍套掏槍出來。”
“他講了什么?”
“我記不得。我想班特利伸手去抓槍,韓克先打了他一槍,然后轉向我,不斷開槍。我感到腿挨了一槍,就倒下了。”
“你們帶進來的嫌犯呢?”
“他也中槍了嗎?”
“是的,不過醫生說那是個著男裝的女人。”
“什么?”史威尼掙扎著要坐起來,卻又痛得不得不放棄。
“是個女人?”
李歐波點點頭。“你為什么逮捕她?”
“葛羅斯和我正臨檢菲爾德大道的那些人們下班后去的酒吧。當我們把車停在老雅典店前時,這男的——我們當時以為是男的——就走了過來,用個空瓶砸破那家酒吧的前窗。我們跳出來逮著他。我們以為逮了個酒鬼,打算回去給他做筆錄。”
“看起來韓克認識你們的人犯嗎?”
“我怎會知道?如我所講的,直到他在那兒掏出槍時,我才見到他。”
醫生自帷幕后出現。“現在最好讓他休息一下。天亮后還可以來看他。”
李歐波捏了捏史威尼的肩,“放輕松點,我會再來看你。”
“是的,組長。請查出他為何這么做。”
“我正努力。”
出來以后,李歐波問醫生:“那女的怎樣?”
“差一些。不過我們認為她活下來的機會比較大。查出她的身份了嗎?”
“什么也沒有。讓我看看她的衣服。”
醫生帶他到一間小房間,打開一個服裝袋,上面有個號碼牌,以及“身份不明”這幾個字。李歐波注意到外套和襯衫前面彈孔附近的鮮血。除了有個標簽說明這衣服是購自市區一家廉價男裝店外,衣服看來干凈又普通。李歐波問:“這衣服合身嗎?”
“我沒注意這個。但我想大概合身。”萊斯醫生回答。
“我在想,不知道她是買給自己穿的,還是跟別人拿的。”李歐波沉吟著,搜著口袋。除了一條手帕、幾個銅板,和一張弄皺的五元糧票之外,沒有其他東西。李歐波問:“有沒有吸毒的現象?”
“我看沒有。”
一個年輕的實習醫生探頭進來。“萊斯醫生,他們都在手術室等你。”
萊斯告訴李歐波:“我得幫忙做韓克的手術。失陪。”
“祝一切順利。”李歐波真心地說。
他在走廊等,等到他們把韓克從他身邊推過。韓克的雙眼緊閉,呼吸也不規則。一個手持靜脈注射瓶的實習醫生走在旁邊。
李歐波默默地問:“去他的,韓克,你為何要這么做?”
早上,當佛來契全力應付報界人士時,李歐波開始辛苦地整理韓克最近的行跡。李歐波發現,韓克正從事麻醉藥方面的秘密任務,但韓克的上司認為韓克其實在做其他的事。
“他在查一條新的線,”麥威爾少尉告訴李歐波,“在一次藥物突檢中,他發現有人以失竊的十萬元糧票來購買運貨。”
糧票。
李歐波想起在那不知名女人的口袋內皺縮的糧票。“這是什么時候的事?”
“大約兩個月之前。他告訴我他有一條關于失竊糧票來源的線索,要求免去麻藥方面的任務,來查那條線。我和相關的聯邦機構聯絡后,他們同意進行。事實上,韓克今天本來應該跟一個司法部的人會面,談談他調查的情形。”
“聽來不像他有任何感情方面的困擾。”
“似乎沒有,”麥威爾同意著。“他只是做他的工作。對于今早發生的事,我跟其他人一樣震驚。”
“然而一定有什么使他拔槍射殺四個人,會是什么?”
“我知道才怪。在這一行里,有時壓力在經年累月的累積后,才突然爆發出來。”
“我了解,”李歐波同意著。“但局長不會滿意這樣的回答。”
“韓克能活下來告訴我們答案的機會如何?”
“我四點離開醫院時,他仍在手術室。我現在要過去看。”
隨著早晨的來到,急診室也回復了它平常復日的步調。這時,不過是些兒童手臂骨折,或腿割傷的事件。李歐波來找萊斯醫生,被引導到二樓的一間房間。那兒,他發現這外科醫生正悶悶地看著一個空咖啡杯。
“漫長的一夜?”李歐波問。
萊斯點點頭。“韓克一個半小時前死了。他在手術完時還活著,卻在恢復室內死去。”
李歐波難過地搖頭。“我可以用你的電話嗎?”
“我已經打給局長了。”
李歐波說:“我是要打給那個開槍打他的人。”
他打到隊部去,但人們告訴他佛來契回家休息了。李歐波遲疑了一下,然后撥了佛來契家里的號碼,希望佛來契會來接,而不是他妻子。他運氣不錯。
“哈羅,佛來契。你好嗎?”
“精疲力竭。組長,我想睡一個禮拜。”
“韓克一個半小時前死了,”李歐波告訴他。“我想你會想知道。”
“謝謝你。我想,當我開槍打他時,在我心目中,他已經死了。”
“試著睡一下。”
李歐波掛了電話。轉身面向萊斯醫生。“其他人怎樣?”
“葛羅斯的情況愈來愈好。那女人已清醒了,你要見她嗎?”
“當然。”
萊斯送他到三樓的一間私人病房。“我要在這里安置一個警衛,”他告訴醫生,“我會安排。”
“好的,你可以單獨跟她談五分鐘。”
李歐波進入房間,走到床那邊。他一眼就看到這女人醒了,正用她那很迷人的深藍眼珠望著他,只是他現在沒心情欣賞。她大概快三十歲了,棕色頭發剪得像男人那般短,但李歐波實在難以想象,葛羅斯和史威尼怎會沒看出她是女的。她的高顴骨,以及柔和的五官,使她的面龐非常女性化。
“我是李歐波組長,”他告訴她,“來調查昨晚的槍擊案。”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說著,閉上了眼睛。
“讓我們從你的姓名開始。你是誰?還有你為何要打扮成男人?”
“我叫卡希。我是個藝術家,并且我沒有打扮成男人,我只是穿我平常穿的衣服。他們沒理由逮捕我。”
“你用瓶子砸破了老雅典店的窗戶,”李歐波指出,“并且很不巧的,你是在一輛未標示的警車前干這件事。”
“不管我干了什么,我總不該挨槍吧!”
“是的,”他同意。“槍擊你的人是個名叫韓克的警探。這名字對你有任何意義嗎?”
“沒有。應該有嗎?”
“他未曾警告就開槍打你,以及其他的幾個人。我只是想找出理由。”
“他怎么了?”
“他被我的一個部屬開槍打中,不久前才去世。不過醫生向我保證說你會沒事的。”
“謝謝。”她說。她的眼睛開始有些濕潤。
“我會需要記錄下你的地址。不過,我認為你不需擔心你的起訴。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它們都會被撤銷的。”
她說出舊市區某地的住址,離她被逮捕之處不遠。“我現在想要一個人獨處。”她告訴他。
“當然,”李歐波表示同意,“不過還有一件事——你口袋內有張五元糧票,你在哪兒拿到的?”
“在銀行。藝術家有時賺不到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
李歐波點頭,離開了房間。他對她給的答案不滿意,但她太虛弱了,沒法問下去。過些時候他會再來,或許到時會有一些答案。或許他可以知道為何當他告訴她韓克死了時,她似乎在哭。
葛羅斯警探是個有著太多贅肉和太少頭發的中年男子。他傷得比史威尼嚴重得多。平躺在床上,鼻里、臂上各插根管子,看來好像不只是挨了韓克一顆子彈。
“韓克死了。”李歐波告訴他。
“組長,那算不上是什么損失。他總是怪怪的。”
“哪些方面?”
“喔,對每個人都懷疑。自從他在幾年前逮到他妻子背叛他后,他就認為每個人都想背叛他。我不懂麥威爾怎能忍受他這些年。”
“我從來都不知道那件事。或許我沒有我想的那般了解他。但,葛羅斯,他昨晚為何會拿槍打人呢?”
“我還以為你是來告訴我的。”
“你和史威尼逮捕的那個嫌犯做了什么?”
“那男人用瓶子砸窗戶。”
“是個女人,打扮成男的。”
“真的?那地區什么事都可能發生。”
“韓克在開槍前曾經看到她嗎?”
“當然,她就和我們一起站在那兒。”
“戴著手銬?”
“當我們帶她進來時,便把手銬去掉了。”
“韓克跟她說話了嗎?”
“一個字也沒有。”
“當你逮捕她時,你對她的印象是——譬如,她吸過毒、喝醉了,還是什么?”
“說老實話,組長,都不是。我的直覺是這男人——我們以為她是男的——存心要被逮捕。你知道,就像歐·亨利小說里那個想借坐牢來避冬的家伙。”
“我知道,”李歐波,“只不過現在是夏天。”
那晚他努力不去看報,上面有關于這次槍擊的聳動的頭條新聞。有韓克和班特利的大幀照片,史威利和葛羅斯的小幀照片。
沒刊出卡希的照片,但某個小標題稱她為這個案件里的“神秘女郎”。這事件在首頁被大幅報導。發生在“皇冠超級購物店”的火災,則被擠到報刊內頁。
李歐波在總部待到很晚,他希望當佛來契來上班時,能見到佛來契。那就是為何當司法部的那人到來時,他會在他桌子那兒。司法部的那人名叫艾力斯,蓄著小胡子,是個膚色淺黑的黑人。
握手時他面帶微笑地說:“麥威爾少尉說我該來找你。我知道你負責調查昨晚的悲劇事件。”
“似乎是我沒錯。”李歐波承認。
“我在今天下午由華盛頓搭機,要來和韓克見面。那是在我知道他被殺了之前。”
“麥威爾告訴我說你在同一地區工作。”
華盛頓來的這男人點頭。“調查失竊的糧票。它會變成一個大問題,尤其在都會地區。黑社會拿它們當錢用,購買麻藥、槍支,以及幾乎其他所有的東西。從實用觀點而言,它們形同金錢,但比較起來,它們比錢好偷多了。”
“但這些糧票最后會怎樣?”李歐波問。“最后總要有人把它們兌換成金錢,明知這些糧票是偷來的。”
“那就是韓克正在查的。我們相信它們流入大型超市,大概是每一元券兌換五角或兩角半。商店經理樂意賺取利潤,風險很小。”
“超市,”李歐波復述著,“有人告訴你昨晚的火災嗎?”
“發生在哪里?”
“皇冠超級購物店。它在槍擊案前不久起火的。”
“有人縱火?”
“我不曉得,”李歐波說,“但我打算查出來。”
“讓我跟你一起來。我得做些事,免得白費了這趟奔波。”
李歐波拿起了一份縱火組的報告,上面說有證據顯示,皇冠的火災起源可疑。他和艾力斯駕車去現場,但在黑暗中看不到多少東西。“屋頂塌陷,”當他們繞著這毀壞的建筑走時,李歐波說,“看來全毀了。”
“一個很好的毀滅證據的方法。”艾力斯說道。
“什么證據?”
“失竊的十萬元糧票。有人在上個月搶了我們的一個發票中心,但我們沒讓此事上報。錢的數目不大。那地方是在聯邦大樓后的一個停車庫。某個了解內部的人在午餐時間進去,拿了筆糧票。有了把復制的鑰匙,他只要避開電視攝影機的鏡頭,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這使得李歐波吹了聲口哨:“韓克正在調查這件事?”
艾力斯點頭。“他的線民告訴他失竊的糧票經由當地超市兌現。我曾就各地居民的相對收入制作了每家超市的兌現數目的電腦圖表。就它的所在地而言,皇冠兌現了過多的糧票。那就是我為什么今天要來見韓克的原因。我打算明天突襲搜索皇冠,因為這些最近失竊的糧票很有可能就在該地。我在電話里告訴韓克,我們明天會申請搜索票。”
李歐波嘆口氣,踢了塊焦黑的木頭:“麻煩是,你的韓克是個能干的秘密警察,我的韓克卻在局里發瘋,開槍打了四個人。”
“聽來真像兩個不同的人。那超市經理呢?縱火組的報告上一定有他的名字。”
他們回到車里,查了一下。名字是葛泰德,地址在某個較高級的郊區。“生意一定相當好,”李歐波說,“讓我們去看看他。”
艾力斯猶豫了一下。“我不去。在我調查的這個階段,或許我們最好還是別見面的好。讓這件事保持在地方性的層次,但盡你所能地去查。”
李歐波在市區的一家旅館放艾力斯下車,單獨開車去見葛泰德。當他抵達葛泰德的家時已快十一點了,屋里沒有燈光。李歐波正打算明早再來,一部計程車彎進街里,停在屋子的前面。
一個男人打開門,付錢給司機。
李歐波下了車走上前去,“打擾了。”當這男人沿著黑暗的路走向他的房子時,李歐波叫道,“葛先生嗎?”
男人遲疑了一下,或許擔心是打劫:“有事嗎?”
“我是李歐波組長。想問你幾個有關昨晚火災的問題。”
當李歐波走近時,他發現葛泰德是個五十幾歲的人,瘦長,灰發,有張看來似曾相識的高顴骨面龐。“組長,我才度完辛苦的一天。我相信你懂我的意思。我的店被火燒了,我剛才去探望我的女兒,她病了。我相信我所能告訴你的,你都早已知道了。”
“我保證只要花幾分鐘。”
葛泰德嘆了口氣:“好吧,你可以進來一下。”
李歐波跟他進入那棟殖民時期型式的大房子,等在客廳里,葛泰德去開燈。“我夫人不在,”他解釋,“這些日子我就像個單身漢。請坐。”
李歐波坐在鋼琴對面,上面陳列著一些家族的畫像。“你必須知道,昨晚的火,起源可疑,”他開始說道,“縱火組找到有定時裝置的證據——”
“我對那一無所知,我只是經營這家商店。它不是我的。火災令我難過,但公司有保險費。”
“有人說這次縱火可能不是為了保險費,而是要銷毀一個嚴重罪行的證據。”
“什么?你在講什么?”
但就在李歐波回答之前,他的目光停在鋼琴上那些畫像正中的那張。突然他明白葛泰德的臉為何看來熟悉。“畫里的女人必定就是你的女兒,”他說,“她看起來很像你。”
“我擔心她有點野,就像今天的許多年輕人那樣。”
“你是說她生病了嗎?”
“我——是的,沒錯。”
“在醫院吧,我想。”
“我是那樣說的嗎?”
“我今天見過你的女兒,葛泰德先生。這畫像非常逼真。她用的名字是卡希,報紙稱她為‘神秘女郎。”
“老實說,我是去跟她說別干傻事。”
李歐波突然發現這謎團的片段開始組合了起來。“葛泰德先生,那韓克呢?”
“他怎么了?在他槍擊我女兒之前,我沒聽過他這個人。并且我向你保證,針對這次我女兒被槍擊之事,我不會善罷甘休,一定要訴訟到底。”
“你怎么知道躺在醫院里的是你女兒?”
“她今晚早些時候打過電話給我。我猜她怕我向警察局報失蹤。”
“她住在這兒嗎?”
“不,她有間公寓,她在那里做她藝術家的工作。但她在我店里幫忙我做簿記。”他刻意地看看表,“我很累了,而且我看不出我女兒的事跟這火災有什么關聯。”
“這火災和槍擊你女兒之間可能會有關聯。”李歐波說,他站起身,“謝謝你的協助,葛泰德先生。”
早上李歐波回到醫院。他在卡希的門外等,萊斯醫生正在看她。“她愈來愈好了,”醫生離去時說,“但盡量別問一大堆問題,她需要休息。”
李歐波進去,坐在她的床邊:“覺得怎樣?”
她回答說:“比昨天好一點。”
“昨晚我跟你父親聊過了。”
她的表情似乎僵硬起來。“我沒——”
“沒理由否認你的身份。”
“好吧,你同我父親談過了。那又怎樣?”
“我想你可能有話要告訴我——關于你自己,還有韓克。”
“你在講什么?”
“是因為在局里看到你,他才發作的,不是嗎?他跟你相當熟,就算你打扮成男人,他也認得你。你的手銬已經去掉,他不知道你是被逮捕的。他以為你是要到那兒背叛他,就像另一個女人——他前妻——曾經以不同的方式背叛他。”
她開始哭,不像昨天那樣強忍住淚。李歐波轉開身,望著窗外一會兒。他想起在他臥房看火災的情景,也想起了他為何在這里。他有工作要做;韓克忽略了他的工作,而那是他的致命傷。
他轉過身,面對哭泣的女郎。
“當韓克偶然發現這違法的糧票失竊事件,他遇到了你,不是嗎?你們倆在過去幾個月享受著你們特別式的瘋狂生活。”
“不是瘋狂!是愛!”
“韓克從聯邦大樓車庫偷了那捆糧票,是不是?你也幫了他。他需要你的幫助,因為他的糧票必須流入你父親的商店。但司法部一個名叫艾力斯的男人用電腦調查,查出皇冠兌現了超出它所在地的人民收入所該有的糧票數目。艾力斯今天要申請搜索票,突襲你父親的店。失竊的糧票就在那,你又沒時間把它們移走,所以你就把那地方燒了。假使你父親也涉入的話,他是可以及時把它們移走的,但由于某種理由,你就是無法及時移走它們。”
“我把它們藏在倉庫,”她淡淡地說,用張面紙拭著淚。“打算等安全時賣給政府。我口袋內有一張,因為我們想在其他地方把它們賣掉——但槍案發生后,大家都感到害怕,尤其報紙又只字未提。我們不知道司法部想要怎么做,于是就把糧票擱在我父親的倉庫。然后韓克聽說艾力斯已鎖定皇冠,并申請一張搜索票。但我只能在店開門時才能進去,他們又正在盤點。周五前我都沒辦法進去,而拖到那時就太晚了。”
“你如何能在你父親不知情下,做這么多事?”
“當我做簿記時,我就做糧票兌現的事。過去這兩年,我一直都是跟當地的人們購買糧票,再經由他的店把它們賣回政府。他從不過問,他信任我。”
“但你寧愿辜負他的信任,把店燒掉。”當她沒回答時,他繼續說:“你把自己打扮成男人,以防在你裝置燃燒彈時,有人看到你。然后當兩個便衣警察在看時,你砸破窗戶,以得到一個完美的不在場證明。假如火災的原因查到你身上時,你可以聲稱火災發生時,你在牢里。當然,一旦縱火組找出了定時裝置的殘余部分,你的不在場證明就會失效;不過你當時沒想到這點。”
“我沒想清楚,”她承認。“韓克也沒有。”
“他當然沒有。他前晚走進局里,看到你和葛羅斯以及史威尼在一起。很可能他壓根兒沒注意到你穿什么。很可能他那一整天都在發狂的邊緣,擔心在艾力斯從華盛頓來時會做什么。然后他看到你,以為你背叛他,出賣他來保護你自己。他也不稍等一下,聽聽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拔出他的左輪槍。當班特利警官撲過去奪槍時,他挨了第一顆子彈。然后在佛來契巡佐槍殺他之前,他打了你兩槍,葛羅斯以及史威尼各一槍。”
“狂亂的一刻。”她說,眼淚又涌了出來。
“你愿意談這件事嗎?”李歐波問。“我是說,在一個公正的陪審團面前?”
“那對我會是很痛苦的,不是嗎?”
“沒有韓克的一半痛苦。”
(摘自中學生讀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