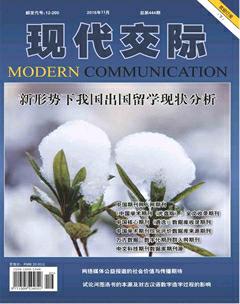列夫?托爾斯泰女性觀探析
喬磊
[摘要]《戰爭與和平》是列夫·托爾斯泰長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文中描繪了三十幾位女性形象。本文以娜塔莎和海倫兩個迥然不同的貴族婦女形象為典型范例,從她們對待愛情及兩性關系的態度、家庭社會責任等方面,論述托爾斯泰筆下女性形象的最終宿命,借此來審視托爾斯泰女性觀的特征。
[關鍵詞]愛情 家庭責任 最終宿命 完美標準 女性觀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2-0104-02
“人生的一切變化,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陰影構成的。”①是托爾斯泰的一段名言。《戰爭與和平》中出現了活潑善良、恪守封建傳統道德的完美女性娜塔莎、瑪利亞公爵小姐等;也有和海倫一樣淫邪放蕩、寡廉鮮恥的女性形象。在“光明”與“陰影”世界中行走的女性,構成了托爾斯泰女性觀的部分表征。
一、對待婚姻愛情的態度
人作為獨立的個體,總有其存在于世界的價值。人類的關系紛繁復雜,婚姻與愛情話題是文學作品中亙古不變的表達。婚姻與愛情是最自然不過的社會關系,男女之間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也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
托翁在《戰爭與和平》中,用上帝手中的命運之牌指引了眾多女性的前行之路。女主人公們的愛情均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波折,她們也曾迷惘過、徘徊過、踟躕不前過;也曾在男性救贖中完成自我的脫胎換骨,當然也有死性不改、粉身碎骨的妖婦們。托爾斯泰以其男性的視角,主宰了女性的命運,更好地詮釋了男權社會的集體欲念。
貴族少女娜塔莎從天真無邪到情感受挫、直至走入婚姻、相夫教子,充分適應賢妻良母的角色轉換,她心安理得地接受著男權制社會所賦予她的身份。她沒有原則,一味順從,失去自我。她曾極度渴望愛情,無私地愛著安德烈公爵。其實,她對安德烈的情感更多的是一種崇拜與敬仰。她自覺變得卑微、多疑、猜忌,極度缺乏安全感。當看到尼古拉和索尼婭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時,她也為之動容。然而,自己的愛情道路注定曲折。從一開始,她們之間就是不平等的。她總是患得患失、極不自信,甚至自卑!而安德烈公爵的若即若離使娜塔莎的內心備受煎熬。她看到的只是安德烈公爵如何的優雅與優秀,卻忽略了自己本身的魅力。其實,她的活潑與多情,也備受貴族青年的青睞。然而,這都無濟于事,娜塔莎仍然在患得患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安德烈公爵走后,花花公子阿納托利適時地出現了。情感空虛且迷茫的娜塔莎,迷醉于阿納托利英氣逼人的外表和甜得醉人的蜜語,在他的溫柔鄉里沉淪、墮落,也徹底葬送了與安德烈公爵之間難能可貴的感情。雖然,安德烈公爵在臨死前原諒了娜塔莎,但是,情感的扭曲和處事的偏頗,必然受到作者的懲罰。愛情和幸福再次離她遠去。而與皮埃爾的結合,是托翁為她設置的自我救贖。她也必然按照男權社會的標準來做人、行事。她享受著作為妻子的責任和榮耀,甚至不修邊幅,曾經詩意盎然的娜塔莎不見了,她始終在被動中被他人支配著。三段感情中,娜塔莎始終沒有自我,心靈上的自覺臣服才是關鍵。
接下來,我們來看托翁筆下臉譜化的蕩婦角色—海倫。她是邪惡的化身。女性邪惡論在西方文化中歷史悠久。中世紀的布道詞明確宣稱,“女人是邪惡的,她們淫蕩如蛇蝎,多變似鰻魚,好奇、冒失、尋釁成性。”②③于是,《戰爭與和平》中最另類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作者不遺余力地將海倫塑造成只知縱情聲色、毫無道德可言的邪惡化身。海倫總是“毫不吝惜地讓每一位來賓欣賞她優美的身段”,用豐滿的肩膀、時髦的酥胸和光滑的脊背勾引各色人等。作者描寫了海倫的美貌與淫邪,而且大肆渲染。誘惑男人與追求情欲享樂是海倫在兩性關系中固守的法則,她可以用盡渾身解數與任何男人周旋,只要那個男人對她來說是有價值的。就像日后成為她丈夫的皮埃爾,雖然只是一個其貌不揚、有些肥胖,外表上沒有任何吸引力的男人,不過海倫在與皮埃爾認識不久后就用眼神和豐腴的身材色誘他,“您沒注意我是一個女人嗎?”她甚至恬不知恥地說道:“我是一個可以屬于任何男人的女人,也可以是只屬于您的女人”。難道是海倫饑不擇食嗎?當然不是!海倫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皮埃爾很可能繼承一筆巨額遺產……一切疑慮迎刃而解了!
海倫的世界中充滿了赤裸的兩性法則,無論在家庭內部還是外部,始終充斥著道德淪喪的丑聞。海倫不僅讓自己的哥哥阿納托利愛上了她,而且在整個歐洲有太多的貴族子弟淪為她法則下的玩偶。這些男人們為之傾倒、甚至爭風吃醋、大打出手……而海倫卻樂此不疲地享受這類關系帶給自己的快感,仿佛這就是其女性價值的最好體現。與海倫如影隨形的是放蕩和道德的缺失。海倫是一個被托翁妖魔化的女人,他也把這種女人的死亡結局設置得痛苦卻大快人心。其實,海倫的扭曲人格和最后結局,也是男權社會為其安排的宿命。海倫看似活得自我,其實是被男權社會丑化和奴役的犧牲品。
二、家庭責任的抉擇
列夫·托爾斯泰作品中所呈現的女性角色,她們的人生悲歡和成長脈絡,無不充斥著男權社會主宰的話語權。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庸,必然屬于從屬地位。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家庭生活僅僅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始終無法擺脫枷鎖的束縛。托爾斯泰的女性觀著實體現在婚姻與家庭問題上,是圍繞著男權社會共同體來編織主人公的人生軌跡。
托爾斯泰的女性觀在娜塔莎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婚后,娜塔莎放棄了自己的愛好和追求,遠離曾經的社交圈,全身心地投入到相夫教子的“事業”中來。她在三年的時光里,為丈夫皮埃爾生下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肥胖和身強力壯的家庭婦女形象,成為了娜塔莎婚后的標簽。她失去了原有的青春活力,放棄了曾經的美好追求。作為旁觀者, 無不為她感到惋惜。然而,娜塔莎卻樂在其中,并且將婚后發生的一切變化,稱之為“幸福”。她的生活單調而繁忙。她每天所做的就是圍著老公、孩子們轉。曾幾何時,美麗、青春、優雅的娜塔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忘掉自己的形象,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費盡心力為家庭和社會付出著自己的全部,并樂此不疲。這份毫無怨言地堅守和矢志不渝,是作者以男性視角來塑造的完美典范。
而“妖婦”海倫,卻是非常極端的例子,與娜塔莎的賢惠、善良、無私形成鮮明的對比。她荒淫無恥、欲壑難填,毫無責任感,沒有愛國心。她只關心如何享樂,如何在其他男人身上撈到實惠。在國家存亡的危難之際,她竟然為了名正言順地和情夫出國享樂,寫信向丈夫皮埃爾提出離婚。當奸情暴露時,還無恥詭辯;當皮埃爾忍無可忍提出離婚時,她竟然厚顏無恥地索要財產。她們全家都做著背離國家和人民的勾當。此外,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與信任,海倫公然偽裝成虔誠的基督徒,她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擇手段!她從不受法律和權威約束,我行我素,放縱淫亂。
“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④西蒙·波伏娃的論斷如此之深刻。其實無論是理想型婦女—娜塔莎,還是人人唾棄的危害性婦女—海倫,都體現了作者的男權主義觀念。托爾斯泰對婦女的判斷標準也是宗教的虔誠,被動、從屬、家庭化。這些被認為是女性的天性,違背這些標準或者這種“天性”,就是破壞社會秩序,而這種秩序恰恰是建立在兩性絕對差異之上的。
三、最終歸宿
其實,托爾斯泰所塑造的大多數女主人公,她們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某種“罪孽”,這是對宗教道德標準的背離,必然會受到應有的懲罰。《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雖然也因為受到情欲的驅使,在宗教道德上有所背離,但是她通過隱忍和祈禱,在經歷諸多苦難后,最終獲得了救贖,收獲了幸福。托翁為了安排了一條陽光大道,娜塔莎在婚后,尊重家庭、相夫教子、把家庭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她完成了虔誠的祈禱,得到了作者的諒解,擁有了靈魂復活的契機,幸福生活的來臨自然水到渠成。
而天生的尤物—海倫,則沒有那么幸運了。因為她的所作所為已經超越了大眾的底線,對于自己的惡行,她沒有絲毫的懺悔。她始終作為邪惡的化身,存在于作品之中。最后,托翁也為海倫安排了非常痛苦的死亡方式,將她那沉淪與墮落的靈魂和肉體統統毀滅。托爾斯泰一直在用父權制社會的價值標尺來衡量和評判女性形象。不論是神圣化還是妖魔化,都是男權制社會對女性的期望與控制。
四、完美標準
在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很多擁有真、善、美的女性形象,在外表美和心靈美之間,托爾斯泰更注重精神之美。
在俄法戰爭時期,娜塔莎無私地救助傷員,甚至將家中的三十輛馬車騰出來,運送傷員。她無微不至地照料著身負重傷、生命垂危的安德烈公爵,也因此安德烈公爵更加愛娜塔莎,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收獲幸福與溫暖。婚后的娜塔莎,也成為托爾斯泰筆下典型的賢妻良母形象。
而對外表性感妖嬈的海倫,卻是極大的諷刺。她的外表美無可爭議,但內心是骯臟的,精神世界是虛無的。正如皮埃爾所感受的那樣,海倫在他身上引起的不是愛情,而是骯臟、丑陋的感情。托爾斯泰刻意將海倫的外表與內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卑污的靈魂是海倫等同類女性角色的真實寫照。
綜上所述,托爾斯泰的女性觀是受到宗教道德和男權制社會的標準制約的。筆下的女性角色是男權制社會的產物。首先,美好善良的心靈是得到作者喜愛的基礎。作家認為:沒有單純、善良和真實就沒有偉大。只有極富內涵的心靈才是王道。只有擁有高尚的靈魂之美,女性角色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其次,托爾斯泰一直用宗教道德的標準主宰女性的命運。遵從宗教道德,完成自我救贖就可以擁有全新的人生。反之,只能遭遇悲慘的命運。總之,托翁筆下的女性形象,滿足的是作家的設想原則,即對母愛、家庭、婦女職責的定位。
注釋:
①轉引自山東省2010年高考語文試卷作文試題.http://www.ks5u.com/News/2010-6/27201/.
②伊利莎白·巴丹特爾.男女論[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108.
③陳慧敏.真正的美麗與愛情——從《戰爭與和平》看列夫·托爾斯秦的審美觀與愛情觀[J].遼寧教育學院學報,2003(03):83.
④(法)西蒙·波伏娃.李強選譯.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49.
【參考文獻】
[1](俄)列夫·托爾斯泰(著).張云緋,傅慧(譯).戰爭與和平[M].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
[2]鄭克魯.外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張良村.世界文學歷程[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8.
[4]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M].北京:三聯書店,1996.
[5]列夫·托爾斯泰.藝術論[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法)西蒙·波伏娃.李強選譯.第二性[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7]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M].北京:三聯書店,1995.
[8]克里斯·威登.女性主義實踐和后結構主義理論[M].大不列顛,1987.
[9]陳慧敏.真正的美麗與愛情——從《戰爭與和平》看列夫·托爾斯秦的審美觀與愛情觀[J].遼寧教育學院學報,2003(03).
[10]王永奇.天使和妖婦——談《戰爭與和平》中的兩類女性形象[J].重慶交通大學學報,2007,12(06).
[11]劉麗輝.托爾斯泰作品中三位女性人物命運分析[D].黑龍江大學,2008.
[12]楊政.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兩大悖論[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09(05).
[13]賀萍,侯旭.性別視角下的透視——哈代小說創作中的女性意識[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8,11(06).
[14]林學錦,托爾斯泰“道德自我完善”的重新評價[J].汕頭大學學報,2001(01).
[15]于美玲.《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與《大雷雨》中的卡捷林娜對比試析[J].黑龍江科技信息,2009(31).
[16]康正果.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述評[J].文學評論,1998(01).
責任編輯: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