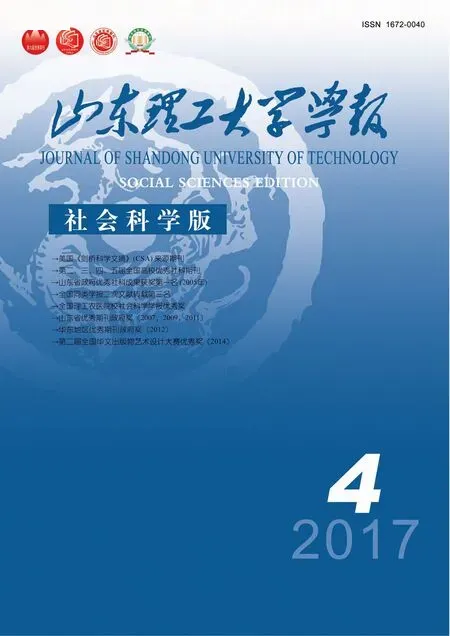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釋讀
祝 秀 權
(淮陰師范學院 文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釋讀
祝 秀 權
(淮陰師范學院 文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
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語,兩“琴舞九絉”當各自歸下文,連“元入啟曰”讀。《周公之琴舞》詩篇與《周頌·敬之》是根據同一底本創作的不同版本,不是同一創作版本的不同流傳。楚人在據周公、成王原有的言辭創作詩歌時,必然會帶上楚國詩歌特點,這就是《周公之琴舞》的來源,也是它與《周頌·敬之》之異同的根源。
周公之琴舞;周頌;敬之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簡稱《清華簡(壹)》)自2011年公布、出版以來,學者們對其做了多方面研究。《周公之琴舞》(下簡稱《琴舞》)是已公布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中的第4篇,記錄了以周成王名義所作的詩篇九首(九啟),每首詩均以“亂”為終。第一首即今所見《詩經·周頌·敬之》篇,其余八首不見于典籍記載。迄今為止,學者們對《琴舞》進行了多方位解讀,李學勤、廖名春、李守奎、徐正英等學術大師都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發表了見解,他們的闡述、論證包括《琴舞》的斷句、釋讀、與《詩經·周頌》的關系、學術價值、所反映的楚文化特征等方面。但現今《清華簡(壹)》的研究還處于起始階段,現有研究結論還有待商討和論證。本文擬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對《琴舞》簡文的釋讀、詩義的理解、《琴舞》組詩的創作性質、與《詩經·周頌》及楚文化的關系、《清華簡(壹)》的學術價值等方面,談談筆者看法,以請教學界大方。
一
略引《琴舞》原文如下:
周公作多士敬毖。
成王作敬毖。
琴舞九絉,元入啟曰:“敬之敬之,天維顯帀,文非易帀,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其事,卑監在茲。”亂曰:“訖我夙夜不逸,敬之。日就月將,教其光明。弼寺其有肩,示告余顯德之行。”
再啟曰:“假哉古之人,夫明思慎,用仇其有辟。允丕承丕顯,思悠無斁。”亂曰:“已,不造哉!思型之,思毷強之,用求其定。裕彼熙不落,思慎。”
我們認為,“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云云,清華簡這話只是說:周公作多士敬毖而已,并未作琴舞九絉。在句讀上,“琴舞九絉”當屬下文。同樣,“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云云,也只是說:成王作敬毖之辭,并未作琴舞九絉。“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其潛臺詞是:成王作敬毖之辭,現根據其辭作琴舞九絉。
如果說清華簡《琴舞》有與《毛詩序》相似“序”的話,那么只有“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是“序”語,而兩“琴舞九絉”當各自歸下文,是連“元入啟曰”而言之辭。周公、成王作敬毖,與簡文所記琴舞之作,是不同的兩件事,在時間上也有很大距離:一是西周初期之事;一是離清華竹簡形成時間不遠的戰國中后期之事。故本文按此理解,把“周公作多士敬毖”和“成王作敬毖”二語各自成段。這與《清華簡》公布后前賢的理解不同。
如果按照前賢的解釋理解,那么不僅詩是周公、成王作的,就連琴曲和舞也是周公、成王作的,這可能嗎?其實,即使理解為“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詩也不是周公、成王所作。《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無論是《周頌·時邁》,還是《周頌·武》《大武》樂章,都不是武王所作,而是另有詩人所作,《左傳》只是托以武王之名而已。這樣的表述在古籍中很常見。楚人作詩的性質與《詩》作者作詩的性質是相同的。
《琴舞》中第一首詩的創作底本,無疑與《周頌·敬之》篇的創作底本相同。《周頌》組詩中,《閔予小子》等三首詩不見于《琴舞》,《琴舞》中成王之詩的其余八首不見于《周頌》,但它們的主題是相同的,都是君臣之間的警策、告誡之辭。故李學勤認為,即使成王之詩九首中,也似有周公之辭41。這足以證明《琴舞》組詩的主題性質,亦可證成王只作敬毖之辭,并未作琴舞九絉。《周頌》和《琴舞》這兩組詩篇是誥辭的靈活應用,它折射出誥辭的大意,能補史籍之缺;誥辭則是詩篇創作之所本,兩者互補、互證。無論是《周頌》還是《琴舞》,都非成王本人所作,而是詩人根據其言辭而作。
二
以現存言辭為底本而創作詩歌,這應是《詩經》中多數早期詩篇的最初創作方式,亦是中國早期詩歌的主要創作方式。孔穎達《毛詩正義》于《周頌·烈文》詩曰:“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又于《臣工》曰:“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于《訪落》曰:“成王既朝廟,而與群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于《敬之》曰:“成王朝廟,與群臣謀事,群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于《小毖》曰:“周公歸政之后,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對于這一組君臣戒勸之詩而言,“詩人述其事”,其實就是“詩人述其辭”。又,孔穎達《毛詩正義》于《出其東門》詩曰:“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于《巧言》曰:“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此均與《周頌·烈文》組詩和清華簡《琴舞》的創作方式、創作性質相同。
中國早期詩歌是根據現成的言辭加工創作的。它們以詩的形式記錄了當時各類言辭的大體含義。《周頌》的創作方式是記,記的方式有兩種:記言和記事。記言者,誥辭及祭祀誦辭諸詩是也。記事者,頌祭祀者及描寫祭祀場面諸詩是也。它們雖曰“記”,但實際上兩者均是創作。記事類詩篇是創作自不待言,記言類詩篇也是創作,因為它們不是實錄意義上的記,而是對原始文辭——誥辭、誦辭、語辭加以概括、提煉,記其大意而已。因此,我們在史籍或銘文中找不到完整的與這些記言詩相對應的文辭,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或相似的對應文辭。如康王時的青銅器《盂鼎》銘文:“王若曰:‘盂!不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載武王受文王作邦,闢厥慝,敷有四方,畯正厥民。’”此與《周頌·執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語相近。《盂鼎》又有“畏天威”之辭,亦與《周頌·我將》“畏天之威”對應。李學勤在《走出疑古時代》中提到陜西出土的一件銅器“史惠鼎”,其上銘文寫著“日就月將”12,這便是《周頌·敬之》中的詩句。銘文不可能源自詩篇而記,詩篇也不是詠銘文而作,實際情況應該是,銘文所記和詩篇所詠均源自于其時儀式中的誥辭,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記錄誥辭而已。這就證明了,《周頌·敬之》所詠一定是當時某種儀式上的成辭。史籍、銘文中與《周頌》相對應的文辭還是很多的,史籍方面主要集中于《逸周書》《尚書》等。這些相似的對應很能說明《周頌》記言詩的創作方式。
中國最早的詩歌理論是“詩言志”,《周頌》正是中國最早的詩歌。從《周頌》的創作性質是“記”這一特征,我們可得出結論:“詩言志”者,詩言記也。“志”在古代雖有多種含義,但“記”是其最早含義。例如《周書》又稱《周志》,《禮書》又稱《禮志》。《國語·楚語上》:“教之故志。”劉毓慶也說:“原始的詩是為幫助人類記憶而產生的藝術語言,它的特殊功能是‘記物’和‘記事’。”242對此,聞一多先生在《神話與詩·歌與詩》中有精當論述:
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三個意義正代表詩的發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詩’字訓‘志’,最初正指記誦而言。……一切記載既皆謂之志,而韻文產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記載)就沒有不是詩(韻語)的了。承認初期的記載必須是韻語的,便承認了詩訓志的第二個古義必須是“記載”。《管子·山權篇》“詩所以記物也”,正謂記載事物。《賈子·道德說》篇:“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戒也。”151-154
這些言論正揭示了早期詩歌的創作性質和方式。詩人們用記的方式,使各種誦辭、誥辭之類變成易于朗誦和記憶的韻文,使之易于傳唱,流傳后世,使后人牢記傳統,不忘各種修身治國的禮儀,不忘祖先創業之艱難、稼穡之艱難等。王小盾說:“儀式記誦是詩最早也最重要的應用方式。各民族最早的文學,都是因儀式記誦需要而產生的韻文。”126
李學勤先生說:
《正義》在《訪落》《敬之》《小毖》三篇下都說明是“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這是很恰當的。《琴舞》講“周公作”“成王作”,不一定是該詩直接出自周公、成王,就像《書序》講“周公作《立政》”,而《立政》開頭便說“周公若曰”,顯然是史官的記述一樣,我們不可過于拘泥56。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琴舞》與《周頌·敬之》是根據同一底本而創作的不同版本,而不是同一創作版本的不同流傳。這個底本就是西周初期周公、成王對“多士”的“敬毖”之辭。這一結論并未降低《琴舞》的價值。如廖名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篇對比研究》詳細比較了兩者的異同,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他認為清華簡:“訖我夙夜不兔(逸),敬之。”則《敬之》當標點為:“維予小子不聰,敬止。”而今《詩經》因四言詩整齊劃一的需要,皆標點為:“維予小子,不聰敬止。”102這種比較而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對于讀懂今本《詩經》是有價值的。
李學勤先生說:“《周公之琴舞》是由十篇詩組成的樂詩,性質同于傳世《詩經》的《周頌》。”這話很正確,因為根據同一底本而創作的詩篇,其文本和性質畢竟不會相差太遠。《周頌》中的《閔予小子》《訪落》《小毖》幾首詩,清華簡沒有,只不過因為其原辭為楚人所不取而已。同樣,清華簡中楚國詩人據“成王作敬毖”之辭而作的“琴舞九絉”,除與《周頌·敬之》相對應的“元入啟曰”一首外,其余八首,《周頌》沒有,也只是因為其原辭為《詩》作者所不取而已。
《琴舞》成王第一首詩與《周頌·敬之》有部分言辭的不同,這并不能說明孰是原稿孰是加工稿,孰更真實的問題,因為它們都是根據周公、成王的原有言辭加工創作的,它們是根據同一底本而創作的不同版本。至于創作上孰先孰后,因《琴舞》出現了琴,故《琴舞》的創作應該比《敬之》晚,即晚于《詩經·周頌》的創作時間。據專家考證,“時代較早的文獻中,瑟是弦樂的代表,語言中以琴代表弦樂是戰國及戰國以后文獻的特點”836。不同的創作版本,而兩首詩有大部分文辭的相似,是因為這兩首詩與周公、成王的原有言辭十分接近的緣故,兩個創作者都沒有對原辭作較大的加工、改動。推而言之,我們認為,《周頌》中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組詩與《琴舞》中成王的九首詩,創作者也沒有對原辭作較大的加工、改動。
西周初年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人關于治國、修身的言辭,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中,被當作經典性語錄傳抄和改寫,其中一部分言辭被周王朝的詩人和各諸侯國的詩人改寫為詩歌,加以演奏和傳唱。這就是《周頌·敬之》和《琴舞》的來源,也是它們之異同的根源。
中國早期詩歌是根據現成的言辭加工創作的,楚人在據周公、成王原有言辭創作詩歌時,必然會帶上楚國詩歌特點,所以我們看到《琴舞》有“啟”有“亂”,而與之相應的《周頌·敬之》及其他詩篇卻沒有“啟”和“亂”,就是這個原因。李守奎先生說得好:“因為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不同寫本,用字必然不同。”934
通過《琴舞》與《周頌·敬之》的對比,我們看出:《敬之》篇詩句比較整齊,比《琴舞》讀起來更通順,更耐讀。由此我們推測:《詩經》中今天看到的詩篇,可能經過編輯整理者對原創詩篇做過一些整齊劃一的整理修飾。
清華簡《琴舞》與《周頌·敬之》的這種關系還可以證明前賢所論的一些失誤。如,并非《詩經·周頌》中也有過“九體”詩的存在[10]62,而是楚國人按照楚國詩歌的體例模式加工改造了周公、成王的原有言辭而已。清華簡《琴舞》并不能證明孔子刪詩十去其九[11]55,因為《周頌》中《閔予小子》《訪落》《小毖》三首詩卻不見于清華簡《琴舞》,這該如何解釋?
三
筆者認為,研究清華簡應注意一個傾向:即先主觀認定清華簡是正確無疑的,然后以之對照古籍,凡古籍中與清華簡不一樣、不一致的文字,都認為是錯誤的。不一樣、不一致的記載,原因應該是多樣的,不可以清華簡為唯一準繩而衡量其他古籍。比如:清華簡整理者說:“《傅說之命》三篇簡文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它再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確系后人偽作。”清華簡證明古文《尚書》為偽,似乎成了目前學界的共識。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公布、出版于2011年,至今也只有幾年時間,人們對它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隨著將來研究的深入,必將有新的發現和結論。在對清華簡文本的性質沒有深入研究、沒有普遍一致的定性結論情況下,不能斷然認定《尚書》為偽作。定性為戰國中后期的竹簡,記載的是西周初期的事情,這本身就決定了不可輕率以清華簡文本斷決、衡量其他古籍的真偽。《琴舞》中只有成王之第一首詩與《周頌·敬之》相同,那么《閔予小子》《訪落》《小毖》三首詩是否也是偽作呢?筆者在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域外《書》文獻整理”時發現,韓國保存的《尚書·太誓》一篇與國內所見《尚書·泰誓》的內容、文字完全不同。孰優孰劣、孰真孰偽,需仔細研究,不可輕率下結論。又如,《琴舞》成王之“再啟曰”詩中有如下詩句:“丕承丕顯”“思悠無斁”“不造哉”“思型之”“用求其定”。這些詩句在《周頌》中也有相似詩句存在,但它們分布于不同詩篇,如《清廟》《烈文》《閔予小子》《賚》等,清華簡這些詩句卻出現于同一首詩中。孰優孰劣、孰真孰偽,何者更接近于原貌,很難遽然決斷。但筆者以為,清華簡詩文的真實性、可信度應該不會在《詩經》之上。“先秦楚歌幾乎都被相嵌在故事中得以保存下來,詩歌和敘事是相互說明和印證的”[12]89。但這些楚歌和故事很可能經過了一定藝術加工,很難當作歷史文獻看待。
先秦文物留給后人可資研究的東西太少了,以至一旦有新文物發現,人們便如獲珍寶,奉之若神,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知道:新出土的未必就是最好的、最真的,未必就比一直流傳的更有價值。對它們的使用、引證應保持理性認識,加以冷靜細致的思考和研究。對于今人來說是新出土的文物,古人未必就沒有見過。它們為何沒形成文獻而流傳后世,也應是經過一番選擇和淘汰的。朱東潤說:“現代人提到‘作’字,總會聯想到‘創作’,其實古人底‘作’當是‘改作’,所以《論語》說‘何必改作’。漢人何休也主‘有所增益曰作’。”[13]58這或許更接近《琴舞》詩篇創作的真實情況。
綜上所述,本文對清華簡《琴舞》的斷句、釋讀提出了新觀點,有別于前人所認為的“琴舞九絉”是成王、周公所作的觀點。對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創作性質、創作時間提出了新觀點,認為《周公之琴舞》的創作符合中國古代“詩言志”的理論。提出了中國早期詩歌是根據現成言辭加工創作的,楚人在據周公、成王原有言辭創作詩歌時,必然會帶上楚國詩歌的特點這一觀點,糾正了前人一些說法。對《清華簡》的價值做出了比較適中的評判和理性思考,有別于前人一味夸大其地位的做法。
[1]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1).
[2]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
[3] 劉毓慶.雅頌新考[M].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
[4] 聞一多.神話與詩[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5] 王小盾.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詩六義原始[M].上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 李學勤.再讀清華簡《周公之琴舞》[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4,(1).
[7] 廖名春.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周頌·敬之》篇對比研究[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6).
[8] 李守奎.先秦文獻中的琴瑟與《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時代[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1).
[9] 李守奎.清華簡中的詩與《詩》學新視野[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3).
[10]李穎.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楚辭“九體”[J].中國詩歌研究,2013年第十輯。
[11]徐正英.清華簡《周公之琴舞》與孔子刪詩相關問題[J].文學遺產,2014,(5).
[12]孟修祥.先秦楚歌的文學模式[J].江漢論壇,2010,(5).
[13]朱東潤.公羊探故[M].北京:中華書局,1983.
(責任編輯 魯守博)
2017-04-18
江蘇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詩經》‘雅’‘頌’與周文化考論”(13ZWB008)。
祝秀權,男,安徽六安人,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I207.22
A
1672-0040(2017)04-006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