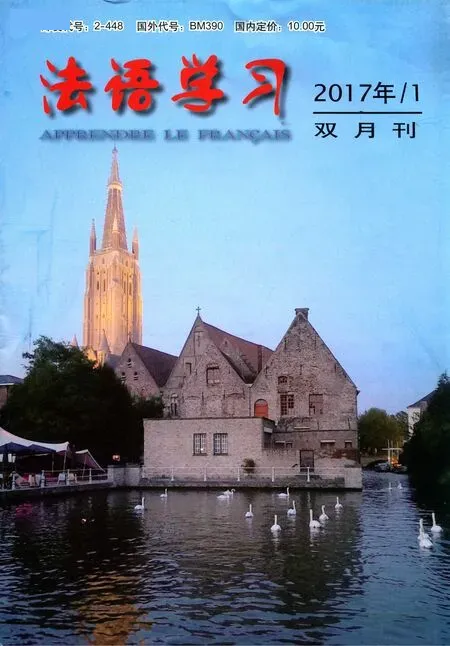從語音符號的即逝性看口譯的特征①
陳 偉
從語音符號的即逝性看口譯的特征①
陳 偉
在口譯和筆譯當中,承載意義的語言形式不盡相同,因此兩種類型的翻譯活動所遵循的邏輯也各有差異。“話語易逝,文字永存。”口語交際中承載信息的語音符號的即逝性,無疑會對口譯活動的特征產生巨大的影響。本文試圖從語音符號的即逝性出發,探討其對口譯活動造成的后果,并籍此對一些相關的問題——如口譯活動覆蓋的范圍、其所遵循的邏輯、譯員記憶的內容、口譯質量的標準、翻譯語言的方向等——闡述筆者的看法。
口譯;語音符號;即逝性;記憶;意義
①本文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校級區域國別研究中心項目《法國翻譯思想史》(項目編號QYGBYJ15CW)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翻譯,就是在譯語中用最為貼切自然的對等語再現源語的信息——首先是就意義而言,其次是就風格而言。”奈達(Eugene A. Nida)這一被引用了無數次的關于翻譯的經典定義告訴我們:翻譯的對象是信息,翻譯的目的是傳遞意義;無論是口譯還是筆譯,譯語和源語的表達形式必然會發生變化,但其所表達的內容——即意義——則應對等。
奈達的上述論述得到了廣大譯者和學者的廣泛認同。然而,由于在口譯和筆譯當中,承載意義的語言形式不盡相同,因此兩種類型的翻譯活動所遵循的邏輯也各有差異。“話語易逝,文字永存。”*《 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 》. ( Les paroles s’envolent, les écrits restent. )口語交際中承載信息的語音符號的即逝性,無疑會對口譯活動的特征產生巨大的影響。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從語音符號的即逝性出發,探討其對口譯活動造成的后果,并籍此對一些相關的問題——如口譯活動覆蓋的范圍、其所遵循的邏輯、譯員記憶的內容、口譯質量的標準、翻譯語言的方向等——闡述筆者的看法。
一、 語音符號的即逝性
在語言交際中,信息的發布者主要是通過語言符號來承載意義、傳達意義的。根據交流方式的不同,承載意義的媒介大致可分為文字符號(筆語)和語音符號(口語)兩種。雖然它們同屬語言符號,但在滯留的時間性上,卻迥然相異。
文字符號一旦落到紙上,即可長久地保存下來,供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讀者反復閱讀,正如千百年來,一些膾炙人口的文字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能夠為世界各國的不同讀者反復誦讀、長久流傳一樣。
但在口語中,語音符號卻沒有像文字符號那樣可長期滯留的特性。事實上,聲音由物體振動而產生,以聲波的形式存在,并通過某種介質傳播。盡管所有固體、液體和氣體都可以充當聲音傳播的介質,但通常我們聽到的聲音則是經過空氣傳播的。隨著聲波振動的停止,聲音也就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基礎而告消逝。由此可見,構成語音鏈的語音符號,無論是其存在形式(聲波)、還是其承載媒體(空氣),都不像文字符號那樣有形、具體、可捉摸。語音符號幾乎在其被發出的同時,便消失于無形之中,沒有任何穩定性可言。
誠然,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已經掌握了保留聲音的技術,可以通過各種不同手段,將語音符號記錄下來,使其和文字符號一樣,具備跨越時空的可能性。但是,就口譯活動——特別是同聲傳譯和交替傳譯——而言,這樣的聲音保留技術,除了方便事后的資料查閱和翻譯質量評估之外,對口譯特征的影響或改變不起作用。在口譯譯員眼里,語音符號仍然是轉瞬即逝的意義載體,這一點并沒有因為錄音技術的發明和廣泛使用而改變。
語音符號的即逝性,不僅僅取決于該符號所賴以存在的形式及其承載媒體的無形性,更重要的還與人類記憶的特點有關。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達尼察·塞萊斯科維奇(Danica Seleskovitch)就指出:人的記憶有短期和長期之分。*Danica Seleskovitch, Langage, langues et mémoires, étude de la prise de notes en 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 Minard Lettres Modernes, Paris, 1975.在她的論著中,“短期記憶”(mémoirecourt terme)也被稱為“即時記憶”(mémoire immédiate)、“言語記憶”(mémoire verbale)、“聽覺記憶”(mémoire auditive)、“操作性記憶”(mémoire opérationnelle)、或“記憶閾限”(empan mnésique),這一類記憶能夠將讀者或聽者所感知到的語言符號及其意義記錄下來,在頭腦中保留極短的一段時間。“長期記憶”(mémoirelong terme),亦稱“認知記憶”(mémoire cognitive),它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記住已經和語言符號剝離——也就是已經褪去語言外殼——的意義內容。無論是筆譯還是口譯,任何一位譯員在其翻譯過程中,均會不同程度地調動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記憶。
“長期記憶”之所以能夠長期保存意義內容,是因為后者已經與其載體——即語言符號——剝離,意義猶如經過壓縮的文件,使得記憶有足夠的空間來儲存它們。這解釋了為什么一個人可以憑借其短期記憶,將一部電影中的某一段對白、或一本小說中的某一段文字逐詞逐句地復述出來,但在較長時間以后,他能夠記住并回憶的只可能是這部電影或小說的內容,而不會是原原本本的相關對白或文字。
較儲存意義內容的“長期記憶”而言,儲存語言符號的“短期記憶”,其記憶時間功能要弱得多。事實上,短期記憶的能力——或“記憶閾限”(empan mnésique,一個人最大限度所能記住的符號數量)——因人而異,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取決于當事人的文化程度或教育水平。實驗表明:在筆語中,一個人的短期記憶能力“等于其視覺幾乎同時感知的7—8個字或詞”*許鈞、袁筱一,《當代法國翻譯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p.218.;而在口語中,一個人“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可以記住由5—9個‘符號’(詞語、字母、數字等)構成的語音鏈片段,并能在記憶中保存2—3秒鐘”*G. A/ Miller, cité par Danica Seleskovitch & Marianne Lederer, 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p.243.。此后,這些語言符號就會逐漸淡化乃至消逝,以便騰出短期記憶的空間,接受下一個“閾限”的語言符號。
短期記憶的上述特點,在筆譯中并不影響文字符號的穩定性,因為雖然文字譯者的短期記憶能力通常無異于口譯譯員,但鑒于承載文字符號的載體的物質性特點,文字譯者可以隨時隨地依靠反復閱讀,彌補短期記憶的不足。而在口譯中,語音符號的不可捉摸性、以及譯員在獲取信息時所使用的記憶的短期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擁有和文字譯者同樣的優勢。從這個意義而言,語音符號是即逝的。
語音符號的這種即逝性,對口譯的特征有很大影響。
二、語音符號的即逝性對口譯特征的影響
1. 口譯通常不以文學作品為對象
索緒爾(F. de Saussure)將語言符號的形式——即聲音或文字——稱為“能指”,將該形式所承載的概念稱為“所指”。米歇爾·阿吉安(Michèle Aquien)借用索緒爾的上述概念,指出口譯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所指邏輯”(logique du signifié)*Michèle Aquien, L’Autre Versant du langage, Paris, José Corti, 1997, p.59.。在口譯過程中,“話語易逝”,隨著說話者嗓音的消逝,語音符號的形式很快淡出于譯員的短期記憶,但其所承載的意義卻在被譯員理解之后,存入長期記憶之中;后者的任務,就是將他所理解并且記住的意義用譯入語重新表達出來。鑒于語音符號的易逝性,譯員難以對承載意義的語言形式做更多的關注,因此在信息再表達的過程中,他的工作重點通常是信息內容而非形式的再現。這一點和筆譯——特別是文學翻譯——有著本質的區別。
阿吉安還認為,筆譯——特別是文學翻譯——所遵循的邏輯是“能指邏輯”(logique du signifiant)*同上。。這不僅是因為在筆譯過程中,譯者有可能對長期滯留在眼前的文字符號進行反復閱讀,更重要的是,筆譯、尤其是作為其最高境界的文學翻譯,對語言形式有著特殊的要求。在文學作品中,文字被視為擁有特殊內在功能的載體,是內容表達的重要手段,有時甚至還成為內容本身的組成部分。作者通過遣詞造句,充分運用音韻、節奏等各種文體手段,令讀者在腦海中產生豐富的形象和聯想。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把文學作品中語言符號的這種內在特殊功能稱為“詩性功能”,認為它“突出了符號可觸知的一面”*Roman Jakobson, 《 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 》, in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rad. N. Ruwe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3, p.218.。而文字符號的“詩性功能”,正是筆譯不可忽視的因素:譯者不僅必須理解、而且必須再現這些功能。換言之,他有責任在向譯語讀者傳遞原作內容的同時,再現其修辭和美學特點,包括原作者的風格、文字的音韻、句子的節奏,等等。如果譯文不能滿足語言形式上的要求,那么譯文作品的文學效果只能是一種奢望。
從翻譯的角度來看,筆譯的“能指邏輯”和口譯的“所指邏輯”是不相兼容的。雖然兩種翻譯活動均以忠實傳遞源語文本或話語的信息為原則,但它們傳遞信息的方式卻大相徑庭。由于文字符號的穩定性特點,意義的產生變得更加復雜:譯者往往只要在閱讀中稍微停頓一下,便可能發現隱藏在文字符號背后的更加豐富、更為深邃的涵義——而在口譯過程中,除非發生特殊情況,否則譯員是不可能打斷連貫的口語交際,要求說話者停頓或重復的。換言之,鑒于筆譯的“能指邏輯”,譯者在意義的理解、信息的表達、以及譯語形式的選擇等方面,往往需要比口譯譯員花費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精力,以便深入思考和反復推敲;而文字符號可以反復閱讀的特點,事實上也給了譯者這樣的可能性。古今中外,一部文學品花去譯者幾年、幾十年、甚至畢生精力的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文字符號無法為譯者的短期記憶所儲存。前文所言,由于語言形式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因此它是翻譯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如果說,文字的穩定性特點使得筆譯譯者有條件重視語言形式的話,那么,口譯譯員受其短期記憶能力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給予語言形式過多的關注。
因此,鑒于口、筆譯所遵循的邏輯的不同,口譯、特別是同聲傳譯,一般涉及的都是那些遵循“所指邏輯”——即以傳遞信息內容為主要目標——的功能類文本,而不會把文學作品列入翻譯的對象之列;即使迫于需要,必須對文學作品進行口譯時,譯員通常也只能滿足傳遞內容的要求,而無暇顧及作品的形式再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作品是不適合以口譯的方式加以傳播的。
2. 口譯以意義為記憶內容
維奈(Vinay)和達爾貝勒奈(Darbelnet)曾經說:“譯者傳遞的是思想和情感,而非文字。基于這一原則,(他)需要尋求的(翻譯)單位是思想單位(unité de pensée)。”*Jean-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ais et de l’anglais, Paris, Didier, 1977 (1958), p.37.從這個意義而言,如果不談文學翻譯對文字的特殊要求,那么口譯的本質和筆譯是一樣的。
維奈和達爾貝勒奈所說的“思想單位”,在釋義派翻譯理論家的筆下被稱為“意義單位”(unité de sens)。“意義單位是翻譯中幫助建立等值的最小成分”*許鈞、袁筱一,《當代法國翻譯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p.196.,它與特定的語言長度并不吻合,既不是字、詞,也不是句子或其他語法單位,而是儲存在短期記憶中的語言符號作用于長期記憶中的語言知識和言外知識、并與后者交互交融的產物。在口譯中,譯員捕捉到語音鏈并對其語義進行初步識別,識別的結果和該語音鏈一起進入他的短期記憶,喚起他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認知認識,加上交際環境、語言環境等因素的介入,從而產生意義單位。意義單位相互疊加、相互滲透,最終形成意義。而新的意義則作為新記憶的內容,被儲存到譯員的長期記憶乃至認知認識庫中,為他的后續理解活動提供支持和幫助。
可見,在口譯譯員對意義單位及意義的捕捉和理解過程中,記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也只有意義單位和意義——亦即被理解的內容,才可能成為譯員長期記憶的組成部分。正因如此,塞萊斯科維奇指出:“在口譯中,記憶和理解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D. Seleskovitch,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 probl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1968, p.74.“絕對的不理解意味著忘卻(……),而理解則是記憶的同義詞。”*同上, p.76.換言之,理解是記憶的前提,記憶是理解的結果,有時兩者甚至混淆在一起,難分彼此。
在口語交流中,構成語音鏈的符號通常以5—9個的數量進入短期記憶,在那里停留2—3秒,隨即淡化乃至消逝。如果一個講話者的語速是每分鐘180個字,那么記憶力再好的譯員,也不可能按講話順序記住所有的詞。不過,雖然符號在記憶中消逝,但其喚起的意義,一旦被譯員理解,便可同語言形式剝離,留存在長期記憶之中。因此,其實“(口譯譯員)毋需具備超乎尋常的記憶能力,他只需關注意義的分析,一旦達成理解,意義便自動被記錄在記憶當中”*F. Isra?l & M. Lederer, La Théorie interprétative de la traduction (tome I), Genèse et développement,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2005, p.60.。事實上,譯員在聆聽講話時的時候,并不進行語言分析,也不試圖記住構成講話的每一個詞;也就是說,他關注的并非是捕捉語音符號(能指),而是對交際意義(所指)的理解——“理解是記憶的同義詞”。
但在口譯實踐中,似乎存在著一個與上述論斷相悖的現象,就是譯員的筆記。從表面上看,譯員通過記錄,將聽到的語音符號轉換為文字符號,使其擁有了更大的穩定性,從而解決了因語音符號的易逝性而造成的短期記憶不足的問題。但就筆記的本質而言,事實并非如此:譯員的筆記不以語音符號為內容、也不以記錄語音符號為目的。任何一位有經驗的譯員,他的筆記從來都不會全部由文字組成,而是文字和其他各種符號的混雜,甚至只有符號而沒有文字;即使是口譯筆記中的文字,它們的地位和功能也與其他符號無異。這是因為,口譯筆記只是“一種記憶的技術手段,一種‘備忘錄’,用以喚起對聽話時所理解的意義的記憶”*同上, p.81.。換言之,筆記的功能是喚起譯者對意義內容的記憶,而非承載該意義的符號。因此,如果說,口譯中筆記的本質,的確是為了解決語音符號的易逝性問題、進而彌補譯員短期記憶不足的話,那么筆記的內容和目的,從來就不是語言的符號或形式。
3. 口譯以目標受眾為導向
在意義被理解并且被記憶之后,譯員就必須使用最符合譯入語的口語表達方式,將其表達出來。在這一階段,語音符號即逝性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的。
與口譯相比,一篇在用詞、文法、或表達方式上存在這樣或那樣問題的筆譯譯文,通常更容易為譯入語受眾所理解。因為,后者可以通過耐心反復地閱讀、大量地查閱資料,彌補譯文在表達上的不足,進而實現對譯文的理解。口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口譯聽眾和口譯譯員一樣,他們所捕捉到的語音符號同樣也是轉瞬即逝,他們的短期記憶同樣也只能持續2—3秒鐘,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像筆譯讀者那樣,在遇到晦澀難懂的文字、或有悖于規范的表達手段的時候,可以通過反復閱讀和思考達到最后理解。口譯聽眾需要的,是能夠幫助自己即時抓住話語意義的翻譯。因此,正如釋義派翻譯理論家們所主張的那樣,口譯必須清晰易懂:“口譯譯員的表達必須非常清晰,同聲傳譯聽起來不能像多少有點笨拙的翻譯,而應該像正常的話語。”*Danica Seleskovitch & Marianne Lederer, Pédagogie raisonnée de 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p.137.
有鑒于此,很多人認為,在表達方式上,口譯是以取悅目標受眾為目的、以目標受眾的接受習慣為導向的翻譯活動;衡量口譯質量的標準,除了信息再現的準確之外,同樣重要的還有表達的清晰度。而表達是否清晰,恰恰取決于譯員所用的譯入語是否符合目的語聽眾的接受習慣:譯員所用語言越是為聽眾所熟悉,后者對意義的捕捉和理解就越容易,他也就越會認為信息的表達是流暢、清晰的。由此可見,口譯應力圖使用聽眾所習慣和熟悉的譯語表達方式,以使其方便快捷地理解話語的意義,從而滿足“清晰”的標準。“如果口譯表達不清晰、不能即時被理解,如果譯員不能做到像原說話者那樣自如地運用自己的語言、而是用另一種語言的方式來表達思想,那么他的翻譯立刻就會變得晦澀難懂。”*同上, P.137.
也正是為了滿足口譯表達的“清晰”原則和目標受眾導向的要求,翻譯界一致公認,理想的口譯方向是從B語言(外語)譯成A語言(母語)。的確,一名譯員,無論他對B語言及其文化的掌握有多么精深,但在表達思想和情感的時候,肯定是使用A語言更加得心應手。如果說一名高水平的譯員使用B語言進行表達,也可能達到遣詞的規范、造句的正確,那么當他使用A語言時,毫無疑問會顯得更加自如、更加貼切、甚至更加優雅。因為A語言是他自幼浸潤于其中的語言,使用A語言是他發自本能的、幾乎是下意識的行為;他在使用A語言時所表現出的自信、自然,是任何一個使用B語言的人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在從B語言翻譯到A語言的情況下,譯員更有可能做到“像原說話者那樣自如地進行表達”,從而使意義的傳遞更加清晰易懂,更好地滿足聽眾的理解需求。
結論
口譯是一個難得的實驗室,通過它我們可以發現語言在某些特殊條件下轉換的機制。
語音符號的即逝性,決定了口譯是一種遵循“所指邏輯”的跨語言交際活動。受到上述特性和邏輯的影響或者說限制,口譯活動在其覆蓋的范圍、針對的內容、翻譯產品的質量評判、翻譯語言的方向等方面,都顯示出與筆譯的諸多不同。
語音符號的即逝性,要求口譯譯員不僅僅做到對信息的“實時”理解和傳遞(這意味著譯員必須以正常的交流語速捕捉信息、實施翻譯),而且還必須自然、清晰地進行實時傳遞——也就是說,譯員應讓目標聽眾覺得,信息似乎并未經過翻譯、而是直接用譯入語表達出來。正因如此,研究語音符號的即逝性,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口譯本質、特點、及其與筆譯的差異,進而更加深刻地認識“目標受眾導向”的口譯理念。
許鈞,袁筱一.《當代法國翻譯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Aquien, M.L’AutreVersantdulangage. Paris, José Corti, 1997.
Israёl, F., Lederer, M.LaThéorieinterprétativedelatraduction(tome I),Genèseetdéveloppement.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2005.
Jakobson, R. 《 Linguistique et poétique 》, inEssaisdelinguistiquegénérale, trad. N. Ruwe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3.
Lederer, M.Latraductionaujourd’hui,Lemodèleinterprétatif. Hachette F.L.E., 1994.
Oustionoff, M.LaTraduction. Coll.Quesais-je? PUF, 2003.
Seleskovitch, D.L’interprètedanslesconférencesinternationales—problèmesdelangageetdecommunocation. Paris, Lettres Modernes Minard, 1968.
Seleskovitch, D.Langage,languesetmémoires, étudedelaprisedenoteseninterprétationconsécutive. Minard Lettres Modernes, Paris, 1975.
Seleskovitch, D., Lederer, M.Pédagogieraisonnéedel’interprétation. Paris, Didier érudition/Office des publications officielles des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2002.
Vinay, J.-P., Darbelnet, J.Stylistiquecomparéedufran?aisetdel’anglais. Paris, Didier, 1977 (1958).
Quelquesparticularitésdel’interprétationvuetraverslecaractèreévanescentdessignessonores
Résumé : Dans la traduction écrite et l’interprétation, les formes linguistiques véhiculant le sens se diffèrent. Pour cette raison, les logiques suivies respectivement par les deux types d’activités traduisantes précédemment mentionnés sont aussi différentes. 《 Les paroles s’envolent, les écrits restent. 》 Il va sans dire que le caractère évanescent de signes sonores a un impact important sur l’interprétation. Le présent article essaie donc d’étudier les conséquences engendrées par l’évanescence des signes sonores sur l’interprétation, tout en envisageant certaines questions corrélatives, telles que le champ d’action de l’interprétation, la logique qu’elle suit, l’objet de la mémorisation de l’interprète, le critère de jugement de la qualité de l’interprétation, le sens idéal de l’interprétation, etc.
Motsclés: interprétation ; signe sonore ; évanescence ; mémoire ; sens
(作者信息:陳偉,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研究領域:翻譯理論與實踐)
H059
A
1002-1434(2017)01-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