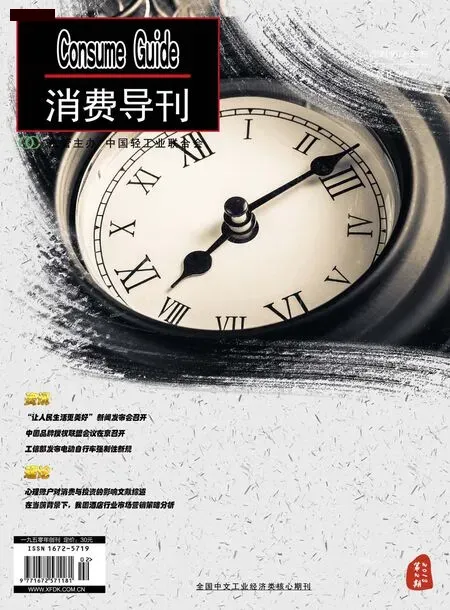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的主觀認知問題研究
楊帆
摘 要:網(wǎng)絡電信犯罪常常具有非接觸性、小額多筆、與技術(shù)灰黑產(chǎn)業(yè)聯(lián)系千絲萬縷,受害面廣、偵破難度大等新特點,故辦案機關(guān)在承辦此類案件時常常存在行為主觀“明知”如何證明的種種困惑。2016年12月19日,‘兩高一部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辦理電信網(wǎng)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于解決實踐中網(wǎng)絡銷贓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電信網(wǎng)絡犯罪里犯罪嫌疑人主觀明知如何認定問題提供了明確的解決途徑,為解決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的主觀認知問題初步提供了切實有效的規(guī)范依據(jù)。
關(guān)鍵詞:掩飾隱瞞犯罪所得 主觀明知 綜合認定 證據(jù)鏈條
一、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行為人主觀認知問題概述
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的蓬勃發(fā)展,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新浪潮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工作享受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巨大便利,然而,另一方面,網(wǎng)絡電信詐騙犯罪也日漸猖獗,給廣大社會公眾造成了愈來愈嚴重的損失。而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這一新的公共領(lǐng)域及技術(shù)灰黑產(chǎn)業(yè)提供的用于詐騙、以及詐騙得手后洗錢的計算機軟件,一些犯罪團伙屢屢實施針對特定目標群體的互聯(lián)網(wǎng)詐騙及后續(xù)洗錢銷贓等違法犯罪,并形成了上下游分工與較為嚴密、層階化且以合法企業(yè)形式為掩蓋的犯罪組織,且呈現(xiàn)出受害人地域分布廣,行為隱蔽,犯罪行為過程中反偵察、規(guī)避監(jiān)管意識強,違法犯罪活動與正常合法經(jīng)營活動雜糅等新特點,給偵查、審理此類案件帶來了很多刑事司法程序?qū)用娴奶魬?zhàn),比如缺乏或極難收集據(jù)以定罪的直接證據(jù),證據(jù)多以電子數(shù)據(jù)及其傳來形式呈現(xiàn),證據(jù)之間不能“一一對應”構(gòu)成印證等等,特別是對于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主觀構(gòu)成要件上,實務中更是存在著諸多爭議與疑難之處。
在圍繞著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主觀認知相關(guān)的證據(jù)收集與審查判斷上,這類網(wǎng)絡電信犯罪案件中呈現(xiàn)出來的特點為:辦案機關(guān)查獲、扣押、提取的證據(jù)多為間接證據(jù),且基本都是以電子數(shù)據(jù)形式呈現(xiàn)的,但是一般來說缺乏賴以定罪的直接證據(jù),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認從事的系違法犯罪活動,故難以獲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尤其是有罪供述。
由此產(chǎn)生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方面構(gòu)成‘明知的故意?由于實務部門攝于傳統(tǒng)的“印證證明模式”、很難獲取“一一對應”的印證性直接支持證據(jù),因此一方面在面對數(shù)量繁多、類型多樣的海量的以電子數(shù)據(jù)形式呈現(xiàn)的間接證據(jù)時束手無策、以至于無法認定基本的案件事實,或是陷入證據(jù)收集的誤區(qū);而另一方面,辦案機關(guān)只能接而求助于使用“司法推定”來佐以證明,但是實定法上對于“推定”規(guī)范表述的嚴重不足及至漏洞,更是讓辦案機關(guān)無所適從、如臨雷池,不敢積極作為,最終導致實踐中辦案機關(guān)在對于行為人主觀認知的證明上左右為難,乃至于影響到對于網(wǎng)絡電信犯罪的依法懲治打擊的效果。
二、“意見”出臺后對犯罪嫌疑人主觀明知認定的依據(jù)
然而,實務部門遇到的上述困境還是得到了有權(quán)機關(guān)的積極回應。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guān)于辦理電信網(wǎng)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為進一步健全工作機制、加強協(xié)作配合以堅決依法有效懲處遏制電信網(wǎng)絡詐騙等犯罪活動祭出又一套法律“組合拳”。
總體來說,“意見”體例上分為“總體要求”、“依法嚴懲電信網(wǎng)絡詐騙犯罪”、“全面懲處關(guān)聯(lián)犯罪”、“準確認定共同犯罪與主觀故意”、“依法確定案件管轄”、“證據(jù)的收集和審查判斷”六大部分,涵蓋了實施電信網(wǎng)絡詐騙的犯罪數(shù)額認定標準、從重處罰的情形、構(gòu)成詐騙罪既遂與未遂的定罪依據(jù)、刑罰的適用,《刑法》中與電信網(wǎng)絡詐騙關(guān)聯(lián)的其他罪名的認定及適用等刑事制裁電信網(wǎng)絡詐騙犯罪相關(guān)的實體與程序規(guī)則的方方面面。其中的一大亮點便是:“意見”對于解決實踐中網(wǎng)絡銷贓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電信網(wǎng)絡詐騙關(guān)聯(lián)犯罪里犯罪嫌疑人主觀明知如何認定問題提供了明確的解決途徑——“意見”第“三、(五)”部分第一款這樣規(guī)定:“…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轉(zhuǎn)賬、套現(xiàn)、取現(xiàn)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有證據(jù)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5.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通過手機充值、交易游戲點卡等方式套現(xiàn)。”這就解決了現(xiàn)實里很多在辦案件中懸而未決的疑難問題:在沒有被害人陳述的情況下,若有其他證據(jù)證明犯罪嫌疑人在知情的狀態(tài)下實施以明顯異于市場的價格套現(xiàn)的行為,且這些證據(jù)經(jīng)查證屬實并可資形成完整證據(jù)鏈條的,則足以認定該犯罪嫌疑人系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的主觀認知證明難題似乎有了規(guī)范依據(jù),“意見”對相關(guān)司法實務的指導、參考價值,著實值得肯定。
但是,“意見”對于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的行為人主觀認知證明的方面,仍存在著一些局限:前述“有證據(jù)證明確實不知道的除外”這一條款對于解決證明網(wǎng)絡銷贓犯罪行為人主觀明知與否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有利于解決定案的困境。但若細究之,證明主體由何方承擔,文本里找不到確切答案,但是根據(jù)上下文體系解釋,可推知證明主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這就牽涉到了一個問題——‘證明明確不知道的證明標準如何?需要達到怎樣的程度方可證明行為人“確實不知道”,倘若這個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則該條款的實際應用效果恐會大打折扣。因此,除了實定法尤待進一步完善之外,在現(xiàn)有法治條件下還需探索一條主觀認知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完善的途徑,以期更適切地解決疑難、復雜網(wǎng)絡電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主觀認知的證明問題。
三、主觀明知認定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完善的途徑
在筆者看來:若要妥善地解決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主觀認知問題,需要建構(gòu)一條確立在‘證據(jù)鏈條證明模式基礎(chǔ)上的‘綜合認定途徑,也即:通過收集篩選現(xiàn)有的諸多間接證據(jù),接著將其編織成一條完整的證據(jù)鏈條,然后在這基礎(chǔ)之上,綜合與案件法律論證與證立的“小前提”相關(guān)的所有材料,通盤考量推出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具體而言,這條司法實踐中完善的途徑有以下幾個要點:
首先,在缺乏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以及被害人陳述等直接證據(jù)的情形下,對行為人主觀明知的認定只能依靠一系列間接證據(jù)。而如何在紛繁復雜、數(shù)量眾多的間接證據(jù)中篩選出可供證明案件事實并能編織成證據(jù)鏈條的那一部分,則倚賴經(jīng)驗法則(everyday logic)的指導和推定的適用。
經(jīng)驗法則,通俗的說就是日常經(jīng)驗與生活常識,即通常所說的“常識、常理、常情”。但需要注意的是,經(jīng)驗法則不能僅僅停留在個別人所特有的個別經(jīng)驗水平上,而應該是至少能獲得相當一個范圍的人們普遍承認的命題。
其次,在間接證據(jù)的使用中,必然涉及到推定適用的問題。這里所說的推定,是指利用已知事實,推斷出未知事實,屬于歸納推理范疇。
司法活動中的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兩種。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主觀認知爭議問題牽涉到的多屬于事實推定的范疇。事實推定是一種從基礎(chǔ)事實A推斷事實B,而且可以反駁的推定。
為防止使用間接證據(jù)進行推定可能產(chǎn)生的偏誤甚至悖謬,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保證所搜集的間接證據(jù)全面、系統(tǒng)、真實,使通過間接證據(jù)形成的證據(jù)鏈符合事實發(fā)生的邏輯。因而法庭在審查判斷時,要對其進行充分的辯論、質(zhì)證,以此實現(xiàn)案件事實的合理和可接受性。在這一過程中,除了既有的證據(jù)規(guī)則外,仍然需要求助于經(jīng)驗法則,同時還要考慮到間接證據(jù)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綜合考量方能得出周延可靠的事實推定。
接著,間接證據(jù)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要素也是利用間接證據(jù)來編織完整證據(jù)鏈條、既而認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邏輯性要件之一。借鑒英美法律辭書之圭臬——《布萊克法律詞典》中的定義,“關(guān)聯(lián)性是指那種有助于證明有關(guān)假設的屬性,這種假設一旦成立,將從邏輯上影響爭議事項。證據(jù)的關(guān)聯(lián)性描述了向法庭提交的證據(jù)與某一案件中的關(guān)鍵命題或可證明的命題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是證據(jù)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但即使是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證據(jù),客觀上也不必更不能悉數(shù)搜集,亦須進行必要的挑選。唯有建立在邏輯性、合理性、良好的意識以及準確判斷的基礎(chǔ)之上,證據(jù)的關(guān)聯(lián)性才能得以保障。
最后,在利用‘證據(jù)鏈條理論來證明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行為人的主觀認知時,可酌情引入域外法中情狀證據(jù)理論來佐以推論。所謂情狀證據(jù)(circumstantial evidence),來源于英美法證據(jù)規(guī)則,系指用推論的方法,證明案件中待證事實的真?zhèn)巍D壳拔覈鴮W界對情狀證據(jù)的認識尚不統(tǒng)一,甚至還缺乏理論界的廣泛認同,且該類證據(jù)與間接證據(jù)有很多方面有重疊之處,但是在對情狀證據(jù)的范圍進行限制并與間接證據(jù)及其適用方法作區(qū)分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援用情狀證據(jù)的概念來指那些可憑直覺和逆向思維判斷行為人動機、知情與否等行為的主觀要素的證據(jù)。
綜上,筆者所歸納的主觀明知認定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完善的途徑,即:先利用經(jīng)驗法則、歸納推理以及借助情狀證據(jù)理論對網(wǎng)絡電信犯罪案件中呈現(xiàn)的一系列間接證據(jù)進行篩選,再將篩選出來的間接證據(jù)憑借其相互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編織出一條完整的證據(jù)鏈,來證明行為人在實施網(wǎng)絡電信犯罪時主觀上是否屬于“明知”的路徑。該路徑不僅論證過程較為周延、嚴謹,有著比較充分的理論支撐依據(jù),而且也是符合上位法精神的、實踐中利于操作的方法。
伴隨著我國刑事訴訟“以審判為中心”改革的有序推進與刑事證明制度的不斷完善,網(wǎng)絡電信犯罪中的主觀認知問題一定會在法律層面得到適切、圓滿的解決!對此筆者充滿信心、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龍宗智.印證與自由心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模式[J].法學研究.2004年第2期。
[2][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M].童世駿譯,三聯(lián)書店(北京)2003年版:247頁。
[3]何邦武.小額多筆網(wǎng)絡電信售假和詐騙犯罪的取證現(xiàn)狀[J].政治與法律.2016年第8期。
[4]陳瑞華.刑事證明標準中主客觀要素的關(guān)系[J].中國法學.2014年第3期。
[5]凌云 俞硒.間接證據(jù)定案規(guī)則在快遞員身份認定中的適用[N].人民法院報,2014-12-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