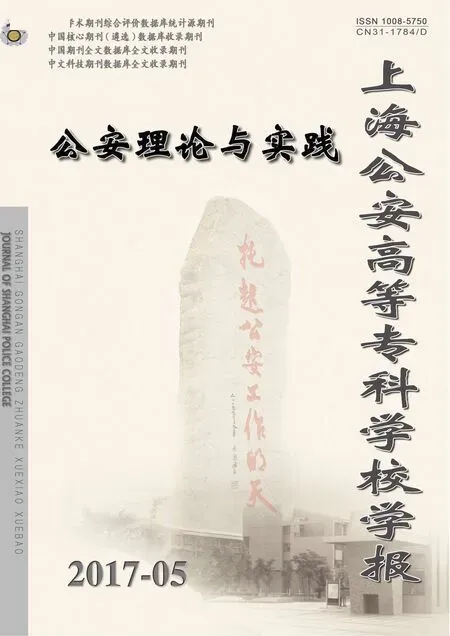盜竊、搶奪、搶劫等侵財案件未遂認定疑難問題解析
項 谷,朱能立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上海 200052)
盜竊、搶奪、搶劫等侵財案件未遂認定疑難問題解析
項 谷,朱能立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上海 200052)
盜竊、搶奪、搶劫等侵財類犯罪既遂與未遂的界定,特別是未遂的認定,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問題。入戶盜竊、扒竊與普通盜竊一樣,均屬侵財類犯罪,區分既未遂堅持以獲取財物為標準,不以財物數額為標準,但獲取財物的方式有取得和接觸等表現形態;公然奪取型搶奪罪既未遂標準,應以被害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為既遂的主要衡量標準,以搶奪行為人實際控制財物為參考標準;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標準,應參照普通搶劫罪認定,即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屬搶劫既遂。
入戶盜竊;扒竊;公然奪取型搶奪;轉化型搶劫;未遂
盜竊、搶奪、搶劫即俗稱的“兩搶一盜”案件是我國當前高發多發常發的侵財類案件。以盜竊為例,2014年上海法院受理一審盜竊案件7,882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4.6%。司法實踐中如何正確認定該類犯罪的既遂和未遂,對于正確適用法律、有效打擊侵財犯罪、維護人民群眾人身財產安全和社會治安穩定均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行為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狀態。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且司法解釋規定對不以數額巨大的財物或者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的盜竊未遂不定罪處罰,因此,犯罪未遂是這三類侵財類型犯罪重要的定罪量刑情節。當前,《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的盜竊罪,以及公然奪取型搶奪罪、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認定及法律適用,在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多,又缺乏統一規范的認定標準。為統一執法認識和尺度,有必要對該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希望對司法實踐有所借鑒和參考作用。
一、入戶盜竊、扒竊未遂的認定及處理
案例一:2015年8月1日19時許,梁某至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鎮被害人施某家中,撬窗入室盜竊,但經翻找未竊得有價值的財物而離開。被害人施某回家后發現被翻動的痕跡而報警,警方經調看監控和痕跡比對將梁某抓獲。
案例二:2016年4月18日15時許,張某在上海火車站乘坐軌道交通時,發現被害人王某將一部蘋果6S手機放入褲兜右側,便一路尾隨被害人王某,后趁被害人不備,將被害人的蘋果6S手機盜走。而張某的行蹤早已被上海市軌交總隊的民警通過高清監控探頭獲悉,并已通知就近的反扒民警黃某、趙某,在張某扒竊之前,黃某跟蹤張某,在確認張某得手以后,通知趙某一起合圍將張某抓獲并當場起獲贓物。
案例一與案例二涉及到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盜竊未遂的認定及如何定罪處罰的問題。《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條將“入戶盜竊、扒竊”列為盜竊罪的罪狀,增加了入戶盜竊、扒竊入刑的規定。根據修訂后的刑法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學者認為,《刑法修正案(八)》將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盜竊與竊取公私財物達到數額較大標準的行為作為盜竊罪的并列構成要件,意味著入戶盜竊、扒竊不再有犯罪數額的要求,即只要具有入戶盜竊、扒竊行為的,即使分文未取,也成立盜竊罪的既遂。我們認為,無論是普通盜竊還是入戶盜竊、扒竊、攜帶兇器盜竊,均屬侵財類犯罪,既未遂的區分依舊堅持獲取財物為既遂標準,但不以財物數額為標準,只有實際竊得財物才能構成盜竊既遂,否則是盜竊未遂,當然“竊得”財物的方式根據不同的侵財手段呈現“取得”“接觸”等表現形式。
(一)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盜竊仍屬結果犯存在犯罪未遂狀態
所謂“入戶盜竊”,是指非法進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盜竊的行為。而“扒竊”,是指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財物的行為。有觀點認為,《刑法修正案(八)》對盜竊罪條款修改后增加的入戶盜竊與扒竊均屬于行為犯的范疇。入戶盜竊,是以盜竊的手段行為即“入戶”作為犯罪構成要件,以是否完成入戶行為作為犯罪既未遂的標準,重點處罰的是“入戶”這個行為,而盜竊的數額已不是法律關注的重點。否則就會出現盜竊一塊錢是既遂,而未竊得財物就是未遂的情況。扒竊的情形也是如此。
我們認為,入戶盜竊、扒竊仍屬于盜竊罪的一種,從罪質來看仍屬于侵財類犯罪,具有侵財類犯罪的共同特征,侵犯的主要法益還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從犯罪構成看,入戶盜竊、扒竊犯罪的成立,不僅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故意,還要求客觀上存在竊取了公私財物的犯罪結果。因此,入戶盜竊、扒竊均要求行為人侵犯了他人一定數額的財產,只不過降低了對犯罪數額的要求,不要求達到普通盜竊“數額較大”的標準,但仍屬于結果犯的范疇,不屬于行為犯。因此,入戶盜竊、扒竊作為侵財犯罪,仍應以行為人取得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物作為既遂的標準。因此,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盜竊存在犯罪未遂狀態,案例一中梁某未竊得財物應屬于盜竊未遂。
(二)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盜竊既遂與未遂標準
關于盜竊罪的既遂標準,理論上有接觸說、轉移說、隱匿說、失控說、控制說(取得說)、失控加控制說。應當說,只要行為人控制了財物,就是盜竊既遂。刑法關于盜竊既遂與未遂標準的通說一般采取“控制+失控說”,即行為人事實上占有了財物,建立了新的支配關系,實際上控制了財物。一般來說,只要被害人喪失了對財物的占有,就應認定行為人控制了財物。我們認為,入戶盜竊、扒竊等作為盜竊犯罪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既未遂的標準實踐中主要兼采“犯罪人的控制”與“被害人的失控”相結合作為認定依據。我國刑法通說理論還認為,盜竊是“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只要行為人自認為被害人沒有發覺而取得的,就是秘密竊取。而在現代社會遍布的監控,使盜竊行為難以真正秘密進行,即使被害人沒有發覺,也容易被公安民警等第三人發覺,進而在第三人的監控下完成扒竊行為。如在案例二的情況下,民警的監控是否影響扒竊既未遂標準的認定?有觀點認為,對于扒竊案件,他人注視特別是公安民警的注視、監控本質上等同于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保護,應等同于被害人的注視,只要被害人、公安民警或者第三人的注視不間斷,就是犯罪現場的延伸,是被害人“控制范圍”的延伸。行為人在掩耳盜鈴式公然扒竊的情況下被人贓俱獲,視為被害人對財物未失控,行為人未實際控制,應認定為犯罪未遂。我們不認同上述觀點,在扒竊犯罪中,犯罪既未遂標準的認定,應根據特定場合、被害人“合理控制范圍”等因素,綜合考察被害人是否對財物失控,行為人是否對財物實際控制。具體把握以下三點:
一是強調被害人的“失控說”。“失控說”以盜竊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是否使公私財物的權利人失去了對財物的實際有效控制,作為劃分盜竊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凡是盜竊行為使盜竊目的物脫離了權利人的實際有效控制,為盜竊既遂,相反,未能使盜竊目的物脫離權利人實際有效控制的為盜竊未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失控的主體是針對被害人而言,而不是針對第三方,如路邊旁觀者、公安民警以及監視器等。也不應對被害人所謂的“合理控制范圍”作過多限制或延伸。特別是在公共場所下,公安民警、安保人員或他人的注視、監控與否并不影響既遂的認定,否則在現代社會遍布“天眼”探頭監控下,即使行為人當時成功逃離現場,但因為監控使其最終難逃法網,其犯罪行為永遠難以既遂。實踐中,不應對被害人的失控作過高標準的要求。從證據收集的角度而言,扒竊比其他普通盜竊案件收集證據難度高,由于扒竊犯罪多發生在人員流動量大的公共復雜場所,一般作案時間極短、現場痕跡少、手段比較隱蔽,扒竊的作案者多為具有反偵查經驗的“老手”,且經常多人交替配合作案,只要不當場人贓俱獲,扒竊贓物一經得手即被迅速轉移,被抓的人矢口否認,而扒竊者與被竊者相互間無一定關系,即使有旁證目擊證人往往對當事人的情況也多不了解,難以形成證據鎖鏈,需被害人、公安人員或其他人以快制快,爭取人贓俱獲。這種在公共場所扒竊的,如等被害人徹底對財物失控,扒手完全控制財物,才能認定既遂,既遂后再實施抓捕,恐怕已失去了最佳時機,即使在公安機關布控下也難以實際控制。筆者認為案例二中,被害人王某的蘋果6S手機被張某從褲兜右側盜走即為失控。
二是強調犯罪人的“接觸說”。“接觸說”是以盜竊行為人是否實際接觸到被盜財物為根本標準,認為只要犯罪嫌疑人實際物理接觸到財物就已經實現了盜竊既遂,物理空間上沒有能夠實際接觸到財物的就是盜竊未遂。應注意的是,在認定盜竊罪既未遂時,必須根據財物的性質、形狀、體積大小、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狀態、行為人竊取狀態等進行判斷。由于扒竊的對象一般體積較小,如手機、錢包等財物,一般應當以行為人將手伸入被害人衣褲口袋或者背包、挎包中接觸、拿到財物,即為取得財物的既遂標準。案例二中,張某將手伸入被害人放入褲兜右側,接觸到被害人的蘋果6S手機,從被害人口袋拿出即為既遂。
三是強調被害人的“無反應說”。所謂“無反應”,是指被害人對盜竊行為人的行竊沒有覺察到,沒有作出反應。特別是扒竊行為人扒竊“技術”高、手段隱蔽、作案時間短且被盜物品體積小,被害人往往來不及反應財物已經失竊。扒竊案多發生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場所,即使被害人沒有注意到被竊,旁觀第三人往往有所覺察,可以說扒竊者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行竊。因此,認定扒竊時一般對秘密竊取的要求程度較低,只需行為人自以為秘密竊取即可。如案例二中,行為人張某在公共場所進行扒竊被害人褲兜右側的手機,被害人因沒有覺察到而沒有作出反應,即使民警已經通過監控發現扒竊者蹤跡,不影響犯罪既未遂的認定,張某將被害人的手機拿到手中或放入口袋時即構成盜竊既遂。
(三)入戶盜竊、扒竊犯罪未遂的定罪處罰
入戶盜竊、扒竊等未遂狀態下應當如何處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盜竊解釋》)第十二條規定,盜竊未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的,以及其他情節嚴重情形的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而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類型盜竊未取得財物的未遂,是否依據《盜竊解釋》十二條規定不構成犯罪,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我們認為,入戶盜竊、扒竊未遂的,也應追究刑事責任。《盜竊解釋》第十二條將盜竊未遂的處罰范圍限定在“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珍貴文物為盜竊目標”等情節嚴重情形,針對的對象應是普通盜竊,而不適用于入戶盜竊、扒竊、攜帶兇器盜竊等特殊類型的盜竊。犯罪的構成標準與犯罪形態的既未遂是刑法上兩個緊密關聯但又本質不同的概念,故意犯罪的基本構成要件一般以犯罪既遂形態為標準而設定,如普通盜竊犯罪的入罪門檻。而犯罪既未遂形態描述的是特定危害行為的停止形態,成罪標準表達的僅僅是不同行為構成犯罪的最低刻度。入戶盜竊、扒竊等特殊盜竊沒有規定入罪的數額標準,無需像普通盜竊一樣,要以數額較大的財物作為構成犯罪的門檻,實際上是調低了扒竊等特殊盜竊的入罪標準。況且,入戶盜竊、扒竊的“數額巨大”與“數額特別巨大”的處罰標準也與普通盜竊犯罪相區別。如《盜竊解釋》第六條規定,入戶盜竊數額達到“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百分之五十的,可以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或者“其他特別嚴重情節”。
當然,對入戶盜竊、扒竊型盜竊罪未遂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時,還應遵循刑法總則規定,入戶盜竊、扒竊的未遂能否構成犯罪,不能只看犯罪數額,還要看情節是否嚴重,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和刑罰懲罰的必要性。如入戶盜竊有其特殊性,增加了“入戶”這一嚴重情節,侵犯了公民住宅權,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危害性和刑罰處罰的必要性,應追究刑事責任。而扒竊由于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不僅侵犯了他人財產權,而且對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威脅,甚至擾亂了公共場所的秩序,其未遂也應追究刑事責任。如果入戶盜竊、扒竊未遂,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
二、公然奪取型搶奪犯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
案例三: 2012年11月24日11時30分許,劉某步行至上海市廣元西路、恭城路路口,趁被害人楊某不備,公然奪取楊某左手握著的紅色錢包一個(內有現金人民幣866元等物)及三星牌GT-I9300型手機一部(價值人民幣3318元)。被害人楊某即大聲呼救并追趕劉某,行人趙某等人聞訊相繼加入追趕。當日11時40分許,公安民警巡邏至此,發現楊某正追趕劉某,也立即追趕抓捕。劉某從廣元西路、恭城路路口作案后逃跑,先沿著廣元西路向東逃跑至華山路右轉,再沿著華山路逃跑,最后在軌道交通9號線徐家匯站16號口處被民警抓獲。案發現場距離被抓獲地點約有500米,劉某在逃跑途中將搶奪的錢包藏于自己衣服內,將搶奪的手機丟入路邊綠化帶中,后被路人發現交還給被害人楊某。
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搶奪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乘人不備、公然奪取他人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屬于結果犯,其既未遂是以法定結果的發生與否作為是否完成犯罪的標準。而搶奪罪中法定結果的發生就是行為人實際控制他人財物,同時,被害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目前,司法解釋尚未對搶奪罪的既未遂標準作出具體規定,但根據刑法理論通說,搶奪罪的既遂以被害人“失控說”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行為人“控制說”作為參考標準。
從被害人失控的角度而言,有觀點認為,行為人公然搶奪他人財物,在逃跑途中被人贓俱獲的,應構成搶奪罪未遂。因為, 行為人實施搶奪行為后,被害人在第一時間大聲呼救并追趕,后在過路行人與民警的幫助下將行為人人贓俱獲。眾人共同努力的抓捕行為使得行為人實際上無法真正控制財物,而在被害人及第三人不間斷的“目擊控制”下財物并未失控。所謂“目擊控制”,“即將財物近距離置于自己的視線范圍之內,以便保管、控制。如學生、運動員等在運動場上活動時,經常將衣物等隨身財物暫時放置于籃球架旁或運動場的一隅,這些就近暫放的衣物等就是目擊控制下的財物。成立目擊控制,不以財物主人保持不間斷的目擊狀態為必要,有時主人可能與熟人交談,一度疏于看管財物,有時主人還打起瞌睡或者陷入熟睡而忘記財物,這些短暫情形的發生,一般不影響認定主人目擊控制著身邊的財物。”
我們贊同“目擊控制”是一種對財物的控制方式,但有一定的適用條件和范圍,并非適用于所有的侵財類型犯罪。“目擊控制說”一般適用于盜竊犯罪,以“秘密竊取”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而搶奪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手段,就是乘人不備、公然奪取。因而,在此種犯罪手段上,必然會導致被害人的“目擊控制”,如果被害人追擊行為人,那么被害人的“目擊控制”會一直延續下去直到行為人被抓獲或逃脫。根據搶奪罪的特點,搶奪罪的既未遂區分標準在于行為人、被害人雙方對財物的實際控制狀態,而不在于該財物是否處于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目擊控制范圍內,否則可能出現“眼睜睜”看著財物被他人搶走而束手無策的情況。反觀案例三也不適用“目擊控制說”。因為,劉某從被害人手中奪取錢包和手機后,在逃離現場途中將手機丟落在地,錢包被其藏于衣內,被害人及參與抓捕者均無法進行有效目擊控制,而行為人的控制力遠遠超過被害人目擊控制力。實際上被害人已經失去了對財物的控制,而在民警和群眾的幫助下被害人恢復了對財物的占有,屬于失而復得的自救行為和追贓行為,不影響犯罪既遂的認定。否則,就會出現被害人只有放棄追捕才能認定行為人犯罪既遂而受到嚴懲,而被害人與群眾的積極追贓結果卻為犯罪嫌疑人減輕刑責,顯然不符合司法邏輯。
從行為人控制的角度而言,有觀點認為,搶奪的既遂應以行為人實際控制、實際利用到搶奪的財物為標準。我們認為,在搶奪犯罪中,無需以行為人實際利用到搶奪的財物為既遂的標準。所謂“實際控制”,“是指行為人已經取得并能實際支配所奪取財物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下必然排除原所有人對該財物的控制,同時又建立起新的實際控制,且這種新的控制是一種事實上占有的狀態,行為人能夠依據自己的意志使用、支配、處分該財物,而這種實際控制并無時間長短的要求,也不要求行為人實際上已經利用了該財物”。按照該判斷標準,結合當時搶奪的時空環境認定。案例三中,劉某在鬧市區公共場所公然搶奪,嚴重危害公共秩序,其搶到被害人財物后,在逃跑途中將搶奪的錢包藏于自己衣服內,將搶奪的手機丟入路邊綠化帶中時,已完成對被搶奪財物的處分,無需以其實際利用到搶奪的財物為準。因此,劉某的行為已構成搶奪罪既遂。
三、轉化型搶劫犯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
案例四:2007年11月17日2l時許,楊某、徐某騎摩托車進入上海南站3號輕軌1號進出口處自行車停車場內,竊走一電動自行車上的電瓶(價值人民幣150元),上海南站社保隊員吳某發現后進行攔截。楊某、徐某為抗拒抓捕,分別用大力鉗、拳頭對吳某實施毆打,楊某掙脫吳某的抓捕后逃逸,徐某在逃跑途中被抓獲,遺留在現場的摩托車和電瓶被公安機關扣押。吳某的傷勢經鑒定構成輕微傷。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關于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該條規定實踐中通常稱為轉化型搶劫罪,而刑法理論上也有稱之為事后搶劫或準搶劫。這種轉化犯一般是由法律明文規定,屬于法律擬制,基于特定行為在一定條件下由一較輕犯罪轉化為較重犯罪定罪處罰,如將原本不符合搶劫罪構成的行為擬制為搶劫罪。對于轉化型搶劫既未遂的認定標準,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較大爭議,至今難以達成共識。第一種觀點認為,先前行為(盜竊、詐騙、搶奪)既遂時,轉化型搶劫既遂;第二種觀點認為,不管先前行為既遂與否,只要行為人為抗拒抓捕、窩藏贓物等當場采取了暴力、脅迫行為的,就成立轉化型搶劫的既遂;第三種觀點認為,先前行為的既遂不等于轉化型搶劫的既遂,只有當行為人最終取得了財物才能成立轉化型搶劫,且行為人為了窩藏贓物而當場使用暴力,但財物被被害人最終奪回時,仍然只成立轉化型搶劫未遂。
我們認為,轉化型搶劫犯罪的既未遂標準應參照普通搶劫罪既未遂的標準,即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之一的,均屬于搶劫既遂。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應著重從以下三方面理解:
一是轉化型搶劫罪與普通搶劫罪的罪質基本相同,轉化型搶劫罪的既未遂可參照普通搶劫罪的標準。因為,兩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均屬于故意犯罪,均具有劫財的目的;客觀上都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均具有雙重客體,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和人身權利。兩罪的主要區別在于普通搶劫罪使用暴力、脅迫在先,劫財在后;而轉化型搶劫罪是占有財物在先,使用暴力、脅迫在后,而暴力、脅迫行為也往往是為了維護先前行為已非法獲取的財物。兩罪的行為只是占有財物的先后順序有差異,兩罪在犯罪構成上并無實質區別。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相關規定,搶劫罪具備劫取財物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兩者之一的,均屬搶劫既遂。因此,對于轉化型搶劫罪既未遂應同樣采用上述標準。
二是轉化型搶劫罪中“劫取財物”的認定,應以最終是否劫取財物為既未遂的標準。司法實踐中,劫取財物是以盜竊等先前行為中非法獲取財物時為準,還是以使用暴力、威脅轉化成搶劫罪后最終是否劫取財物為準,存在一定爭議。我們傾向于以最終是否劫取財物為既未遂的標準。因為,行為人之所以使用暴力、脅迫往往是為了維護先前非法占有財物的狀態,也就是說盜竊先前行為的既遂不必然導致轉化成搶劫后行為的既遂。聯系到案例四中,楊某、徐某先盜竊了價值人民幣150元的電瓶,但為抗拒抓捕在此后的逃跑過程中將電瓶遺留在了現場,最終并未實際劫獲財物。因此,應認定楊某、徐某在盜竊轉化為搶劫犯罪中并未實際劫取到財物。
三是既未劫取財物又未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的,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的未遂,符合刑法關于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也符合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轉化型搶劫中,行為人轉化成搶劫的先前行為只具有盜竊、詐騙、搶奪的故意,客觀上通過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需要說明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僅僅是轉化型搶劫罪成立的條件,不能以此作為區分既未遂的標準;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與通過暴力直接劫取財物相比,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因此,轉化型搶劫罪比普通搶劫罪的罪責稍輕,在罪責承擔上應有所區別。而轉化成搶劫后最終并未取得財物,也未造成被害人輕傷以上后果,如認定為轉化型搶劫既遂,其處刑比普通搶劫(未遂)重,可能導致量刑偏重,罪責刑不相適應。案例四中,楊某、徐某最終并未實際劫獲財物,其實施的暴力行為也只造成被害人輕微傷的后果。因此,楊某、徐某的行為應構成轉化型搶劫罪的未遂。
結語:目前刑法理論界關于侵財犯罪既未遂的認定標準主要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犯罪結果是否發生;二是犯罪目的是否實現;三是犯罪構成要件是否齊備。本文通過對入戶盜竊、扒竊、公然奪取型搶奪、轉化型搶劫等典型案例的分析,不論是“控制說”還是“失控說”,抑或“失控加控制說”,均應兼顧犯罪構成要件是否齊備作為區分既未遂的參考。而判斷某一要素是否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以及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備了某種犯罪的全部構成要件,不能僅以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為依據,還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和社會公眾的一般認識。通過對“兩搶一盜”等侵財類案件既未遂標準的適用,特別是針對未遂疑難問題的進一步研判,希望對司法實務有一定的借鑒參考作用,以期統一執法尺度。
[1] 高院刑二庭,閔行法院課題組.盜竊罪新疑難問題研究(上)[J].上海審判實踐,2015,(4):43.
[2]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1日作出的某刑事判決書。
[3] 北京順義區人民檢察院.侵財案件既未遂的法律適用[J].中國檢察官,2011,(4):53.
[4] 周加海.關于入戶盜竊但未竊得財物應如何定性問題的研究意見[J] .司法研究與指導,2012,(3):61.
[5] 張明楷.刑法學(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6:963.
[6] 張明楷.刑法學(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6:949.
[7] 北京順義區人民檢察院.侵財案件既未遂的法律適用[J].中國檢察官,2011,(4):55.
[8] 高銘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J].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42.
[9] 高銘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J].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41.
[10]張明楷. 刑法學(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6:963.
[11] 黃祥青.盜竊罪的認定思路與要點[J].人民司法,2014,(7):42.
[12] 黃祥青.論刑法上財物控制關系的認定[J].人民司法,2006,(12):36-37.
[13] 趙秉志.侵犯財產犯罪[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237.
[14]王奕,陸文奕.轉化型搶劫犯罪是否存在未遂[J].刑事審判參考,2011,(2):28.
[15] 張明楷.刑法學(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6:975-977.
[16] 張明楷.刑法學(第5版)[M].法律出版社,2016:987-988.
[17] 周加海.關于入戶盜竊但未竊得財物應如何定性問題的研究意見[J] .司法研究與指導,2012,(3):62.
Analyze the Puzzles Concerning the Cognition of Such Attempted Property-Related Crime as Burglary, Snatch and Robbery
Xiang Gu, Zhu Nengli
(First Branch of Shanghai People's Procuratorate, Shanghai 200052, China)
The definition of completed or uncompleted property-related crime such as burglary,snatch and robbery, especially cognition of uncompleted property crime remains quite a big problem in judicial practice. Burglary, pocket-picking and other common theft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ropertyrelated crime. The standard of differentiating the completed crime from the uncompleted crime lies in getting property, not in quantity of property. But the way to get the property differs in possession and touching. The standard of completed or uncompleted flagrant seizure lies in whether victims control or lose control of property. The standard is whether the snatch perpetrators actually control the property.The standard of cognizing completed or uncompleted transformed robbery should refer to the cognition of common robbery, that is, the robbery of property and slight injury of victims, either of which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completed robbery.
Burglary; Pocket-picking; Fragrant Seizure; Transformed Robbery; Uncompleted
D631
A
1008-5750(2017)05-0044-(09)
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7.05.006
2017-09-04責任編輯何銀松
項谷(1960—),男,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研究室主任、檢察員,全國檢察業務專家;
朱能立(1982—),男,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助理檢察員,法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