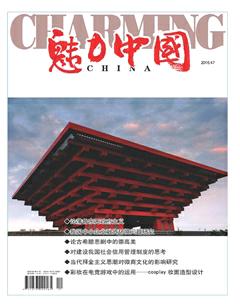水中之刀的困局
鐘坤煜
摘要:《水中刀》是著名導演波蘭斯基的長片處女作,也是為他帶來國際聲譽的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影片當中,波蘭斯基大量地運用了符號化的隱喻以及非符號化隱喻,而“水中刀”的意象隱喻就是關系到情節走向的一條“緊密的線”,同時三人之間的或對抗或制約的關系則成為了故事一張“聯系的網”,這幾個關系對于整個故事起到了符號化的隱喻。
關鍵詞:水中刀;隱喻符號;社會轉型
著名導演波蘭斯基的長篇電影《水中刀》于1962年正式問世,作為導演的長片處女作。這部電影奠定了波蘭斯基走向藝術殿堂的奠基和其獨特風格的標桿。故事背景發生在冷戰時期的波蘭。在這個時期,不僅僅是波蘭乃至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政治都處于激烈的變化之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于陳舊的政治體制不滿,通過各種形式與手段發泄出來,例如美國的“嬉皮士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還有日本的“赤軍事件”,各國政治運動風起云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停滯相互廝殺,不分高下。
作為二戰反法西斯戰爭中做出巨大犧牲的波蘭,他們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全境淪為了以德國為首的法西斯國家和保衛祖國的蘇聯的主戰場,國內的經濟環境和人民的生活條件急需和平重建,然而戰爭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仿佛陰影緊隨波蘭。
面對激烈的社會轉型,年輕的電影人逐漸的找出了一種適度的現實主義的方法,與老一代導演瓦伊達的浮華精致的“巴洛克”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為年輕一代的導演波蘭斯基卻逐步的摒棄了同時代的現實主義風格,轉向了一種以強烈的戲劇感,技巧華麗的方式來進行電影拍攝。
轉型中的社會動蕩帶給人們無形的禁錮和不安全感,令眾多電影人不敢放開手腳,但是波蘭斯基借助隱晦的表達方式在《水中刀》展現導演對未來的自我思考。電影之中存在三對較為明顯的隱喻:①年輕人與中年人的沖突;②漫無目的的航行;③人們的挫折感。
《水中刀》首先展示了丈夫帶著妻子駕駛小轎車前往海邊的場景,這個單一的場景中丈夫駕駛著汽車,聽著自己喜歡的節目,對于妻子則不聞不問。時閃時現的樹葉的陰影打在了汽車的前窗,有趣的是,妻子的臉在陰影的覆蓋下時隱時現。喋喋不休的丈夫終于和妻子交換駕駛座后,兩人繼續上路,丈夫還是壓制著妻子,直到年輕的旅行者意外闖入。丈夫半是帶著炫耀半是帶著憐憫允許年輕人與他們同行,直到他們一起上了私家游艇。故事才真正的開始——兩個男人的對抗正式拉開序幕。
兩人的對抗恰似二戰結束后波蘭獨裁專制體制所受到的公開反抗。曾經有評論家這么說道,誰有這個權力去規范、去改寫他人己經存在的人生閱歷?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人存在,那么還有誰能使自己或他人確信無疑:我,是一個有著正常智力,普通判斷力與人權的人?因為你甚至不能對自己的回憶和動機有控制權。同樣的,對于權利和地位的渴望是通過丈夫和這位年輕人之間持續不斷的對立與沖突來表現的。年輕人曾經在試圖在丈夫和妻子在水中游泳時獨立操控這艘船,但不幸的是帆船只在原地打轉乃至失去控制,纜繩在空中四下飛舞,就在這岌岌可危之時,丈夫沖上了帆船,推開年輕人,自己拉住纜繩。很快在丈夫的控制下,帆船奇跡般的回復原裝,丈夫重新掌握了控制權。此時的丈夫得意洋洋,看起來活像一個獨裁者,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正是他的粗暴和獨斷才避免了一次危險的事故,與此同時,丈夫的行為和舉止有意無意傷害了年輕人的自尊心。就像當時的波蘭社會高高在上的統治集團,雖然被來自東方的蘇聯所控制,但是他們自身日積月累的治理國家的能力并不能否認,甚至在某些時候,強硬的手段和老練的智慧遠遠超出了下層人民,間接帶領波蘭有驚無險的跨過各種艱難困境。然而,丈夫嘲笑年輕人時,卻絲毫沒有考慮到他在起風時曾經多么努力地想要控制這艘船,就像人民為了國家做出的犧牲,不被上層人士重視甚至輕視,一切努力都是不相干,沒有意義的。
繼續出現的對比隱射意識形態的斗爭就是核心物件——小刀。年輕人一直將刀帶在身邊,而且他擅長利用小刀做一些危險和刺激的事情,雖然在掌控風帆的行為上,年輕人處于下風,但是隨后年輕人利用小刀玩起了一些驚險刺激的小游戲時,丈夫被年輕人矯捷的身手所吸引,并且接過小刀,試圖像年輕人一樣玩弄之時,卻意外發現自己的身手確實不如年輕人一般矯捷。年輕人仿佛就是人民中的一員:既然公開的政治場合人民處于劣勢,毫無話語權和管控的能力,那么就應該在另外的領域另起爐灶——而這正好是上層精英所不擅長的。自己發明一個屬于下層人民的舞臺,擁有了獨立話語權后,那么傳統的由單一統治者或某個統治集團制定的規則的權利話語模式不能百分之百解決所有問題。
除了冷戰時期的困難情形與挫敗感有關聯之外,妻子對她丈夫的不滿也與此相關,她不滿丈夫傲慢的態度以及對年輕人不斷的挑釁和在欺騙她得手之后洋洋自得的優越感。
不過總體來講波蘭民眾是順從于政府的,他們只是嘗試著用非暴力的方式來使個人的意志獲得尊重。就像妻子,從不過問她丈夫的行為,她尊重他的權威和裁判。丈夫和年輕人之間有著持續的意志的較量,就像政治意圖和社會觀的碰撞,通常也包含著性別意識上的對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丈夫傲慢的態度和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引起了他和年輕人之間的摩擦,可到頭來挫敗的卻是丈夫自己和妻子,可丈夫沒有意識到這種挫敗,他還在樂此不疲的挑起爭端,可以說,正是持續的爭端貫穿了本片。
除去顯而易見的符號隱喻,波蘭斯基還在利用場面調度中人物位置的關系來達到隱喻的目的的,即非符號化隱喻。在這樣一艘狹長的帆船上拍攝各種角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現實中,一條船上三個人物的位置關系是比較簡單的,但波蘭斯基通過攝影機不同的取景讓觀眾看到了這三個人物之間微妙的關系。當丈夫和年輕人處在同一個畫而中到時,多數情形是丈夫處于前景,而年輕人處在后景,或者丈夫站在高處,年輕人站在低處,這樣丈夫明顯比年輕人顯得高大,具有壓倒性的氣勢。丈夫和年輕人之間的較量其實最終都是指向妻子,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影片中三個人物共同出現在畫而上的時候,妻子大多數是處在兩個男人的中間,她身穿泳衣,豐滿而性感,儀態萬方地在兩個男人中間穿梭,吸引著他們的目光,尤其撩撥著年輕人躁動的心。最值得注意的是,攝影機還常常將其中一個男主角的半個身子置于前景,而后景中則是女人和另一個男主角,這顯示出一種偷窺的效果,年輕人偷窺夫婦二人的生活,丈夫也偷窺年輕人和妻子的舉動,同時更暗示女人與兩個男人之間的關系。波蘭斯基正是這樣通過巧妙地丈夫排人物的位置以及攝影機特殊的視角來達到隱喻的口的,從而增加人物關系以及劇情的張力。
參考文獻:
[1]《羅曼·波蘭斯基于術刀式的電影語言》,《電影畫刊》.2003年第5期。
[2]【法】羅曼·波蘭斯基《波蘭斯基回憶錄》,培康譯,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頁,第169頁。
[3]羅曼·波蘭斯基《水中刀》(電影劇本),陳梅譯《當代電影》.1988年第1期。
[4]【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林克朗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M],陜西:太白文藝出版社,2004。
[5]【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邵牧君譯.電影的本性〔M].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6]【美】美尼克·布朗.徐建生譯.電影理論史評[[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
[7]【德】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邵牧君譯。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3。
[8]【美】大衛·波德維爾《世界電影史》.范蓓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