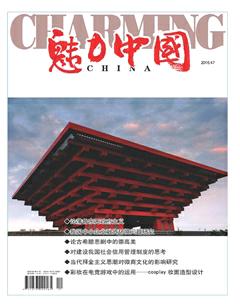《論語》對辛詞的影響
摘要:《論語》是我國儒家經典之一,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豪放派一代詞人,辛棄疾及其創作也深受《論語》影響。比如《論語》中“行藏用舍”的思想、顏回等人物和典故詞語等都對辛棄疾的詞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論語》;辛棄疾;創作;影響
辛棄疾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詞人,其創作悲壯激越,雄渾豪放。《論語》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在思想傾向、道德引導方面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辛詞也深受《論語》的影響。
一、《論語》中的儒家思想對辛棄疾的影響
辛棄疾生于靖康奇恥之后的紹興年間,其時山河破碎,強敵深入,戰亂頻繁,哀鴻遍野。但是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世皆圖茍安于一隅,不思復國、只圖一時享樂。辛棄疾立志興復大業、拯國救民,但是當時朝廷不僅自身不圖進取、偏安享樂,而且憚于重用有才之士。辛棄疾欲建功立業而不得的痛苦深深地折磨著他,使他心中充滿了愁苦,“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流露出他的孤憤之情。“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鬢須。卻將萬字平戎策,換的東家種樹書。”撫今追昔,沉痛無限,感慨極深。辛棄疾秉性執著,“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胸中常盤結一股勃郁憤懣之氣,觸處輒發。“言為心聲”,辛詞正是辛棄疾心中誠意的外化,他就是要在詞作中抒發他郁結的塊壘,表達他請纓無門、報國無路的不平之意。
辛棄疾這種憂國憂民的思想無疑是與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分不開的。儒家倡導“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積極的人世態度來面對人生的挫折和考驗。辛棄疾經常以儒自居,不斷用“真需”“通儒”“圣人”“鄒魯儒家”等語自勉或贊人。例如:
“憔悴賦招魂,儒冠多誤身。”——《阮歸朗》(山火燈前欲黃昏);
“公卿元自要通儒” ——《江城子》(看君人物漢西都);
“功名本是真儒事” ——《水龍呤》(渡江天馬南來);
“而今付之真儒,上將屬以大事” ——《賀袁同知啟》;
“君詩好處,似鄒魯儒家。”——《念奴妖》(君詩好處)。
且不說辛棄疾以儒士自居,他還用儒家的標準去衡量友人抑或贊揚他人的品行,我們當然不能將此處的儒等同于儒學,但是我們仍可以看出辛氏心中的“真儒”乃是他首肯的有氣節、有才識的讀書人。
二、《論語》中的語詞對辛詞的影響
《論語》對辛棄疾詞的影響還可以從詞語、形制等方面看出些許端倪。辛棄疾對《論語》典故的運用可以分出幾種不同的類別:一是運用《論語》中的詞語意象以代替典故,進而表達與之相關的涵義。如“卻笑盧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試手否?”(《破陣子》)“牛刀”一詞就是取自《論語·陽貨》“割雞焉用牛刀?”孔子教育子游的典故,辛棄疾因看到妻兄范南伯為張南軒辟宰盧溪而又遲遲未行,所以在這一首詞作里勉勵他戮力國事,規勸他人不可無大志,但是萬里功業總須從小處做起,“牛刀”一詞貼切地表達出“大材小用”的涵義,卻又使得范南伯易于接受規勸,在此的用事取譬有的放矢、讓人讀來倍感親切。二是化用《論語》原句,變換句式或句法,傳達自己的獨特感受。如“命由天,富貴在天”(《行香子》)就是化用“死生由命,富貴在天”這一句,而且變換句式,表達了貧富無常、得失難料的道理。三是以一二言語帶出《論語》中一段典故,抒發辛棄疾自身的個人情志和理想。如《水龍吟》:“稼軒何必長貧,放泉癚外瓊珠瀉。樂天知命,古來誰會同,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曾問:‘飯蔬飲水,何為是、棲棲者?且對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蒼顏照影,故應零落,輕裘肥馬。遶齒冰霜,滿懷芳乳,先生飲罷。笑掛飄風樹,一鳴渠碎,問何如啞。”在這首詞里,“行藏飲水”、“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飯蔬飲水”、“何為是、棲棲者”、“輕裘肥馬”都 是《論語》的用事和典故,雖然出自不同的章節,但辛棄疾將它們糅合在一起,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嫌,滿腹的牢騷見諸字句之間,而樂天知命、恬淡閑適的心境又使得詞作顯通達豪爽。四是直取《論語》中富于諧趣的口頭語或者感嘆詞,表達出別樣的風味和特有的意蘊。如《六州歌頭》“吾語汝:只三事,太愁余……”“吾語汝”三個字就好像我們平時所講的“我給你說”,給人一種親切而又語重心長的感覺,自然引出下文、使詞讀起來流暢順和。
三、《論語》中的人物對辛詞的影響
辛棄疾還言及《論語》中的諸多人物,從而顯現出自己的品評標準和思想內質。辛棄疾對于孔子嘖嘖稱道 的顏回也是尊崇有加,“人不堪其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就對顏回的貧而好學、不改其志的品質欣賞備至,從中我們也可窺視出辛棄疾的價值取向和理想所在,雖不能一展鴻圖也不會沉下去,即使獨處窘境也會怡然自得。又有《哨遍》“世間喜慍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取典《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只稱令尹子為忠而未能為仁人,蓋遠未達圣人之舉,辛棄疾也是感嘆人間喜慍之無常、反笑令尹子文三仕三已這件事情,不免有苦笑之感啊!在《踏莎行》(進退存亡)一詞中,稼軒欲歸田稼穡,所以說“進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請學樊須稼”以小人自居自是取孔子評價樊須之義,樊須只知有感年歉而學稼圃,欲躬自事農以導領民眾辛勤勞作,卻未想到“好義”、“好信”之重要,辛棄疾自是知道樊須之乏信乏義,但是為表事農之決心也就以“小人”自許,實則抒發了一種不滿現實、無可奈何的心理狀態。長沮、桀溺耦耕一事,可以看出孔夫子不愿與隱退之人歸入同類的思想,透出他積極入世、不甘落寞的情懷,在《踏莎行》(進退存亡)和《水龍吟》(稼軒何必長貧)兩篇詞中,稼軒雖都自嘲棲棲何為、徒事口辯,不過可以見出對地長沮、溺這類人物的厭棄!對人物的品評很能看出辛棄疾自己的價值傾向,但切不可只從字面去闡釋稼軒心計。
四、結語
從《論語》可以見出孔子的基本思想,而辛棄疾作為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愛國詞人,在繼承傳統文化和承繼儒家思想上作出了突出的成就。通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論語》對辛棄疾詞的影響之深遠。辛棄疾雖然是儒、釋、道思想兼備,但是占據其思想主體的仍然是儒家傳統,《論語》中相關的語詞、人物也對辛棄疾創作產生影響,可以透視出他對《論語》審美價值的選取和承繼。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作者簡介:周可欣(2000—),湖北省武漢市人,武漢市漢陽一中高三(15)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