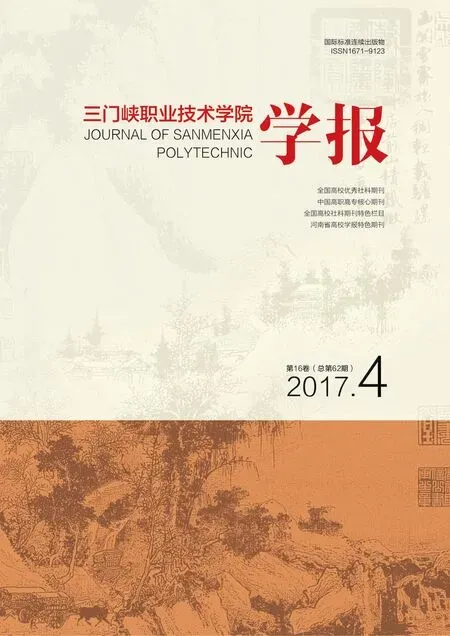一個以技能為路徑的鄉村經濟變遷史
——艾約博《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業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評介
◎陳 蓉
(河北大學 歷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手工業是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到目前為止已有不少成果出版。①如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翔:《中國近代手工業的經濟學考察》(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彭南生:《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彭南生:《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7年版);顧琳:《中國的經濟革命:20世紀的鄉村工業》(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曾小萍:《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而就手工業行業史而言,棉紡織業是學界討論的重點。雖有研究中涉及造紙業,也只是概述性的介紹,缺少有關中國鄉村造紙業的專著。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主任艾約博,長期以來致力于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史的研究。20世紀末深入四川夾江縣進行田野調查、口述訪談,運用歷史檔案等官方資料、民國時期期刊和報紙等史料著成《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一書。同過往手工業研究以行業興衰為軸線相異,著者聚焦造紙技能在當地的實踐,借用年鑒學派布羅代爾“長時段”的研究法,縱觀20世紀四川農村手工造紙技藝從業者社區的社會變遷,繪制出中國四川鄉村社會的歷史圖像。
一、技能視角下解讀鄉村社會經濟
技能,或被形容為技藝嫻熟的手工業者所擁有的財產和所有物;或被描述為內化于單個人身體中的“知識”和“話語”。不管技能是作為客觀物質性的存在還是主觀話語訴求的建構,“生理意義上在體性的或者社會意義上嵌入性的”[1],并不意味著彼此之間相互排斥。技能存在于有技能之人與其所屬環境之間的互動,如布迪厄所界定的“慣習”與“場域”之間的關系一樣,“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成了某個場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織的場域,它們彼此交融或歧異的程度,正是慣習的內在分離甚至是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屬性體現在身體上的產物”[2]。四川夾江縣作為一個特定的場域,其不管是自然環境還是社會環境都形塑著該地民眾生活的必備技能。該書以“以竹為生”為標題,提綱挈領,旨在詮釋如何利用與使用竹子來謀生,顯示了技能作為一種默會性知識的實踐。造紙技能的根植性恰恰是對夾江縣造紙人生存狀態的明證,為20世紀鄉村社會經濟提供了一種解讀方式。
技能的研究更多是停留在文本層面,很少關注技能實踐對社會的反映和影響。而“技術系統論”和“技術社會論”都夸大了技能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艾約博否認“技術決定論”,將目光投向夾江縣造紙技藝者的身上,與彭南生從“地方能人”[3]的視角分析近代手工業發展的原因有所不同,著者將問題聚焦在20世紀社會變革下造紙技能轉型同社會經濟變遷,闡釋技能如何進行再分配及如何喪失權力的掌控;造紙業如何應對近代化、工業化浪潮及如何被卷進國家市場。
20世紀初,面對資本主義工業和先進技術的沖擊,鄉村手工業逐漸呈現出衰頹的跡象。在現代化話語權下,手工業該向何處去,前途是否一定是資本主義工業。在曾小萍和顧琳分別在高陽和自貢對紡織業和鹽業的研究中,強調中國工業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由本土的傳統手工業發展而來的,更加注重傳統實踐與現代工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可見,她二人的觀點較為樂觀。相比之下,黃宗智則認為傳統手工業支撐著小農經濟的發展,因而,阻礙了資本主義工業的進步。[4]基于“內卷化”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試圖從中國鄉村內部找尋近代經濟變遷的軌跡,卻略顯偏激而不夠全面。彭南生對此看法就相對客觀,他認為手工業同機器工業可以處于二元并存的模式,并且這種互補的關系也是近代手工業長期存在的原因之一。[5]李金錚也稱,“手工業與機器工業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6]。然而,著者對夾江縣造紙業的考察,表明從20世紀初期開始,造紙業并沒有發展成為機器工業,造紙技能也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黃正林對黃河上游區域的研究也表明“手工業技術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7]。二者結論相契合,反駁了西方學者對于“布雷弗曼式”去技能化的探討,認為“技能進步在制造新技能的同時也破壞了舊技能”[1]。這種說法忽視了國家在近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斯科特式”的去技能化卻完美地詮釋了這一點,事實上,20世紀后半期國家對造紙業的“去技能化”也回應了此觀點。所以,將造紙技能作為一面鏡子,能夠真實客觀地透視夾江縣鄉村社會經濟的變遷。
二、鄉土技能與生活模式的塑造
相較于其他的手工業,“造紙是一項復雜、有精細勞動分工的高技能工藝”[1]。前前后后要經過72道工序,由于竹子的生長受季節影響,造紙過程中的“蒸活兒”便成了一道季節性的工序。造紙人在五六月開始砍伐嫩竹,收獲后再進行將竹子劈開、切斷、浸泡等多道工序。然而,全年都可操作的“抄紙活兒”使得造紙人并不會像根植于土地上的農民一樣有著季節性的調息。艾約博運用了大量的圖片和造紙技術的特有術語,生動形象而又不失專業地將這一復雜的技能躍然于紙上。鄉土技能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區域社會的生活節奏、生活方式及處世價值觀,呈現出與這種技能相對應的鄉村生活模式。
造紙作坊以家庭為中心,幾乎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要投入到作坊工作中。一個功能完整的作坊最起碼需要四五個全職工人的勞動投入,人手不夠時還需雇工,或是采用鄰里之間互助的方式來完成剩余的工作量。而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娶個兒媳婦、倒插門女婿或是領養個兒子倒像是雇了一個長期工,充當著家庭勞力的補充。三者相比之下,過繼的兒子有望獲得家庭造紙的繼承權,女婿和兒媳婦雖然也擔負家庭的責任,卻不能成為繼承人。對于有絕對繼承權的兒子,“造紙技藝可以說是這個圈子內的男子從娘胎里帶來的財富”[1]。這種親緣體的優勢,明晰了技能在代際之間的縱向傳承。造紙技能屬于一種默會知識,并沒有書面文字的記載,完全是父親將技能傳承給兒子,大多數情況是意會的。書中舉了一個例子,16歲的兒子離家出走三次,每次回來都會挨打,不過最終還是接受了自己的命運。造紙人甚至認為反復的鞭打可以讓技藝永久地嵌入到身體里,就如艾約博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中所談到的,“學手藝是在親屬群體或村莊里社會化的一部分,而非單獨的受教育過程”[8]。誠然,造紙技藝的習得并非是簡單的學習經驗,而是參與整個社群必備的技能。在這一點上,女性同男性的命運似乎不同,女性也需要接受技能的培訓,但始終不會接觸核心技術,因為女兒終究是要嫁人的。擁有自己作坊的夫婦,源于最初技能在性別上分工的不同,他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空間也有相異的分工。性別的分工將女性排除在特定生產工序之外,很難成為核心技能的擁有者。表面上性別分工考慮到男女體力上的差別,但其本質還是家長制權威下對女性儀式化的羞辱。然而盡管同工業時代的分工相比,性別分工顯得十分低級,忽視了諸如知識、技能等其他因素,但這種正當的男女分工能夠保證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性,也如王加華所言,男女勞動力的投入情況呈耦合態勢,共同維持著家庭經濟的正常運轉。[9]
艾約博對夾江縣居民的祖先、戶籍制度、社會組織、宗教組織等條分縷析,認為宗族社會體系維系著夾江不同村落及造紙手工業的生產秩序,并指出輩分在宗族體系的重要意義。同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理論所關注的不同,艾約博強調“與宗族范式相重疊、講求實際的、以有用為取向的親屬關系領域”[1],跨越家庭生活空間,描繪了宗族里同輩之間在造紙上的合作。盡管并沒有直接沖擊“宗族范式”理論,但卻是一種補充。“宗親就是技術知識的‘天然’容器”[1],同輩之間的合作實現了造紙技藝的橫向分享,也推動了造紙業的發展,表明宗族關系并不是農村手工業發展中的障礙。這同曾小萍對自貢鹽業的研究一樣,鹽井的最初合伙同樣發跡于家庭與家族之間,承認宗族在商業組織變遷中的作用,并認為富榮的大家族“鞏固了早期經濟的成功和現代管理技術的發展”[10]。馬克斯·韋伯最早指出,中國宗族是資本主義工業的一種羈絆,倡言氏族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11]他秉持著“歐洲中心觀”來審視中國,從一開始便引起了眾多學者的質疑。彭玉生將宗族網絡視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如諾斯提出“制度變遷理論”一致,“宗族網絡對工業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私營企業家的促進,因而具有強大宗族網絡的村莊可能更傾向于私有制的工業化道路”[12]。艾約博從中國社會本身發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內在動力,進而找尋20世紀夾江縣社會變遷內在的因素,既回應了過往的學術成果,也豐富了宗族與社會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
夾江縣居民的生活中心始終圍繞著造紙。性別分工中男子通過縱向的血緣傳承技藝,而女性卻被邊緣化在核心技術之外。鄰里之間的換工與互助成為了生活常態,造紙技能在宗親關系中特別是父系同輩內的橫向分享,都表明夾江縣的生活模式是以技能為軸心的。造紙技能有其鄉土性,不僅僅嵌入在夾江的自然環境中,使之不能簡單地復制到其他地區,同樣也嵌入在社會關系中。而著者對造紙工藝生動地描述,不只再現了造紙作坊整個家庭、家族及其生存環境的圖景,更飽含著一種對鄉土社會人文的關懷。
三、技術變遷與造紙業的存續
在工業化和城市現代化的浪潮下,20世紀的中國鄉村社會經歷了急劇的變動。鄉村社會變遷反映了近代中國發展演變進程中的軌跡和特點,艾約博在書中考察了夾江縣在20世紀的物質條件和民眾的日常生活,將研究主題置于中國鄉村研究,但學術視野并非囿于一隅,而是從一個更為宏大的史學觀著眼,闡明鄉土技能在20世紀革命的大背景下,如何嬗變、再分配以及其掌控權的轉移,這也是著者的中心論點。通過長時段的對造紙技能轉型的剖析,造紙業在社會變遷中的境遇成了該書的另一條主線。20世紀的中國社會發展經歷了兩次重大的轉折:世紀初之革命道路的抉擇與世紀末改革道路的走向,這兩次重大的變革都是從農村開始的,因而鄉村史的研究十分有必要。書中第四章開始追溯歷史,從縱向上來梳理造紙技術變遷的脈絡,以此探尋造紙業的發展。隨著“歐風美雨”的浸潤,機器工業與現代技術傳入,瘋狂地吞噬著農業文明,傳統手工業日漸衰微。1936年到1937年和1941年到1942年的一段時期內的糧食危機讓造紙業陷入了蕭條期,當時國內的媒體對此完全是一套悲觀主義的論調,宣稱帝國主義的侵略必將導致夾江造紙業的沒落。即便當時有不同的聲音與見解,但不管是持悲觀論者還是樂觀論者,都只是對問題的虛設,并沒有從數據上分析洋貨如何影響土貨而使之衰落。針對這種情況,艾約博從紙品進出口的海關統計數字上作分析,指出進口的紙品少于出口的數量,并且強調進口紙同手工紙用于不同的領域,表明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顯示機制紙會取代手工紙,以此,對20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入侵論和農村工業破產論提出質疑,并贊同費維愷的觀點,認為造紙業即使在社會動蕩的時期仍然在緩慢的發展。
造紙業經歷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去技能化”,一個是資本主義工業時代機器技術對傳統技能的解構,一個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對傳統手工藝的收繳。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手工業被視為傳統且技術落后的生產方式,基于此國家實施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對造紙業進行重組。夾江縣除了同其他地區一樣分配了土地外,技能和知識也被重新分配和洗牌。國家對技能的提取致使手工技術趨近臨界點,調查報告和“樣板作坊”的流行也讓造紙技藝不再有保密性,造紙人的職業身份成功轉變為造紙工,然而卻沒有改變夾江民眾的生活模式、社會關系、輩分規范、性別角色。因此,這一時期雖然國家大刀闊斧地對造紙技能進行改進,卻并沒有真正觸動技能的革新,造紙工仍然沿用著以前的工藝,同美國人類學博士穆爾克在云南的考察研究一樣,整個集體化時期彝族社區仍然保持著傳統的手工紡織的生活模式。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家庭作坊生產的回歸和技術革新促進了造紙業的迅速復蘇,著者將技術創新的迅速爆發歸因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場的推動,這也契合了該書始終貫之的詹姆斯·C·斯科特的“國家的視角”,同時又回應了科羅尼爾的觀點:既要關注國家怎么看,又要關注市場怎么聞。日本學者顧琳對高陽紡織業的研究同樣表明市場刺激了高陽工業區的快速增長,不過著眼于高陽企業家的傳統問題以及其如何指導當代工業。[13]著者強調新時期內造紙技能在“國家的視角”下如何轉型,亦如彭南生對近代手工業的描述,“技術進步、區域外市場與多元共存的生產形式構成半工業化的重要特征”。稱從理論上講,是由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護手工業的措施。[14]二者的觀點不謀而合,艾約博對夾江地區的考察為手工業的存續再一次做了注腳,指明造紙技能的褫奪是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合謀”。
社會變革下傳統手工業的前景問題,始終是學界所關注的熱點。李金錚認為家庭手工業得以延續是由于“傳統與現代的兩股合力”,又強調這兩股力量之間“以傳統力量為主,現代因素為輔”[15]。顧琳也承認當代鄉村工業對傳統經營方式的繼承,如此看來,“鄉村工業在技術和在組織上變了質”,就可以“有前途”[16]。著者正是對造紙技能如何“變質”進行了論述,而其“變質”的過程也是對中國社會變遷的另一種書寫。
四、問題與反思
《以竹為生》一書從鄉土技能著眼,縱橫交織出20世紀夾江縣民眾的生活圖景和造紙業的坎坷歷程,與其說是一部四川手工造紙村的社會史,倒不如說是中國革命下技能與知識分配的變遷史。盡管切入視角有其獨特之處,但也不免存在一些疏漏和偏差。問題的出現并不等于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在尊重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反思鄉村經濟史的研究。
(一)問題
該著透過弗里德曼“宗族范式”、施堅雅“環境決定論模型”、黃宗智“內卷化”、斯科特“國家的視角”、埃德蒙·利奇“親屬關系是談論財產的另一種方式”和杜贊奇“文化權利網絡”等概念,行文敘述中,同前人的學術觀點進行交流與交鋒,其中不乏精彩的理論解說、運用及質疑。著者借用西方理論的手法可謂嫻熟,也足以知其史學功底之深厚。然而,即便是采用了柯文的“中國中心論”,作為一名海外學者對中國鄉土的個別解釋,仍尚有可商榷之處。
著者在“換工與互助”一節中,并沒有厘清“換工”及“互助”等概念。基于滿鐵調查所做中國農村研究的日本學者旗田巍、戒能通孝、福武直、內山雅生等對此早已有著述,而著者并沒有參見,只是依據當地人的解說作以自己的結論。正因為此忽略了一個概念“幫工”,指“農家間單方面的無償農耕援助”[17],按照福武直的說法,“換工也叫做幫工,是一種不采取雇傭付工資的方法,而是先接受別人的助力,對此返還以同樣的無償勞動”[17]。以此看來,“幫工”比“換工”更加廣泛,女性去鄰居家的“搭把手”,只能算作是“幫工”,并不能稱為是“換工”。這樣“幫忙”在中國農村很常見,著者以局外人的視角能夠客觀地解讀鄉村文化,然而卻無法深刻地理解。歸根到底,著者只是對于鄉村的現象,就事論事,并沒有放在整個鄉村內去考慮。如果放入布洛赫“鄉村共同體”的理論中便很容易理解,夾江縣的造紙技藝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通過經濟的、感情的聯系而形成的這些‘鄰居’組成了一個小社會”[18]。鄰里之間的關系又建構出一張張人際網絡,“幫忙”本質上脫胎于小農經濟的母體,是鄉村共同體下私人關系網絡鉤織出的必然產物,因此也是鄉土文化和倫理的延續。
(二)反思
鄉村手工業是鄉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回顧既往鄉村手工業的研究,無論是整體性的綜論,區域性的分論,還是行業性的專論,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不免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整體研究中停留在淺層次,缺乏深入的探討;普遍存在地域和行業的不平衡,棉紡織業一直都是學界熱議的話題,而榨油業、造紙業、磚瓦業、釀造業、制糖業、陶瓷業等鮮少涉及;區域研究中多集中于江南、華北,而西南、西北、東北等地尚有待挖掘。艾約博選擇了西南四川一個小鄉村的造紙業,無疑在區域上、行業上豐富了目前鄉村手工業經濟史的研究。
柯文“中國中心論”的提出對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開始將研究轉向一個省、一個縣、一個村,內容更多的是對鄉村宗族、群體、社區的深描。著者同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對夾江縣造紙技藝進行了細致考察。然而夾江縣的調查結論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著者本人也未敢斷言,這也是區域研究中頗有爭議的議題,有學者認為區域性研究會拋卻全球史,囿于細枝末節。筆者不否認存在這種情況,但鄉村史本來就是典型的區域研究,誠如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言“小范圍的深入實地的調查,對于宏觀的研究是一種必要的補充”[19]。因而,從某一個區域著手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方法是可取的,至少可以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一個好的樣本或是可供比較的材料。不管是艾約博對夾江縣造紙業的考察,還是顧琳對高陽紡織業的研究、曾小萍對自貢鹽業的細探、李金錚對定縣農村經濟的思考以及李懷印不論是在華北鹿縣還是江蘇東臺縣調查,他們都是對中國某個區域的研究。所以,豐富鄉村經濟史的研究仍然亟待開展更多的區域性研究,共同呈現出鄉村經濟演變的全面而又真實的面貌。
綜覽,《以竹為生》叩問時下眾多學術熱點,豐富了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的研究。著者對檔案、文獻、口述等多元史料的運用及拿捏,著實讓人贊嘆,又以技能為切口,為了解四川鄉土社會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該著作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區域經濟史或行業經濟史研究,而是一本微觀視野和宏觀結構相結合的社會經濟史著作,為后續鄉村問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1]艾約博.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業造紙村的20 世紀社會史[M].韓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17,14,27,47.
[2]皮埃爾,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71-172.
[3]彭南生.“地方能人”與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J].江蘇社會科學,2003(4):142-147.
[4]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1986:203.
[5]彭南生.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13-320.
[6]李金錚,鄒曉昇.二十年來中國近代鄉村經濟史的新探索[J].歷史研究,2003(4):169-182.
[7]黃正林.農村經濟史研究——以近代黃河上游區域為中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351.
[8]Jacob Eyferth,胡冬雯.書寫與口頭文化之間的工藝知識——夾江造紙中的知識關系探討[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7):34-41.
[9]王加華.分工與耦合——近代江南農村男女勞動力的季節性分工與協作[J].江蘇社會科學,2005(2):161-168.
[10]曾小萍.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M].董建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324.
[11]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M].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51-156.
[12]彭玉生,折曉葉.中國鄉村的宗族網絡、工業化與制度選擇[C]//黃宗智.中國鄉村研究:第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51-272.
[13]顧琳.中國的經濟革命:20世紀的鄉村工業[M].王玉茹,張瑋,李進霞,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193-226.
[14]彭南生.半工業化:近代鄉村手工業發展進程的一種描述[J].史學月刊,2003(7):97-108.
[15]李金錚.傳統與現代的主輔合力:從冀中定縣看近代中國家庭手工業之存續[J].中國經濟史研究,2014(4):3-17.
[16]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34.
[17]張思.近代華北村落共同體的變遷:農耕結合習慣的歷史人類學考察[M].商務印書館,2005:38,40.
[18]布洛赫.法國農村史[M].余中先,張朋浩,車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89-190.
[19]費孝通.江村經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