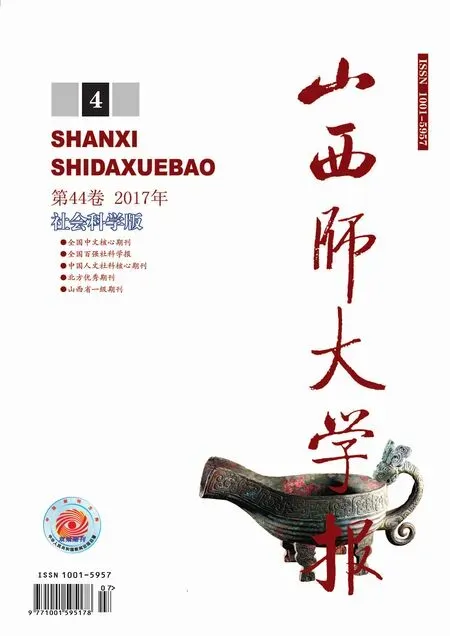汪廣洋詩歌藝術簡論
張 星 星
(武漢大學 文學院,武漢 430072)
汪廣洋(?—1379年),字朝宗,江蘇高郵人,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少從余闕學,淹通經史,善篆、隸,工詩歌。元末舉進士,流寓太平,太祖渡江,召為元帥府令史,后跟隨朱元璋南征北戰,出參軍事,參政行省。洪武三年(1370年)封忠勤伯,四年拜右丞相,十二年貶廣南,行至太平,賜死。廣洋有《鳳池吟稿》十卷,詩作五百三十余首,《列朝詩集》錄廣洋詩一百首,《明詩綜》錄三十一首。
宋濂《〈汪右丞詩集〉序》作于 “洪武三年四月廿一日”[1]863,王百順《辨疑》亦載“洪武三年,汪公已進封忠勤伯,而集亦刻于是年”[1]953,可見廣洋詩初刻于洪武三年。宋濂稱“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山林之下,誦公之詩者,莫不被其沾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1]863,評價頗高。然而跌宕的人生經歷與悲劇性的人生結局,加之明代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汪公名跡久淹聞于后者”,幸“賴有文字之懿”[1] 952,一度沉寂之后,明珠難暗投,萬歷四十五年王百祥重印《鳳池吟稿》,稱“汪先生當草昧之初,力挽宋元舊習,為明朝詩學正宗。所著《鳳池吟稿》,膾炙人口,不啻夜光和璧”[1]952。王世貞評曰:“汪朝宗如胡琴羌管,雖非太常樂,瑯瑯有致。”[2]258穆敬甫道:“汪詩如春林舒葉,嬌鳥群飛。”[3]102朱彝尊稱“忠勤詩饒清剛之氣,一洗元人纖縟之態”[3]102,《四庫全書總目》評價其“究不愧一代開國之音也”[4]1465。可見,在明清兩朝,汪廣洋享有極高的文學聲譽。
一、被忽視的“一代開國之音”
清末陳田《明詩紀事》中說:“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于弘、正,極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明初。若犁眉(劉基)、海叟(袁凱)、子高(劉崧)、翠屏(張以寧)、朝宗(汪廣洋)、一山(李延興)、吳四杰、粵五子(孫蕢等)、閩十子(林鴻等)、會稽二肅(唐肅、謝肅)、崇安二藍(藍仁、藍智),以及草閣(李曄)、南村(陶宗儀)、子英(袁華)、子宜(張適)、虛白(胡奎)、子憲(劉紹)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詩家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出,無前后七子相矜相軋之習。”[5]1此后,明詩盛于國初的觀點逐漸為學術界所共識,對其研究或群體或個人也都燦若星河,屢見新篇,然而汪廣洋卻是其中被忽視的一位,文學史中幾乎無聞,單篇論文也僅有一篇考據性質的《〈送許時用歸越〉》(非汪廣洋作)[6]。其他則散落于一些專著中,或于佐證史料時零星提及,或于地域文學分野中別列專章,如李圣華的《初明詩歌研究》第十一章第四節《汪廣洋爽豁之詩》從“偏淺”“柔奸”之辨與調寄爽豁兩個方面對汪廣洋身處政治漩渦的悲劇人生與高朗清新之詩歌創作進行了論述。[7]459—464上海師范大學郁步生碩士學位論文《明代揚州府作家研究》第一章第一節《開國之音——汪廣洋》[8],對汪廣洋的悲劇人生與詩歌成就進行了簡要分析,然而其依據汪廣洋生活與創作時代晚于戴叔倫就判斷《蘭溪棹歌》為戴作極不嚴密,且文中多有謬誤。*關于此論文中謬誤,現指出兩點:(一)第一節第一部分《有善始沒善終的仕途人生》中稱:“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為了限制楊憲的權利膨脹,火速提拔汪廣洋,然楊憲并不把汪廣洋放在眼里,獨斷專行,而且對汪廣洋違背其意愿辦事,甚是痛恨,遂唆使手下侍御史劉炳彈劾汪廣洋不夠孝順父母。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聽信讒言,罷黜汪廣洋,放逐還鄉,但楊憲依然不放手,再次上奏,朱元璋將汪發配到海南。……洪武八年(1375)冬天,朱元璋加封其為忠勤伯。”按:據《明太祖實錄》與《明史》,汪廣洋于洪武三年拜左丞,時楊憲先入為右丞,專決事,廣洋依違之,猶為所忌,欲逐去之。六月庚辰,楊憲嗾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后復入,再奏,上覺其奸,召廣洋還,憲誅。十一月乙卯,封忠勤伯。此皆為洪武三年事也。(二)第三部分《一點辯駁》中稱:“《明詩綜》不錄汪廣洋詩。”按:此處系斷章取義,陳田《明詩紀事》謂:“忠勤七律風格高騫,《詩綜》不錄茲體,特登之以補其缺。”《明詩綜》非不錄廣洋詩,不錄其七律也,《明詩綜》錄廣洋詩三十一首。
這些研究都較簡略且不夠深入,對汪廣洋生平之考證與作品特色之把握相對其詩歌成就與明初地位尚遠遠不夠。何以在明清兩代都評價極高的汪廣洋在現代學術史上難有一席之地?
筆者淺見,原因有三:
其一,論明初詩者多好以地域分野劃分不同的創作群體,如胡應麟:“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啟),越詩派昉劉伯溫(基),閩詩派昉林子羽(鴻),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9]342將明初眾詩人按地域之不同分成吳、越、閩、嶺南、江右五大創作群體,加深了作者之間的聯系與群體效應,明初以詩著者也多涵括其中。后世研究者多從其說,現代學術界則挖掘更深、劃分更細,形成了流派紛呈、各放異彩的群體研究,如《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10]《元末明初浙東文人群體研究》[11]《元末明初吳中文人群體研究》[12]等,然而汪廣洋不屬于這五大群體中的一員,故無論是文學史的書寫還是歷史文學生態的研究都極易將其忽視。朱彝尊《明詩綜》評汪廣洋“五言如‘平沙誰戲馬?落日自登臺’……可入唐人主客圖,靜居、北郭猶當遜之,毋論孟載也”[3]102。認為廣洋詩較高啟或有不足,然遠高“吳中四杰”中其他三子,四庫館臣亦以為朱氏所論“頗為允愜”[4]1465。廣洋詩歌創作成就極高,在當時文壇盛名一時,然而游離于主流創作群體之外,是造成其在文學史上缺席的主要原因。
其二,汪廣洋大起大落的人生歷程、作為政治犧牲品所鑄就的悲情人生與明朝統治者殘酷的高壓政策,使得一段時期內人們對談論明初人物噤若寒蟬,其文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得流傳,兼之明初文獻諸多隱晦與缺失,使得汪廣洋形象本身也迷霧重重。例如洪武三年封忠勤伯,誥詞稱其“剸繁治劇,屢獻忠謀”[13]3774,比之子房、孔明,而洪武六年以“巽柔怠政”[14]1426“無所建白”[13]3774而謫廣東參政,十二年竟以此斃命,如此自相矛盾的種種都使得汪廣洋其人其詩的研究困難重重。對于現代學術界而言,汪廣洋的詩集尚無校勘本、散佚訛誤嚴重,史料缺失所造成如廣洋家世、出生年月、元末舉進士時間等皆不可考,這些都造成了汪廣洋在文學史上的缺席。
其三,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論,廣洋詩“當時為宋濂諸人盛名所掩,世不甚稱”。有明一代,宋濂是受關注最多的文人,太祖即推其“為開國文臣之首”[13]3787,后世對宋濂的研究更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在后世形成的長期持續、聲勢浩大的研究隊伍加以推崇、宣揚,致使汪廣洋為數不多的傳世詩文,逐漸為群星麗天的明初詩壇所掩。
本文從汪廣洋詩作入手,著重分析其詩歌創作風格與特色,還原歷史情境,以期挖掘被譽為“一代開國之音”的明丞相汪廣洋的詩歌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二、從征伐則震蕩超越
汪廣洋天資聰穎而博極群書,有極強的濟世之心,“經國正期行素志,讀書端不事虛文”[1]923。元末舉進士后,流寓太平,后跟隨朱元璋征戰,壯烈生動的軍旅生活在其筆下表現出與之相應的慷慨激昂之態,即宋濂所謂“震蕩超越”者。如《康山觀兵》:
樓船兩翼挾艨艟,垂老觀兵膽亦雄。炮火震天飛霹靂,剛風立海走豐隆。重瞳首寄龍泉下,獨眼尸歸馬革中。戰罷神威猶震怒,蒼涼落日貫長虹。[15]1243
康山,又名康郎山,位于江西省余干縣城西北鄱陽湖東南湖中。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1363),朱元璋大破陳友諒軍于康郎山下,戰事慘烈,廣洋妹婿程國勝亦死于此戰,詩或作于此時。“樓船”,《太白陰經》載曰:“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旗幟、開弩、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 “艨艟”,亦作蒙沖、艨沖,東漢劉熙《釋名》:“外狹而長曰艨沖,以沖突敵船也。” “樓船”“艨艟”,戰備之精良,戰陣之整飭也。“炮火”“霹靂”,戰事之激烈,聲勢之浩大也。前兩聯寫目之所睹,耳之所聞,視覺與聽覺相結合寫遠景,從宏觀落筆。頸聯“重瞳”與“獨眼”,“寄首龍泉”與“尸歸馬革”,運用對偶互文手法,以特寫鏡頭,從微觀寫近景,無論重瞳與獨眼皆戰死無聞,戰爭之殘酷、傷亡之慘重可見一斑。尾聯以“猶”字生動傳達出勝利之師的威武神氣,而“貫”字氣勢如虹,收束以“落日”“長虹”,則渲染出一種悲壯的色調與氛圍,雖勝利之師,回顧戰爭經過、死傷之眾亦不由不寒而栗,蒼涼沉重。尾聯寓情于景,悲壯之中自有悲涼,又寫遠景也。整首詩由遠及近,再由近及遠,聲色一體,讀之使人如臨其境,如聞其聲,正如宋濂所論:“當皇上龍飛之時,仗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蕩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后先。”
又如《從軍樂》:
從軍樂,右插忘歸左繁弱。天子有詔征不庭,重選前鋒掃幽朔。出門萬里不足平,宛駒照耀黃金絡。去年鏖戰蔥嶺東,今年分戍蓬婆中。蓬婆城外一丈雪,半夜紫馳號北風。少年忽憶慷慨事,便起酌酒澆心胸。酒酣耳熱聲摩空,手舞三尺青芙蓉。前將軍,右都護,壯士在榮不在富。一朝手格樓蘭歸,人擁都門看馳騖。朝承恩,暮承顧,出入三軍稱獨步。都門富兒空萬數,人生豈被從軍誤。[1]897
詩歌節奏輕快,氣勢磅礴,描繪出一個雄姿英武、激情滿懷、渴望建功立業的少年形象。上半部分通過少年的裝束“忘歸”“繁弱”“宛駒”“黃金絡”,少年的心態“掃”“不足平”,一個英俊有為的少年形象躍然紙上。中間四句,“去年”“今年”傳遞從軍時間之久與捷戰信息,“一丈雪”“號北風”,則從側面描寫征戰環境之艱苦。在緊湊壯闊的渲染中少年忽憶“慷慨事”。何為“慷慨事”?陸游《秋韻感舊十二韻》有:“往者秦蜀間,慷慨事征戍。”[16]1904以廣洋詩證之,“賦詩橫槊慷慨事,笑指闌干近斗牛”[1]921。“慷慨事”,沙場點兵、的盧飛快,論戰觀兵、橫槊賦詩者也。少年憶及昔日慷慨之事,彼時情景,歷歷在目,不覺熱血沸騰,酒放豪腸,如臨其境,惟“手舞三尺青芙蓉”,亮劍出鞘,足之蹈之而已。下半部分寫少年之志,光耀門楣,三軍獨步,充滿積極昂揚的用世之心與對前途的信心。
又如其《遠游陪師西征》:
朝發庾公樓,夕扣滕王閣。長歌奮激烈,清風蕩寥廓。張帆江水秋,伐鼔關月落。予亦將遠游,明當造黃鶴。[15]1145
首聯“朝”“夕”,時間之迅也,“發”“扣”,功成之捷也,寥寥四字,舉重若輕,干凈利落地刻畫出其隨大軍克九江、入豫章,一路所向披靡的氣勢與豪情。頷聯緊承上句,勝利之師何以為樂?滕王閣上長歌奮發,壯懷激烈,江上清風浩蕩,似乎也為這勝利歡呼。頸聯“江水”“關月”這樣開闊的意象與“張帆”“伐鼓”的洋溢著雄健、陽剛之美的畫面相結合,寓情于景,渲染出詩人與士兵們澎涌而出的豪情萬丈。在如此氣勢中,詩人以“明當造黃鶴”收束全篇,將伐湖廣之大捷在望溢于言表,妙不可言。整首詩情致高邁,一往無前。如此類酣暢淋漓的快詩還有“詠古三臺”《歌風臺》《戲馬臺》《凌歊臺》,表現人生志趣的《長歌行》,贈友砥礪之作《田將軍》等,雖非皆為軍旅中作,然皆高朗有致、快意舒展,誠如王兆云所評:“汪右丞詩氣骨雄渾,語意爽朗,卓然可傳。”[17]87
三、哀民生則沉郁悲涼
戰爭畢竟是殘酷的,它所帶來的災難是沉痛的。汪廣洋生活于兵連禍結的元明之交,目睹了元朝漸衰、群雄逐鹿的過程,又多次隨軍參謀軍事、指揮作戰,親歷戰火紛爭之無情與時局動蕩、百姓流離之痛苦,諸多作品詩風沉郁蒼涼,讀后令人想見當日情懷,甚或淚下者。如《過通許》:
廣西少年輕學文,學武游遠從北軍。檄書催渡蔡河水,廣西少年同日死。黃沙滂滂河水渾,髑髏鎖血埋腥魂。惟有當時戰殘鐵,夜夜寒芒燭華月。[1]894
詩后有注:“乙未年,廣西軍戰敗于此,迨今,人馬朽骨迷滿堤岸。”一將功成萬骨枯,詩歌通過對廣西少年不幸命運的喟嘆,深沉控訴戰爭之殘酷與罪惡。眼底雖不見血肉橫飛、尸橫遍野的戰爭場面,然而渾濁的黃河水猶血腥不散,遍地的人馬枯骨仍觸目驚心,殘損之兵器猶在月光下夜夜泛出森然的寒光,此情此景怎不令人觸目驚心、心寒膽戰!對殘酷戰爭之控訴與對戰亂災難中人民苦難命運之悲憫,在廣洋詩集中多有體現,如:
中原板蕩十余載,五兵血戰三精虧。黃沙漫漫草離離,髑髏如霜骨如雪。(《野禽鳴》,卷二)[1]899
列郡摧殘灰燼余,生民痛死溝壑里。(《珠湖篇》,卷二)[1]892
在其詠古七絕《月夜過馬嵬坡》中,汪廣洋對李、楊愛情固然有著“關月明明良夜何,秋風腸斷馬嵬坡”[1]946的同情,然而個人的離愁別恨較之戰爭所造成的累累白骨實在是微不足道,“也應不為真妃惜,只憾當初白骨多”。
汪廣洋擅長從戰后黃沙散漫、殘骸遍地、荊棘叢生中窺測當日戰亂之苦、戰事之烈。在其五言律詩《過潁州廢境》中,這種滿目興亡之感則尤為分明:
倡亂伊誰始,頻年戰未休。風云隨變態,淮水尚安流。綠野彌荊棘,黃沙慘髑髏。移舟暫臨眺,掩涕不勝憂。[1]914
戰爭所帶來的生靈涂炭已是可嘆,而天災荒年、旱澇蝗蟲,百姓餓殍遍野、十室九空的悲慘境遇投注在詩人的筆下,顯得格外沉痛、悲哀。如其洪武元年參政山東時所作《曹州》:
河北生靈苦,曹州最可哀。兵興多在難,水溢屢為災。蒿草侵城合,狐貍上冢來。傷心寥落地,一顧一徘徊。[1]914
這首詩與《過潁州廢境》寫作手法一致,由抒情起,由特定意象組成一幅幅令人不忍直視的畫面,前者定焦“綠野荊棘”“黃沙骷髏”這兩個典型場景,這首詩則取“蒿草侵城”“狐貍上冢”這兩幅生動的圖景,刻畫出曹州兵難、水災接連而來所造成的城池破敗、民不聊生的蕭條境況。頸聯與尾聯緊密銜接,意蘊無窮,詩人見此情此景,傷心寥落,步步回首。抑或廢城春深,一只或幾只野狐來這亂冢之上找尋舊日的伴侶,臨去不忍,頻頻回首?兵水無情,生靈有愛,狐猶如此,人何以堪?末四句在抒情上雖不如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擲地有聲,細細揣摩,若身臨其境,亦令人肝腸寸斷,嘆息連連。兩首詩皆終之以無法自已的哀思,“移舟暫臨眺,掩涕不勝憂”、“傷心寥落地,一顧一徘徊”,與老杜“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有異曲同工之妙,皆傳承自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讀來令人傷心淚下。
對世亂年荒中黎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在廣洋詩中亦隨處可見,如:
世亂人家少,年饑草澤深。(《陳州》,卷五)[1]914
關中兵旱久,黎庶竄亡多。(《贈張主事關中講究運道回》,卷五)[1]918
破屋哀哀啼老孀,只因兵后又年荒。一家十口存無二,廢盡門前陌上桑。(《宿井山廢寺四首》其四,卷十)[1]918
淮河西與蔡河接,八百里程無一家。廢邑經年埋草莽,遺民何處夢桑麻。蟬聲嗚咽沿堤柳,狼跡縱橫匝路沙。唯有傷心舊時物,毀垣髙倚夕陽斜。(《太和縣》,卷八)[1]931
對民生疾苦關懷的另一面,則表現為對順應民心之舉措,或好雨時至之天時的一種贊賞,如“大抵喑嗚非帝德,由來寬厚合民情”[1]931。又如《過鼎湖得雨》:
好雨來天闕,層云覆鼎湖。九農承厚澤,四海慰來蘇。豐稔行將見,炎蒸坐覺無。老夫殊有喜,狂舞動三呼。[1]918
詩后有注曰:“南陜久旱,御香一至,甘霖大降。”久旱之后,甘霖大降,農事承澤,四海復蘇,豐稔可見,暑熱頓消,此情此景,作為一位時刻心系蒼生、關懷黎庶的詩人之欣喜自是無以復加、躍然紙上。
四、抒感懷則深沉悠遠
陳田《明詩紀事》評廣洋七律“風格高騫”[5]93,其七律中一些感懷之作,融合以世運之治亂、興衰之代變則顯得尤其深沉悠遠。如《過高郵有感》:
去鄉已隔十六載,訪舊惟存四五人。萬事驚心渾是夢,一時觸目總傷神。行過毀宅尋遺址,泣向東風吊故親。惆悵甓湖煙水上,野花汀草為誰新。[1]930
元末,社會動蕩、戰亂頻繁,汪廣洋雖常年行游在外,但對故鄉高郵情感深厚,《鳳池吟稿》中收錄其多首吟詠故鄉風物之作,如《珠湖篇》:“湖光倒浸玻璃冷,湖水彌漫幾千頃。中有峰頭玉井蓮,靚理凝妝照秋影。”[1]891記憶里的故鄉寧靜而美好,然而,“一朝萬事隨轉燭,伐鼓鳴鉦戰艦過。戰艦飛來截湖水,彩幟牙檣半空起”。戰火無情,所及之處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故時隔十六年后,詩人再過高郵,所見所聞令人倍感悲哀。首聯“十六載”與“四五人”,鄉思歲月之漫長與舊友親朋之零落形成巨大反差,“已”與“惟”,兩個虛詞串聯其中則情感盡現。別離后日日相思,歸來時物是人非,記憶與現實的對比讓人懷疑這萬事驚心渾然只是一夢,而觸目所感,一切又如此真實,令人徒增傷感,只得去向那些被戰火燒毀的故宅找尋舊日的遺址,向著東風灑淚祭拜故親。1367年,朱元璋大軍攻克蘇州,汪廣洋與老母舉家完聚,方得知兄長繼先已于乙未年(1355年)病故,作《哭繼先兄二首》,有“想在艱難際,悲來淚徹泉”“幽恨何時已,空悲到日斜”[1]912句,意悲情切,真摯感人。親友亡故者多,家鄉也面目全非,面對這從前可憐可愛的五湖煙水,詩人不覺更加惆悵,萬物皆在流轉更迭,惟草木不知愁,看這年年依舊的野花汀草,它們為誰而開為誰而妍呢?以此收束全詩,含蓄蘊藉而遙旨深遠,深得姜夔“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余致。整首詩對仗工整而不著痕跡,疏朗有致,情感自然,為廣洋七律佳篇。
如此類詩還有《曲阜縣》:
狐兔縱橫走夕陽,斷籬荒徑入牛羊。可憐東魯成焦土,曾是西周奠故疆。汶泗尚余春寂寂,龜蒙遙對晚蒼蒼。偶披荊棘懷前古,獨有弦歌思激揚。[1]933
此詩作于汪廣洋參政山東之時,詩前自注:“拜軒轅少昊墓于郭外,謁先圣廟于魯城,遂與衍圣公孔士行歷郊原、披荊棘,訪周公廟址,靈光殿基于荒煙杳靄間,及觀顏子廟、望孔林,蒼翠聚蔚,使人悲感交至,不能自已于懷。乃賦詩紀所見云。”寥寥幾筆,東魯文明馥郁之地橫遭戰火荼毒,兔走狐悲,荊棘遍野,先賢往圣之廟宇盡淹沒于荒煙杳靄,其悲哀與無奈盡現。
然而,其深沉悠遠不限于悲涼之態,亦有著爽豁超然之致。如《嶺南殘臘遣懷》:
一麾長憶出南京,萬里車書載筆行。驛路通關疑隴蜀,人家瀕海似蓬瀛。三冬地暖花爭發,半夜雞鳴潮又生。公館莫言岑寂甚,草蟲啾唧到天明。[1]922
這首詩作于洪武六年汪廣洋由右丞相貶為廣東行省參政的冬天,被貶的原因是“畏懦迂猾,于其伸冤理枉,略不留心,以致公務失勤”[18]25。這與汪廣洋早期仕途經歷和朱元璋對其任用是相矛盾的,如除中書右丞誥詞中稱其“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屬陜右之地初入職方,輟自端臺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效已著”[1]866。這是一種智者的沉默,抑或懦弱的逃避?汪廣洋先與楊憲同位,“憲惡其位軋己,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慊,欲逐去之”[14]1217。百般隱忍依舊遭到排擠,三年六月,楊憲嗾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母無狀,帝切責,令還高郵。事實與否,已難定奪,然廣洋詩中“慈親膺壽考,諸弟喜平安”[1]911、“最喜慈親健,都忘兩鬢斑”[1]918等對母親、對家人的關懷與惦念,收到家書之欣喜屢屢可見,因此,說他對母親不孝,似是難以信服。憲猶以為不足,“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上覺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14]1217。后與胡惟庸共事,惟庸“陰執國命,漸起邪謀”[19]48,較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樣上猜忌而兇狠,下處心而積慮的環境中,廣洋自顧不暇,只得“浮沉守位”[13]3774,如此,依舊不能幸免,洪武六年被貶,十年復位,十二年被下詔賜死。伴君如伴虎,汪廣洋兩度拜相,兩度罷相,每一次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給人以懦弱無能之感。然而,一旦離開這水深火熱之地,他的詩中便充滿了熱血與活力。面對瞬息萬變的宦海浮沉,他始終以豁達超然的態度面對,無論是艱辛坎坷的羈旅途中,抑或荒涼偏僻的貶謫之所,他始終保持著謙遜平和的心態,融入新的環境,自得其樂。如此,雖述羈旅之狀、荒寒之苦,亦爽豁超然。“一麾長憶出南京”,萬里之遙,對京城的思念與不舍固然有之,路途之艱辛與漫長固然有之,然而沒有牢騷,沒有抱怨,只是時刻帶著發現美、感受美的眼光去發掘、體驗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路途之遙,似通隴蜀,然而煙水繚繞,又如置身蓬萊。雖是寒冬,而南方地暖,百花皆已綻放,令人驚喜。夜半無眠,側聽那雄雞長鳴伴隨著拍岸的潮聲,似乎透露出淡淡的感傷。然而,詩人筆調一轉,雖說在這里孤獨寂寞,但窗外尚有啾唧的蟲鳴伴我到天明,春天已經來了。
又如《嶺南雜錄三十首》其五:
牂牁流水碧潺潺,潮落潮生草木閑。一片海云吹不起,越人遙指是厓山。[1]948
《明詩評選》選錄此詩,王夫之評曰:“無限厓門之悲,一字不涉。此公自英雄,那得有棧豆之戀!”[20]326廣洋之爽豁超然,可見一斑。
汪廣洋詩作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其詠物之作亦匠心獨具,別有趣味。如《梅杖為西霞霍維肅賦》:
錚錚古干鏘鳴鐵,拄到西湖淺水涯。素質可能韜玉潤,溜皮猶自著霜華。臨風倚竹幽香在,和月敲門瘦影斜。一段陽春舊清致,等閑來伴老西霞。[1]932
霍維肅,元末人,與余闕師門都有交游,余闕有《送霍維肅令尹》[21]4—5,余闕弟子郭奎亦有《答霍先生書》[22]等。首聯“錚錚”寫梅杖之瘦硬蒼勁,亦可想見梅之傲雪綻放,凜然不屈也。“錚錚”二字,主人翁之品性盡現。“古干”,經霜歷雪而后沉淀者也。“鏘鳴鐵”,鐵骨錚錚,擲地有聲也。通過首句的刻畫,梅杖與其主人之形態大略已出,更顯含蓄蘊藉、旖旎風流矣。“拄到西湖淺水涯”,拄梅杖想見梅花之態“疏影橫斜水清淺”,見此態又如臨西湖梅盛之景“千樹壓西湖寒碧”。用語平易,卻能引起諸多美好的聯想。頷聯亦如之,蘊玉潤霜華于素質溜皮中,尤見品格。頸聯則熔鑄前人而自鑄新詞,匠心卓絕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使人如聞其香,如見其態。行文至此,主人之風骨、神韻早已躍然紙上,而“陽春舊清致”又增其高雅、絕塵之態。全詩雖為詠物,實則寫人,象征手法的運用爐火純青。整首詩情致搖曳、活色生香,無纖靡之態,無粗糲之弊,實為明初詩作之善者。其他詩如《梅信》《梅魁》等,也都別具幽致,誠如穆敬甫所評:“高朗有致,構思頗覺不苦。”
汪廣洋詩作中還有一些生動活潑、清新自然的民歌。如《竹枝詞三首》,其一:
澗水泠泠清見沙,妾心如水諒無他。愿言莫學楊花薄,一逐東風不戀家。[1]950
以澗池水之清澈見底喻妾心之忠貞無暇,愿君心亦如我心,莫學輕薄楊花之游蕩無家,純真曉易,富于濃厚的生活氣息。又如《涉江采荷花》:
郎騎白馬臨江滸,妾采荷花涉江浦。郎情若比藕絲長,妾心勝似蓮心苦。藕絲長,難綰結,蓮心苦,莫如妾。天長地久此心存,花落花開任情絕。[1]897
清新爽朗、纏綿歡快,深得南朝樂府風味。其他如《東吳棹歌》《淳安棹歌》,也多從江南民歌與樂府古題中取材,并熔鑄于自己的心胸、情感,描摹江南風物,風格清麗可喜,不飾雕琢,自然天成而又韻味悠長。又如這首一組著名的《蘭溪棹歌》:
涼月如眉掛柳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溪三日桃花雨,夜半鯉魚來上灘。野鳧晴蹋浪梯平,越上人家住近城。箬葉裹魚來換米,松舟一個似梭輕。棹郎歌到竹枝詞,一寸心腸一寸絲。莫倚官船聽此曲,白沙洲畔月生時。[1]951
三首詩風格一致,明朗歡快,動靜結合,優美如畫。然而,對其中第一首與另一首《蘇溪亭》*《蘇溪亭》: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煙雨杏花寒。的著作權,一直以來爭議不斷。于此,蔣寅先生在其《大歷詩人研究》下《戴叔倫作品考述》一節中已有考證[23]507,茲補充之。據國圖重印萬歷四十五年刻本之《鳳池吟稿》,已收錄二詩,而廣洋集中與二詩風格相近或類似表達之作甚多,如“越中山色鏡中看”與“鏡里青山畫不如”[1]951,“蘭溪三日桃花雨”與“東風連日桃花雨”[1]948、“桃花春漲近來生”[1]950,“夜半鯉魚來上灘”與“雪色鰣魚上水來”[1]942等,以詩歌風格而論,二詩更接近汪作。
同時,汪廣洋作品中這樣清麗可喜之作尚有許多,如《淳安棹歌》其一:
淳安縣前江水平,越女唱歌蘭葉青。山禽只管喚春雨,不道愁人不愿聽。
王夫之評曰:“全在脫手處好。俗筆亦往往以此自驕,孰知不然。”[20]327
汪廣洋詩風格多樣,詩藝精妙,享譽一時。以上只簡單分析學術界關注較少的幾種,其他如朱彝尊所推崇“饒清剛之氣”之五言律詩,如“相望隔千里,目斷楚云飛”[1]902“對客開春酒,當門掃落花”[1]904;題畫詩中與自然山水的寤寐神交、相親如故之“山如游龍水如練,寤寐神交久相識”[1]895“落花溶溶江水春,江上好山如故人”[1]895;運筆流暢若行云流水、氣勢雄渾之“一朝縱筆恣揮灑,萬里長江落胸臆”[1]896等,皆朗朗有致,卓然可傳。
自然,廣洋詩中也有部分應制之作,如宋濂所謂“典雅尊嚴”類臺閣之文者,如《大祀》《上壽》《大祀圓丘喜甘露降應制》等,這類詩“宣教化而弼皇猷”,自然藝術水準不會太高。然而,在元末“鐵崖體”所造成的纖靡綺縟之風橫行文壇時,廣洋諸詩震蕩超越、氣骨雄渾、清剛典重,無疑為廓清元末積習之一大先驅,后明朝詩學先后兩次掀起聲勢浩大的復古運動,與包括廣洋在內的明初詩人群體對漢唐壯闊氣象之積極追尋與成功實踐是分不開的。在這個意義上,汪廣洋的詩歌創作可謂是引導了明朝詩學之正宗,堪稱為有明“一代開國之音”。
[1] 汪廣洋.鳳池吟稿[M].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695冊[C].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2] 王世貞.藝苑卮言[M].濟南:齊魯書社,1992.
[3] 朱彝尊.明詩綜[M].北京:中華書局,2007.
[4]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C].北京:中華書局,1965.
[5] 陳田.明詩紀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徐永明.《送許時用歸越》非汪廣洋作[J].殷都學刊,2001,(4).
[7] 李圣華.初明詩歌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2.
[8] 郁步生.明代揚州府作家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文學院,2004.
[9] 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 王學太.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J].文學遺產,1989,(5).
[11] 王魁星.元末明初浙東文人群體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1.
[12] 李茜茜.元末明初吳中文人群體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4.
[13] 張廷玉,等.明史[C].北京:中華書局,2013.
[14] 姚廣孝,等.明太祖實錄[M].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15] 程敏政.新安文獻志[C].明弘治十年祁司員彭哲等刻本.
[16] 陸游.劍南詩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7] 王兆云.皇明詞林人物考[M].明萬歷刻本.
[18] 雷禮.國朝列卿紀[M].明萬歷徐鑒刻本.
[19] 潘檉章.國史考異[M].清初刻本.
[20] 王夫之著,周柳燕校點.明詩評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1] 余闕.青陽先生文集[M].四庫全書本.
[22] 郭奎.望云集[M].四庫全書本.
[23] 蔣寅.大歷詩人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