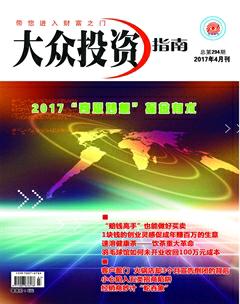“一帶一路”戰略下PPP投資爭端解決方法研究
【摘要】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后,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投資面臨重大機遇,PPP項目因其利于基礎設施建設、方便融資、收益共享等優點,成為中國投資者的焦點。在PPP項目投資中,中國企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各自投資爭議。本文在梳理了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區域主要的投資爭議解決辦法后,針對國內救濟效率低、國際仲裁耗時長、費用高、執行難的問題,提出采取政治手段和司法手段向結合,構建區域性的爭端仲裁機構,公平、高效、靈活解決投資者同東道國之間的爭議,保障PPP項目的順利進行。
【關鍵詞】一帶一路 PPP 爭端解決機制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和熱烈響應。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政策已經成為中國的重大發展政策,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機遇。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一帶一路”建設更強調于基礎設施建設,以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改善民生,實現共贏。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府部門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不足以支撐整個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個時候,PPP模式就成為一個很好的選擇。
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是指是指政府部門通過與私人部門建立伙伴關系,通過長期合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一種公共產品提供方式,其具有平等合作、分擔風險、利益共享等優點,從而為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提供了良好機遇。
但受PPP投資規模大、時間長等自身原因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家的國情影響,中國投資者和外國政府不免發生紛爭,這時,就需要構建合理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在維護我國企業合法權益的同時,實現與沿線國家的發展共贏。
一、“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適用PPP模式分析
第一,“一帶一路”主要橫穿東南亞、中亞和西亞地區,該地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資源豐富,尤其是西亞和中亞地區,蘊含著大量的石油和礦產資源。但是,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普遍落后,同時基礎建設的資金和技術缺乏,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中國企業采用PPP模式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可以實現與沿線國家政府和社會資本力量的合作共贏,更可以為我國資源東入開辟新的渠道。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經過多年來在PPP項目上的實踐,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并頒布了相關的PPP法律法規,為PPP項目的開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如菲律賓、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柬埔寨、科索沃、約旦、科威特等國均有相關的特許經營法律法規和PPP 程序條法。
第三,近些年來我國企業,積極參與國內和海外PPP項目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沿線PPP項目建設,不僅有利于企業進一步“走出去”,參與全球范圍的投資競爭,提升自己的國際投資的水平和國際投資的影響力。同時也有利于緩解我國產業過剩情況,實現供給側結構調整,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
第四,針對PPP項目時間跨度大、資金需求量大情況,我國積極開辟“一帶一路”融資的新模式、新平臺,與相關國家共同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金融支持;以自己的資金實力,成立了絲路基金,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投資“一帶一路”建設。
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PPP投資爭端及解決模式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到五十多個國家,這些沿線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狀況差異很大,貿易投資和爭端往往如影隨形,中國企業面臨著諸多的法律問題,不免與項目所在國政府或其他投資方、社會組織發生爭議。面對爭議,中國企業必須選擇合理的爭議解決方式,盡最大努力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當PPP項目發生糾紛時,東道國政府既可能違反了東道國與投資者的母國之間簽訂的雙邊或多邊投資協議,也可能違反了東道國與投資者簽訂的PPP項目合同。這時,投資者可能以違反條約之訴將爭端提交國際機構尋求救濟,也可以以違反合同之訴向東道國法院訴訟。此外,一些雙邊或多邊條約中還規定了需用盡當地救濟,這就要求投資者在面臨PPP爭端時,必須尋求合理的解決方式,以化解矛盾,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一)國內法的爭議解決方式
PPP合同具有一定的民事契約性質,可以采用國內法的民事糾紛的相應解決方式。對投資者而言,國內法的救濟方式主要有協商、調解、行政程序、仲裁和訴訟。
1、協商和調解
一般合同中都會約定因為合同發生的糾紛雙方先協商解決,協商不成采取訴訟或者仲裁等手段。在協商階段,矛盾是可以調和的。爭議雙方就PPP項目的焦點問題進行溝通,綜合考慮項目各方的利益,以達成新的合意,繼續履行合同。這種解決方式高效、成本低,也有利于后續工作開展。調解可以由一個居中的組織如調解委員會或其他在東道國較有威望的組織主持進行,他們可以從專業的角度對案情進行審查,提出解決的方案,從而更好在協商中達成一致。
2、行政手段
由于PPP項目的一方為政府部門,PPP合同也具有一定的行政合同性質。面對涉及到東道國政府的監督和管理的爭議,投資者可以通過東道國政府的行政程序尋求救濟。如我國的行政法中規定的對政府具體行政行為如特許經營權的授予與取消、行政處罰等采取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但因東道國的政府自身效率和利益的影響,一些時候投資者難以得到公平。
3、仲裁和訴訟
所謂仲裁,是指爭議當事方根據雙方達成的仲裁協議將爭議提交給他們共同同意的仲裁庭進行裁決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仲裁是解決國際商事糾紛的常用辦法,但PPP項目主合同產生的爭議,一般因為涉及不平等的主體,除非在合同中事先約定采用仲裁方式,否則國內商事仲裁很少被采用。
PPP項目的主合同涉及到的糾紛多采用訴訟解決。國內訴訟主要指東道國法院采用本國法律對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的爭議作出裁決。但訴訟耗時長,成本高,一般只適用當地法律,如果用盡了東道國的救濟手段,投資者的權益仍不能得到保障,就必須求助于國際法的救濟途徑了。
(二)國際法的爭議解決機制
依據卡爾沃主義,東道國對于本國境內發生的投資爭端理所當然地享有管轄權,適用本國法律。但如果窮盡當地救濟,爭議仍然不能得到合理解決,國際法上的投資爭議解決途徑主要有外交手段、雙邊投資協定、國際爭端解決機構仲裁等。
1、外交方式
通過政治途徑解決投資爭端,手段通常包括談判磋商、調停、調解、外交保護等。這種解決大多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如試圖維護共同的經濟或政治利益、保護國家主權等,但對雙方是否能達成一致以及協議是否能得到履行,并沒有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執行反復和困難情況。
2、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
雙邊投資協定(BIT)是由東道國與投資國共同簽署的,為了保護和鼓勵雙方私人投資的書面形式的條約。很多雙邊投資協定中也涉及爭端解決方式,既可以解決投資國東道國國家間的爭端,又可以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截止2016年12月,我國已經與至少104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其中包括哈薩克斯坦、泰國、新加坡等50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這些雙邊投資協定中,對可仲裁事項的規定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可對于投資有關的所有爭端進行解決,另一類是僅僅只能解決關于征收帶來的補償額度爭端。這些雙邊投資協定對解決我國投資者同東道國PPP項目的爭端提供了有效的途徑。
3、區域爭端解決機制
中國已經積極參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可以利用該區域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同“一帶一路”沿線伙伴的PPP投資糾紛。該爭端解決機制包括磋商、調解、調停、仲裁等手段,運用極為靈活,程序可以自由選擇,也可以隨時開始、隨時終止。該機制下的仲裁庭報告具有終局性,但缺乏執行報告的強制約束力。
4、國際仲裁
基于PPP爭端的一方是他國投資者,一方是東道國,“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ICSID)在近些年來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ICSID來說,其管轄權需滿足以下三個要件:第一,主體方面,一方須為締約國,另一方須為締約國他國國民;第二,爭議須為直接投資引起;第三,爭議雙方需一致同意將爭端提交ICSID管轄。對于法律適用,ICSID堅持意思自治原則,由當事雙方協議選擇。ICSID裁決對爭端各方都具有拘束力。因此,ICSID以程序上的公平性、裁決的中立性、有力性獲得了歡迎。“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都是ICSID的締約國,具備將投資者與東道國的PPP投資爭端提交ICSID裁決的條件。
三、現有“一帶一路”沿線PPP投資爭端解決的困難和缺陷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有的是英美法系國家,有的是伊斯蘭法系國家,還有的是混合法系的國家,法律體系不同,法律文化不同,法律環境也不同。這就導致企業面對PPP爭端,如果想依靠當地救濟,就必須熟悉東道國內的相關法律體系和司法規則,這對大多數中國企業是難以做到的。事實上,投資者在東道國內同東道國政府的談判和訴訟往往處于弱者地位,耗時長,耗費的精力和金錢量同結果不成正比。即使勝訴,往往再次陷入執行難的局面。
基于此,投資者往往會懷疑東道國救濟的公正性,而轉向尋求外交保護和國際仲裁救濟。對外交保護來說,結果往往取決于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政治博弈,母國處于平衡國家間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忽視了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在BIT中,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簽訂的雙邊協議內容存在差異,對爭端解決方式、可仲裁事項、仲裁庭的約定上不盡相同。缺乏統一的標準,對平等解決同各國間投資爭議是存在詬病的。同時,并不是沿線的所有國家都是ICSID的締約國,一些投資者不能尋求ICSID 的救濟。
四、PPP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完善
實施一帶一路政策,鼓勵我國我國企業走出去,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PPP項目,必須構建合理的PPP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堅持在公平、高效、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礎上,將政治手段和司法手段向結合,構建區域性的、多層次的、靈活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一)完善既有的雙邊投資協定(BIT)
我國在簽訂的BIT中,關于爭端的解決幾乎都規定,因此對BIT的解釋或適用所產生的爭端應盡可能先通過外交途徑協商解決,外交途徑解決不了,方提交仲裁庭裁決。針對這一情況,中國政府應同協議簽訂國進行溝通,可以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進行磋商調解,確定相應的程序和期限,以不妨礙其他的救濟手段的采納。中國與他國簽訂的BIT中規定了外交途徑解決不了時,提交仲裁庭裁決。但中國在一些早期簽訂的BIT中往往對可仲裁的事項有嚴格的規定,往往局限于征收、國有化等事項。隨著PPP形式的多樣化和融資的復雜化,PPP投資爭議的內容日趨多樣,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可在未來同其他國家協商修改或簽訂補充協議,涵蓋更廣泛的爭議內容,促進當事人更加自由和合理選擇爭端解決方式。并且,基于“一帶一路”區域內國家相似的經濟利益訴求,中國可以考慮在各國關于PPP投資爭端解決中形成較為一致的解決機制,從而為簽訂區域多邊投資協定打下基礎。
(二)構建區域性的統一的國際仲裁機構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如果想要構建統一的協同發展的區域經濟共同體,就必須建立高效的、正式的國際司法解決機制。針對此,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區域性的統一的獨立的國際仲裁機構,負責“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爭端的解決。除了締約國政府外,企業和個人亦可就政府的可能違約行為訴諸該機構,涉及的領域則可包括貿易和投資。除此之外,爭端機構可以設立上訴機構和執行監督機構,為當事人提供二次救濟的機會。
(三)合理應用ICSID機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部分屬于發展中國家,法治并不健全。作為投資者,中國企業有必要通過國際仲裁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但中國海外投資者目前對ICSID機制利用力度較小,一方面是我國對ICSID機制的宣傳不夠,中國海外投資者對ICSID了解較少;另一方面,中國投資者依法解決爭議的意識還比較淡薄。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一方面要加大對國際仲裁機制的宣傳力度,鼓勵海外企業通過合法的國際仲裁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大對ICSID仲裁機制和仲裁案例的研究,為海外投資者提供有效的指引。
五、總結
“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中國的發展契機,也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和騰飛的新機遇。隨著中國對沿線國家PPP項目的投資增長,所產生的投資爭端也會越來越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會面臨更多的爭端解決上的挑戰。所以,中國必須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結合現有的投資爭端解決方法,構建“一帶一路”沿線統一、高效、公正的區域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以維護地區的投資穩定和PPP項目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1]王貴國.“一帶一路”戰略爭端解決機制[J]. 中國法律評
2016,(02).
[2]蔣圣力.論“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
制的建立[J].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16,(01).
[3]劉明萍.論“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構建[D].云南
大學,2016.
[4]顧斐然.“一帶一路”戰略視角下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研
究[D].浙江大學,2016.
[5]朱偉東.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間民商事爭議解決機制的
完善[J]. 求索,2016,(12).
[6]楊陶.“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及國際法思考[J].喀
什大學學報,2016,(04).
作者信息:王梓霖(1990- ),女,北京市,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