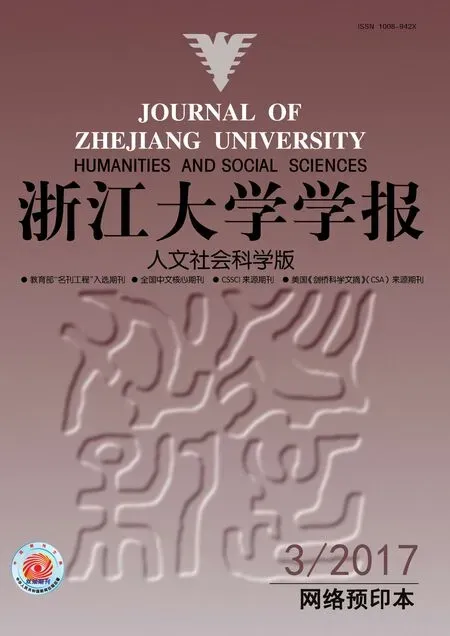筆談:歷史視野中的水環境與水資源
[美] 南德 [美] 馬瑞詩 孫競昊 熊遠報 魯西奇
(1.哈佛大學 環境研究中心, 馬薩諸塞 劍橋 02138; 2.布朗大學 歷史學系, 羅德島 普羅維登斯 02912; 3.匹茲堡大學 歷史學系, 賓夕法尼亞 匹茲堡 15260; 4.浙江大學 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5.早稻田大學 理工學術院, 東京 169-8555; 6.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主題欄目: 中國環境史研究
筆談:歷史視野中的水環境與水資源
[美] 南德1,2[美] 馬瑞詩3孫競昊4熊遠報5魯西奇6
(1.哈佛大學 環境研究中心, 馬薩諸塞 劍橋 02138; 2.布朗大學 歷史學系, 羅德島 普羅維登斯 02912; 3.匹茲堡大學 歷史學系, 賓夕法尼亞 匹茲堡 15260; 4.浙江大學 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5.早稻田大學 理工學術院, 東京 169-8555; 6.武漢大學 歷史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 申志鋒 譯
水乃生命之源,與人類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對水資源的治理、利用貫穿整個人類史。在中國古代,如何處理黃河、長江兩大水系問題是解決國家水資源問題中至關重要的環境議題,對此,中華民族在與自然持久的互動中始終積極作為。這樣的努力同樣體現在對大運河水利網絡的部署中。歷史表明,從最基本的民間生活用水所需到國家層面的水治理戰略,從內地城鄉生活用水的匱乏到沿海居民獲取淡水的艱難,水在社會的各個層次和角落里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黃河; 長江; 大運河; 水治理; 水柜; 苦水; 濱海地域
一、 關于長江中游區域環境史的再思考
南德(美國哈佛大學環境研究中心博士后、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三峽以下長江流域的一千公里曾是一個巨大的季節性濕地,擁有鹿和水牛群,食肉動物如老虎和鱷魚,巨大的候鳥群和豐富的水生生物。通過建造堤壩和排水系統,人類逐漸將這些濕地變成了肥沃的農業區,現在這里已是數億人的家園。長江流域水環境的治理過程歷經兩千多年,但尚未被充分理解。誰都知道這些低地的墾殖化對中國歷史的重要性,但不太認識到它也摧毀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氣候溫和地帶的濕地。我的工作旨在探討農業社會的擴展導致世界濕地*參見M.Williams(ed.), Wetlands: A Threatened Landscap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W.J.Mitsch & J.G.Gosselink, Wetlands(4th Edition), New York: Wiley, 2007。被破壞的背景下長江低地數千年的歷史。
我剛開始研究兩湖平原全新世的環境變遷,該地區的濕地是長江流域規模最大的濕地系統,至今洞庭湖系統中尚未被破壞的一小部分及鄱陽湖地區仍然是華中最重要的濕地。這些濕地常常冬季干旱,而夏季頻發洪水。像兩湖平原這樣的大河漫灘平原在生態上卻是物產極為豐饒的區域[1]。當洪水泛濫時,它們是魚類餌料的重要補給區;當洪水退后,留下肥沃的泥沙層,新生的植物吸引了各種野生動物。這就是司馬遷所謂“云夢之饒”的意思。
我對這個地區的興趣,開始于我對香港中文大學買下的關于堤堰維修的漢朝行政文書“河堤簡”[2]的研究。這些簡牘表明,在漢初該地區就有一些堤防,比先前已知的早幾個世紀,揭示了《史記》和《漢書》的治水記錄偏向于黃河流域大規模水利工程,它們是由漢朝中央政府官員寫的。不過,長沙吳簡也有類似的記錄,顯示古代中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都在維護堤壩和灌溉系統*參見凌文超《走馬樓吳簡采集簿書整理與研究》第八章《隱核波田簿與孫吳陂塘的治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454頁。。
如果回顧一下史前史,我們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人們積極改造環境已有幾千年之久了。湖南、湖北發現的許多史前遺址有大型圍墻,從城頭山文化開始,石家河—屈家嶺文化最明顯,到盤龍城址,圍墻結構也很明顯。其中一些可能是為了抵御洪水。而浙江良渚遺址的防水工程可能不是新石器時代中國南方地區唯一的防水系統,它們只是因浙江考古學家使用先進的測量方法而被第一個發現。換句話說,我期望未來的考古工作能找到史前防水更多的新證據。
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野生動物。一般認為長江流域曾經有過大量的大型動物活動,不過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圍墻似乎保護了農作物免遭野生動物的破壞。例如,一只亞洲大象每天可以吃200公斤的食物,一群大象可以在幾個小時內輕易毀壞整個村莊的農作物(這在像尼泊爾這樣的地方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那里的農民生活在野生動物保護區旁邊)。長江低地曾經是大象、犀牛、野生水牛和鹿的家園,更不用說老虎和短吻鱷;野生動物比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多得多。在過去的幾千年里,人類和牲畜已經逐漸取代了這些動物的棲息地,并用農場替代了它們的棲息地。
這就涉及我的研究的另一方面,即是人類生態學。在早期,長江流域的生產力非常高,人們可能只花少量時間種植水稻和其他食物。剩余的時間他們可以釣魚、收割莊稼和狩獵,這些都是只需較少勞動即可獲得食物的方式。但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們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越來越努力地工作,于是水稻種植成為人們生活的中心。這是有趣的現象,因為水稻是長江濕地的天然植物,它的生長需要適應洪水和干旱的循環。因此,人們在該地區種植當地土生植物。這只是農業系統長期發展的一個方面,它允許人類生活在該地區,并改變其景觀。不幸的是,由于缺乏關于農村的文獻記載,我們對周至唐代的農業開發和動物馴化情況的變化知之甚少。中國考古學的一個特點是,有許多新石器時代村莊的遺址報告,但沒有以后時期的,所以比起漢代以來,我們更了解的是新石器時代的農村經濟。
綜上,我目前的研究側重于追溯兩湖平原的長期墾殖化,基于先前所理解的它是一個非常緩慢和長時段的過程之假設。只有結合自然科學、考古學和文獻,我們才能理解該地區的長時段歷史。
二、 黃土的增加: 北宋時期黃土高原的侵蝕
馬瑞詩(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這里我想談一下我目前有關黃河研究的一些內容,之后還有一個更大的課題旨在探索長時段與大規模的黃河流域環境史,該課題涵蓋的時間段包含了三千年,并將黃河中游侵蝕的歷史與下游洪水的歷史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同時,我的這一研究將黃河建構為一個地球體系和世界體系。作為前者,黃河是一個單一實體,其上游發生的事件對下游具有可預測的影響。然而,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黃河從干旱的邊緣地帶流向濕潤的區域,不可能基于現代環境知識或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來管理黃河。為了證明這一點,我正在進行新的數據分析,并將環境科學融入我的工作中。同時,我也希冀了解有關黃河歷史研究的重要中文研究成果,并介紹給英語讀者。
學界已有一個長期普遍的認識,即約在11世紀,黃河從長期相對穩定的狀態轉變為后來頻繁發生洪澇與改道的狀態。不僅歷史文獻記載了洪災發生的時間和特征,而且土壤本身也揭示了每年沉積物的增加以及這些黃土的來源即黃土高原。盡管氣候變化起著一定的作用,但所有證據證實,變化發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人類在鄂爾多斯盆地草原上活動量的增加,且該黃土區域恰好處于黃河的大拐彎內。在11世紀之前,該區域的定居點是稀疏的,漢人和黨項人之間日漸激烈的爭奪導致雙方都加強了對該地區的重視。至1044年,在草原上有三百多條柵欄。這些地處偏遠、很大程度上自給自足的居民點所屬的田地、牧場及居民的木材采伐破壞了脆弱的地表覆蓋物和暴露的易受侵蝕的沙土與土壤,使得它們通過風和水的沉積過程進入到了黃河。
黃土具有高度滲透性,并且在有植被覆蓋的地方是非常不易被侵蝕的,反之,則極易被侵蝕。在有森林或草地覆蓋的情況下,坡度和降雨強度對水土流失的影響相對較小,但當除去地表覆蓋物后,水土流失則立即開始。黃土高原位于東亞季風帶的西北邊緣,降水量分配不均,極易遭受干旱和暴風雨等自然災害。在旱季,風將黃土和沙子積聚在溝渠中;在雨季,它們常常在暴雨中迅速沉積。在夏季風暴期間,從沙漠到黃土高原北部和西部,黃土土壤與風吹來的沙子混合在一起,被從溝渠沖到黃河的支流,最終進入黃河的主道。當這樣的情形發生時,流經干旱、半干旱和亞濕潤地帶的黃河則成為一種流動著的泥石流。然而,降水本身與沉積物進入河流的積累并不相關。根據最近的研究,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至少30%是人為的,氣候環境則加劇了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水土流失的影響。
直到10世紀,黃河發生洪水只有零星的歷史記載。根據相關的歷史記載,漢代洪水發生的次數增多了,但接下來直至晚唐時期,幾乎沒有黃河發生洪水的相關報告,這也正是譚其驤先生的著名觀點。黃河地區關于土壤的記錄幾乎與歷史時期的洪水記錄完全對應,反映了10世紀之交黃河地區土層沉積的急劇變化。事實上,數據顯示當時發生了巨大變化,即大約一千年前沉積到河流中泥沙的量級陡增。
那么,大約一千年前的黃土高原和鄂爾多斯盆地究竟發生了什么導致這種變化出現?其實,伴隨溫暖期的到來,在北宋和黨項族的西夏之間建立了一個軍事邊界和戰場地區,這場建立在以黃土高原脆弱和容易受損的草原為中心的11世紀的對峙,對整個中國北方生態和水文的均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0世紀時,中國處于一個大分裂時期,黨項族的西夏和契丹族的遼國逐漸強大起來。宋朝在960年建立,1004年與契丹遼國締結了和約,這兩個政權確立了外交關系,并明確了邊界。雖然設防是可持續的且能被良好管理,但在宋和西夏政權之間則不是,而是需要宋王朝修建大規模的防御設施來抵抗黨項族。1038年,這兩個政權之間的戰爭爆發,且一直持續了7年。1040年,以興建堡壘和城墻為主的戰爭結束,而此時宋已經有居住在黃土高原的670個部落的340 00匹馬和155 600個居民,還有由20個禁軍兵營和900個藩鎮兵營所組成的32 580名軍人和民兵。1042年的另一場防御戰爭旨在填補空缺,至1044年,在黃土高原上有500個禁軍兵營,約50萬軍隊,與30萬西夏的騎兵形成對峙之勢。因而戰爭以相持狀態結束。黨項騎兵無法打破宋的堡壘,宋的步兵亦未傾力將騎馬的黨項族趕回他們自己的領土。
在11世紀40年代第一次宋夏戰爭結束之時,政治家歐陽修公開反對用于分布在整個高原上廣大密集的小堡壘和城墻之間的人口和資源的巨大開支。然而,所有的堡壘都保持了下來。宋在1080年的另一次攻勢中建立了一個新的更靠北的邊界,并相應地修筑新的堡壘。在11世紀40年代至12世紀20年代之間,宋王朝在黃土地區建立了20多個新縣,以幫助管理和經營邊境地區。每一個縣都是一個新的城鎮,擁有數十名民事和軍事官員。同一時期雙方在反復較量中建立起了300個新的堡壘,每個都管理著數十或數百的馬匹、軍士和其他人員。每個堡壘都各自使用當地資源,獲取盡可能多的食物和燃料,這對當地脆弱的生態造成了額外的影響。除了在邊境修建堡壘和軍屯,宋王朝還在黃河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河流域黃土地的南部開發了土地作為農場和畜牧場,并且開辟了從那里到北方邊境地區的幾百英里的道路。
到11世紀末,半干旱的鄂爾多斯盆地從草原和稀疏森林相對完好的地區變成了一片片被風和水侵蝕、被溝渠割裂的裸露著的淤泥和沙地,且一旦這種沉積物以不可預測的速度沖入黃河,華北平原的整個命運就改變了。
三、 明清時期大運河北段水柜的部署和管理: 前現代社會人力作用于環境的一個案例
孫競昊(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教授):水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至關重要的資源,水利事業關系到國計民生。利用水資源的運河工程由來已久,隋唐時期開始出現全國規模的運河網絡,元代重修大運河,連接江南與京師,而后在明清時期成為王朝的財政生命線。為了維系大運河上的漕運以及運輸貿易,明、清政府從物質、體制、政策諸方面傾力投入。在地勢高、氣候干燥、水源短缺的北部運河流域,大運河運行的最大挑戰是缺水。明清時期水柜的設置是保障運河供水的關鍵一環,其存廢與運河的興衰相始終。濟寧地區的“北五湖”和“南四湖”即著名的運河水柜。作為政府積極干預運河沿岸環境和社會的方式,水柜的設置改變了當地水文結構、地理環境和社會生態,其復雜曲折之過程以及成敗得失,為我們思考前現代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國家與地方社會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案例。
1411年宋禮重開會通河之始,設立安山湖、南旺湖、馬場湖(皆在濟寧以北)、昭陽湖(濟寧以南)四大水柜。而南旺湖事實上又析出蜀山湖、馬踏湖二湖,這是北五湖的由來。北五湖所處的濟寧北部地區地勢高于濟寧南部地區,維系運河供水尤為艱難。至明末清初,除了蜀山湖外,其他各湖趨于枯竭,盡管之后偶顯恢復的跡象。濟寧南部地區的水源相對豐沛,除了昭陽湖,其他三湖南陽湖、獨山湖、微山湖在明末出現,在清代擴大,并連成一體,也合稱為微山湖。總的說來,運河以西的水柜因地勢低于運河以東,疏導東流的黃河、淮河等的泄洪作用明顯,所以更多地被稱為“水壑”。通過對濟寧地區水柜的考察,我們可以歸納出當時在改造自然過程中各個因素的作用與機制。
其一,水柜起源于自然水泊或積水,它們之所以變成水柜是由于人力的行為,即經過人工改造、擴大、規范化,由政府主導日常管理或監督,旨在為運河保持恒量用水,而防洪排澇、農業灌溉以及漁業生產都屬次要考慮。
其二,盡管因環境的變遷,水柜不斷整修和改善,但缺水是持久的問題。在濟寧北部地區,只有蜀山湖的功用相對穩定。這種情形自晚明以降變得嚴峻,因為黃河在河道南移后不再成為北方水柜的水源。
其三,當政府堅定不移地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時,這些水柜方能儲備足夠的水量,保障運河的供水和調節;反之,則會萎縮,最終枯竭。同時,不能否認水柜等運河水利設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當地水流運動的不確定性,說明了被改造、治理的環境具有優越性的一面。
其四,當地民眾千方百計利用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從水柜取水,用于農業灌溉,但政府在水資源的分配上擁有決定性權力。如政府規定了從水柜等水源取水的官渠與民渠的比例,唯有民渠的水可以用于灌溉。
其五,水柜的設置犧牲了大量耕地,故附近地區的民眾通過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機會侵占湖田,導致水柜的消損,這種情形在北五湖地區特別嚴重。而在南四湖地區,當地居民不僅侵占湖地,還在湖區從事捕魚、水產養殖。文獻中有政府與民眾以及相鄰村莊之間爭水、爭地的大量記載,當然政府具有解決糾紛的權威。
其六,政府為漕運確保水柜蓄水而與當地民眾圍墾湖田的沖突加劇了湖澤和周圍洼地的環境惡化,使其難以抵御泥沙淤積、沼澤化,并加重了旱、澇交替發生的態勢。考慮到水流的不可測和土地占有權的不確定,湖田不是穩定的農田。
包括水柜在內的大運河是一個涉及自然環境、基礎設施、財政和管理的復雜系統。我們可以看到人力、技術和組織等因素改變了既有的生態環境結構,使之服務于人類社會的需要,從而產生了可操縱和不可操縱的環境后果。通過對水柜的審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前現代社會里人力作用于環境所涉及的以下幾個宏觀議題。
其一,人類工程技術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大運河的修建是基于人類可以通過意志和才智改造自然以服務于人類的信念。在北部運河段,工程主要是開拓、匯集、儲蓄水資源,水柜至關重要。但這種對環境的改造不是全然的征服,而是遵循大禹治水的疏導方式。盡管如此,人類干預自然的客觀后果并不完全由主觀愿望決定。在濟寧南部地區,水柜對環境的影響十分復雜,難用正面或負面一言概之。洪災常常由于政府蓄水保運的抉擇而愈演愈烈,天氣的干旱、植被的減少、人口的增加都在蠶食著自然的和人為的環境,所以水柜等運河水利設施的長時段后果顯現出人力及其技術的局限性。但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人類對自然因地制宜的適度干預可以起到積極的效應,這是為什么大運河在明清時期大體上實現了既定目標。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運河水利設施的主要功能并非預防自然災害和改善生態系統,而是為了國家及社會的生存和發展。這也意味著人們重新建構自然的理性技術邏輯必然需要與主要來自國家和地方社會的各種力量適當協調的社會邏輯相適應,以提供技術解決的人為氛圍。
其二,王朝國家—地方社會的關系與區域環境—社會的變動。大運河作為王朝的生命運輸線和農業社會的多功能水利工程之存在,受到社會關系和政治權力的制導和規范。為保障農業社會的穩定而維系其防洪功能十分必要,同時用于耕地灌溉和保持土壤(淤泥)肥力的蓄水問題同樣值得重視。當政府的水利工程綜合考慮、協調這些目標時,它們能比較持久地發揮預期的作用,因為來自地方社會的抵制小。明清兩朝的多數時期,雖然運河基本暢行,但大大小小的“水權”爭執案例層出不窮,特別是在濟寧這種干旱的北方地區,對稀有水源的分配之爭最為激烈。水柜、水渠、池塘都連接于或修建于引展的運河網絡上,是漕運季節里國家和地方“水權”紛爭的集中地。當水柜消損,農戶爭奪湖地,這種情形隨著人口增長而日益惡化。一般說來,地方官員由于征收田賦的壓力以及與地方社會勢力的利益關系,往往并不情愿執行朝廷為保運而嚴禁濫墾的敕令。在清代中后期,微山湖成了山東西南部最重要的運河水源,其被“豪強”及“細民”侵墾的記錄俯拾即是。清末漕運衰微直至廢止,侵占湖田的大勢便不可逆轉了。
其三,國家權力的威力與地方環境變遷的不同命運。如前所述,一個區域或地方的興衰固然受制于生態環境與技術手段之間的關系,但國家權力常常主宰著環境的變化,進而牽制著地方經濟與社會的波動。運河的開鑿與維護增加了地方自然環境的復雜性和可變性,而自然災害或急或緩地肢解既有的生態系統。國家有限的資源需要在各地區間不均衡地分配。幸運的是,明清時期由于濟寧地區的繁榮與國家的戰略利益密切相連,水柜的作用不僅是濟運,而且還有助于提高當地防旱排澇的能力,更勿論政府對濟寧這樣的重點地區的災害救治、賦稅減免的重視和投入,如對微山湖受災湖區設立沉糧地、緩征地的優惠政策。與此對應的是,作為沿運河地區腹地的其他地區往往被忽略、被犧牲,山東西部的大多數腹地地區都是如此,而膠東半島亦歸于不被重視的邊緣地區。視野再擴大些,淮北、蘇北成為損失更大的犧牲品。運河流域社會的命運系于政府政策,缺少經濟自主再生力。當社會動亂、政權衰微時,國家主導的生態模式的負面作用顯著。如明清易代之際,運河設施與生態危機并現,北五湖大部分枯竭了,盡管清代有所恢復;南四湖在清代的興盛與自然變遷趨勢有關,也與政府的強勢干預有關。中國東部以運河為中心的水利和環境結構大體上維持到19世紀40年代初,接著黃河河道的北遷給山東西部環境和經濟帶來災難性的打擊,這也是自然與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然。19世紀中葉以來,王朝中央權力的式微使得運河設施不可逆轉地衰亡,曾經繁榮的濟寧地區在自然與社會災害面前更為脆弱。
從濟寧地區水柜等運河水利設施的運作功能和歷史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區域生態環境變遷中自然與人力的兩種作用力,而國家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水柜的舊事演繹了前現代社會人為世界與自然世界謀求平衡的一個范例。
四、 苦水: 北京的傳統環境困境
熊遠報(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學術院教授):水是與生命、人類起源和文明的發展持續密切相關的物質,同空氣一樣,培育、涵潤了生命與文明。水是生命和文明存續不可或缺的原初環境,在前現代技術條件下,降水、洪水、海潮、水流失、水蒸發等是難以控制的自然現象,人在與水的互動關系中往往很被動。不過,人類正是沿著水源、河流在地球上遷移與擴展的,在不同的水與自然環境中創造了風格相異的文明,對水的利用與防范技術也就成為各地區文明的重要部分。
由早期人類的定居點發展起來的聚居點,已經開始具備城市的一些基本功能,集聚和拓展了人類的智慧,為文明的薪火相傳提供了堡壘。聚居地、定居地的選擇離不開水源,而規模(人口與地理范圍)龐大的城市如果沒有足夠的、可持續供給的水源,則難以生存下去。缺乏長時段規劃的早期傳統城市往往會因為過度擴張而在多方面面臨困境,生活用水為其中之一。天然水在通常情況下無色無味,地表水在流動過程中經過沉淀作用,適于飲用。人對水的味覺反應因體質差異等會有不同程度的表現,但水甜、水苦并非一個人的主觀自我意識與獨特感受,而是水中所含化學物質直接作用于味蕾而產生的生理反應。在進行社會經濟史特別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時,城市居民生活的飲用水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課題。但長期以來由于對此問題缺乏關注,也因為現存文獻的局限,我們其實不清楚傳統城市居民日常飲用水的具體狀況,當然更不知道飲用水對居民健康產生的影響。
華北地區屬于半干燥地區,降水量有限,平均每年約600毫米,而且降水時間分布不均,多集中在六七月間,水的流失與蒸發嚴重,在晚近的一千年間,發生旱災的頻率很高,往往為三年兩次,發生洪災的年份也可能同時發生旱災,整個地區長期以來處于慢性缺水狀態,缺水導致環境調節與修復能力脆弱。北京是古代華北平原北端的一個重要聚居點,很早就成為一個重要城市。在元朝成為龐大帝國的首都后,城中常聚數十萬人口,16世紀中期擴建外城以來,人口規模更大。在傳統技術與市場條件下,近百萬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對城市的基礎供應帶來巨大壓力,歷代政府為確保漕運、城防、防災以及宮廷用水,對城區地表水嚴格管理,禁止取用,北京普通居民日常生活不得不主要使用水井,但大多數水井的水質不佳,居民長年飲用的是來自地下的所謂“苦水”。即便在隨著技術進步飲水環境有所改善的20世紀前期,據當時市政當局對水井的調查,水中依然含有如阿摩尼亞(NH3)、亞硝酸、硝酸、硫酸與氯、鹽分,以及細菌和大腸桿菌等多種損害味覺與健康的有害物質,水的硬度很高。即使按照低標準,到20世紀40年代,北京適合飲用的水井也僅為20%,尤其是居民日常生活利用的絕大多數淺水井被污染率很高。這一調查結果實際反映了元代以來文人學者常常提及的北京居民日常生活仰賴苦水的事實*有關20世紀中期以前北京居民飲用水狀況的研究請參照筆者的論文:《清代民國時期における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載《社會経済史學》2000年第66巻第2號,第47-67頁;《18—20世紀における生活給水と都市の外來労働者》,見都市史研究會編《年報都市史研究》12,第33-34頁,(東京)山川出版社2004年版。。
北京地下水苦澀的成因,除土壤與巖石所含礦物質等地質因素外,北京居民作用于環境的行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據日軍對北京水井水質的調查分析,超過30米的深井水質較好,不足30米的淺井水水質不佳,水質苦澀多為4至10米的淺水井。淺水井水苦當然有地質因素,但北京淺水井水質不佳的主要因素是人的活動與環境行為要素的影響,在抽樣調查的水井中,水質主要受地下土壤中礦物質等化學成分影響的水井只占約12%。參見佚名《本市自來水井水之檢驗》,載北京市衛生局衛生月報編輯室《衛生月報》1942年第36期,第5-9頁。。在現代市政系統確立之前,人為因素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層面:其一,北京并沒有建立完善的處理生活污水和人畜排泄物的技術系統。其二,北京并沒有建立一套保持環境衛生,有效處理生活污水、垃圾、人畜排泄物等公共事務的制度以及組織系統,城市公共領域的服務缺失,或任由市場決定。在行政不作為的情況下,追逐經濟效益的“糞道”系統橫行,在處理排泄物的過程中,糞尿處理行業有意使用了不能密封的容器,導致糞尿日常性地在大街小巷泄漏、擴散*相關研究參照筆者的論文:《排泄物との格闘——十五世紀—二十世紀、北京における人畜 の排泄物の処理システムの成立について》,見奧崎裕司等編《明代中國の歴史的位相山根幸夫教授追悼記念論叢》,(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版,第643-664頁;《胡同と排泄物処理システム》,見吉田伸之·伊藤毅編《伝統都市4》,(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0年版,第161-184頁;《18-20世紀の北京における下水道·糞尿処理にみる公共観》,見藤田弘夫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公共性の変容》,(東京)慶応大學出版會2010年版,第259-280頁。。其三,北京城內居民排泄與處理生活垃圾的行為、習慣的影響。據當時人的觀察,北京居民經常在大街小巷隨地大小便,民宅平時隨意將排泄物傾倒在街道上的行為嚴重污染了北京的環境。明清時期,生鮮垃圾未經特別處理,生活垃圾堆積在城內,加上居民的燃料主要為煤炭,其排放的煙塵與殘渣中含有大量硫化物,這些垃圾與沉積物中的有害物質經風沙雨雪作用進入溝渠,或持續滲入地下,直接、間接地污染了地下水源。
在數百年間,技術與制度系統的缺乏、排泄物處理者道德缺失的經濟活動、居民的利己環境行為,給北京的飲用水與生活環境帶來了災難性后果。除了因降水量不足導致的環境自我修復能力受限的自然要素影響外,歷經數百年百萬規模人口的環境累積性行為,也導致北京生活環境每況愈下,地下水質日益惡化。居民既是苦水的被害者,同時他們的行為也是苦水的重要成因,被害與加害惡性循環的狀態在北京延續了數百年。其實不僅僅北京如此,舊時中國城市居民在環境上的利己主義行為普遍存在,他們及其子孫也因此飽嘗了利己行為的苦果。
五、 水資源環境與濱海人群的生計適應
魯西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關于傳統中國水資源和水環境的研究,主要是從農耕人群的立場出發,觀察并分析農耕人群生存、生活與發展所依靠的水資源和水環境,以及人們對水資源的需求、開發與利用,包括由此而引發的水環境的變化與反饋。研究的核心問題集中在灌溉和防洪兩個方面。近年來學界對生活用水(包括缺水區與豐水區的生活用水以及城市生活用水)及其引發的水污染的關注,側重于人與水環境的關系,拓展了此一領域的廣度和深度,并指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離開功能主義的立場,不僅僅把水資源看作人可以開發利用的對象以及可污染的對象,而且把人與水(以及其他因素)看作一個整體,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與制約、共同變化或發展的系統,即人與水共存共生,也可能一起衰退和“死亡”,從而去探討其“歷史過程”、變化機制,以及尚不能確定是否存在的“科學規律”,分析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一些經驗與教訓。
這也是我們開展中國歷史上濱海地域研究的學術理念的一部分。所謂“濱海地域”,乃是指瀕臨海洋、居住人群之生計與海洋環境有密切關系或受海洋環境影響甚巨的地區,包括大陸的沿海地區、沿海諸島嶼及相關水域。與大部分農耕區域不同,濱海地域的水環境是海洋環境與陸地水環境共同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其構成、變化與利用迥異于一般農耕區域的水環境。就水資源而言,它也包括海水資源與淡水資源兩大類。這兩類水資源以及對它們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并制約著濱海人群的生計適應和選擇,乃至其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
海水給靠海為生的濱海人群提供了其生計所需的基本資源。在19世紀以前,資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以魚為主的各種海產品,獲取的手段主要是捕撈和養殖。二是海鹽,獲取的方式主要是煮海水為鹽,后來發展為曬鹽。三是海路,海岸港灣提供了便利的停泊點(港口),廣闊的海洋提供了海上交通與運輸的便利(近海航路),從而給濱海人群提供了一種重要的生計手段,即做水手,從事航海運輸。海產品、海鹽與海路乃是濱海人群賴以為生的三項最主要的生計資源。
直到最近,有關中國海洋漁業史的研究仍然是主要根據一個世紀以來對海洋漁業資源的現代調查,去追蹤歷史時期海洋漁業的分布、漁業活動。這一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假設古代的人們對海洋漁業資源有較為全面的了解與把握,自然而然地會集中在漁業資源豐富的海域從事漁業生產。可是,我們根據文獻的記載與個案分析,發現近代以前的漁業活動及其分布地區主要集中在渤海灣、萊州灣、海州灣、長江口兩側、杭州灣以及浙南福建沿海各海灣及其島嶼間,珠江口兩側、北部灣等近海水域,特別是黃河、漯河、浮河、無棣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椒江、甌江、閩江、九龍江、珠江、符江等河流入海口及近海島嶼附近水域。濱海漁業產品,除各種海魚之外,還見有海蠣、海蛤、海蚶、海螺、海珠及紫菜、菰米之屬。據此推測,近代以前的海洋漁業當屬于沿海漁業,漁業活動大抵限于距離海岸(包括離島海岸)一日航程以內的海域;捕魚撿蛤應當是濱海漁民的主要生計活動,除了在潮間帶插網捕魚、利用馴化的海鳥到稍遠的海域捕魚之外,在沿岸淺灘及島嶼采集貝類與海藻亦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
顯然,傳統漁業生產的分布與現代海洋資源調查所得的認識并不一致,或者說,舊時傳統漁業活動集中的地區并不一定就是海洋漁業資源豐富的地區;而近海捕撈更是傳統漁業主要的生產活動;漁業活動的周期性也未必與魚汛形成對應關系。這雖然受到漁業資源、航海技術與捕撈方式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漁民需要在漁船上裝載淡水和谷物,他們的船太小,也不夠堅固,所以他們很難在遠離海岸的海上過夜;另一方面,漁民需要將他們的海產品賣給岸上從事農耕的人家或市場,而農耕人家及市場都集中在河流入海口附近。
同樣,近代以前鹽業生產地區的分布與鹽業資源的分布之間也并不完全對應。在理論上,海鹽生產主要受到海水的含鹽度及海岸地帶的物質環境兩方面因素的制約或影響。顯然,近海水域海水含鹽度越高,越便于海鹽生產,特別是在廣泛采用“煮海為鹽”生產技術的中古時代更當如此。同時,在“煮海為鹽”的制鹽技術下,寬廣的潮間帶(便于提取鹵水)和蘆葦灘(可以提供燃料)是海鹽生產的兩個必備條件。在黃河奪淮入海之前,今蘇北沿海近海水域的海水含鹽度很可能是較高的,它又有寬廣的潮間帶和蘆葦灘,是最合適的海鹽生產區。漢唐北宋時期,這里也是最重要的鹽產區。可是,黃河奪淮入海之后,蘇北沿海的含鹽度顯然大幅降低,但在元明清時期,兩淮鹽場的產量及其重要性不降反升。而渤海西南部近海水域以及長江、錢塘江之間的東海近海水域,由于受到黃河、海河、長江等河流注入的較大影響,海水含鹽度并不高,在理論上并不是很好的鹽產地(雖然它們滿足地勢低平、蘆葦灘寬廣的條件)。但事實上,這兩個地區(特別是渤海西南部沿岸)自漢唐以來就集中了許多鹽場,分布著眾多的鹽灶,并且生產了大部分的海鹽。
何以會如此?重要原因也許正是上述地區密布著眾多的河流與湖泊。較大的可以航行的河流是用于運輸的,將鹽區產的鹽外運,并將鹽區需要的谷物、工具等運進來。我們更要注意那些小的河流及湖泊,它們雖然不能運輸大宗物資,但對鹽民來說卻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們乘著很小的船去收割蘆葦作為燃料,汲取淡水,采集菰米、蓮籽、蓮藕,以彌補谷物的不足。
由此,我們觸及了濱海漁民與鹽民生計的一個重要特征,即不能自給自足。受到文獻記載的限制,我們無法估算海產品在沿海漁民食物構成中的比例,但它應當不會很高。換言之,濱海漁民絕非總是吃海魚或貝類,而鹽民更不會以吃鹽為生。他們需要從外界獲取糧食、衣物或其原料,甚至淡水。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生產資料也需要從外界輸入:濱海漁民需要獲得木料以打造漁船,得到麻等織物以編織漁網;鹽民生產所需的鐵鍋等工具,大都是先向官府或控制海鹽資源的巨商借的,然后用生產出來的鹽來償還。
因此,考慮到濱海漁民、鹽民在食物上的結構性短缺,特別是其生活必需的淡水、谷物以及生產必需的造船用的木料、紡織漁網的織物及鐵鍋等,必須從其生計系統外面獲取,我們把濱海漁民與鹽民的生計界定為一種不能自足的生計形態,而由此形成的區域經濟形態則是一種結構性短缺的經濟。
弄清楚漁民與鹽民生計的不自足性及其經濟的結構性短缺之后,從事海上運輸的“艇戶”的生計就一目了然了:海上運輸本身更不能生產任何食物,其賴以為生的船只也需要從外界獲取原材料才能打造。所以,艇戶的生計更不能自足;而海上運輸在近代以前甚至不能構成一種經濟類型。
那么,漁民、鹽民以及艇戶又是如何解決這種生計的不自給性或者經濟形態的結構性短缺的呢?第一,是適應,即盡可能將從事漁業、鹽業生產的地點選在靠近淡水資源又便于采集野生谷物的地方。第二,是交易,即通過不同途徑,用自己的產出(海鮮與海鹽)與勞動力(對從事運輸業的水手來說)換取必需的糧食、衣物或其原料、木材、鐵鍋等生活、生產必需品。第三,是墾殖,即采取不同手段,自己開墾土地,從事農耕。濱海洲灘與島嶼的早期墾殖很可能相當大的部分即出于濱海漁民、鹽民等人群之手。第四,是搶掠和走私,即通過搶掠和走私手段以獲取糧食、財物,將之作為一種生計手段或補充。在這個意義上,做海盜是一種生計方式,而海盜們搶掠的對象與走私的“合作伙伴”則大多是生活在河口地帶的農耕人群或城市人群。
顯然,濱海人群生計的不自足性及其經濟形態的結構性短缺,促成了濱海地域經濟網絡的外向性和流動性:自古以來,濱海地域就需要通過與外界的交流與貿易,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濱海人群通過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將海洋與陸地聯系起來,將海洋環境與陸地環境容納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共生共存的環境系統與社會經濟系統。
[1]P.B.Bayley,″UnderstandingLargeRiverFloodplainEcosystems,″BioScience,Vol.45,No.3(1995),pp.153158.
[2] B.Lander,″State Management of River Dikes in Early China: New Source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entral Yangzi Region,″T’oungPao, Vol.100, No.4-5(2014), pp.325-362.
A Conversation on the Study of Water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rian Lander1,2Ruth Mostern3Sun Jinghao4Xiong Yuanbao5Lu Xiqi6
(1.CenterfortheEnvironment,HarvardUniversity,Cambridge,MA02138,USA; 2.DepartmentofHistory,BrownUniversity,Providence,RI02912,USA; 3.DepartmentofHistory,UniversityofPittsburgh,Pittsburgh,PA15260,USA; 4.JiangnanRegionalHistoryResearchCenter,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5.SchoolofScienceandEngineering,WasedaUniversity,Tokyo169-8555,Japan; 6.SchoolofHistory,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Based on shared concerns for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five contributors in this symposium articulate their viewpoints from their respective case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 how to deal with the Yangzi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the two largest rivers, were key environmental issues on national water resource solutions, and the Chines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constant interactions with nature.Brian Lander’s research on the early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entral Yangzi valle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Yangzi lowlan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s wetlands by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The wetlands on the Lianghu Plain were originally one of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 in the world. A rich variety of aquatic lives, plants and wildlife in this region earned it the reputation of ″wealth of Yunmeng.″ However, why has it mostly been converted to farmland? According to him,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revealed thousands of years of immigration, farming and dike building in this region. He argues that over the long ru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ydraulic construction by increasing population steadily reshaped the original regional ecosystem.Ruth Mostern introduces her large project of exploring the long-term and large-scale history of the Yellow River, covering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time and integrating the history of middle-course erosion with the history of lower-course flooding, and highlights data approach from environmental science. Focusing on why the Yellow River shifted from a long-term condition of relative stability to a later state of frequent floods and course changes, she argues that such changes resulted from intensification of human activity in the grasslands of the Ordos basin. From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mounting conten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Tanguts led both sides to fortify the region. The fields, pastures and lumber operations of these remote and largely self-supporting outposts destroyed fragile ground cover and exposed erosion-prone sand and soil that made its way into the Yellow River through a process of wind and water deposition, thereby transforming the entire fate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Chinese activism in nature was exemplified more intensivel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rand Canal hydraulic network. Sun Jinghao explores the managements of water resources to sustain the Grand Cana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investigating the fluctuations of reservoirs in the Jining Region of western Shandong. The operation of the Grand Canal heavily relied on continual 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comprehensiv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in which reservoir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northern sections. In order to combat the tremendous problems of water shortage, as well as flooding in monsoon seasons, massive reservoirs were vigorously installed or modified in the Jining region to reserve and moderate water for canal navigation. Although the state’s manipulations of water resources by reconfiguring the regional hydrological network generally achieved its anticipated objective, this was an extremely difficult accomplishment due to the complex reactions from both nature and local society.Water is people’s basic necessities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China the lack of drinking water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lack of fresh water, related to how to survive, on the coast are lasting severe issues. Using the term ″brackish water,″ Xiong Yuanbao depicts water consumption in late imperial Beijing, involving natural conditions of water resources, water consumption by citizens, as well as municipal rules and institutions that regulated the extrac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Mostly shallow and close to the land surface, these ″brackish water″ wells were both a product of soil and mineral contents and a consequence of human activity. Besides the absence of basic infrastructures for water and sewage treatment and the government’s negligence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regulations, the urban residents of Beijing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creating, disposing, and neglecting various kinds of waste that infiltrated the land to pollute the underground water.Lu Xiqi turns his attention to the livelihood of coastal fishers and salt-workers with regard to water environment. In his views, the mainstream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cean has neglected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their livelihood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people and the sea. He focuses on sea food and sea salt, trying to reconstruct the livelihood of fishers and salt-workers living in the coastal regions during the medieval age fr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in the subsistence system of coastal fishers and salt-worker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necessities of living and production such as freshwater, cereals and shipbuilding timber, iron pans for boiling seawater and netting fabrics, forced them to acquire daily necessities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trade and even robbery. Their lack of self-sufficiency contributed to the openness of the economy in the coastal region, and the fluidity of coastal society.
the Yellow River; the Yangzi River; Grand Canal; management of water; water tanks; bitter water; coastal regions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10.122
2016-10-12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7-03-23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
1.南德(http://orcid.org/0000-0001-5122-4483),男,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后研究人員,布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環境史研究; 2.馬瑞詩(http://orcid.org/0000-0001-8219-7174),女,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及世界環境史研究; 3.孫競昊(http://orcid.org/0000-0002-7864-0628 ),男,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 4.熊遠報(http://orcid.org/0000-0003-2737-0135),男,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學術院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城市史研究; 5.魯西奇(http://orcid.org/0000-0002-2883-9196),男,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歷史地理與中國古代史研究。
本欄目特約主持人: 浙江大學 孫競昊教授
[譯者簡介] 申志鋒(http://orcid.org/0000-0001-6226-9142),男,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明清環境與社會經濟史研究。
【主持人語】 環境史無疑是當前歷史學發展前沿中的一個重要方向,它充分考慮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盡管中國學術界對環境的研究由來已久,但無論是自然科學史,還是歷史地理,都是把環境作為研究的客體,與環境史的視野、路徑、方法歧異可辨。因此,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環境史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在中國環境史研究的范疇內,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到各個歷史時期人民的生產、生活,以及歷朝歷代政府主導的、涉及整個社會運轉的整治和管理,乃至當今面臨的生態危機及其對策,水環境與水資源都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本欄目選取中國和美國幾位學者于2016年4月在哈佛大學舉辦的“水資源”工作坊的部分筆談,特別就水環境與水資源問題做一探討,希望對中國環境史研究有所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