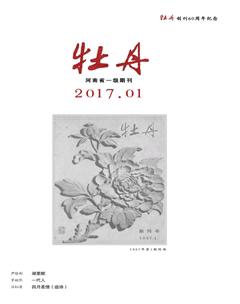宋代的《史記》文學評論
馬菽蔓
《史記》是中國文史著作中的扛鼎之作,歷代對其都有非常多的評論。《史記》是文史結合的典范,關于它的文學評論是與史學評論同步的,漢魏南北朝時期就已開始,唐代進一步發展,并奠定了《史記》的文學地位。宋代作為我國思想與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其文學評論的相關思想具有極高的研究與參考價值。本文針對宋代對《史記》的評論進行簡述。
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歷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獨有的紀傳體體例為后世史書的寫作開創了新的道路。《史記》是一部系統性研究中國歷史的史書。該書主要是將我國的歷史資料進行系統性搜集,然后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從全社會的角度探尋歷史問題,這樣能將歷史從以往狹小的空間引入到廣闊的大千世界里,即讓歷史從微觀走向宏觀,建立新型的歷史認知系統,為以后的歷史編撰奠定堅實基礎。作為一部著名的史學巨著,《史記》規模之宏大,體系之完整是其他書籍無法相比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關于中國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說對中國歷史乃至中國民族有著深遠的影響。《史記》問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學者的關注,對其的評論不可勝數,本文主要就宋代時期的筆記探究《史記》。
一、宋代時期對《史記》的歷史學評論
《史記》的宗旨是,通過細致的觀察,看到一個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時了解前世治國中的優點和缺點,以實現“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統化的思想體系,通過對歷史的評述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筆記中就有關于司馬遷的《史記》評述,具體的思想方面評論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第一,論述“史公三失”。《史記》問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特別是漢代的楊氏父子對《史記》有著極高的評價,其實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對后世有著極大的影響,部分后世的學者都是以此為契機開展評論的,包括宋明時期的筆記中也有相關評述。根據相關的評論能夠獲悉,從體例的角度考慮,部分評論者始終認為司馬遷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傳。在分析有關《刺客》《游俠》等內容的時候,始終認為司馬遷作傳有的是遇到事件發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過事件來警醒后人。第二,論《史記》中的微言大義。司馬遷開始編著《史記》與《春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所以《史記》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即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都蘊含著無數微言大義。《野客叢書》中有段話能印證這一觀點,“若要說《新唐書》與《史記》有何不同,其實兩者有著較大的不同。《新唐書》主要是講述真正的風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風景上略施筆墨,讓人見了有心服之感,其實所有的用意是在筆墨之外。”這里用筆墨之外比喻《史記》,實際上是講述有關史記以外的內容,敘述的內容有著
其他深意。
二、宋明時期對《史記》的文學評論
歷史著作的關鍵是能還原歷史,給后人一個完整的歷史評述,文學作品的特點是通過創造讓人喜歡去讀,所以兩者存在較大的差距。《史記》是歷史性的著作,問世后就開始受到學術界的認可,在其文學性質認識方面正在歷經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史記》自身的文學價值也被后世逐步認同并推崇。魏晉南北朝之前,文學和歷史是一體的,且史學一致是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們對《史記》進行評述的時候更關注其文學價值。
(一)敘事特色
《史記》開創了我國的紀傳體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國紀傳體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相較于一般的文學巨著,《史記》有著較大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敘事的主體內容。《史記》在作為史學著作存在之時,其自身的文學性不可磨滅。其實無論是史學巨著還是文學巨著,都要有良好的敘事性。歷史主要是記錄事件,所以在記錄期間要讓整個事件的條理更加清晰,內容更加明確,特別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講清楚說明白,讓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為一部紀傳文學,文字要生動形象,能真實地反映事件。古代沒有先進的技術,不能通過影響將很多歷史保留下來,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記錄,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動感,具有可閱讀性。其實,司馬遷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記》猶如一部敘事的藝術瑰寶,讓歷代的文人都對其不斷地進行挖掘。
(二)論體例
一部著作的體例指的就是其組織形式,通過何種方式或者方法將所有的主體部分進行串聯。體例對于《史記》這樣的宏篇歷史著作至關重要。體例將作者的歷史觀、寫作思想等核心內容進行統一,其合理與完善程度直接關系著作品的成敗。本紀、世家、列傳等構成了《史記》的獨特體例,使《史記》最終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嚴謹的紀傳體體系。《史記》的五體結構開創了一個先河,也為之后的歷代正史提供了一個真正的主干模式。
1.論五體。宋洪邁有言曰:“子長書出,規制既定,后世作者難紊。”《史記》五體義例深著,開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認可《史記》的五體,在《朱子語類》中直接說《史記》中所記錄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貫穿性,本紀里面提到過的事件,在傳記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書如《資治通鑒》采用的編年體體系就有很大缺陷,這個年代的事件記錄過后,便沒有可以再找到相關資料的地方。譬如說漢高祖劉邦鴻門宴事件的記錄,除了高祖本紀里面有詳細的記載之外,在張良傳、灌嬰傳等處也有同樣詳盡的記載,使讀者能夠在讀到一處之時想起另一處。
2.體例與思想。宋代各家對于《史記》體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體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司馬遷在著作的過程中著重通過體例的獨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義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馬遷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體歸納上有不當的地方。譬如宋項安世的《項氏家說》中曾寫到:《史記》記錄了戰國時期的十三個國家,卻稱為十二諸侯,因為秦國完成了統一十三國之壯舉,秦王登基稱帝,因此將秦史納入本紀中,從世家的層面上才有十二諸侯之說,與列傳中實際上是七國而只做六國列傳一樣。
宋黃震在《范蠡大夫種傳》中寫道:司馬遷將范蠡的生平記錄于《貨殖傳》,卻將范蠡的功績與聲名記錄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應該參照《春秋》中的內容重新編寫《范蠡傳》。
(三)論取舍
宋代對于《史記》的取材有很詳細的分析,認為《史記》選材范圍非常廣,但是也進行了相當嚴格的取舍。張大可認為司馬遷的取舍標準是取材義例。
取材途徑有六種,分別是:皇家藏書;文物與建筑之上所記錄的信息;游歷天下,實地考察;事件的當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轉述;詩詞歌賦;歷代遺留的史書。
取材標準也可以概括為六點,分別是:六藝的標準以及儒家理論;文辭規范的遺留文獻;不記錄神怪之事;不是關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記錄,世與傳中的人物只記錄軼事;可信的事件與有一定異議的事件要用兩種說法共同記錄;將不同思想的經傳與諸子百家的思想統統記錄并予以整合。
三、結語
《史記》做為我國史書中的經典,為我國歷代史學家所研習與繼承。宋代做為我國文化最為發達的時代之一,對中國古代其他文學評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些評論術語如“精神意氣”“意味”“氣象”等,在繼承前代基礎上又有新發展,即使在今天仍有無窮的魅力。對于《史記》,宋代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與評述,其研究與異議涉及到了各個層面,在我國古代文學評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所包含的豐富的前人思想,對于現代人也同樣值得參考。
(河北定州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