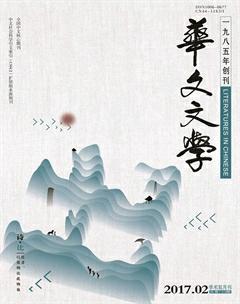夏濟安及其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述評
王宇林
摘要:述評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濟安的翻譯,第二是夏與《文學雜志》的關系,第三是夏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第二部分已有豐富的文學成果,而有關夏濟安的翻譯的討論,在深度與廣度上都未能很好的展開。第三部分則會隨著研究者對其兄弟的書信集的解讀的增多而更具內涵。此外,文章還指出了夏濟安與通俗小說、通俗文化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夏濟安;翻譯;《文學雜志》;《黑暗的閘門》;《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
中圖分類號:I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7)2-0124-05
一、從夏氏兄弟書信集的出版談起
2015年4月,夏濟安夏志清昆仲書信集由臺北聯經出版社出版,書信集名為《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至此,書信集第一卷的整理與編注便結束了。同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簡體字版。大陸的版本,將由一著名出版社出版。待大陸出版社的版本推出之后,三個版本的比較應會吸引對夏氏兄弟的感興趣的文化與文學史研究者。因為夏濟安與夏志清之間的通信多以書信形式遺留下來,有六百多封,刊之梨棗,尚有五到六集。夏志清從大陸至美國學習,取得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后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夏濟安輾轉香港至臺灣、最后留在美國。1947年以后的中國社會環境,詭譎多變,而夏氏兄弟的書信,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彼時政治、經濟、學術傳播、學人交往的重要窗口。《書信集》起于1947年夏志清致夏濟安的信,訖于夏濟安逝世。本文梳理學術界對夏濟安相關研究的成果,以期研究者能更好地使用《書信集》,并將漢學研究與家國離散相聯系,擴大研究范圍與研究深度。
夏濟安先生(1916-1965),本名夏樹元,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1934年畢業于蘇州中學,在校刊《蘇中校刊》上發表《被選為國語演說代表有感》。①有關夏氏生平教學,無論是其后的任教北京大學、西南聯大,還是到港后任教新亞書院,抑或抵臺任教臺灣大學,這些都是研究者熟識的了。我在這里要指出的是兩次夏濟安赴美之因緣。1955年2月,夏濟安之赴美,乃受錢思亮之推薦,本想申請Yale,后來被派往Indiana。照合約,夏應在1955年6月30日返回臺灣,其生活費是替USIS編anthology而取得的。事實上,夏是8月底才返回臺灣。1957年加州伯克利分校成立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陳世驤(1912-1971)是主持人。1959年夏濟安再次赴美,其在華盛頓大學之后的工作便是陳世驤提供的。1966年7月莊信正接替夏濟安在中國研究中心所遺的職位,1969年張愛玲接替莊信正。而在夏濟安之前,則是李祈擔任此職。②
無論是在兩岸三地,還是旅居美國。夏濟安都未曾留下大量的著述,除了主編《文學雜志》期間發表的有限幾篇論文外,其留下來的著作,部分是在美期間寫的。夏原是英美文學教授,第二次赴美后方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專注于共產中國之研究,以期能在美國學術界揚名。研究之成果曾以小冊子方式刊行,計有Metaphor, Myth, Ritual, and Peoples Commune(《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A Terminological Study of the Hsia-fang Movement(《下方運動》)、The Commune in Retreat as Evidenced in Terminology and Semantics(《人民公社制的潰敗》)三種。均由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出版,分別出版于1961、1963、1964年。③1965年夏濟安死后,其弟夏志清為其整理遺著,以《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將已刊未收入集子中的和未刊的幾篇論文整理出版。
若我們算上夏濟安編、譯的著作,可以發現經他之手而產生的文本其實是不算少的。而有趣的是,對夏濟安的研究則狹隘得許多。大體可以分為對夏濟安的翻譯的研究、夏濟安與《文學雜志》之關系研究和夏濟安對左翼思想研究的成果的思考。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為夏濟安贏得盛名的是《夏濟安日記》的出版。而且讀者對該書的關注是多于夏氏的其他書籍的。不過,一般的書評以外,嚴肅地探討夏濟安情感生活的似乎并沒有,因此在寫作中,與此相關的文獻將會付之闕如。
二、夏濟安翻譯作品及思想研究
宋奇是夏濟安好友,夏在港期間及以后之翻譯,多由他介紹。夏濟安以筆名齊文瑜翻譯了一些通俗長篇小說和論文集,如《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坦白集》(The God That Failed)、《草》(The Burned Bramble)、《淵》(The God That Abyss)。④但這四部作品并未贏得研究者的注意,雖然其中的部分作品亦重版發行。為夏濟安贏得名聲的翻譯是《美國散文選》和《名家散文選讀》(第一、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后,臺北英文雜志社曾予重印。大陸方面,上海譯文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都對其中的部分進行重版,其中復旦版是朱乃長校對后的版本,⑤夏譯儼然被認為是翻譯之翹楚。
至少從1992年起,就有研究者對夏濟安的翻譯表示出了相當的興趣,對夏譯著作的書評是這方面的證據。⑥1997年至今,討論夏濟安翻譯的文章平均每年一篇。不過也顯示出了相當的局限性。一方面,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上,對夏濟安翻譯進行研究的寫作者大多沒有進行廣泛的資料收集,造成分析的篇目相重,其論點論據的偶合性較高。另一方面,研究者在使用美學/翻譯理論進行論文寫作時,并未對原來的理論進行批判性的借用,以致當多人都借用該理論進行寫作的時候,文章的結構和內容的相似性較為明顯。
《美國名家散文選讀》共收入11位作家15篇散文。這15篇文章中,已被分析的篇目如下:《冬日漫步》、《霍桑論》、《西敏大寺》、《古屋雜憶》、《英國的農村生活》、《作者自敘》、《禽獸為鄰》、《論美》。其中《冬日漫步》、《西敏大寺》、《古屋雜憶》受到研究者青睞,出現率較高。此外還有7篇還未得到研究者的另眼相加。它們是《飛蜘蛛》、《浮游》、《美腿與丑腿》、《民主教育》、《詩歌與我們的時代和國家的關系》、《愛德華茲論》、《二百年前的新英格蘭》。
在對夏濟安翻譯進行研究的文本中,有兩個常用的詞是經常出現的,那便是“增加”和“減少”。所謂的“增加”,是說研究者在寫作文章時候常指出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句進行的意義補充;而“減少”則主要是句式上的,即就是漢語句式較短,復合從句不多,在英譯漢的過程中需將從句譯成短句,以符合漢語語言的規律。這種分析方法是結構式的,應是在結構主義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其弊端非常明顯。將這種分析方法具體運用到文本中,便會發現作者的情感以及研究者的個人思想受到排斥。文本以貌似客觀的狀態存在于研究的論文中,然卻少了真知灼見。“格式塔”理論的應用可涵蓋上文提出的問題。
研究者將格式塔理論教條化,利用“增加”或“減少”方法,在一篇文章中找對應的觀點,而非從翻譯文本出發,進行文學的比較或翻譯研究。另有文章從語料庫的收集與分析研究夏濟安所譯《西敏大寺》,還有從翻譯來看翻譯者的宗教觀、女性觀與愛情觀,不過因為彼時可用資料的欠缺,研究者進行文本分析時到底還是不夠深入。我們對這些文章進行統計分析,可以歸納出如下的三個方面的特征:第一,研究者試圖從美學角度對夏譯散文進行分析或賞析;第二,研究者也嘗試從翻譯技巧上對夏的散文翻譯風格特點進行分析研究;第三,是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研究夏的散文譯作。
三、夏濟安與《文學雜志》的關系
《文學雜志》創刊于1956年,是夏濟安東游美國后與劉守宜、吳魯芹合作創辦的,想必與其在美國的見聞與學習有關。夏濟安為主編,劉守宜為明華書局老板,任《文學雜志》經理,吳則幫忙籌措經費,宋奇負責海外稿件。至1960年,共發行48期,每半年合成一卷,共8卷,內容以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為主,“中國文學部分,詩歌總計75首,散文42篇,小說83篇,文學評論68篇;外國文學方面,詩歌11篇,散文3篇,小說25篇,文學評論35篇,影劇7篇,其他7篇。”⑦可見夏濟安主編時期,他對文學評論的重視,也可以反映出夏濟安的治學取向。
相比對夏濟安翻譯的研究,研究者在將夏濟安與《文學雜志》放在五十年代的臺灣文學的大環境之下,產生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楊宗翰、張新穎、梅家玲、許俊雅、褚昱志、柯慶明等諸位研究者都有專文討論《文學雜志》與夏濟安的關系。此外,學院博碩士論文也有所討論,⑧且論述有精到之處。夏濟安個人生活空間的復雜,造成了后世對其研究的復雜化。其中之一便是《文學雜志》因受美國新聞處資助,有的研究者則將其作為“美國權力對東南亞地區的文學宣傳品”⑨,貶低雜志寫作者和主編在寫作中的功能與效用,這與發生在夏志清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事情恰相一致。⑩有文章在討論《文學雜志》時,強調新批評對其的影響{11},這是其來有自的。不過文章也指出,無論主編還是寫作者,或許都沒有在下意識中使用此理論。在此需要討論的是許俊雅、梅家玲的文章。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論夏濟安與〈文學雜志〉》{12}是較早全面討論夏濟安及《文學雜志》的力作。文章將夏濟安生平事跡與政局動蕩聯系起來,勾勒出大社會之下的個人生活與學術空間的激變、回轉與消亡。其為“夏濟安”與“《文學雜志》”單列篇章,也是有識之見。文章還詳細討論作為“學者兼翻譯家的夏濟安”,并將雜志編語作為討論的對象,凸顯出了較高的文學眼光。尤其是大家對有著相同歷史背景之下的大陸的文藝狀況有些許了解之后,對編者按語、主編的話等“殘言小語”的關注,更能窺一斑而見全豹。
而梅家玲則再三致意,將其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上選讀的稿件整理,反復修改與打磨《夏濟安、〈文學雜志〉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志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13},將《文學雜志》視為50年代臺灣“最重要的文學雜志”之一,并將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文學接受結合起來,探尋作為媒介的《文學雜志》。顯然的是,梅文使用的文化研究方法,將生產、印刷、消費及閱讀合觀,構成闡釋的場域,進而研討文學生態。
夏濟安與《文學雜志》之關系可從許、梅二人的文章得出大概,至于其他有關《文學雜志》本身的研究,如其敘事方式、與《中外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關系以及更為廣泛的現代文學的關系,則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文學雜志》雖是在美國新聞處的資助之下進行的,仍然有著極其鮮明的個人印記。尤其是當我們回顧50年代臺灣的文學書寫時,《文學雜志》以其“樸實、理智、冷靜”的作風而備受注意。
四、夏濟安個人創作、思想研究
大陸研究者之熟識夏濟安,靠的是翻譯。1981年10月,樂黛云主編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出版,書中收入夏濟安《魯迅作品的黑暗面》{14}。1965年夏濟安逝世后,其生前的創作類部分文章被收入《夏濟安選集》{15}。陳子善在為修訂版寫的序《不要忘了夏濟安》里說:
1981年10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樂黛云先生編選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書中收錄夏濟安的《魯迅作品里的黑暗面》一文,這是大陸讀者和文學研究者首次知道夏濟安先生的大名。但是,迄今整整十八年過去了,夏濟安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等更為廣大的領域里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貢獻,卻仍不為大陸讀者所知,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16}
至今,十六年過去了。夏濟安的大名似乎還停留在“反共”上面,他逝世后出版的那本《黑暗的閘門》也未有中文全譯本,更別說他的其他的小書了。與其胞弟夏志清憑《中國現代小說史》而成為北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相比,夏濟安則落寞得許多。好在研究者不僅對他的情愛故事感興趣,也對他的個人創作和學術思想多有剖析。最為顯著的便是對《香港——一九五○》和《黑暗的閘門》所構成的知識譜系進行梳理與概括。
《香港——一九五○》創作于1950年4月,附錄在1950年4月30日“夏濟安致夏志清”的信上,原題《香港》{17},從香港寄送遠在美國的夏志清。原詩共10節44行,節內押韻,有些像中國古代的排律。1958年8月,《文學雜志》第六期發表《香港》,并刊登了陳世驤《關于傳統、創造、模仿》于詩作之前,權作紹介之功能。發表的詩作則9節44行,是將第五、六節合成第五節;詩作也略有修訂之處,除去增加標題中的“一九五○”和副標題“仿T.S. Eliot的West Land”外,計有10余處改動。
改動最大的是將第二節第四句“我只好咽下這一口痰”改為“但是哪里可以吐痰?”和第三節第四句將“走定了?好!吃馬,將!”中的問號“?”改為逗號,改變了原文的語氣與含義。夏還刪除了原來的兩個注釋,這些注釋他沒有在其為《香港——一九五○》寫的《后記》中作出說明。其一是“見韓愈祭鱷魚文”,位于“羊-豬-我帶來”后;其二是位于“宋玉臺”后夏注曰“‘宋王臺,宋帝昺避元蹈海處,在九龍,遺跡不存”。
陳世驤指出,“既不說是‘奇文,又不說是‘好詩,我倒覺得《香港——一九五○》是一首相當重要的詩”{18}而其重要性,可從研究者在推究《香港——一九五○》時,往往與白先勇小說《香港——一九六○》對照閱讀的關系中得到,這樣做的目的是借以探尋詩作與小說之間的迂回與繁復。張新穎在發覺二者之間的關系上,用力甚勤。《“借來的空間”,“身份”的“傳奇”——從夏濟安〈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19}考索了夏濟安與白先勇創作上的某些認同:
但我們仍然不妨試探:《香港——一九六○》是否可以看作是夏濟安偶爾的詩作延宕的回聲?或者,小說以自身的聲音,喚起文學史對一首詩的記憶和重新發現?更進一步,在這兩個文本之間,有沒有可能蘊含著超乎個人關系的時代性精神體驗和隱蔽的文學史線索?{20}
作者的目的于焉可見,“兩個作品互相對照,互相激發,從而充分釋放出我們單獨閱讀其中任何一個文本時容易忽略的豐富信息。”作者在對異質文化的勾勒中,將個人胸懷與感時憂國剔幽抉微,顯示出非常廣闊的論述空間。而同樣由張新穎點撥的《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詩與一篇小說的關聯閱讀》一文大致“梳理了《香港——一九六○》的創作動機與精神資源, 從標題來看也許是對老師詩作的唱和(是否可以視為《香港——一九五○》延宕的回聲?或者,小說以自身的聲音,喚起文學史對一首詩的記憶和重新發現?)其中也有白先勇個人的擔負,可能還受到《荒原》的影響。這里并非是搜求影響性的證據,只是說:在《香港——一九五○》與《香港——一九六○》的溝通中,《荒原》可以搭建起一座橋梁。”{21}
無論是《“借來的空間”,“身份”的“傳奇”——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還是《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詩與一篇小說的關聯閱讀》,兩篇文章都是以相同的文本來解讀文學思想的文章,相比前文的家國書寫,后文更注重二者之間在書寫“現代性”上的相似之處。夏志清也從練字及立意等方面對其進行批評,并認為“全詩名句很多,確在吳興華、卞之琳之上”。{22}
如果說文學創作還只是夏濟安寫作的一個方面,那么我們必須注意到他的另一方面方能完整地呈現出夏濟安研究的全貌——那就是文學研究及其批評。夏濟安首先是作為一位教授、一位文學研究者而知名的,他的小說寫作只能算得上是“副業”而已。《現代性的政治》{23}呼之欲出,文章認為夏的研究“對1950年代兩岸重振‘五四精神和海外學界高彰‘抒情傳統的思潮均作出了及時的回應”,并探討了夏著中“美學、政治、自我”之間的多重對話關系。文章還論證了“夏濟安本人的‘五四情節和‘抒情通路”,后者以《黑暗的閘門》為代表,“閘門的書寫接續了當時海外學界正日漸高漲的抒情傳統論述”,雖然不盡能令人信服{24}。
五、結論
誠如許俊雅在文章中指出的,夏濟安研究其實并未相當展開。我以為這是一個研究的吊詭,我們一方面接受、闡釋和辯駁夏濟安文中的觀點,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又對他的研究進行消費閱讀,這固然是夏濟安留下的作品不多(多乎哉?)的原因所致,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研究者“趨利避害”的思維導致的。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出版為我們提供了這么一個契機。通觀已經出版的第一、第二兩卷,夏氏兄弟先是談京劇,繼而討論電影。后來,兄弟二人同在美國,書信上寫的有關京劇、電影方面的內容漸少了起來,更多的篇幅開始向著學術展開。
綜上,我們可以將夏濟安及其文學批評的研究分為三大部分。第一是夏翻譯,第二是夏與《文學雜志》的關系;第三是夏的文學創作及文學批評。第二部分已有豐富的文學成果,而有關夏的翻譯的討論,就總數來說,應該是有許多的了,不過深度與廣度都未能很好的展開。第三部分則會隨著研究者對其兄弟的書信集的解讀的增多而更具內涵。如夏濟安與中國俗文學研究的展開(包括“鴛鴦蝴蝶派”和武俠小說),他對京劇和電影的喜好將會構成論述的重要環節;傳統儒道二家思想對夏濟安的影響等命題都深具意義。
① 沈慧瑛:《多情才子夏濟安》,《檔案與建設》2010年第12期。
② 參見1966年6月26日張愛玲致莊信正信,見莊信正:《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張愛玲來信箋注(一)》,《書城》2006年第5期。
③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下)——論夏濟安與〈文學雜志〉》,《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④ [澳]白倫敦(Geoffrey 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香港:中一出版社1952年版;臺北:大地出版社1979年版。紀德(Andre Gide)、西隆涅(Ignazio Silone)等人著《坦白集》,香港:友聯出版社1952年版。[奧]Mane Sperber:《草》,香港:友聯出版社1953年版。Mane Sperber:《淵》,香港:友聯出版社1955年版。
⑤ 夏濟安:《美國散文選》,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夏濟安:《名家散文選讀》(第一卷、第二卷),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臺北英文雜志社將第一二卷合訂,于1989年重印。夏濟安譯:《美國名家散文選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夏濟安評注:《現代英文選評注》,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張龍寬:《夏濟安先生翻譯賞析》,《中國翻譯》1992年第5期。
⑦ 李家欣:《夏濟安與〈文學雜志〉研究》,臺灣“國立中央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第35頁。
⑧ 有關臺灣的碩士論文,請參見李家欣《夏濟安與〈文學雜志〉研究》,“國立中央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吳佳馨:《1950年代臺港現代文學系統關系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臺灣“國立清華大學”2008年碩士學位論文;陳冬梅:《試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以〈文學雜志〉〈現代文學〉為中心》,廈門大學2009年博士論文。
⑨ 王梅香:《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雜志〉與〈現代文學〉》,《臺灣文學學報》2014年第25期。
⑩ 程光煒:《〈中國現代小說史〉與80年代的“現代文學”》,《南方文壇》2009年第3期。
{11} 程曉飛:《試論臺灣〈文學雜志〉對新批評的介紹和運用》,《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4期。
{12}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上)——論夏濟安與〈文學雜志〉》,《華文文學》2002年第6期;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下)——論夏濟安與〈文學雜志〉》,《華文文學》2003年第1期。
{13}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志〉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志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006年創刊號,該文又曾刊于《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2期。
{14} Tsi-an Hsia,“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ü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3,No.2(Feb.1964).
{15} 這里指的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的版本。《夏濟安選集》原由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系收輯刊在《現代文學》中的“夏濟安先生紀念專輯”中的文章而成。夏濟安先生逝世后,《現代文學》、《幼師月刊》、《文星》都曾在不同年份推出紀念文章。
{16} 陳子善:《不要忘了夏濟安:〈夏濟安選集〉內地增訂版序》,《博覽群書》1999年第5期;亦收入《夏濟安選集》。
{17} 參見107封信,見王洞主編、季進編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1947-195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2-375頁。
{18} 陳世驤:《陳世驤文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頁。書中于陳世驤《關于傳統·創造·模仿——從〈香港——一九五○〉一詩說起》后附有夏濟安《香港——一九五○》及其后記。
{19}{20} 史佳林、張新穎:《“借來的空間”,“身份”的“傳奇”——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華文文學》2008年第12期。
{21} 金理:《從夏濟安的〈香港——一九五○〉到白先勇的〈香港——一九六○〉一首詩與一篇小說的關聯閱讀》,《上海文化》2010年第6期。
{22} 參見(第一卷)第108封信,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第376-379頁;(第三卷)第356封信。
{23} 余夏云:《現代性的政治:論夏濟安左翼文學研究的意義》,《南京社會科學》2011年第11期。
{24} 可參見王德威為海外“抒情”作出的系譜,見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亦見王德威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責任編輯:黃潔玲)
A Running Commentary on Tsi-an Hsia 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search
Wang Yulin
Abstract: This commentar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being translations by Tsi-an Hsia, the second being his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ry Review, and the third being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Although there is rich literary achievement in the second part, discussion of Hsias translation is yet to be well extended in depth and width. The third part, on the other hand, can be enriched with an increased reading among researchers of his letters with his brother.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touch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ia and popular fic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Keywords: Tsi-an Hsia, translation, Literary Review, The Gate of Darknes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si-an Hsia and C. T. H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