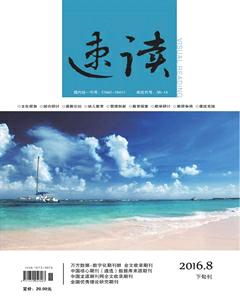什么是有力量的知識?
王強
兩年前,我聽一位生物老師給高三學生講授傳統發酵技術。當時就想,實踐性這么強的內容卻只是為了考試講講而已,實在可惜了。
今年,我擔任學校綜合實踐活動課的教學。我決定借助綜合實踐活動這門課,讓學生對傳統發酵技術在做中學、研究著學。
學生的興致很高,但問題很快就出現了。任何研究的第一步一定是查資料。既然是一些實踐型的研究,所查閱的資料應該涉及這些食品發酵的原理和方法。然而我驚奇而無奈地發現學生似乎對原理不大感興趣,他們更關心食品發酵工藝本身。就像常年做米酒的老婦,她并不關心在米酒發酵過程中涉及到哪些微生物的哪些生化活動,她們只知道米要泡透、蒸透,要密封,否則就不出酒。
中國歷代出了那么多的工匠、手藝人,可就是出不了科學家,他們的技藝非常精湛,他們的頭腦卻處于“老婦”的水平。我們的先輩們一次次的總結經驗,可就是不愿去探究事物本身的奧秘。于是技術發展了,科學依然匍匐。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扯起科學和民主的大旗,但我們的教育到現在也沒有教給學生科學,更沒有教給學生民主。授受式的教育教給學生的是知識,不是科學,鼓勵的是聽信,不是民主。灌輸式教育在“傳授科學知識”的幌子下對學生進行愚弄、誘騙甚至教唆,這樣的教育不會培養出有民主思想的公民,只能培養子民、順民或者暴民。
我要求我的學生必須尋找相關的原理,每個研究小組要做一個PPT給同學們介紹自己的課題。這個處理多少見效,部分學生可以做到腦指揮手,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有限的“閱讀——實踐——反思”的研究型學習者。
這次綜合實踐活動教學的效果是傳統的課堂講授所達不到的。先是有些同學的米酒陸續被帶到班上接受品嘗和評價,然后是酸菜、葡萄酒、蘋果醋、酸奶、啤酒。先是不敢嘗,后來就變成了搶。最后學習小組在理論探索和實踐基礎上寫出了研究報告并在班級交流。
有的小組成功了,有的小組失敗后成功了,有的小組以失敗告終了。然而中學生的課題研究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關鍵是他們在課題研究過程中經歷了知識產生的方法和過程。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可是什么知識才是有力量的?
我認為知識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我們在中小學學的這些科學知識,是科學家們科學研究的結晶,并且經過教育者的處理,變成了系統、完成的知識體系。
第二個層次是關于方法的知識,包括觀察的知識、實驗的知識、比較的知識、概括的知識等等,科學家們正是運用了這樣的知識,發現了第一層的知識。
第三個層次是關于過程的知識,這個知識是策略性的,是對研究過程的設計和實施的知識。
策略性知識主過程,方法性知識主細節,我們教科書上的科學知識,那些知識點,不過是結果性的知識而已。
什么樣的知識有力量?我認為情景中的知識才有力量。你置身于一個真實的問題情景,運用了一定的方法,設計并經歷了研究的過程,然后獲得的知識才是鮮活有用的知識。
這些方法和過程的知識具有很好的遷移性,掌握了這些知識,你就可以用它來探索新知,解決新問題,才會具備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
我們教給學生的知識實在太多,學生在有限的時間里要學那么多知識,只有靠老師講解灌輸。沒有了過程和方法的知識,就成了僵死的知識。沒有了過程和方法的教學就成了教條的闡釋,學習就成了記背和機械訓練的功夫。學生下了這番功夫,知識自然可以記得,但是考試結束后,大部分知識就忘記了。
我認為理想教學的教學內容要少,但應注重方法和過程,一個在我們看來可以5分鐘講明白的知識要讓學生運用研究的方法,經歷研究的過程,自己把這些知識“生產”出來。這樣,雖然知識量少了,但知識的質量是很高的。
我們教給學生大量的沒有力量的知識,但缺乏有力量的知識,缺乏關于過程、方法和策略的知識。
但是還沒有完,我認為綜合實踐活動不但讓學生經歷過程與方法,學到有力量的知識,而且應培養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公民意識。
在運用方法經歷過程的探索過程中,學生需經過兩種活動,一是獨立探究,二是集體討論。獨立探究使人具有獨立思考的習慣,集體討論使人具有尊重別人觀點的意識。
獨立自主的人,思想自由的人,尊重不同意見的人,是民主體制下公民的必備修養。不具備獨立思考的習慣,不尊重別人的意見的人,要么成為管制別人的獨裁,要么成為別人管理的奴才。
由此看來,民主不僅僅是一種體制,它要求體制下的人是具有民主思想(獨立、自由、尊重)的公民(不是臣民)。滲透方法與過程的科學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是塑造民主社會之公民的教育。闡釋知識教條的教育是霸道的教育,是知識擁有者以知識霸權者的身份對受教育者的奴化。
所以,當我們提出科教興國的時候,不僅僅是用科學知識興國,是要用科學的思維方法來武裝人的頭腦,是塑造具有民主意識的新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