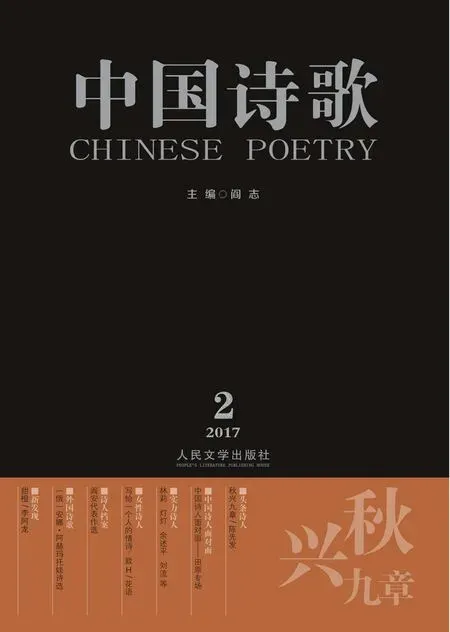獨立而沉默的鄉土
——蘇金傘新詩導讀
□潘丹丹
獨立而沉默的鄉土
——蘇金傘新詩導讀
□潘丹丹
蘇金傘,從15歲時開始嘗試寫詩,這一活動陪伴了他后來的很多日子,以至他在九十歲高齡時,還完成了最后的詩作《四月詩稿》。他是二十世紀詩歌創作周期最長的中國詩人之一。蘇金傘的詩歌創作,和他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1920 年他考入開封第一師范學校,一方面接受新文學的啟蒙、嘗試新詩創作,一方面熱情地投入學生運動。1927 年在開封兩河中學任教時,因參加進步活動受到逮捕,度過了一年零兩個月的監獄生活。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以一系列詩歌作品呼喚農民拿起武器。在他這個時期的詩歌作品里,總是夾雜著抗日的愛國之心、對國民黨的仇恨之心和對共產黨的仰慕之心。國內惡劣的形勢讓他不得不利用自己踢足球的特長,先后在河南省多個中學和大學任體育教師。1940 年代的他生活顛沛流離,詩歌創作卻獲得了收獲。1947 年和 1948 年,他接連出版了詩集《地層下》和《窗外》。新中國成立后,在擔任河南省文聯主席的同時,仍然堅持寫詩。1951 年出版詩集 《入伍》,1957 年出版詩集 《鵓鴣鳥》。然而不幸的是,1957 他被定為“胡風分子”,劃為右派,下放到農村鍛煉。“文革”期間又遭到長期的批斗,最后到“五七”干校接受勞動改造,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平反。復出后的蘇金傘,繼續熱衷于詩歌創作,于 1983 年出版詩集 《蘇金傘詩選》,1993 年出版 《蘇金傘新作選》。蘇金傘前期的詩歌和鄉土生活相關,主要表現上世紀農村生活的場景,進入晚年的詩歌創作仍描述生活瑣事,但語言更質樸,于平緩的語調中表達閱盡歲月滄桑后的簡單干凈。
蘇金傘詩歌的思想特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以自我的方式記錄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蘇金傘詩歌中對農村的描寫和他早期的生活密不可分,鄉土情懷雖然是無奈的選擇,也是他記憶中最溫暖的部分。他從小在豫東平原的農村生活,后又因各種原因不斷參與農村工作,土地上的一切他都那么熟悉,閉上眼睛它們便一一呈現在眼前:“馬蹄 走過,/帶著女人的啜泣聲 /和孩子的帽鈴聲”、“破音的嗩吶,/嗚嗚啦啦地吹過來” (《窗外》),他看到了漫天飄蕩的楊葉,“有一張楊葉 /落在陽臺上曬衣少婦的胸前” (《一張楊葉》),他還看到一個農民“熱饃掉在地上,/皮也不揭,/連泥吞下去” (《泥土》)。他抱怨那些泥濘的小路,“腳后頭還常常跟著落葉,/在泥濘小巷里,/老是粘掉我的鞋”,他又喜歡那些甜蜜的小路,“在楊家湖南岸,/我們曾一路走著一路接吻” (《尋找》),還有那些通往農民田地里的小路,“哪一條土路上,/沒長著蒲公英?/當天空響起一串一串春雷,/蒲公英在蝸牛身邊,/生出小小的蓓蕾” (《蒲公英》)。在他眼中,春天的田野里,“在冰雪的枝頭,/偶然發現了剛露出的胎芽” (《胎芽》),夏天的田野里,“我擔著稻草擔子,/跟別的年輕人 /一同往稻場里跑” (《稻草擔子》),秋天來了,年輕的媽媽帶著孩子在田野里摘棉花,“孩子爬在地下啃泥土,/聲音已經哭啞了,/媽媽毫不關心地在摘棉花”(《摘棉花》)。而冬天的田地里,“蓋上一層厚厚的白雪,/雪化了又結成冰” (《蒲公英》)。天上剛剛還有太陽,“午陽 /明暖地照在窗紙上。/有一個人 /靠在窗外曬暖”(《窗外》),轉眼間,“從天空飄來一片黑云,/突然響起了雷聲,/使人們猝不及防,/從窗口又涌進閃電” (《雷聲》),他剛剛想笑,卻發現原來剛才自己睡著了,在平原上的人腦子里卻做了一個大海的夢,他變成了大海的一部分,“沉淀在海的夢里,/海也沉淀著我的夢,/迷糊了我的前生和來生” (《大海的夢》)。在農村生活過的人,泥土是與他們相依為命的親人,他們信賴泥土,依賴泥土給他們提供的生活所需。不過,蘇金傘描寫泥土、農村和農民的筆調是凝重和深沉的,詩人在記錄平淡的生活中透露著自己不甘心卻又無可奈何的蒼涼感,讓我們似乎重新經歷了那段歷史,見證了那個風雨漂泊的時代。在《泥土》一詩中,詩人運用對比的手法寫出了農民生活的艱辛,表面上寫的是泥土,泥土上生活的人們,實際上又是對某個特定時期政治經濟的記錄。農民執著地信賴泥土,粘在饃饃上的泥土可以吃下去,墻上的泥土可以治療腿上的磕傷,帶有腳印的泥土可以治療小孩子的發燒。然而,對泥土懷有濃烈感情的人們,“等到餓得倒斃時/卻找不到一塊隙地 /讓他們埋葬尸身” (《泥土》)。 《窗外》 也同樣是如此,透過小小的一扇窗戶密切關注外面喧囂的世界,從早上到中午又到夜里,窗外的各種聲音,各色人等的身影。相比之下,屋內則是受到監視的“我”,“我”對外面的世界無能為力,“我要發出聲音 /助助威。/但我剛開開門 /就已掉進陷坑里了” (《窗外》)。不過,詩人在沉重和失望之外,并沒有忘記對明天的期待,因為舊的歲月遲早會被拋掉,留下的是讓人信賴的、永恒的“太陽”、“春天”和“時間”,“太陽總是最可信賴的”,“春天總是最可信賴的”,“時間總是最可信賴的” (《信賴》)。在詩人的筆下,農村生活的人,土地里生長的莊稼,自然界的雷雨、陽光等都傾注了詩人濃厚的情感,通過這些記錄生活痕跡的文字,我們讀出了詩人生活的時代特征,詩人對家鄉民眾生活境況的擔憂,詩人的不甘心和文字之外的抗爭,以及詩人對未來生活的向往。
第二,以一顆童心挖掘生活中的激情和時代生活的光明。七十歲之后的蘇金傘,仍然止不住對詩歌創作的熱情,創作了更多被人稱頌的詩作。其后期作品在沿襲早年樸實語言的基礎上,更加注重詩歌藝術技巧上的提升。他說,“詩人必須樸素醇厚,富有泥土氣息,但不純用鄉土形式”①。他沒有因為生活的艱難而一蹶不振,相反像 《兒童節》、《早晨和孩子》、《雷聲》、《胎芽》、《蒲公英》等詩歌中帶有新時代的氣息,閃爍著一顆孩童般的不老的心。以《兒童節》為例,已經到了晚年的詩人,仍然眷戀著孩子們的兒童節,雖然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他仍勉勵自己保持童年的笑容,“臉上現出無邪的癡笑 /這種溫馨可能保持到老年” (《兒童節》)。同樣,在 《早晨和孩子》 中,詩人將早晨升起的太陽比喻成茁壯成長的孩子,同時又勉勵孩子和太陽一起共同成長,“跟太陽一塊滾,/跟太陽一塊長,/太陽馬上就要高過胸脯了,/就抓住它跟它一同起程” (《早晨和孩子》)。盡管詩人身體已經衰老,但他的心卻越來越年輕,因此,越到老年,他詩歌中的生命力越是旺盛,自然界中生命的成長給了他無限的靈感。聽,“雷聲排除一切距離,/沖破一切禁區,/大氣層里充滿了呼喚,/在人心上降落一陣春雨”(《雷聲》)。詩人寫雷聲,與其說春雷的聲音刺激了詩人的聽覺,不如說是雷聲喚醒了詩人的視覺,詩人于雷聲中不僅觀察壯觀的“黃河”,貼著春聯的“窯洞人家”,他還觀察到“葫蘆的觸須”,“第一窩乳燕”。詩人寫雷聲其實是寫雷聲給自然界帶來的變化,或者說詩人在雷聲中對自然界變化的想象,雷聲由此在詩中得到生動而豐富的展現。事實上,生命的成長在自然界中隨處可見,詩人只是以獨到的眼光將他們以詩歌的形式保存下來。如初春的胎芽,“這是春天的第一個聲音,/是生命的第一次撞擊,/就像嬰兒的第一顆乳牙,/就像戳破紙窗 /企圖向外探視的小拇指”,“喜歡聽綠色的滋長,/就像聽潺潺的微雨 /最初在耳邊爬,/接著爬進了心窩” (《胎芽》)。如那盆野菊花,“每天都有新蕾開放”,“每一朵花——和你的詩一樣” (《一盆野菊花》)。自然界中萬物的成長觸發了他心底深處的初戀情懷,是那么溫馨,那么的甜蜜,“這不是枯草又發了芽/這是我們埋在地下的愛情 /生了根” (《埋葬了的愛情》)。是的,時光不能倒回,他不能再次參與童年的成長,但他可以繼續探索未知的世界,因為遠方、陌生和下一個春天在前方等待著他。他目光隨著大雁的身影移動,“大雁的呼喚所組成的征程,/卻總是向著遠方,/向著陌生” (《在大雁翅膀下》),他期盼“跟又一個春天相遇” (《一盆野菊花》)。
在藝術上,其詩也形成了兩個方面的重要特點:
第一,意象突出,引人入勝。蘇金傘的許多詩作中的意象來自于自然,如太陽、泥土、早晨、雷聲、大海等。詩人觀察自然并將風景的變化保存下來,他關注的既是一道可以欣賞的自然風景,又包含了自己獨特的心靈表達。詩人在風景的變化中看到了歷史的滄桑,在自然的交替中看到了社會的變化和發展規律。天上的太陽原本普通,可是因為它往復循環,世界萬物尤其是人類因為它的重要性開始感激并信賴它,“太陽總是最可信賴的。/它準確無誤地給我們送來 /一個又一個滾燙的日子,/一個又一個星光燦爛的夜,/一個又一個春天” (《信賴》)。日出日落是永恒的象征,永恒則預示了“滾燙的日子”、“星光燦爛的夜”和“又一個春天”的循環和持久。然而同樣是太陽,詩人對它又充滿憤恨,“誰叫你帶來與黑夜不分 /而又同樣可怖的白天哪” (《控訴太陽——哀聞一多先生》)。作者以太陽來寄托感情,“我”信賴太陽,“我”又仇恨太陽,太陽像詩中的“我”一樣,充滿了感情色彩,由此,太陽在閱讀者心中就變得富有詩意,給他們留下難以忘懷的意味。春雷和雷聲也是如此,他不止一次地寫過春雷,雷聲給他聽覺上帶來震撼,似乎也賦予了他預知的能力,“雷聲排除一切距離,/沖破一切禁區”(《雷聲》),“當雷第一聲鳴響時”,“所有一切枯萎的生命 /也都為這生長的啟示所鼓舞 /而抬起頭來” (《雷》)。在詩人眼中,任何一處風景不僅僅是風景,風景中的物象是詩人的語言工具,是引起閱讀者共鳴的工具。詩中的意象因詩人強大的想象力變得富有感情,詩歌的內容對閱讀者來說也變得富有感染力。
第二,境界闊大,在樸實的語言中,表現了開闊的視野與胸懷。蘇金傘早年倡導白話的詩歌語言。早在開封第一師范上學期間,他就受到國文老師嵇文甫的影響,嵇文甫曾經大力夸贊他自由的詩歌形式。②他和“七月派”詩人有過接觸,在河南大學任教期間,曾作為《中國時報》的兼職編輯,發表了胡風、牛漢、魯黎、彭燕郊、阿垅等詩人的詩歌,③他還和艾青、臧克家關系親密。從一些詩作的題目中,如 《頭發》、 《獨輪車》、 《稻草擔子》、 《摘棉花》、 《蘆花和棉絮》、 《貨郎挑》、 《跟媽媽說》、 《破草帽》、《鵓鴣鳥》、《老牛回家》、《蒲公英》等,可以看出其詩作的主題與思想之現實性與生活化。然而,在詩人樸實的語言中埋藏著他對和平和真理的渴望。“蒲公英根植在農民的心上,/爛入農民的記憶,/又在農民的墳地上生生不息” (《蒲公英》),土地上生長的蒲公英,不懼怕沉重的牛蹄和馬蹄,不在乎冬天厚厚的白雪,在蝸牛身邊長出小小的蓓蕾,在叢林中開出耀眼的黃花。蒲公英的品格不正是中國世世代代農民堅韌品格的寫照嗎?詩人從眼前的一棵蒲公英看到蒲公英的一生,從一朵小花看到下一代的成長,從蒲公英的根看到了人類的墳地,從生生不息的蒲公英看到世世代代生長在土地上的農民,詩人的觀察力不停滯在表面,不悲傷于眼前,于細微中見長久,于現象中見本質,詩歌宏大的意境將詩人豁達的胸懷表露無遺。
蘇金傘的土地情結是他早期和后期詩歌的主要內容,不論他生活在多苦多難的舊中國,還是生活在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他一如既往地以生活中的常見物象為感情寄托,以開闊的胸懷書寫時代的特征,因此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創作風格。詩人將農村、農民、土地納入詩歌的體裁和范圍,體現了詩人對現實的感知以及對于當下生活的憂慮,對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考,詩人在思考的過程中認識到了歷史的厚重感和規律感,這也正是他在詩歌中懷揣童心,挖掘美好明天的重要原因之一。余光中認為“蘇金傘是早期詩人中雖無盛名卻有實力的一位”, 《頭發》 雖然短小,“撼人的強烈卻不輸魯迅的小說”。臧克家認為蘇金傘的詩歌“樸素”、“味道卻極醇”,“情感是頗為濃烈的”。周良沛說臺灣許多詩人,至今很珍貴地保存著年輕時蘇金傘詩歌的手抄本。④寫于 1934 年的《出獄》,是他第一首正式發表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他從國民黨監獄里出來的情形。一年后,另一首代表作 《雪夜》 發表在戴望舒主編的 《新詩》 上,后被聞一多先生選入《現代詩抄》。寫于 1946 年的詩作 《頭發》,多次被刊物轉載或收錄,1995 年被臺灣九歌出版社收錄在 《新詩三百首 (1917—1995)》 中。他的第一本詩集 《地層下》 收入臧克家主編的“創造詩叢”,詩集 《窗外》 收入巴金主編的“文季叢書”。更難能可貴的是進入晚年他仍然堅持寫詩,筆調清新,感情自然,將詩歌藝術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蘇金傘一生獻身于詩歌,然而生活經歷坎坷,與外界交流甚少,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他在中國詩歌領域里的影響力,導致他相對沉默的詩人地位。上個世紀的很多詩人,囿于當時經濟和政治的因素,有意無意地以農民題材和農村活動為詩歌的創作主題,他們對農村現象和農民生活的記錄,成為現代城市人了解上個世紀農村發展和變化的珍貴材料,成為我們回憶上一代父母生活情境的真實參照。讓我們懷念的不僅僅是和農民農村有關的一切現實,更讓我們懷念的是,這片養育了父輩們的土地,繼續以博大的胸懷養育著我們下一輩以及更多的后輩們,讓我們生生不息,代代長久。蘇金傘的詩歌秉承現代鄉土作家的風格,著重表現讓他刻骨銘心的農村泥土,用波瀾不驚的語言表達自己開闊的胸懷和獨立的時代思考,書寫和記錄著這片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生長著的農民的希望,記錄著詩人永不磨滅的向往美好的一顆童心。
① 苗得雨,中國百家鄉土詩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5
② 周良沛,中國新詩庫 (七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499
③劉增杰,新發現的一批七月派史料——《中國時報》文學副刊一瞥,平頂山學院學報,2010 (1) :62-66
④ 李鐵城、蘇 編,蘇金傘詩文集,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13
中國詩人面對面

中國詩人面對面——田原專場
據我了解,日本的現代詩歌更加關注的是現代性、個人性以及在現代化都市社會的焦慮、孤獨等等,但是我認為中國的現代詩歌的活力是要遠遠大于日本的。
——田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