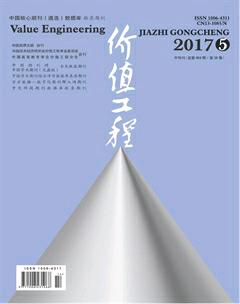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國際經驗比較
石娟



摘要: 針對我國目前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新階段,為了探索我國未來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道路,本文采用文獻研究法,結合美日德各國基本國情,研究各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路線,得出各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政策隨各國國情不同而呈現差異性,通過分析、總結差異性,提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意見,即在的縱向深度和橫向廣度上加快新能源汽車發展。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w stage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article appli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combines with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Japan to research their development route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y and then explores the way of ours. Based on it, a conclusion is propos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policy route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y along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ut forward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depth of lengthwise and the width of crossing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s development.
關鍵詞: 新能源汽車;政策路線;美日德;差異性
Key words: the new energy vehicle;policy route;the United States,Germany,Japan;difference
中圖分類號:T-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14-0238-05
0 引言
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是我國應對能源危機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同時,技術創新和新能源種類繁多為新能源汽車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1]。一些發達國家對新能源汽車研發和市場推廣較早,具有一定的經濟、政策基礎。新能源汽車是亟待開發的藍海,目前我國形成了自上而下式的戰略定位——項目制定——項目實施——市場推廣的模式,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也預示著我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新階段的到來。應對新能源汽車發展新階段,我國政策出路在哪?目前,我國學者對不同國家新能源汽車政策的研究純熟,但是研究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忽略了政策與本國基本情況之間的聯系,所以本文從我國國情著手提出改進意見;此外,本文有關新能源汽車市場銷售量、投資額的最新數據為政策意見提供有力支持。
1 國際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
1.1 美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
美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歷程概述。美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歷程隨著美國歷任總統更替呈現出階段性特征,如表1[2]。政策特點可以總結為:前期單一地靠政府政策拉動,基于能源安全制定國家能源政策和規定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聯合本國三大汽車龍頭企業制定目標,通過投入大量資金,引導企業加入到新能源汽車研究、生產上來,以達到關于能源利用效率和生產成本上的要求;中期隨著規模擴大,相關政策、稅收、法案相繼提出,激勵企業和個人,激活新能源汽車市場;后期注重新能源汽車配套產業與刺激消費者購買的補貼政策,為規模化奠定基礎。
美國基本國情下新能源汽車政策體系:
①能源安全對政策的基礎作用。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使美國政府提出在1980實現能源獨立自給的目標,在1975年首次對汽車的燃料效能提出要求,加大其他新能源的開發[3]。由此能源安全是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初始考量,并貫穿整個過程;此外,降低汽車尾氣排放,緩解環境壓力對新能源汽車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如學者張政、趙飛提出,中美兩國發展新能源汽車戰略存在發展目標導向不同,即美國以改善環境為導向,我國偏向以實現“彎道超車”為導向[4]。
②法律法規對政策的保障作用。美國是典型法制國家,法律法規對新能源汽車發展起著重要的保障、規范作用。1975年起,美國制定了系列能源政策法案、能源投資法案、能源效率法案、消費者保護法案和標準等,除此之外,其他各州制定本州的能源法案、能源效率法案和汽車尾氣排放標準等[3];奧巴馬政府之后配套產業的發展路線、政策補貼和免稅政策等相繼提出。
③資金對政策的支撐作用。美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緊緊依賴于政府和汽車龍頭企業資金支持。克林頓政府時期投入15億美元用于新能源汽車研究開發,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賴斯勒1999年投入的項目開發資金達9.8億美元;布什政府時期僅在2004年到2008年計劃將對氫燃料電池汽車的研究經費投入高達12億元,在《2007能源促進和投資法案》中,美國將由石油企業征收的290億美元支持新能源企業;2009年制定EV Project,政府出資10億美元通過以舊換新的補貼政策推進新能源汽車市場,截止2013年底,全國充電裝置達10096套;DOE計劃2015年政府將投入4億元支持基礎設施建設[2]。
1.2 日本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
日本對新能源汽車的認識早于世界第一次能源危機,1965年就開啟了電動汽車研發計劃,并歸入國家發展項目中,1967年成立日本第一個電動汽車協會,1971年制定《電動汽車開發計劃》,確立了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地位,斥資加快新能源汽車發展[5]。雖然日本對新能源汽車研發很早,但是由于早期技術、資金、新能源發展水平限制,取得的成效卻不明顯。日本與美國財大氣粗式發展不同,日本更注重政策的高效性,充分調動一切資源。
①財政支持及其成效。以宏觀的能源和環境政策為依托,日本在新能源汽車發展上有著完善、全面、高效的產業鏈政策體系,涵蓋技術研發、補貼政策、稅收政策、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推廣等。日本2003年預算投入3.5億日元,開展燃料電池汽車市場推廣,并根據2005燃料汽車普及情況,首次制定了世界氫氣燃料電池汽車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標準,同年預算投入2.15億日元用于推進燃料電池巴士的應用,并于2006年確定了其所需的技術標準。在新能源汽車技術跨國申請專利方面,混合動力汽車1990年到2011年累計738個[6],混合動力汽車躍居世界領先地位。金永花曾在文章中指出,不同油價對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影響不同,當油價每桶60美元、150美元、300美元時,到2020年日本新能源汽車的市場份額將分別占12%、28%、45%[7]。2009年日本實施《下一代汽車普及戰略》以來,汽車的結構分布有明顯變化,在2015年日本汽車銷售比例中,常規汽車和新一代汽車占百分比分別為:73.50%、26.50%,而HEV車型占新一代汽車的83.77%。日本近年來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PHEV)、電動汽車(BEV)的累計銷量如圖1[8]。
②成效分析。與美國不同,在新能源汽車重點發展的定位上,日本并沒有較大的出入,而混合電動汽車取得位居世界前茅的成就與之密切相關;此外日本還積極開拓氫燃料、生物燃料電池、鋰電池等,在以混合動力汽車發展為契機,成功實現了傳統汽車向零排放、低成本汽車的過度轉型。日本在補貼政策和稅收政策方面呈現出涉及范圍廣、分類條目細的特點,因此提高了政策實施的有效性,使接受到扶持的企業、單位、個人受到很好的監督,也為相關企業、單位提供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如日本在導入低公害汽車的支援制度中,詳細列述補助制度、各類車型、補助對象、補助率和涉及部門等。日本取得顯著成效與傳統汽車競爭地位是離不開的,據數據統計,日本豐田獲得2015年世界汽車銷量排行榜第一名,有明顯的市場份額優勢,我國與其存在較大差距,但國2015年新能源汽車33萬輛銷量,為我國實現新能源汽車“彎道超車”提供無限可能。
1.3 德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研究
德國是燃料汽車的鼻祖,也是傳統汽車強國。德國發展新能源汽車與美國、日本既存在宏觀上的相似性,又存在著微觀上差異性。
①宏觀相似性。德國、日本、美國都以能源安全和本國汽車競爭地位來定位新能源汽車。能源短缺、環境污染嚴重,一場以能源為信號的變革正在展開,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各國已達成共識。在新能源開發方面,美日德居世界領先地位,在研發上都集中在核能、太陽能、生物質能氫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并各具本國特色。在新能源汽車優先發展戰略定位上,德國與美國相似,也經歷過新能源汽車車型重點發展戰略的轉變,美國經歷過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電動汽車的戰略定位的轉變,德國前期重點發展清潔燃料汽車和燃料汽車,后來受到中日美等國家對電動汽車研發熱情影響,2009年歐盟正式擬定電動汽車發展路線[9]。在電動汽車的研究上,德國相較于日美兩國起步較晚。美日德在新能源汽車宏觀政策上相似,主要表現在:技術研發都采用政府、企業、科研機構協同推進;都確定了本國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車型,同時又積極展開其他新能源汽車車型;高度重視配套設施的建設;市場推廣上都采用示范運行再推廣的技術路線等。
②微觀差異性。各個國家在發展新能源汽車的宏觀政策上差異不大,但是在具體實施上存在較大差別,對于我國而言這些微觀上的差異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德國與日本都是發達國家,相較于日本德國在人口、可用資源上占優勢;其次,在地理位置上德國南臨非洲,西鄰亞洲,相比遠在亞洲鄰角上的日本有更廣闊、便捷的市場。基于這些劣勢,使得日本居安思危,在能源問題、國際市場競爭上比德國更加急切,比如日本早在1965就有了電動汽車的構想,“官民一體”的構想等都是充分利用國家資源的一種體現,反觀德國在2009年才出臺電動汽車發展綱領性文件——《德國聯邦政府國家電動汽車發展計劃》,2010年5月成立電動汽車國家平臺,并于2011年5月該平臺發布電動汽車未來發展三個階段:2011-2014年重點研發、示范的準備階段,2015-2017年配套設施的市場推廣階段,2018-2020年電動汽車規模化階段[10]。另外,德國在新能源研究上的成效顯著,技術成熟,新能源應用普及化程度級高,據IEA統計數據表明:德國現在已經經過高能耗的工業發展,進入低能耗后工業發展階段,1980年以后CO2排放量逐年遞減[11]。德國氫能源和生物能源發展較好,所以新能源汽車重點發展清潔燃料汽車和燃料汽車,后來拓展到電動汽車;而日本國內資源稀少,加上2011年發生核電站泄漏事件,導致日本國內能源供應更加緊張,尤其是電力供應,如果繼續發展純電動汽車,顯然不具優勢而不得不做出戰略調整。另外,在政府投資上德國與美日兩國明顯不同。2016年德國聯邦政府和德國汽車工業界就購置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達成共識:各方按照1:1均攤12億歐元補貼金額[8]。同時,德國政府投資偏重于技術研發和新能源汽車發展的能源系統、網絡布局。比如德國政府年原計劃于2013年投入10億歐元用于電動汽車研發,2011計劃將其提高至20億歐元,目的是要提高能量儲存技術、車輛驅動技術,并且保障材料可獲得性、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供應體系完善[9]。
2 我國新能源汽車發展政策建議
經過以上對美日德三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政策研究發現我國發展優劣勢并存:起步晚,在關鍵零部件、品牌價值、市場份額、產品質量、標準制定、制造企業核心競爭力與其他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但是我國科研技術水平取得跨越式進步,新能源汽車市場大,增速快。鄧立治、劉建峰通過梳理美日近15年頒布的關于新能源汽車扶持政策,在激勵、保障、限制政策角度分析得出:美國扶持政策模式屬于市場帶動型,突出對市場因素的扶持;日本扶持政策模式屬于技術領先型,突出對技術因素扶持;德國扶持政策模式屬于創新主導型,突出對創新活動的扶持[12]。在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新階段,我國新能源汽車升級的出路在哪?扶持政策又該如何定位?
2.1 提高我國硬實力與軟實力
經濟全球化趨勢下,未來新能源汽車市場是廣闊的國際市場,我國政府在努力搭建更好的新能源汽車發展平臺的同時,也應該持續打造“中國制造”品牌,因為“中國制造”是具有持久競爭力的品牌,蘊含巨大經濟效益,尤其是作為剛興起的新能源汽車。比如增加新能源汽車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保護我國新能源汽車專利技術;通過出售中高端產品和領先技術進行多邊合作,對外滲透“中國元素”,提高我國在其他國家的地位和認可度等。美國約瑟夫·奈指出:國家軟實力來源于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三個方面,而我國的軟實力必將會與我國的硬實力的增長并駕齊驅[13]。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胡錦濤書記將文化定位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14]。所以提高軟實力關乎到我國長遠競爭能力問題。
2.2 加強新能源汽車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地位
相比與國際社會競爭,在國內確立新能源汽車競爭地位更具有優勢。圖2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體系構成,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政策與其他國家無異,但是在組織結構、網絡化布局和系統協調上存在差異與不足。
①組織結構的差異與不足。我國新能源汽車的主導單位是“四部委”,包括財政、科技、工信和發改委,由于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特色,應增加能源局,一方面監控汽車能效,另一方面可以結合新能源汽車發展情況監控我國新能源系統,優化新能源結構;還應增設環保部、交通局等。此外,應加強政府職能轉換。政府與企業脫節導致信息不對稱,影響決策水平;政府職能過重加大了政府工作量,同時容易導致地方政府忽視發展新能源汽車的真正意義,過分追求政績。最后,確立企業地位,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我國新能源汽車前期發展偏重政策拉動,而忽視了市場作用。新能源汽車產業作為新興產業,涉及標準、法律法規、投資、交通系統、城市規劃、能源結構、環境等各個方面,所以扁平式的組織結構更適合新能源汽車發展。
②網絡化布局和系統協調的差異與不足。新能源汽車發展網絡涵蓋:生產技術、原材料、產品制造、市場、政策、標準、電池回收、汽車維修以及各相關組織、個人。明晰的網絡布局有助于整體系統的協調發展,如美國以法律法規為輻射源對新能源汽車的網絡規劃,如德國以新能源為輻射源對新能源汽車的網絡規劃,再如日本以資源配置為輻射源對新能源汽車的網絡規劃。全面、富有彈性的網絡布局是系統協調的前提;反過來,系統協調發展強化完善、強化網絡結構。我國應加入新能源和法律法規對新能源汽車的網絡布局,加強系統中各要素協調性,避免新能源汽車配套基礎設施落后于新能源汽車市場發展速度,阻礙產業發展;避免只注重前端后忽略電池回收、汽車維修等后端服務,巨大的新能源汽車市場預示著巨大的電池回收、二次利用的商機;避免不同城市因新能源汽車推廣程度不同所帶來的壁壘,加強“城-城”之間的新能源汽車以及配套基礎設施的布局;避免產業粗放式發展導致核心技術不強,產品性能低,競爭能力弱。
③全面推進小康社會的促進作用。雖然我國GDP值很高,但是存在嚴重貧富差距,我國大多數人是處于生理需要層面,所以要進一步擴大新能源汽車市場,就要持續推進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提高國民收入水平;關于我國與美國新能源汽車推廣存在目標導向差別,從兩國的經濟實力和實際國情來看,我國以經濟效益為導向也更合乎情理,而且新能源汽車取得經濟效益也意味著環境保護的成功,二者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所以,一方面要提高國民經濟水平、消費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強國民環境保護意識,增大新能源汽車知名度,吸引更多潛在客戶購買新能源汽車。
2.3 充分發揮我國新能源汽車鏈企業帶頭作用
在我國新能源汽車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一些互聯網企業紛紛加入,與新能源汽車制造企業合作,并帶起了一股投資熱潮,其中鋁塑膜、充電樁、和電動物流車等概念股已開啟加速模式[15]。這說明,我國政府在新能源汽車推動上的政策已經起了成效,一組數據也說明了這一點:預測“十二五”期間新能源汽車直接投資規模已達1027.84億元,“十三五”期間新能源汽車銷量和直接投資規模見圖3。
從圖3我們可以看出:樂觀情況和中觀情況下,投資規模和汽車銷量均存在較大差距,并且相同情況下的投資規模和汽車銷量呈現相同的變化趨勢,即樂觀情況下,投資規模曲線和汽車銷售量曲線陡峭,中觀情況下,曲線則較平緩。新能源汽車市場情況與其投資規模相互影響。我們期待樂觀情況下的結果時,也必須承認中觀情況的存在,但是,只有實現新能源汽車樂觀情況才會使各方受益最大化,企業各方的努力應以實現樂觀情況展開。實現樂觀情況生產企業應具備以下必要條件:
①經濟支持。經濟支持是發展新能源汽車的重要基礎,雖然我國政府沒有要求企業必須與政府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擔其相關費用,但是我國很多企業已經自覺的投入到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中來,新能源汽車興盛離不開那些具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們,所以要取得勝利,必須舍得為新能源汽車發展“花錢”。摒棄只顧眼前利益,忽略長遠利益的想法,企業應做長遠利益的思想準備和行動準備,既要避免過多激勵導致資金浪費和分配不合理,也要避免由于盈利模式模糊導致投入研究、配套設施費用不足。
②技術突破。技術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關鍵所在,技術突破要進一步增強在電池的續航能力、穩定性、安全性,還有其他新材料電池的研發,廢舊電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突破等;完善的電動汽車充電系統,實現快充和慢充及其他無線傳能等形式的充電技術突破;關鍵零部件技術突破,實現逐步減少對國外技術依賴,推進中低端產品向中高端邁進,提高整車的盈利價值。
③不斷創新商業模式。商業模式是一種把技術可能性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啟發性邏輯[16]。新興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需要不斷創新商業模式來提供其發展的動力,同時,產業的發展也推動不同形式的商業模式創新[17]。目前主要的商業模式有三種,包括整車銷售+自充電模式、整車租賃+自充電模式、裸車銷售+電池租賃+充換兼容模式,其中第三中商業模式是前兩種商業模式的創新,具有銷售價格低,并且也消除了顧客對電池質量、壽命等方面的顧慮的優點。目前,電動汽車的電池技術面臨瓶頸,希望通過模式運作規避技術瓶頸,可以繼續開拓市場。而電池方面比如續航能力、充電等的模式突破是最為關鍵的突破,未來商業模式也應繼續圍繞其展開創新。
④良好的企業品質。一方面企業要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質,即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的企業,要承擔國家和社會責任,嚴格遵守國家規定進行新能源汽車的生產,保證汽車質量和安全性,保持新能源汽車市場“清潔”,樹立國民對新能源汽車的信心;另一方面有能力的企業要起帶頭作用,以發展成國際領先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為發展目標,逐步確立主導地位,為企業自身發展和國家“彎道超車”厚積。
⑤營銷創新。婁卓、劉軍等通過“態度—行為”模型論證了行為傾向對企業聲譽起重要作用[18]。新能源汽車生產商和銷售商在保證產品質量、安全性能同時,要以廣泛宣傳為突破點增強顧客對新能源汽車的信賴:一方面,生產企業要制定戰略計劃,有效運用網絡平臺和消費者之間行為傳播作用,致力形成新能源汽車品牌企業,品牌汽車,打造品牌效應;另一方面,銷售端要充分利用行為傳播對銷售的作用,制定戰術,注重打造客戶對新能源汽車的高端體驗感受,突出產品在動力方面的創新,提高客戶對新能源汽車探討度,打造以行為傳播為基礎的傳播網絡。
參考文獻:
[1]邢洪金,汪波.新能源汽車競爭戰略與策略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0(7):59-63.
[2]陳小復.從PNGV到FreedomCAR——看美國的新一代汽車開發項目[J].上海汽車,2002(07):40.
[3]徐小杰.美國能源獨立趨勢的全球影響[J].國際經濟評論, 2013,2:34-59.
[4]張政,趙飛.中美新能源汽車發展戰略比較研究——基于目標導向的研究視角[J].科學學研究,2014,32(4):531-535.
[5]張鐘允,李春利.日本新能源汽車的相關政策與未來發展路徑選擇[J].現代日本經濟,2015(05):71-86.
[6]龐德涼,劉兆國.基于專利分析的日本新能源汽車技術發展趨勢研究[J].情報雜志,2014,33(5):60-65.
[7]金永花.日本新能源汽車市場推廣策略對我國的借鑒[J]. 東北亞論壇,2012(03):105-112.
[8]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 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報告(2016)[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358.
[9]陳翌,孔德洋.德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政策及其啟示[J].德國研究,2014,29(1):71-81.
[10]李立理,王乾坤,張運洲.德國電動汽車發展動態分析[J]. 能源技術經濟,2012(01):47-52.
[11]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2011 Edition)[M]. Paris; IEA Publication, 2011.
[12]鄧立治,劉建鋒.美日新能源汽車產業扶持政策比較及啟示[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4(06):77-82.
[13]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J].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2009.
[14]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15]周永祥.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全面開啟“瘋狗”浪[J].股市動態分析,2016,23:26.
[16]Zott, Christoph. The Business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M]. Forthcom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17]陳志.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的商業模式創新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12(01):112-116.
[18]劉彧彧,婁卓,劉軍,宋繼文.企業聲譽的影響因素及其對消費者口碑傳播行為的作用[J].管理學報,2009(03):348-353,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