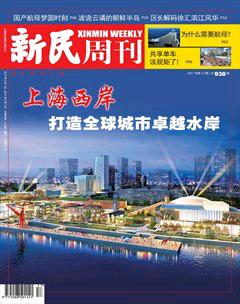自行車王國的顛覆時刻
何映宇
曾經的自行車王國,我們印象中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一個磨之不去的印象就是騎著自行車的上班一族,鈴聲響起一片,人潮如海浪洶涌,那是中國人最重要、最普及的代步工具。
賈樟柯的《站臺》海報上,三個人騎著一輛單車,王宏偉飾演的崔明亮倒坐在后座上,眼神中有那個時代的迷惘,和張靜初在《孔雀》中的意氣風發恰成對照。
2000年,王小帥拍攝了《十七歲的單車》,像是一個時代的挽歌,又像是對意大利導演德·西卡的名片《偷自行車的人》的隔世回響。影片結束時,男生小貴扛著被砸壞的自行車悲傷地走過喧鬧的街頭,震撼了所有的觀眾,這是電影悲壯的結尾,但更像是自行車在中國悲壯的謝幕。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自行車行業通過混改、經營模式轉變,大多從國企制改為民營企業,市場處于充分競爭狀態。捷安特等臺資企業占據中高端市場后,鳳凰、永久、飛鴿等組裝廠在中低端領域的價格競爭十分慘烈。
1989年,中國自行車產量達到峰值,第二年,樂極生悲,“雪崩”不期而至,1990年下滑到3141萬輛,比上一年減少1/4。從1990年開始,中國自行車產量逐年下降,國內傳統車型市場從此一蹶不振,自行車逐步被汽車、電動車等便捷的交通工具所取代。就是天津飛鴿這樣的行業領頭羊,近年的日子也不好過。
而共享單車的出現,讓國產中低端自行車制造業從行業低谷陡然迎來共享單車的千萬級大單,從艱難“去產能”到糾結是否“擴產線”。
目前一窩蜂的共享單車對于中國自行車行業而言意味著什么?自行車王國正在復興嗎?當下的中國,是否真的需要這么多的自行車嗎?
起死回生:忽如一夜春風來
忽如一夜春風來,整個自行車行業都懵圈。
遍布大街小巷的共享單車為市民出行提供了方便,也給生產企業帶來新活力。疲軟的自行車市場,被共享單車這把火瞬間激活,中國自行車的產業鏈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
共享單車之所以會風行一時,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己的車會丟,而現在,共享單車解決了這個難題,自然讓騎行者趨之若鶩。
2017年1月13日,李克強總理在聽取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的座談會上說,“摩拜單車聽上去是經營方式的革命,但基礎還是自行車,還是要靠實體經濟支撐。反過來,實體經濟也要靠服務變革來帶動。”
繼去年9月獲得超1億美元的C輪融資,10月獲得C+輪之后,今年1月,摩拜獲得了2.15億美元的D輪融資。僅僅幾天之后,摩拜又宣布獲得富士康公司的戰略投資,富士康將開辟摩拜單車生產線。富士康計劃在位于國內及海外的多家工廠分別開設摩拜單車生產線,通過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技術能夠協助摩拜單車進一步優化車輛投放流程、加快投放速度,降低新車跨地區運輸投放成本,還能夠盡可能縮短城市運營團隊的響應時間,提升加車效率,滿足快速增長的用戶需求。
3月1日,共享單車企業ofo宣布完成4.5億美元的D輪融資。據不完全統計,共享單車領域已經有30多家投資機構的數十億元資金投入其中,資本的涌入也激活了傳統自行車企業的生產線。
傳統老牌自行車廠家飛鴿、永久、鳳凰、喜德盛、凱路仕等企業先后殺入共享單車,飛鴿、鳳凰與ofo達成合作,永久攜手優拜。摩拜在無錫自建工廠,每天產量達1.4萬輛,與富士康合作后,預計年產量達到560萬輛,使得摩拜單車的總產能將超1000萬輛/年。老牌自行車企業天津飛鴿自行車有限公司,僅2017年2月一個月就給ofo供應了40萬輛共享單車。
天津是重要的自行車生產基地,天津愛瑪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天津靜海的自行車制造商,主營中高檔自行車、自行車運動相關各類體育運動器材、服裝、服飾等,該公司的年產能本為“300萬輛中高檔自行車”。但2017年與摩拜簽訂了500萬輛的代工合同。
天津富士達自行車生產基地濱海新區工廠每天有2萬余輛共享單車下線運往全國各地,訂單從3月的35萬輛劇增到4月的85萬余輛,增加了一倍多。為滿足訂單需求,企業各條生產線開足馬力生產。
天津市武清區王慶坨鎮的王慶坨自行車商會是中國北方最大的自行車生產基地,2015年,該鎮自行車總產量達到1200萬輛,出口260萬輛,占全國自行車年總產量的10%以上。2016年9月起,大量訂單涌入,從零部件生產到整車組裝,不一而足,共享單車這種快速興起的城市出行方式,讓自行車生產廠家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2017年,ofo給天津富士達自行車公司下了1000萬輛訂單,天津愛瑪自行車公司則獲得了摩拜的500萬輛訂單。過去1000輛車的生產訂單就是“大單”了。但現在,共享單車平臺給出的訂單“動不動就幾萬輛(件)”,簡直可以用“爆炸”來形容。在共享單車的及時雨到來之來,王慶坨的自行車廠其實倒閉了不少,而共享單車的興起立馬挽救了王慶坨已顯沒落的自行車生產行業。鎮上大大小小約六七百家自行車生產企業中,有20多家企業承接了共享單車零部件生產或整車組裝業務。
南方的盛夏,第二次瘋狂
原本平淡的自行車制造行業就這樣被突然引爆,這場火還從北方一路燒到了南方。
看看全國各大城市里洶涌的共享單車潮,原本以天津地區生產共享單車為主的產能,顯然已不能滿足共享單車在各城市的投放速度。多家共享單車紛紛提出投放百萬輛的年度計劃,其中ofo從1月12日到1月22日,更是以“一天一城”的速度在10天內進入11座城市。不僅如此,摩拜、優拜、小鳴、小藍等多家共享單車企業也均有著不同程度的自行車需求量,布局共享單車市場。
北方的廠家已不能滿足需求,于是,南方的廠家紛紛投入這場狂歡之中。
深圳市益缽通自行車配件有限公司從去年下半年共享單車火了之后,訂單翻了一番多,原本每個月只能接到40萬的訂單,如今每個月約有100萬。深圳市雷克斯自行車有限公司接到手的訂單是150萬輛。
深圳市泰豐永達自行車有限公司車間主任蘇志達說:“現在是最忙的時候了,比去年都忙,去年2016年都是很清閑的,過完年開年以后訂單猛然增長了,增長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的,每天要到八點半到九點左右。”他們增加了500名員工,流水線增加了7條流水線。去年他們還在為自行車市場的低迷犯愁,可是轉眼之間老母雞變鴨,毫無征兆中突然面對這個行業的“第二次瘋狂”。
深圳市麥可斯車業有限公司是深圳市一家以生產高檔山地車為主的傳統自行車廠家,經營著自主品牌自行車,在深圳的工廠只有一條生產線,在生產共享單車之前,每月產量只有5000輛左右。而現在,麥可斯的產量正以10倍的速度增長。
共享單車時代的來臨如此突然,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讓這些原本在行業寒冬中苦苦支撐的廠家聞到了盛夏的氣息。在這突如其來的熱火朝天中,有的廠家大喜過望,積極拓展生產線,以迎接大客單;有的則四處出擊,希望能搶得先機;而有的,則茫然不知所措,這就是單車火爆市場后的廠家眾生相。
似乎不需要有什么后顧之憂,經過一個多月的洽談,ofo和麥克斯達成了合作訂單。ofo小黃車給接單的深圳市麥可斯車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薛家明提的要求是: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生產速度越快越好,產量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有沒有上限?真的沒有上限?
在深圳市光明新區鐵塔工業園區的一間麥可斯生產線的流水線廠房里,20多道組裝工序,只要半個小時,一輛小黃車就閃亮登場了。
麥克斯感覺工廠的產能不足,于是開始在深圳擴建廠房,并在東莞以及佛山分廠增加生產線,一共開辟了12條生產線全部用于投產共享單車,預計產能每月由原來月產5000輛迅速增長到月產50萬輛,產能擴張100倍。
不僅生產自行車的廠家如此,連配件廠商也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去年他們還為市場銷售犯愁而今年的井噴行情卻不期而至,讓他們接單接得都手軟。
桂盟鏈條以前主要是生產高端汽車、摩托車、運動自行車鏈條的,現在因為共享單車的興起,自行車廠家對鏈條的需求一下子激增,所以公司也決定增加一條生產線,以應對這場風暴。
一向不怎么加班的深圳市益缽通自行車配件有限公司,現在每天晚上都燈火通明,加班加點生產自行車配件。摩拜一個月要30萬個自行車坐墊,ofo一個月要給50萬個!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似的,生意就這樣來了,讓人措手不及。
野蠻生長,居安思危
有訂單自然是好事,可是這場風刮得太突然太猛烈,讓所有人心里都不禁要打鼓。當年的滑板車給自行車行業帶來的行情只持續了一年,給后續投資擴建的廠商造成了損失。那么這場野蠻生長的風暴又能持續多久?一旦出現當年滑板車那樣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景象,會不會這次也一樣,不過是又一次的輪回?到時候整個產能一定會過剩,新招的工人又面臨沒活干要下崗的危機,怎么辦?
即使生意這么火爆,對于自行車生產廠家來說,寒冬依然沒有完全過去。共享單車的訂單雖然很大,但是利潤卻很微薄。普通自行車叉架的生產原料大多是鋼鐵,成本30-60元/輛,而共享單車叉架使用的是鋁材,在烤漆、強度測試等環節都要按更高的標準來生產,成本往往高達100-200元/輛。
與共享單車的火爆成鮮明對比的,是傳統自行車市場的進一步萎縮。共享單車對傳統自行車行業沖擊很大。以去年下半年為例,北京市場銷售的中低端自行車銷量大幅度萎縮,同比減少了近三分之一。不少經銷商都抱怨,被共享單車搶走了生意,沒辦法賣了。
這是不是一場“風險投資熱”呢?在這樣的局勢下,要時刻保持清醒,不要輕易被市場的熱度沖昏了頭腦。
和其他分享經濟很大的不同點在于,共享單車要向市場大量投放新車,而Uber、滴滴、Aibnb、共享服裝等等都是在原有資源的基本上進行的再分配,使得原有資源可以充分利用。共享單車的分享,卻是以大量制造為前提的,這是否和分享經濟的初衷相違背?是否會產生新的浪費?
為確保中心城區非機動車停放有序,上海市對非機動車停放都有明確規定,以黃浦區為例,區內設置有1000個非機動車集中停放點,這些停放點都設置在人行道上,可以滿足市民日均7萬余輛的停車需求,但這一平衡在共享單車大量投放后被打破,有市民抱怨自己的機動車無處可停放,另一邊則是共享單車的亂停亂放,從不允許非機動車停放的區域一直停到了機動車道上。我們不愿意看到的一個事實正是:共享單車在方便了市民出行的同時,卻破壞了原本有序的非機動車停放。
這就是一對矛盾,針尖對麥芒,簡直就是不可調和,如何處理,是擺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