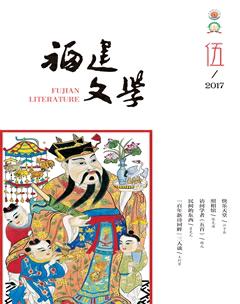海水和根叔
喬夫

一、海水
我是在自家的村子里上小學的。啟蒙時正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盡管村莊有上百戶人家,但只有一所一個老師的初級小學。那年代村人思想還很守舊,能上學的只有男生,沒有一家肯讓女孩上學。盡管老師上門動員,回答的幾乎都一句話,女孩兒終歸是別人家的,懶得花那個冤枉錢!
村里人管學校叫學堂,也叫義學,就坐落在我家上厝的小溪對岸。那是一所很考究的房屋。學堂的門面砌著幾種精致的磚雕圖案,門楣上嵌有磚雕陽文“流芳”二字,筆力遒勁飄逸。那是江西省督學楊中所題。據說清朝乾隆年間,江西省督學楊中遭人陷害,流落到村中政治避難。村里人不僅崇尚讀書,而且對讀書人敬重有加,所以村人不僅收留了他,并且各家各戶輪流供奉。三年后楊中平反,為表謝恩,便在村中留下多處墨跡,并親題巨額牌匾“篤厚栽培”相贈。這塊牌匾至今仍懸掛在我們家庭院附廳的正中。
學堂的大門是雙開的實木門,非常厚重,門上掛著一對花盤襯底的鑄鐵門環,敲擊門環,“當當”作響。入門第一間,算是禮廊,墻上畫著孔子的畫像,旁邊是校訓。屋的正堂是教室,教室的下邊是一口青石條砌就的天井,用于教室采光。正堂隔壁是兩間相連的廂房,一間用作老師辦公,一間用作老師寢居。在教室的后堂,還有一個花臺,上邊種有一大簇的繡球花。每年花開,就像一個個粉彩繡球掛在樹上,煞是好看。
由于女生不得上學,我們的學堂里總共只有二十多個男生,分一至四個年級。二十多個學生共聚一個教室,共用一塊黑板,共由一個老師執教。
四復式班的教學,老師是要很巧妙地安排時間的。一般從一年級的課上起,老師將生字寫上黑板,執教鞭指著領讀幾遍,便叫學生在課堂上練寫生字,之后立即轉入下一個年級的授課。如此這般,四十五分鐘下來,四個年級都要授予新的內容。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天空格外的清爽。老師正在領讀四年級的課文《囚渡》:“海水打腫了解放軍叔叔的眼睛,可解放軍叔叔誰也不說疼……”
“死絕,冤枉我打解放軍!”突然,學生海水站了起來,一邊罵一邊拎起書包就往教室外走,引得全學堂的人哄然大笑。
還沒等老師回過神來,海水已走出校門。“死絕,說我打腫解放軍的眼睛。死絕,這么冤枉還敢寫在書上。”他一邊走,一邊罵,拎著書包跑回了家。
海水是離我家上方好幾個庭院的人,自幼沒了父親,聽說是當年被國民黨抓壯丁抓走的,抓走之后就再也沒回來。海水沒有兄弟,孤兒寡母的,盡管日子過得艱難,海水還是上了學。海水長得人高馬大,眉目也很清秀,只是腦子想事情讓人覺得不是那么靈光,走起路來,也一步一下,有板有眼。他逢人便笑,無論何時與人相遇,總是笑笑地問:“吃過了嗬?”
“吃過了。”
“那好,那好!”海水頭點兩下,便自顧走開。
有一年,海水在外地的姑丈六十大壽,他大年初一就匆匆趕去為姑丈賀壽。那年月,六十以上就算大壽,山里的習慣,凡有人上六十歲大壽,四鄉八鄰的親戚都會趕在正月初六之前上門賀祝。上門賀壽的人,先要在壽星家廳堂的神龕上點燃紅燭,然后燃放鞭炮,“噼里啪啦”,喧鬧紅火,這是山里人賀壽的必備禮節。
海水到得姑丈家,也如數盡了禮節,并且還對著興高采烈的壽星雙手一拱,由下而上做了“加福加壽”的道賀。之后,便站在一旁觀看別的親戚來給壽星道賀。
不知是風吹的緣故,還是底沒粘牢,神龕上一支紅燭突然倒下。海水見狀便大喊起來:“姑丈倒了,姑丈倒了。”只氣得姑丈晴臉轉陰,牙齒咬得格崩響。姑丈可是四鄉八鄰小有名氣的人物,正月初一還真的聽不得這樣的晦氣話。
海水是個勤勞的人,雖說腦子想事不夠靈光,但日子過得勤儉殷實。曾經也有人為他說過幾回媒,可他卻也挑肥揀瘦,總嫌人家是二婚或是子女太多,負擔太重。他老母去世后,就堅持一個人過。
好多好多年后,村里還有人故意在他面前背《囚渡》:“海水打腫了解放軍叔叔的眼睛……”
“你蠢喔,那是海里的水,又不是我!”
海水頭一伸,笑笑地說。
二、根叔
根叔是高我兩個年級的小學同學,因村小是一所擁有四個年級卻只有一個老師的單人校,因而不應稱根叔為校友。
根叔是被家長逼著去讀書的。不知怎的,他就是不愿意讀書。每逢老師提問或在課堂上抽背課文,他都難得讓老師滿意,常常被罰站。因此,他對老師有一種莫名的討厭。
我上二年級那年,根叔上四年級,原先的男老師調走了,換來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女老師的名字很好聽,叫櫻桃。櫻桃老師剪著一副齊肩的短發,一對小酒窩勻稱地鑲嵌在她兩片圓圓的臉蛋上,怎么看都像是在微笑,很甜很甜。
調走的男老師是很威嚴的,在他的講臺上,除了教鞭之外還有一塊專門用于懲罰學生的板子。那是一塊刻有陰文“學無止境”的實木板,形狀大小和厚薄程度都像古代縣衙的驚堂木。
記得有一次晚飯后,村里的孩子聚在一起疊羅漢,結果把一個學生的手骨壓折了。第二天上學,老師滿臉威嚴,把所有的學生逐個叫上講臺,板掌三下。我也被冤枉地叫上講臺,嚇得滿臉蒼白。好在我表哥立即起立給我作證,說我沒有參加,才幸免。那些被板子打過手掌的學生,個個痛得噙淚而泣,勾著頭回到座位,卻不敢出聲。
那時候,根叔雖不愿讀書,但在學堂上卻也不敢造次,因為男老師不僅威嚴,而且是本村人,就住在他家的上厝。
現在女老師來了,根叔被壓抑的野性得到了解放,總是隔三岔五地生事讓老師受氣。比如他總愛把自己從山上采來的野果,像黃拿子啦、牛奶子啦什么的,帶到學堂上來,又不分給同學吃,又愛顯擺。老師給低年級同學講課時,他就偷偷地吃,還把吃掉囊的果皮偷偷塞進同學的口袋或書包。
有一次上課,他又偷偷吃牛奶奶了,同桌伸出小手向他討,他卻一粒也不給,而是把吸掉果囊的牛奶子皮塞到同桌手中,還咯咯地偷笑。同桌不理他,在課桌上畫起了“三八線”,先是用鉛筆,被根叔擦掉,后來同桌就用小刀刻,結果把老師氣個半死。因為前天四年級的課文剛上《桌椅的對話》,那是一篇擬人化的短文,意思就是通過桌椅的對話教育學生要愛護課桌椅,愛護公共財物。
一個夏天的中午,艷陽高照,雖然村子里氣溫不高,倘若站在陽光下面直曬,頭皮卻也是生痛。那天中午,根叔糾集了幾個同學一起跑到小溪的一個潭子里去游泳。下午快上課了,還不見幾個孩子來學堂。經人告密,說是根叔等幾個正在村子東頭的小溪里洗澡。櫻桃老師便帶上幾個學生摸了上去,只見幾個男生赤條條地在水里嬉得正歡。櫻桃老師那時還是個黃花閨女,卻也顧不上許多,臉頰緋紅著,沖到溪邊的大石頭上,把河里洗澡男生的衣褲全部抱走了。本來還在水里嬉戲的根叔們被櫻桃老師的舉動嚇丟了魂,一個個趕忙爬上岸,卻又不敢赤條條地穿村而過。只有根叔急中生智,順手從溪畔瓜棚上采下兩張大大的南瓜葉,一前一后遮住襠部,飛一般地潛回家中。
結果可想而知,根叔們誰也沒能逃過家長們的一頓好打。
先生教我一本書,捉豪豬;
豪豬上山岫,跌斷先生的手;
豪豬跑上排,跌腫先生的奶;
豪豬跑上坡,先生跌起皰;
豪豬滿山繞,先生跌斷腳……
第二天,根叔不知從哪學的,一進學堂門就用方言很押韻地念起了這一大段的順口溜,引得全堂學生哄然大笑。那些個跟著去洗澡的男孩兒也不顧死活地跟著嚷嚷。根叔見有人附和,越嚷越得意,居然還揮手打起了節拍,儼然一個合唱隊的指揮,只是把櫻桃老師氣得不知所措,課也上不下去,當即放了學生的假。學生一走,櫻桃老師便哭得像個淚人,連中午飯都沒吃,第二天上課,雙眼還是紅紅腫腫的。
讀完小學四年級,根叔就再也沒上學了,跟著大人下了田地去掙工分。稍長大后,大人還讓他去學了幾年木匠,但學了幾年,都只會拉鋸刨板、打眼鑿洞的,至于設計放樣、計隼劃墨的,卻讓他為難。既然難出師,根叔還是歸了田。
其實根叔腦瓜子很靈活,學起農活技術來一看就懂,田里的活無論使牛犁田耙地,還是插秧放樣,他無所不通。“都怪我自己從小不肯學書哩,就是打田的命!”根叔說。
后來,根叔成家立業了,生了一對兒女。
“在學堂好好學書喲,可別像我一樣!”
這是根叔對子女的訓話。
責任編輯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