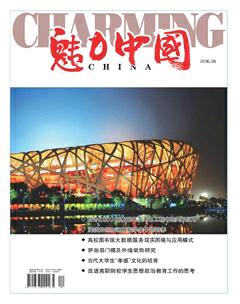近代黑人女性文學對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探索
蘇虹蕾
【摘要】二十世紀初期黑人文學迅速崛起,它兼具黑人民族與文化的雙重特征,它既是獨具魅力的黑人女性文學,又是文學的一部分。在這個作家群體中,黑人女性作家自始至終積極地參與黑人文學的發(fā)展,并在各個階段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部分黑人女性作家已經(jīng)從關注種族問題拓展到早期的黑人女性的自身問題,黑人女性作家便逐步開啟了一條通過作品展示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
【關鍵詞】黑人;女性文學;自我解放
民族歷史與種族身份形成了當代黑人女性文學的特色。她們以黑人群體生活作為主要表現(xiàn)對象,部分黑人女性作家已經(jīng)從關注種族問題拓展到早期黑人女性的自身問題,如弗朗西斯·哈珀為了改變傳統(tǒng)印象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在1892年發(fā)表的小說《伊娥拉·勒勞伊》中塑造的混血女孩伊娥拉,主人公從中產家庭淪為奴隸后,憑借勤奮與斗爭精神,最后不但回歸黑人中產階級并收獲美好愛情的故事。而寶琳·霍普金斯在1900年發(fā)表的小說《兩種力量的抗爭,一部北方與南方黑人生活的羅曼史》繼承了哈珀的風格,同樣描述了一個混血美女的勵志故事。雖然現(xiàn)在看來這兩部小說還不具有典型的黑人女性文學特征,人物形象也與當時絕大多數(shù)的黑人形象不符,但它卻對改變社會公眾對黑人女性的刻板認知,激起黑人女性重新自我定位起到不可小覷的作用,自此以后,黑人女性作家便逐步開啟了一條通過作品展示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道路。
一、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對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探索
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的黑人中產階級作家奈拉·拉森避開了當時熱衷的種族話題,有意識地通過作品表現(xiàn)黑人中產階級女性尋找自我的過程。發(fā)表于1927年的《流沙》有很強的自傳色彩,小說中的主角海格爾·克萊恩就是一個混血女孩,雖然沒有經(jīng)濟上的壓力,但在南方的黑人學校教書時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以白人的價值標準來灌輸,標榜白人的偉大和譴責黑人的無能,容不得半點異議或新思想,甚至熱情或沖動都被視為是缺乏教養(yǎng)的表現(xiàn)。離開學校后她去了北方哈萊姆區(qū)找到了一份銀行工作,她發(fā)現(xiàn)黑人處處以白人生活為榜樣,雖然內心痛恨白人。之后海格爾又去了哥本哈根,在這個沒有黑人的地區(qū),雖然人們恭維她的美麗,丹麥畫家以她為模特并向她求婚,但父母的經(jīng)歷讓她覺得跨種族婚姻的有很強的不穩(wěn)定性。追求心儀男性的失敗使她投入一個黃皮膚牧師的懷抱。并跟隨他去了一個小鎮(zhèn)幫助丈夫為教民服務并曾一度滿足于這種生活,但在懷上第五個孩子的時候,她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陷入生活雜務與生孩子的怪圈,但此時已沒有改變現(xiàn)狀的能力。海格爾的經(jīng)歷反映了她追求自我過程中的矛盾沖突,她像流沙一樣輾轉于各個城市也是她逃避與追求的過程,她痛恨以白人為準則的價值觀和以白人為榜樣的黑人群體,也不愿與低俗的野蠻人為伍,她向往沒有種族歧視、互相理解、自由的婚姻。然而這些需求往往又是矛盾的,就像她的種族屬性使他排斥白人的價值觀,而接受的教育又使他不愿回歸黑人群體,而婚姻又必定是以某種不自由為代價的。拉森的這部小說只是表達了黑人女性在現(xiàn)代生活中自我解放意識的覺醒和探索,而具體目標在哪里以及路該如何走,作者并沒有給出答案。前文說到的赫斯頓在1937年發(fā)表的小說《他們的眼睛望著上帝》同樣涉及了婦女自我解放的問題,不同之處在于,赫斯頓這部小說中的主角珍妮來源于底層社會,最終通過獲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珍妮追求的女性權利只體現(xiàn)在婚姻的自由與婚姻的地位中,因此她追求的自由同樣必須依附于男人才能夠實現(xiàn)。
二、二戰(zhàn)后對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探索
二戰(zhàn)后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形成巨大勞動力缺口,但在很多工作領域并不接納黑人,受二戰(zhàn)期間所倡導的自由以及人道主義精神的影響,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正如廢除奴隸制運動孕育了第一次婦女運動,二十世紀黑人爭取公民權利運動成為當代婦女運動的催化劑[1]。從五十年代至今,涌現(xiàn)出許多優(yōu)秀的黑人女性作家開始從女性的視角審視黑人探索種族問題與性別問題,她們筆下的女性形象日益飽滿,脫離了一味塑造混血女孩的模式,中心人物來自于與不同階層、具有豐富多彩的個性特征與生活閱歷,濃墨重彩地書寫了歷史上不同時期黑人女性的悲慘境遇與抗爭精神,這些作品中黑人女性形象的正面刻畫不但提升了黑人婦女的性別認同,同時使黑人女性主義文學獲得了縱深發(fā)展。這一時期托妮·莫里森、艾麗斯·沃克以及瑪亞·安琪蘿都在其作品中對女性的自我探索與自我解放的問題進行了深刻探索。
1.莫里森對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探索
莫里森在1973年發(fā)表的小說《秀拉》中,塑造了秀拉這樣一位敢于挑戰(zhàn)男權、挑戰(zhàn)傳統(tǒng)女性社會角色定位的黑人女斗士。從小成長于男性缺位的家庭中使蘇拉具有典型的男人性格特征。她從祖母那里繼承了、傲慢、專橫、我行我素的性格,又從母親那里繼承了對男女關系放縱的觀念。種族歧視與男性缺失的生活環(huán)境使她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她既不是白人又不是男人,一切自由和成功都沒有她的份兒,她便著手把自己創(chuàng)造成另一種新東西”[2]。這種新的東西便是自我的解放,為了追求自我,她離開了成長的城鎮(zhèn)開始了自己的生活實驗,她蔑視陳規(guī)舊俗,拋棄主流社會界定的倫理道德,追尋只屬于自我內心的生活模式。十年游學使她認識到,婚姻必須以放棄自由為代價,這是不值得的。秀拉通過與不同的男性發(fā)生性關系而不與其結婚來向男權挑戰(zhàn),并認為這種不參雜情感的性能是感受自我的有效途徑,她與女性好友的丈夫發(fā)生關系的目的也僅僅是通過他為中介來了解同性好友的欲望。然而當秀拉遇到可以心靈交流的男人阿杰克斯時卻產生強烈的占有欲以把幸福定格,男友的離開使她重新意識到愛只會束縛自己的自由。最終秀拉不到三十歲就走完了她孤獨的一生,她不懼怕死亡,對追隨自我內心的生活也毫無悔意,她承認自己是孤獨的,但這種孤獨是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別人強加的。作者通過這樣一位以叛逆的方式挑戰(zhàn)男權、追求女性自我解放的勇士來黑人婦女出路問題加以探索。
莫里森通過小說對黑人女性的自我定位進行不斷的思考和修訂,從發(fā)表小說時間上看,體現(xiàn)出從迷失到反抗、再到理想的漸進過程。在《所羅門之歌》中,她將派拉特塑造為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成熟女性,但與秀拉不同的是,她沒有采用極端的叛逆甚至瘋狂的方式來應對世界,而是具有強烈責任感和包容情懷的善良女性,并通過黑人文化傳統(tǒng)護著實現(xiàn)其女人在黑人群體中的自我價值。
2.艾利斯·沃克對黑人女性自我解放的探索
艾利斯·沃克的小說《紫顏色》中的西莉在被男權壓制下如同行尸走肉地生活時,丈夫的情人西格走入她的世界,這個藐視權威、像男人一樣說話的女人讓她看到女人的另一種生活,這個女人教會了她如何欣賞自己,讓她開啟了女人身體的認知,這也是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步。缺乏愛與情感交流的西莉逐漸將西格視為知己,向其傾訴內心沉積已久的成長經(jīng)歷,這使兩人的感情逐漸加深,最終發(fā)展為同性戀人,這使西莉尋找自我邁出了第一步。沃克采用這種方式來啟蒙西莉的性意識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在男權社會中性愉悅體驗一直被認為是男人的特權,作者也通過這種方式表明,女性的之間的友誼和團結是應對男權主義獲得自我解放的一個途徑。也正是這種女性之間的友誼,使西莉開始敢于痛斥并離開丈夫,最后在沙格的幫助下她獲得了經(jīng)濟上的獨立。顯然沃克通過小說探討女性的自我解放道路時,并沒有選擇像莫里森小說筆下的秀拉那種反社會模式,而是采取了女性結盟的方式對抗男權主義,并通過女性群體的自我啟蒙與相互幫助來獲得經(jīng)濟上的獨立。而經(jīng)濟上擺脫對男權的依附僅僅完成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步,小說的后半段中,西莉經(jīng)歷了被戀人拋棄和喪失親人的一系列磨難的洗禮后又重新站起,說明她已經(jīng)能夠獨立應對生活并獲得快樂。沃克這樣描寫的意義在于表明,黑人女性要獲得完整的自我,就必須學會獨立思考,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應對生活的困境。
與莫里森的類似,沃克通過小說表達女性主義的態(tài)度也從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日趨成熟,在她1976年發(fā)表的小說《梅麗迪恩》中塑造了從迷茫到覺醒的女孩梅麗迪恩,她高中沒畢業(yè)就因懷孕而不得不結婚生子,在加入民權運動后,她與丈夫離了婚并將孩子送了人,再次戀愛后選擇了絕育,她以這種行為表示與男權社會賦予的賢妻良母的角色定位決裂。這種處理方式顯然受當時“極端的白人女性主義”主張所影響,但選擇與男性對立來主張女性權利顯然無法實現(xiàn)平等和諧兩性關系的主張。而后來的小說《紫色》中則選擇了更溫和的處理方式,她讓黑人女性群體的通過友誼來抵制并掙脫男權的牢籠,并從黑人文化傳統(tǒng)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堅韌的性格和寬容的人道主義情懷來看待世界,西麗沒有拋棄孩子,也與丈夫達成和解,最終獲得獨立人格并獲得外界的尊重。
參考文獻
[1]瑪雅·安吉洛.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M].于 霄,王笑紅,譯.上海: 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第115-117頁
[2]Walker, Alice. Meridian[J].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6,p40-47
[3]王 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的女權運動[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頁.
[4]托妮·莫里森.秀拉[M].胡允恒,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