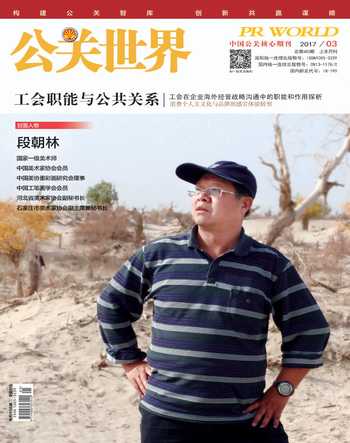日本工會制度與勞動關系的發展變遷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本文的目的是通過介紹和分析日本戰后工會制度與勞動關系的發展變遷的狀況,并比較與中國工會制度的異同點。分析戰后日本工會制度與勞動關系的發展變遷的意義主要有兩點。第一,對于還沒有與發達國家的內涵相同的工會組織的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日本戰后的工會制度與勞動關系的發展歷程可以提供一些參考。因為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日本是在二戰后才制定頒布了《工會法》與《勞動關系調節法》。當時在美軍占領下,聯合國司令部在對日本實行民主化改革的進程中,日本的工會活動才被合法化的。這一點是戰前的日本所沒想到的,對于當時的日本來說,屬于具有歷史意義的巨大社會變革。一些學者在比較分析日本的這兩部法與其他發達國家的類似的法律時,還發現,其具體內容里,日本把“團結權”和“爭議權”當做憲法中的基本人權來保障,這些創新大大超越了當時的發達國家。
第二,研究日本工會制度的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日本良好的勞動關系常常被稱作為是支持了日本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工會這種社會組織自出現以來,貫穿整個20世紀,一方面是一個保護勞動者利益的組織,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具有一定程度的攻擊性的組織。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多數發達國家,工會運動都或多或少地向著和諧勞動關系的方向變化著。在這一方面,日本的工會雖然是最晚被合法化的,但確是最早達成勞動關系和諧的,所以也被稱為是“超越時代發展的日本的勞動關系”。日本勞動關系的和諧使得石油危機引起的工資推動型通貨膨脹能夠比其他發達國家早收斂,并且能更好地支持企業的技術進步。這些特點都受到了歐美國家的特別關注,認為是支撐了戰后日本高度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擁有“和諧的勞動關系”稱號的日本,出現了勞動時間過長、過勞死、人才被企業組織埋沒和公司人等比較深刻的問題。中國在借鑒日本經驗的同時,也需要警惕這些負面的問題。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存在這些負面問題,日本的工會及和諧的勞動關系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確實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戰后復興期日本工會的發展歷程
(一)戰后初期工會的發展歷程
日本的工會變成合法組織是在二戰后。戰爭期間,工人是不可以自愿成立工會的,因此工會組織極少。二戰后,日本被聯合國司令部占領。聯合國司令部認為需要對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個重要措施是工會組織和活動的合法化。這樣,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10月,日本分別頒布實施了《工會法》與《勞動關系調節法》。又由于當時日本面臨著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的自然災害,使得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難,所以基于這兩個法律的工會運動受到了勞動者的積極支持,工會參與率迅猛地增加了起來。到1948年為止,參加工會的會員占到了全部勞動者的50%。
在工會的指導下,各種激烈的勞動爭議頻發,爭議的內容除了提高工資、反對解雇等之外,甚至包括了生產管理等。其結果,在這個時期對于企業的經營管理等,勞動者比經營者都更有話語權和決定權,經營者常常需要在意工會的臉色。對于工資的決定,也有無視物價和企業的支付能力,僅憑交涉能力而決定的情況。這樣,在勞動民主化的改革中,工會成為工資上升的主要因素。
當時工會的提高工資的目標比較容易實現的另外兩個原因之一是,盡管占領軍反復強調應該把工資也列入國家統一控制的對象,但是一直沒能做到。另一個原因是當企業經營陷入赤字時,這個赤字可以通過政府的價格補貼、銀行融資和政府調整官方物價的形式填補。
這個時期工會對工資上漲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臨時性工資的范圍內。因為到1946年9月為止,戰爭期間政府對工資的管制還在持續,因此,勞資交涉的內容主要圍繞著各種補助而展開。例如:化解食物危機資金、家屬疏散費和伙食補助費等。后來,在政府取消了對工資的管制之后,工資交涉主要以臨時性收入為主的這個特點也一直沒什么變化。例如,在公務員的勞動爭議中,工資交涉是最被重視的。其中,每年都會對最低工資水平的確定和生活補助金進行討論。在1947年至1948年中期為止,公務員的工會主導著日本整體的工會運動的方向。
(二)1949-1950年期間的工會運動狀況
1949年4月,日本開始實施了德國的道奇提出的致力于結束通貨膨脹和經濟自立“超均衡財政政策”。這個政策使得日本的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宏觀經濟進入平穩運行的軌道。并且,日本開始撤銷政府對經濟的管制,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的目標。對于工資,開始實施了“工資合理化三原則”。具體內容是,第一,因為提高工資而需要政府補貼時,這個補貼僅限于政府能夠有新財源支付的情況下。第二,銀行不再為了填補企業因為工資上漲而產生的赤字而融資。第三,不允許出現引起物價上漲的工資上漲。這樣企業工資的上漲就限定在了自己能承擔的范圍之內。企業對于自己的赤字只能憑借合理化經營和自己的努力來實現。通過這個措施,與戰后初期相比,工資可以輕易上漲的經濟環境就不存在了。
對于民主化運動,最初非常支持的聯合國司令部,以1947年的全國總罷工為界限,開始出現了抑制的意向。隨著占領政策的改變,“國家公務員法”被修訂了,從此禁止公務員實施勞動爭議。更進一步,在1949年5月,對于《工會法》與《勞動關系調節法》也進行了修訂。這些措施對于工會運動的打擊很大。從此,企業的經營權大幅度回到了經營者手中,經營者的力量漸漸強大起來了。重新獲得了經營權的經營者對企業的勞動人事管理和企業經營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改革,也解雇了一些員工,重新整頓了企業。
以上這些一系列的新措施使得以公務員工會為中心的工會運動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其結果,不僅出現了工會的分裂和會員數的減少,勞動爭議也有過去的激烈的斗爭形式轉變成了相對消極的防衛性斗爭。例如,在1946年起到1954年期間,1949年和1950年的爭議中,工會提出的積極的要求的件數(要求增加工資的件數)比其他年份減少了很多;反之,消極的要求的件數(反對降低工資、定期支付工資、確保雇傭的件數)增加了。與此同時,工資總額的增長率急速地低于之前的時期,其中臨時性工資的增長率在1949-1950年期間幾乎都是負值。
(三)1950年6月-1954年12月期間的工會運動
根據寺西重郎(1993)的研究,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給日本帶來了特需景氣。旺盛的產業活動的結果,使得企業生產和利潤急速增加①。在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在1950年7月日本工會運動史上最大的工會組織“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簡稱“總評”)成立了,號稱擁有365萬名工會會員。這樣工會組織得到了重組。
此時日本人的生活仍然低于戰前水平,非常貧窮。面對再次出現的通貨膨脹和企業利潤的急速增加,工會再次發動了積極的以提高工資為主要目標的勞動爭議,與經營者方面進行了激烈的交涉。但是到了這個時期,由于企業經營權已經大幅度回到了經營者手中,所以對于勞動者發起的激烈的罷工活動,經營者方面斷然以置之不理的態度進行了對抗。這樣,勞動爭議就出現了長期化的傾向,最后漸漸朝著對勞動者不利的方向發展了。另外,在爭議中勞動者方面常常出現違法行為,與刑事事件相牽連,結果爭議以經營者的勝利為終結的例子增加起來。
對于漲工資方面的要求,其解決狀況如下:日本的總工資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固定工資,一是臨時工資。在1952年要求漲工資和增加臨時性補貼的勞動爭議的件數共有842件,各自分別占58%和42%。由此可見,在勞動爭議中,關于增加固定工資方面的爭議占多數。但是從解決情況來看,58%的關于增加固定工資的爭議中,只有40%達成了妥協,另外以增加臨時性補助的形式落實的占40%,剩下的20%是不解決或未解決。這樣842件中只有23.2%的爭議取得了實效。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年分。在1954年,要求增加固定工資的爭議發生了398件,低于要求增加臨時工資的408件。參加人數為1000人以上的大型勞動爭議中,增加固定工資的要求中40%得到了落實,30%轉化成了臨時性工資的增加,30%為不落實或未解決。此處,即使在落實的情況中,固定工資的增長幅度通常都比工會要求的程度要低。完全按照工會要求的程度增加工資的情況很少。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資再加上一些臨時工資的增加的形式達成妥協的情況比較多見。另外,在1953年的參加人數在1000人以上的勞動爭議中,落實為增加臨時工資的有83件,高于落實為增加固定工資的58件。
導致臨時收入增加的情況具體如下:第一,在關于增加固定工資的交涉中,因為難以達成妥協,最后變成了臨時工資的增加;或者雖然雙方達成了妥協,妥協的結果是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資再加上增加臨時工資。第二,工會發起的要求增加臨時工資的爭議獲勝時。第三,在工會提出的反對解雇員工的爭議中,被解雇者被落實到“自愿辭職”的程序中,按照公司的“自愿辭職”待遇,獲得一筆臨時性補貼。此外,在反對解雇的爭議中,以向工會一次性支付失業補助金和解雇金的形式解決了勞動爭議時,或者對于反對關閉工廠的爭議,以支付一次性退職金的形式達成妥協的。
這樣帶來臨時工資增加的勞動爭議的件數就遠超過了增加固定工資的件數。這個現象還突出地表現在每年的12月份。12月的臨時工資的上漲幅度遠大于其他月份。一個原因是,“總評”在著力于增加固定工資的同時,對于年末的“獎金斗爭”也越來越重視。另一個原因是,對于具有永久性效果的固定工資的增加來說,增加些臨時性的補貼的要求,對于經營者來說,比較容易接受。
這樣,在戰后日本的經濟復興期,盡管工會運動非常激烈,但是對于工資的影響,比起固定工資來說,更主要地體現在臨時工資的上漲方面。由于臨時工資占總工資的比重在經濟復興期平均為11%,所以從成本的角度來看,由工會推動的工資上漲給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不太大。
二、日本勞動關系的特點
日本的工會是自二戰后才合法。到現在為止日本的勞動關系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其他發達國家不同的形態。主要特征“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的工資上漲與晉升機制”、“以企業為單位的工會組織”。這些特征的一個突出優點就是勞動關系和諧。
和諧的勞動關系的宏觀意義在于,從供給側來看,可以改善勞動條件、特別是工資水平,從而使得勞動者的收入得到增加。這一點對于日本經濟來說,增加了購買力、擴大了國內消費市場,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另外,順暢和高效的勞資間交流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效果。從需求側來看,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時期,有利于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盡早收縮。因此,盡管與其他發達國家一樣都擁有工會制度,在遇到石油危機時,日本的工資變動更具有彈性,工資物價的惡性循環能夠盡快得到安定。與之相反,美英等國卻不得不需要政府出面采用直接的物價控制措施。其結果,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盡管其他發達國家都長期陷于經濟增長停滯的困境,而日本卻憑借其良好的經濟業績,在發達國家中的地位急速上升。從此,日本勞動關系迅速地被世界矚目。
發達國家的視角關注日本勞動關系的理由主要是在需求側。這一點實際上對于發展中國家也具有重要意義。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常常出現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和通貨膨脹,這兩個因素阻礙著經濟增長,并造成了貧困。
日本的勞動關系雖然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才受到世界關注的,但是實際上,早在石油危機之前,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就和諧的多。此處引用中村隆英(1985)的論述作為旁證“平均每個工會會員的損失的工作天數超過1天的年份,在整個戰后只有1946、48、51、52這4個年度。超過0.8天的再加上1947、50、57、58、59,這5個年度。這個數字比美國和英國少得多,僅次于西德。并且,到50年代為止,工作天數的損失主要是因為出現了反對解雇的長期罷工,發生在電器、煤礦、汽車、鋼鐵等部門,并不是因為整個日本出現了大量勞動爭議。” ②
和諧安定的日本的勞動關系還是日本企業能夠積極成功地進行設備投資的一個重要理由。由于長期以來勞動關系和諧,所以日本的企業在采用新技術或導入機器人的時候,發生的勞動爭議比其他發達國家少得多。這一點為日本能在很長時期都一直能提升國際競爭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日本企業在解雇職工方面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如果沒有連續兩期出現經營赤字,就不可以解雇職工。也就是說,如果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則不可以隨意解雇職工,因此,日本企業在導入機器人時,都是把替換下來的職工進行了重新安置,而不是直接解雇。
在微觀層面上,勞動關系的和諧使得工會存在的必要性不再像過去那么高,許多協調工作通過企業的勞動協商委員會就解決了。其結果,日本的工會的參與率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后,越來越低,降到了10%的樣子。
三、對中國工會制度建設的啟示
中國工會法中,工會的定義是勞動者與企業或政府之間的橋梁,而不是代表勞動者利益的團體。這一點是中國工會制度與發達國家的根本區別。其結果,中國的工會主席常常是由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擔任。而在日本,當一個人在企業的職位晉升到“課長”以上時,就必須退出工會。因為他已經是屬于企業的管理層,他的工作內容是維護企業的利益,不能直接代表員工了。因此,中國還沒有允許勞動者自己組織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中國工會制度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著本質性的差距。
一些中國學者說即使是發達國家,工會組織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所以,中國現在這樣的工會制度也沒什么問題。如果鑒于中國的一些特殊情況,中國需要保持目前的工會制度不變,或許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如果說是因為發達國家的工會制度多種多樣,中國的工會制度也可以屬于其中的一種,則有些想當然了。因為,發達國家的多樣化的工會制度中,沒有中國這種類型的制度(王新梅,2005)③。
發達國家的工會多種多樣,有以企業為單位的、不分藍領白領的工會,各種事項的交涉和決定也主要在企業層面,因企業不同而不同。例如,日本的工會制度,盡管他們也都層層加盟到全國總工會。也有以職業或產業為單位成立的工會;還有主要在全國總工會層面進行事項的交涉和決定的工會制度。無論哪種工會制度,都是各個國家在工會的發展歷程中自然而然演化成的。這些制度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是勞動者自愿成立、自愿參加的、代表勞動者利益的組織,而且工會的領導也由會員選舉產生。他們中沒有一個工會的定位是介于勞動者和企業與國家之間的橋梁。定位于協調工會組織與經營者團體之間利益的組織,在發達國家叫做“勞動關系協調委員會”,是另外的一個獨立的組織。顯然,中國目前把工會定位成了發達國家的“勞動關系協調委員會”。然而,由于中國不允許勞動者自愿組織代表自己利益工會,所以還處于民間社會組織非常缺乏的狀態,嚴重影響勞動者與經營者之間的高效交流。
工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其目的是通過順暢的交流機制來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然而,勞動者利益的保護同時也是建立在企業經營者是否對企業的發展有長遠的目標和規劃,是否有意向和動機把企業引領到一個良好的發展遠景的基礎上。所以,一個國家的工會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與建立一個良好的適宜于企業家致力于企業長期發展的宏觀經濟環境相結合起來進行考慮。否則,如果貿然強調保護工人利益,或者只是單方面鼓勵工會和團體交涉,其結果,可能帶來的只是更多的勞動爭議,而不能給企業和勞動者帶來長期的雙贏。
參考文獻:
①寺西重郎:《安定化政策和生產的擴大與成長》,香西泰、寺西重郎編,《戰后日本的經濟改革:市場與政府》,東京大學出版社,1993。
②中村隆英:《日本經濟:成長與結構》(第3版),東京大學出版社,1985。
③王新梅:《建立適用于市場經濟的勞動關系與工會制度》,本文收錄于蔡昉、張展新主編《轉型中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國人口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