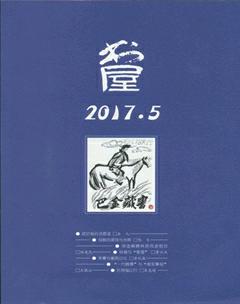胡適解聘林損風波前后
楊建民
1934年4月,北平的《世界日報》上,刊出一封名為《致北大文學院長兼國學系主任胡適》的函件:
適之足下:猶石勒之于李陽也,鐵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塵,損寧計于區區乎?比觀佛書,頗識因果,佛具九惱,損盡罹之,教授雞肋,棄之何惜!敬避賢路,以質高明。林損。
函中所謂“猶石勒之于李陽也”云云,用的是后趙高祖石勒的一個典故。說石勒在微賤之時,常常與一個叫李陽的鄰居打架,只是為了爭得一點麻地。“有所媒孽”,是設計陷人于罪的意思。通篇看去,言辭雖因文言及用典而顯得隱晦,可意思還是明白的,那就是控訴自己遭到胡適“鐵馬金戈,尊拳毒手”般打擊,甚至設計陷害,忿憤異常。因為自己讀得“佛”書,“頗識因果”,所遭受的煩惱,如佛認為的九種,全然領受云云。其中“教授雞肋,棄之何惜!”一句,因形容別致,傳誦一時。
這位署名“林損”者,此時正在北京大學國學系擔任教授。他是一位在中國古文化研究領域有一定造詣的學人,曾撰有《老子通義》、《辨墨》等著述十數種。林損(字公鐸)由于出生時喪母,七歲時喪父,受舅家撫養,雖頗有天分,可養成了孤介自賞、“別成一家”的性格。在北京大學任教,他是出了名的“固執乖僻”。他的同事周作人曾形容其“脾氣的乖僻也與黃季剛差不多……他的態度很是直率,有點近于不客氣”。那么,這次又是因為什么,他用了這種口吻,給胡適寫出這樣一封信呢?
1930年11月,受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聘請,胡適到北大文學院擔任院長。當時的北大國文系是老學者馬裕藻主持,教授有以舊學為業的林損、許之衡等人。胡適是宣傳新思想、大力倡導白話文的學者,兩方面的沖突也就勢所難免。
在此之前,林損就起來反對過胡適與錢玄同等人宣傳的“白話”運動,寫出了長達數萬言的《漢字存廢的問題》予以駁詰。胡適到北大任教之后,林損仍逞“罵座之癖,時時薄胡適之”。林損在北大,“學生中,喜新文學者排之,喜舊文學者擁之,其得于人亦有在講授之外者”。據聽過其講課的張中行回憶:“一次,忘記是講什么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列舉標點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側打一個杠子(案即專名號),‘這成什么話!接著說,有一次他看到胡適寫的什么,里面寫到他,旁邊有個杠子,把他氣壞了;往下看,有胡適自己的名字,旁邊也有個杠子,他的氣才消了些。講得臺下大笑。他像是滿足了,這場缺席判決就這樣結束。”
假若完全是針對胡適,也就罷了,可這些舉動引起了學生的看法,校方便不得不考慮如何處理。有學生寫信給校方,表達對林損不滿。青年學子求新,對新事物有新鮮感,加之當時新文化運動形成巨大影響,講古文且十分保守者,自然不大受待見。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是留過學、了解世界的蔣夢麟。對于國文系一幫古舊人物確實難以容忍,這就有了讓文學院長胡適兼任國文系主任的打算。不僅校方,學生中也有這一方面的表達。
系主任將由胡適兼任的消息傳出后,國文系一干人大為不滿。系主任馬裕藻,教授林損、許之衡等相繼辭職。這其中,林損尤其表現突出。他不僅給胡適寫出那封語帶憤忿、嘲諷之信,還向校長蔣夢麟發信抗議:
夢麟校長左右:自公來長斯校,為日久矣,學生交相責難,喑不敢聲,而校政隱加操切,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損甚傷之。忝從執御,詭遇未能,請從此別,祝汝萬春!林損。
該信指責校長“以無恥之心而行機變之巧……”,苛切之心可想而知。
胡適也許沒有想到,林損的反應會如此激烈。接讀林損信后,他也有些惱火,便提筆疾書,復林損一函:
公鐸先生:
今天讀手書,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論,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章。我在這十幾年中,寫了一兩百萬字的雜作,從來沒有半個字“寓”及先生。胡適之向來不會在文字里寓意罵人。如有罵人的工夫,我自會公開的罵,決不用“寓”也。
來信又說:“頃聞足下又有所媒孽”,這話我也不懂。我對人對事,若有所主張,無不可對人說,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林損接到胡適的信后惱羞成怒。他又草出一函,其中內容、語言更為不堪,甚至有胡適“遺我一矢”、“字諭胡適,汝本亂賊”等亂罵之語。
說起來,胡適與林損,原本關系還并不怎么壞。當年七月,劉半農教授去世,胡適在追悼會上講話時說:“我與半農皆為以前‘卯字號人物,至今回憶起這段故事,頗令人無限傷感。緣半農與陳獨秀、林損及我皆為卯年生,我們常和陳獨秀、錢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間屋里談天說笑,因此被人叫做‘卯字號人物……叫我和半農、林損諸人為‘小兔子。現在我們‘小兔子的隊伍逐漸凋零了……”
此番風波后不久,林損被北京大學解聘了。胡適在1934年5月30號的日記里記有一個解聘名單,其中有“商定北大文學院舊教員續聘人數。不續聘者:林損……許之衡……”的字眼。對于此事的處理,學人中還是有些看法的。譬如當時的學生張中行,就在《胡博士》一文中這樣議論:“說起北大舊事,胡博士的所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學院長,并進一步兼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立意整頓的時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鐸(損)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課喜歡東拉西扯,罵人,確是有懈可擊。但他發牢騷,多半是反對白話,反對新式標點,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權,整頓,開刀祭旗的人是反對自己最厲害的,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
從張中行的文字看去,他本人屬于偏舊一點的人物,所以對胡適有這樣的議論,可同是國文系的學生,當時就有人合伙起來去找胡適,要求他來兼系主任,這又是另一方面的看法。再說,林損本身,如張中行所說,也自有可遭非議的地方。據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回憶:他(林損)講學問、寫文章因此都不免有愛使氣的地方。“一天,我在國文系辦公室遇見他,問在北大外還有兼課么?答說在中國大學有兩小時。是什么功課呢?說是唐詩。我又好奇的追問道,林先生講哪些詩人的詩呢?他的答復很出意外,他說是講陶淵明。大家知道陶淵明與唐朝之間還整個的隔著一個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樣的講的。這個緣因是,北大有陶淵明詩這一種功課,是沈尹默擔任的,林公鐸大概很不滿意,所以在別處也講這個,至于文不對題,也就不管了”。
在這方面,張中行也有切身體會:“又一件,是林公鐸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他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至于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于胡說……他上課,常常是發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八處士》,結尾云,衛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意思是此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這樣講也差得太離譜了。
這樣看去,林損不僅相對守舊,在治學治教的態度上,也有很大逞才使氣的成分。這似乎就不應當了。由此看來,胡適即使不從新學、舊學的沖突考慮,僅從教學態度處理,解聘林損,也有他十分充分理由的。
林損被解聘,也很有新人物表示支持。在報紙上見到北京大學解聘教授的文字,傅斯年特別高興。他寫信給胡適,用他那激烈的語言說:“今日看到林損小丑之文,為之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參加惡戰……此等敗類,竟容許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罪也。”
林損辭職或被北大解聘后,在當年秋受黃侃之邀,到南京中央大學擔任教職;1936年秋,又經于右任推薦,去往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任教。抗戰爆發后,林損回歸故里瑞安。1940年8月因肺病逝世,終年五十歲。林損逝世后,瑞安當地及重慶兩地,舉行了公祭儀式。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頒令褒揚:“前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林損性行英邁,學術湛深,曩年參加革命,奔走宣傳,不辭艱苦,嗣即努力教育,潛心著述,于政學理,多所闡揚,夙為后進欽響。”林損在東北大學任教期間,與校長張學良頗有交往,故張學良亦親筆書寫挽幛:“人師,經師,國學大師”,表達哀悼。
林損與胡適的這段公案,在當時由于林損公開發函叫罵,鬧得沸沸揚揚。他留有的《辨奸論》手稿,特別注明“誅胡適也”,可見怨氣終于不消。胡適到晚年卻還帶著惋惜的心情與人談到林損:公鐸(林損)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罵人,不用功,怎么會給人家競爭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黃季剛,他們天分高,他們是很用功的啊。公鐸當我面時,對我很好,說:“適之,我總不罵你的。”幾十年后,胡適舊話重提,是存一分惋惜,還是有為當年事辯白的意味,還不大好妄揣了。
人們在討論某些思想或學術問題時,常常會提出要求,希望不要把個人之間情緒摻雜進去。可從實際看,個人對問題的認識,往往會加重彼此的意氣,形成個人之間關系的異變。胡適與林損之間的這段公案,可說是這種事實結局的顯明注腳。當然,胡適解聘林損,在他看來,是實現自己學術主張,甚至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所以顯得理直氣壯,至于能否合于北京大學由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風習,就不大顧得上了。張中行認為此舉“不免使人聯想到公報私仇”,不知是否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