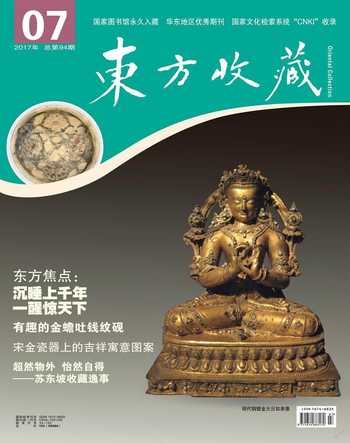再論邛窯外銷陶瓷
董小陳 陳麗瓊
邛窯是四川西南地區的一個龐大窯系,起始于東晉晚期,發展于隋,興盛于唐代,衰于南宋中晚期。以燒青瓷為主,至隋創燒了高溫三色彩繪瓷,自此即兼燒高溫、低溫三色彩繪瓷,以“邛窯三彩”著稱。
關于邛窯的外銷瓷,尚有些學者持疑,其主要原因:邛窯考古發掘材料公布較晚,不為人所詳知,故有研究者把邛窯誤認為其他瓷窯。通過邛窯與唐三彩、長沙窯、越窯對比研究,列舉了研究者把外銷西亞與日本的邛窯誤為越窯,或視為長沙窯感到困惑持疑。根據21世紀長江三峽考古最新出土物與參照文獻為證,提出了邛窯是有外銷的,其路線主要從岷江、涪江、嘉陵江匯長江三峽直入揚州港出海,否定了“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不可能有外銷瓷的臆斷。
邛窯,是四川成都平原及川西南地區的一個瓷窯系,因邛崍市南河十方堂固驛瓦窯山窯最先發現,又最具代表性,故名“邛窯”。邛窯以燒青瓷為主,始燒于東晉,發展于隋,興盛于唐、五代,衰于南宋中晚期,持續時間長達九個世紀。它最大的貢獻,在隋時,受到長江下游越窯的啟迪,率先創燒成功褐、黑、綠的多色高溫彩繪瓷,并對此后的唐三彩及長沙窯的高溫彩繪瓷均有極大的影響。
凡研究我國古陶瓷者,或熱愛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紀的8—10世紀時,我國越窯、唐三彩、長沙窯、邢窯白瓷就以新興的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遠銷到西亞、東非及東南亞領域。“經歷千辛萬苦溝通東西方兩個世界,從而成為中世紀以來深受世界人民所喜愛的貿易商品”。中世紀吋,亦是邛窯的興盛繁榮時期,長沙窯、越窯、唐三彩是外銷貿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窯陶瓷是否也有外銷呢?關于這個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筆者已有論述⑴,但由于當時材料有限,論據尚欠充分,現我們根據長江三峽及邛窯的新發現,進一步與唐三彩、長沙窯、越窯對比研究,認為邛窯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銷瓷商品的。
概述邛窯三彩特點
邛窯主要以燒青釉瓷為主,至隋首先發明創燒了高溫三彩陶瓷,自此后即兼燒多色彩繪瓷,并稱“邛窯三彩”。邛窯三彩的特點,在初創期是采用黑、褐、綠三色或兩色在青釉或米黃白色與灰白色釉上進行彩繪,主要紋飾為聯珠圓圈紋、墨線圓圈紋,相互穿插構成幾何紋;或芳草紋與圓圈紋、聯珠紋構圖,紋樣組合簡雅。這種紋樣在某些方面有似于織錦中的“球路紋”,與古代波斯經常使用的聯圓紋和聯點紋相似。唐代是邛窯成熟與輝煌時期,除沿襲隋之聯珠圓圈紋外,在色彩上,由褐、黑、綠演進為黃、綠、褐、藍、白數色進行彩繪,但以黃、綠、褐三色為主,偶有紅色斑塊紋飾。紋飾組合以黃、綠、褐三色彩繪的芳草紋、卷草紋、祥云紋、寶相花紋;或祥云與芳草紋、芳草與豎條連點紋組合,可更多而廣泛的是隨意揮灑點染的斑塊與散點紋。斑塊紋有的呈圓形、桃尖形和不規則的條形,色彩上有褐色與綠色、綠色與黃色組合,散點形以綠色為主。至五代時,邛窯紋飾更加豐富,點彩技術更為成熟。此外,邛窯還有三彩或兩彩隨意點染于人物或動物的面部與身軀。燒成溫度在1270℃±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邛窯還有低溫三彩,低溫三彩多在黃釉上施褐、綠彩,或模印紋飾。高溫三彩胎多灰黑色、黑紅色、紅褐色、黃褐色,少數黃白色或灰色。露胎部分絕大多數呈深淺不同的黑紅色,黃白色極少。低溫三彩有紅胎、白胎,露胎部分呈磚紅色或黃白色。兩者均在釉下飾白色化妝土(圖1 邛窯三彩)。
邛窯與唐三彩
唐三彩,約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時期⑵。是一種低溫陶器,燒成溫度700℃—800℃之間,其釉色有黃、褐、綠、藍、白等色,而以三色為主,故稱“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單色釉上彩繪,而是以三色點染,色釉相互渾融,流釉明顯,是一種陶器。生產的產品,實用器較少,主要是冥器,但一般的瓶、缽、罐、盤、杯、碗等均屬常見。它的三彩鴨、鵝形杯與邛窯的鴨、鵝形杯多相似,只是質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窯三彩面具、三彩器物蓋以及五代時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細辨別,很可能將邛窯誤認為唐三彩,據唐昌樸先生著《邛窯彩釉的興起及繼承問題》(3),提出了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窯的影響,并推測是武則天將四川的邛窯三彩帶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則天的喜好和推舉,故在武則天掌權以后,京、洛三彩著稱于世。筆者亦贊同這種看法。
邛窯與長沙窯
長沙窯興起于“安史之亂”之際,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⑷。長沙窯亦是在青釉上進行彩繪。兩窯都采用含鐵量較高的粘土做胎,胎之表面多施一層白色化妝土,高溫燒成,紋飾內容豐富,凡邛窯有的聯珠紋、聯圓紋、芳草紋以及褐色、綠色的斑塊紋、條形紋皆有,且變幻豐富勝于邛窯,長沙窯題詩裝飾,及彩繪山水人物畫更是邛窯所不見。邛窯雖早于長沙窯一百多年,在紋飾上不如長沙窯絢麗,但從大的風格看,相似之處亦很迷人。如邛窯和長沙窯在唐代均盛行綠色乳濁釉,邛窯乳濁綠釉始于南朝晚期或隋初,比長沙窯早兩個世紀左右。另外“邛窯與長沙窯的陶工們首先發現了銅紅釉,有意識地進行了試驗,并傳之于世,所以紅銅釉彩的起源應歸功于他們”(5)。關于它們的不同之處,在紋飾上,長沙窯擅長用模印的單件人物與動物紋貼附于執壺或罐之顯眼處,而邛窯則施褐色或黃色斑塊配飾,這是兩窯不同。而邛窯黃色斑塊彩飾,長沙窯至今未有發現。關于碗的裝飾,長沙窯最擅長在碗內進行彩繪,邛窯雖有彩繪但不及長沙窯廣泛與豐富,而邛窯擅長在碗、盤內模印寶相花與昆蟲組合,長沙窯則不多見。在造型上,長沙窯在唐代執壺的短流幾乎全八棱或六至十棱不等,至五代才始有管狀流,邛窯在唐代雖有八棱短流,但絕大部分均為管狀流。碗的造型,長沙窯底足主要為玉璧形與環形圈足,而無餅足。邛窯雖有玉璧底,但絕大多數為餅足,到五代始有環形圈足和圈足外撇。在燒造工藝上,長沙窯是一匣一器,內底光潔無疵,露胎處主要呈黃白色。邛窯是一匣多器裝燒,碗內多有五個不等的墊燒疤痕,露胎處主要呈深淺不同的鐵紅色。盡管有這些不同之處,而共同點仍是較多,關系密切。邛窯與長沙窯所產器物在造型、裝飾方法上多有相似,如邛窯瓜棱形紅彩水盂,長沙窯亦有此類器物傳世,又如邛窯與長沙窯所產之壺,均用褐色斑塊或條形紋在壺身進行裝飾。正如馮先銘先生所言:邛窯與銅官窯(即長沙窯),兩窯所燒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綠斑的風格一樣,輪旋方法上也相同,這些特點不是偶然的相合,說明它們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6)。這密切的關系是什么呢?應是長沙窯繼承發揚邛窯先進技術,又優于邛窯,有別于邛窯(圖2,左圖邛窯三彩,右圖長沙窯三彩)。
邛窯與越窯
越窯歷史悠久,是青瓷創造者。從原始青瓷到成熟的優質瓷器都是它的發展與創造,并于三國晚期首先以釉下褐彩繪制人物、山水與幾何圖案于瓷器上,是最早突破單一青瓷的先驅。唐五代時是它的極盛吋期。邛窯是在它的傳播、啟迪下產生的,還在某些方面繼承發揚了越窯瓷器,如三國晚期的釉下褐彩,邛窯即在它的基礎上于隋代創造發明了釉上釉下的高溫褐、黑、綠多色的彩繪瓷。邛窯由于原料差,胎釉的純凈亮麗、造型的端莊豐富始終不如越窯。但由于市場經濟競爭激烈,邛窯為謀求生存與發展,克服自身原料的弱點,除大力美化邛窯二彩外,還奮力追仿越窯的刻劃、模印紋飾,故在唐五代邛窯在模印紋上表現極為卓越。恰似馮先銘先生所言:“邛窯瓷器在上林湖越窯式花紋很多,還有印花鸚鵡小盒,海棠式杯等”(7)。又如邛窯唐代綠釉印花三出三瓣蓮花紋盤,二出二重仰蓮紋花間蝴蝶飛舞印模,刻劃之細膩,構圖之嚴謹,寫實之生動,雖不言是空前絕后,至少時至今日仍是絕妙的融藝術與實用于一體的杰作。再如越窯五代時的“已”字杯的造型和模印蓮花紋杯,與邛窯內綠釉、外黃釉、內印二重蓮紋杯相似,論其紋飾之優美清晰,胎體之細膩似有勝于越窯(8)。以及邛窯五代的五瓣蓮紋印模,背有銘文“乾德六年(924)二月上旬造官樣楊全記用”,不僅展示出邛窯印花紋精美極致,更充分證實邛窯五代時亦有貢瓷的燒造之務。
唐五代時邛窯有外銷瓷嗎?
中東、東非、西亞以及我國鄰近的東亞與南亞,均在八世紀至十一世紀時出現中國外銷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窯白瓷、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繪瓷,卻不見邛窯瓷器有外銷的記載。究其原因,是邛窯的考古發掘所寫出的詳細報告公諸于世較晚,又或已有撰文發表,實物照片亦不多,故不為研究外銷陶瓷專家學者知曉,同時邛窯與長沙窯、越窯、唐三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淵源關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銷的邛窯陶瓷也誤認為是其他窯的產品,或為不知的窯口對待與持疑。筆者舉例如下:
第一,如《陶瓷之路》日本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開的中國古陶瓷研討會上,把九世紀末十世紀初從中國輸入中東的“寬足圓壁淺碗”定名為越窯青瓷。其論文宣講時,是用彩色幻燈片介紹,我親眼所見,那“寬足圓壁淺碗”實為敞口寬沿,斜弧壁,平足(餅足)碗。特別重要的,在碗底內底有五支燒疤痕,外壁半釉,這種碗,絕不是越窯青瓷碗,十世紀初,即五代時,越窯碗其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內外皆滿釉,多是一匣一器,當然亦有多碗疊燒,亦有內外底有支燒疤痕,可其疤痕特點是長條形砂堆凸起,絕不是似圓非方的無釉疤痕。而這種內底有五支燒似圓非方無釉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窯五代青瓷碗。會中我的論文即《邛窯新探》,還進行交換意見,三上次男先生贊同我的看法。
第二,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葛維漢在撰寫《邛窯陶記》的附注中寫道:“為了寫邛窯陶器這篇文章,我獲得機會訪問歐美一系列博物館,在大英博物館中藏有底格里斯河附近薩馬拉和勃羅明納德遺址(原位)出土的中國瓷器,這些屬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與邛窯出土物極為相似”(9)。這一附注中,又足以說明中東與西亞出土的中國陶瓷中,應有邛窯唐五代瓷器的可能。
2004年筆者曾專程至大英博物館考察薩馬拉遺址8—9世紀出土的中國瓷器,非常遺憾,由于保管人員生孩子休假,未曾見到與邛窯相似的瓷片,但見到了邢窯、定窯白瓷碗、杯等碎片數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紀的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邢窯、定窯、越窯碎片,其中有三片長沙窯彩繪瓷,確實未見有邛窯殘片。可喜的是,在庫存中,看到了20世紀初大英博物館收集的邛窯綠釉龜蓋硯、綠釉小龜、小蛙、三彩人頭塤、葫蘆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窯三彩臉譜殘片與邛窯博物館所藏三彩臉譜極其相似(圖3 大英博物館藏唐代邛窯臉譜,圖4 大英博物館藏唐代邛窯陶瓷),邛窯墨綠彩碗與秭歸出土的邛窯墨綠彩紋碗不僅器型相似,圖案畫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圖5 1996年長江三峽秭歸出土唐代邛窯墨綠彩碗,圖6 大英博物館藏唐代邛窯墨綠彩碗),當然這些不能認定是唐代外銷品,但至少邛窯瓷器也為大英博物館收藏,至于是何時、何地流傳至西亞或歐洲還需研究,不過那臉譜殘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亞或東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館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三,2001年4月在參觀邛窯博物館陶瓷展覽時,當看到邛窯低溫三彩釉時,北大秦大樹教授說:“我在埃及看到這類彩繪瓷時,還以為是清代瓷器,沒想到還是邛窯的產品。”
第四,日本學者失部良明在所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的陶瓷》中寫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黃釉褐彩圓點紋壺,和筑紫野市大門出土的黃釉褐彩圓點紋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妝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來和瓦渣坪窯(長沙窯)同樣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斷是一個窯制的,感到猶豫不決”(10)。即說明在日本出土不少長沙窯的,而其中仍有很難準確判斷為長沙窯出土物,那這又是什么窯呢?迄今為止,與長沙窯相似的只有邛窯,這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共認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在伊朗發現來看,也是長沙窯最多,這足以說明長沙窯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長沙窯,離海岸的貿易港口遙遠,為什么長沙窯會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議的怪事。”(11)。可見三上次男先生對中東與西亞同我國的鄰國出土這么多長沙窯產品,有質疑的感慨,但他僅提出離海岸遙遠為由,我認為那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他所認的長沙窯中有邛窯產品,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第六,國內外學者有認為長沙窯距海岸比邛窯近多了,都有人質疑,同時,又有唐人李白詩言:“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邛窯在蜀中離海岸那么遙遠,會有可能嗎?根據出土物為證,我們認為完全可能:1.據1994年11月中國古陶瓷年會參觀揚州博物館陳列中,即有揚州出土的青釉褐彩斑塊大罐,做工規整,高約40余厘米,施半釉,下腹無釉,露胎呈鐵紅色,未標屬何窯口。筆者當即請問各專家,均言不知,可我確如發現新大陸似的欣喜,這就是邛窯產品(圖7,揚州出土唐代邛窯青釉褐彩大罐)。但是否為長沙窯呢?若單以青釉飾褐彩斑塊而論,長沙窯是有可能的,可長沙窯之青釉多偏黃,此青綠;另長沙窯大件不多,而邛窯在40厘米左右之器較多,從施釉工藝看長沙窯多半釉以下,而最普遍的近足,且其露胎是黃白色。故筆者認為此罐是邛窯的上乘之作,銷售于揚州的貿易瓷,或為外銷海外滯留于揚州(12)。2.筆者近年為考察長江三峽出土歷代瓷器,在峽區沿市縣均見有邛窯陶瓷出土,而以唐代為最多,不僅如此,在峽區還有比邛窯之數量、質量多而美的長沙窯彩繪瓷(13),尤為重要的,于2006年春,專程至峽區的尾端宜昌,溯江而上,在西陵峽考察時,見有2002年巴東、秭歸出土的邛窯唐代陶瓷,粗細皆有,精細的有邛窯三彩模印貼塑蓮花紋薰爐、米黃釉繪綠色單株玉米植物紋大盤。以這些出土物為證,其言“蜀道難”為借口,邛窯不可能有外銷妄作評論而告終罷。

第七,據2007年揚州珍園工地出土的邛窯羊首彩繪褐綠紋壺為證,邛窯絕對有外銷的可能,據揚州文物隊池軍、薛炳宏先生考證,提出揚州唐城出土大量長沙窯彩繪瓷多疊壓于中唐或之前的地層,結合地層關系和伴出物,并參照揚州羅城年代推斷,此件邛窯壺時代可能為中唐時期或之前,邛窯彩繪瓷來到揚州港的時間比長沙窯早。又提出:唐代揚州是全國的重要港口,也是商品的集散地,從全國來到揚州的陶瓷等產品的目的主要是銷售,一部分通過運河及近海轉運到全國各地,另一部分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從東南沿海,直通日本、朝鮮;或從東南沿海,經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東海岸或經紅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邛窯陶瓷來到揚州走的是水路,沿岷江長江順流而下,來到揚州不是孤品,應該是一批產品,從彩繪壺紋飾畫意上推斷可能屬于外銷瓷的一類。(28)
邛窯外銷瓷歷史依據與輸出路線
1.追溯歷史依據
關于成都與邛崍的商品,早在西漢初時,即公元前二世紀左右,就有運至中東與西亞的,具體就是張騫出使西域時,親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與蜀布,據悉是從印度運去的(14)。在漢代,我國與亞歐一些國家已有交往,馬其頓商人(今歐洲巴爾干半島中南部地區),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謂的絲綢之國(中國)販賣絲織物品(15)。至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薩珊王朝遣使來華,其后常有使節來往(16)。到隋,中國和波斯已互遣使節(17),至唐波斯使節不斷來到唐朝,僅永徽二年(651)至貞元十四年(798),正式遣使之記載就有37次(18)。此外,還有唐末隨僖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蘇沙的后裔,與三臺(今四川三臺縣)、成都人融為一體。李珣(855—936)家居三臺,善詞能詩,妹舜弦為前蜀王衍的昭儀女官,地位僅次于皇后和四妃,為九賓之首,長住成都(19)。從以上史料看,成都與西亞的交通和商品貿易、文化交往,從漢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有。
2.唐時的長江商貿
唐代經濟興盛,有“揚一益二”的說法,揚即揚州,益指成都。是唐時兩個著名的經濟繁榮的大都會,兩地商貿往來十分繁忙,以水運最為興旺,杜甫有詩“吳鹽蜀麻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20)及“胡商離別下揚州”(21)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詩,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慶市奉節縣)所作。不僅論述當時成都至揚州水運之暢達,船舶之大、貨物之多,且還有定居中國成都或重慶之波斯商參與商貿,可見成都唐時已是內陸商貿的國際都市了。
3.運輸路線
在唐代,四川交通運輸四通八達。北有金牛道接褒斜道到達陜西;西北有成都與灌縣經桃關、汶川、過松、茂諸州而入吐蕃通西域;從成都經臨邛雋州入南詔而至天竺(22),還有兩岷江、涪江、沱江分別達長江出三峽至揚州。這幾條路線中以水陸最為繁忙,這條航線當時是邛窯輸出的主要交通線。成都是西南航運的重要交通要道。杜甫于成都草堂作詩有“門泊東吳萬里船”(23),說明長江下游的船已航至成都,從出土物看,在長江三峽的巫山、奉節、云陽、萬州至重慶,及三峽下游的巴東、秭歸多出土有長沙窯、越窯、邢窯、定窯、邛窯、洪州窯瓷器與殘片(24)。關于岷江至長江達三峽的記載,有李白詩《峨眉山月歌》(25),“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詩中之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源于四川蘆山縣,流至樂山入岷江,渝州即今之重慶市。關于涪江經嘉陵江至長江向三峽到長江中游轉陸路達河南,有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26)“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今襄樊市)向洛陽。”此外,還有描繪成都與揚州水上航運的詩,即岑參《萬里橋》詩“成都至維揚(今揚州),相去萬余里。滄江東流急,帆去如鳥翅。”(27),是最直接記載成都從岷江出發至長江,與海上交通發達的揚州港口之便捷。
根據以上唐代著名詩人的生活實感所記載,充分闡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發達。因此,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邛窯陶瓷,雖地處內陸,離海岸比較遙遠,然實實在在可從成都直航揚州出海,輸至海外各地的。
后記:照片由邛崍市文管所、尚崇偉先生、宜昌博物館、云陽文管所、大英博物館提供,特此致謝。
注釋:
(1)陳麗瓊《邛窯與銅官窯的關系及邛窯可能有外銷》,載《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論文集》。
(2)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陽博物館編《洛陽唐三彩》,河南美術出版社1985年出版。
(3)唐昌樸《邛窯彩釉的興起及繼承問題》,載《西南師范學院學報》1986年1期。
(4)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出版。
(5)張福康《邛崍窯和長沙窯的燒造工藝》,載耿寶昌等主編《邛窯古陶瓷研究》,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6)馮先銘《從兩次調查長沙銅官窯所得的幾點收獲》,載《文物》1960年3期。
(7)同(6)。
(8)童兆良《上林湖越窯單子款》,載《2002年越窯國際學術討論專輯》195頁圖五十,杭州出版社2002年出版。
(9)[美]葛維漢著,成恩元譯《邛崍陶器》,載《四川古陶瓷研究》第一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
(10)[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時代的陶瓷》,載《中國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二輯,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于1983年編印。
(11)三上次男《伊朗發現的長沙銅官窯與越窯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載《中國古代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
(12)關于揚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塊大罐,經《長沙窯》專著主筆周世榮先生審視,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筆者意見。
(13)胡習珍《長江三峽地區出土的長沙窯瓷器》,載《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輯,303頁。紫禁城出版社2006出版。
(14)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卷123,3166頁,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15)周谷城《中國通史》上冊418頁。
(16)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三冊330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7)同(16)第四冊506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陳坦學術論文集·回回族入中國史略》548頁,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19)魏堯西《雜談西蜀詞人李珣》載《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683年3期。
(20)杜甫《夔州歌十絕句》之六,載《全唐詩》卷230,5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1)杜甫《解悶十二首》,載《全唐詩》卷230,5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
(22)蒙漠、劉琳、唐光沛等著《四川古代史稿》200-20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23)同(21)杜甫《絕句四首》之三,卷415,563頁。
(24)《湖北庫區考古報告集》卷一,95頁,557頁,671頁,卷四24頁,151頁,159頁,393頁,科學出版社出版。《重慶庫區考古報告集》1997卷,91-97頁,181頁,317頁,342頁,1998卷52頁,280頁,287頁,390頁,1999卷24頁,75頁,211頁,447頁,493頁,674-677頁,科學出版社出版。徐光翼主編《三峽文物搶救紀實·永不逝落的文明》139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出版。
(25)同(21)李白《峨眉山月歌》卷167頁,394頁。
(26)同(21)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卷401,577頁。
(27)同(21)岑參《萬里橋》卷198,465頁。
(28)揚州考古隊 池 軍、薛炳宏《沉睡古窯瓷,出土驚天下-談揚州珍園工地出土唐代邛窯瓷器》載《揚州文博研究集》101頁,廣陵書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