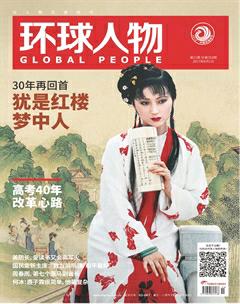姜德明,天生癡情唯有書

每次見到姜德明先生,我總會想到那句“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有一年,我陪《錢江晚報》記者張瑾華、馬黎去采訪黃永玉先生。在畫室的墻上,正好掛著黃先生書寫的這副對聯,后來黃先生還在對聯旁拍了照。
姜德明曾是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退休前幾年還出任了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其間推出了以“百家叢書”為標志的一批好書,是一位具有文人情懷的出版家。他與書有緣,可以說,書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
在1987年調到人民日報文藝部之前,我就與姜德明認識了,一直喊他“老姜”。我與老姜緣起于約稿,相識時他還不到60歲。當時,我在《北京晚報》編輯五色土副刊,開設了“居京瑣記”欄目,因為很喜歡老姜的書話與隨筆,便寫了約稿信。1985年10月,老姜寄來文章《戲單》,寫他留存的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戲單。他在1950年看了此劇,三十幾年后重看戲單,感慨頗多:
翻看這戲單,我的眼睛有些潮濕了。
我舍不得丟棄它,盡管戲單的紙發脆發黃了,卻分明又染著我青春時代血紅的顏色。就像戀人們保存著永不褪色的紅葉一樣,它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今后,我仍將珍惜地保存著它。三十五年來,我很少再在劇場里那樣激動地看過戲了。一翻這戲單,我就想起當年的那些青春伙伴。如今我們山南海北,都已年近六旬,成了老頭和老太婆了。我們當中有的歷經坎坷,包括已經不在人世的,都保持著青春時代的真誠。我愿借著這份戲單,留下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留下那些使人難以忘懷的歷史風雨。
通過戲單,老姜感悟生命,重溫他們那代人從風雨坎坷中走過的青春歷程。我當即去信,請他寄來照片,以便請丁聰插圖。丁聰很快為《戲單》配了一幅精彩的插圖。
從最初相識到同在一個報社工作,三十幾年來,我們每次交談,主要話題總是書:書的版本變遷,作者的命運遭際,逛舊書攤淘書的樂趣……“有意思!真有意思!”他連聲感慨,臉上是掩不住的興奮和陶醉。我覺得,一個人的興趣決定著他的文化情懷與走向。藏書和藏戲單都是老姜的興趣所在。正是這種留存老物件的興趣,使他在前輩唐弢之后,成為當代藏書豐富、藏名家書信豐富的藏書家。
如今,收藏已成為一種時髦,或者說一種投資方式。可對老姜而言,藏書是他偏愛歷史、景仰前輩文人的方式。沒有這樣一種與書的天生癡情,他就不會在貶低文化的年代,還把業余時間和有限的財力,幾乎都用在逛舊書攤和古舊書店上。對文化的特殊情感使老姜具有獨特眼光,他喜歡收藏“五四”時期作家們的簽名本,搜尋到了一些曾受到冷落的孤本、珍本。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真正文人與書之間純粹、真誠的情感。如老姜在《戲單》中所說,是戀人之間的永不褪色的紅葉。
老姜還珍藏了大量前輩文人寫給他的信。有一次在他家,我們聊到興起,他拿出這些信讓我欣賞。葉圣陶、茅盾、俞平伯、巴金、孫犁……他們在信中談書、談掌故、談那些不大時髦卻仍令他們迷戀的話題,可見都把姜德明視為知己。兩代文人的情懷因而連結在一起。
1989年秋天,我常到老姜的辦公室里聊天。一次,他對我說:“你何不去圖書館,找找《國聞周報》,當年丁玲失蹤、被捕后,沈從文的《記丁玲女士》就在上面連載。這個連載后來結集成《記丁玲》,有過不少刪節,你可以去校勘一下。”
多好的建議!我歷來喜歡翻閱史料,從不覺得枯燥。于是一連幾個月,我坐在圖書館里翻看《國聞周報》。讀后,我再將它們復印,細細校勘,在沈、丁半個世紀的交往故事里,追尋文人間的恩恩怨怨。我還分別從唐弢、范用兩位先生那里借來了《記丁玲》上、下兩冊,將之與連載進行校勘。最后發現刪減部分,多達數百處、數千字。
校勘之際,我忽然想到,何不請熟悉的前輩,講講他們眼中的沈從文與丁玲。于是,我在1990年走訪了巴金、張兆和、施蟄存、趙家璧、蕭乾、冰心、凌叔華、陳明、劉祖春、汪曾祺、林斤瀾、徐遲、周明……在他們的回憶中,歷史的恩恩怨怨,漸次分明。看似個人間的交好、決裂,恰是那一代文人身處歷史漩渦之中不同選擇的呈現。
1992年11月,我終于完成了這段難得的歷史追尋,出版《恩怨滄桑——沈從文與丁玲》一書,由老姜寫序。他詳述了與沈從文、丁玲各自的交往,并提出了對我的建議:
我同本書作者李輝同志相識的時候,彼此還是編者與作者的關系。后來他調來我們單位,彼此又成為同事。我們年齡有別,業余愛好卻有些相似。有暇時我們常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但八成離不開現代文學,離不開作家和書刊。我們都有很多美麗的夢,想弄這又弄那。……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無精力做的事告訴他,希望他來完成。當年我曾經想找出最早發表沈從文記丁玲的《國聞周報》,據以校勘輯錄出使國民黨審查機關刪割的文字,我以為這是很重要的工作,應該有人來做。少壯派的李輝一口應承了。從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來,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發展,結果遠遠超過了我原先設想的規模,不僅僅是研究著作,已經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風有雨,有恨有愛,有情有理的可供廣大讀者欣賞的文學讀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書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訪問各位知情者,我很羨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見識和工作熱情。
我感謝老姜。因為有了這本書,我的寫作風格也有所改變,兩年后,在《收獲》雜志開設的“滄桑看云”專欄,由此而延伸。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與思和兄策劃出版“火鳳凰文庫”系列,請老姜編選《流水集》列入其中,并于1997年出版。2000年,我策劃了一套袖珍版“大象漫步書系”,再次約請老姜編選《獵書偶記》列入其中。老姜還為這本《獵書偶記》寫了一篇頗為有趣的前記,記錄了他與人民日報圖書館老館長謝興堯先生的交往故事:
集近兩三年寫的隨筆,編完這本記書人書事的《獵書偶記》,拍拍手松了一口氣。完成一件工作總是愉快的。因想張守常教授托我轉交謝興堯先生的《太平軍北伐叢稿》留在舍間幾天了,這是一本新著,理應讓研究太平天國的專家先睹為快。說走便走,拿起書就上路了。
謝老今年九十五高齡,這天睡到上午十時才起身。我問他天天如此嗎?他說不是,昨夜失眠,今天起遲了。我說何不吃點安眠藥。謝老說,他什么藥也不吃,現在的藥吃了也不管事。這是老人的幽默吧,意指市面上假藥的泛濫。
順問老人對電視連續劇《太平天國》的看法,回答說看過了,那是玩藝兒,娛樂么,怎么拍都可以,不必反對。這同歷史是兩碼事,若講歷史可就沒那么好玩了。又講到他有時還寫點毛筆字,不過幾句題跋之類。別的不敢動了。
老人問我還常寫東西嗎,我說偶一為之。他忽然冒出一段北大往事。那年,他用三十元買了一套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是線裝本,裝滿了一輛人力車。見到胡適時他講到此事,隨口說了句,好像《飲冰室文集》里也沒有太多的東西。胡氏大不以為然,很嚴肅地跟他講起梁氏的學問,認為那也代表了一種新思潮,不應對故人這么漫不經心。這件事對他影響不小。
莫非謝老有意在寫作上想指點于我?因為我寫書話亦時涉前人。
老姜的文字就是如此,少雕琢,平淡樸實,卻借一段故事,談學問與寫作的關系,耐人尋味。
我與老姜同住在一個大院,他的藏書就成了“強大后盾”,讓我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時寫文章,我缺少老書或者舊雜志,便打電話去詢問。不出幾天,他就會找出來讓我去取。
在“滄桑看云”專欄中,我曾寫過一篇關于田漢的《落葉》。多年后,老姜還記得此事。一次去看他,他拿出一個大信封交給我,里面是他整理出來的與田漢相關的資料。多好的前輩,時時想著我寫過的人物,清理資料時總會給我留下一些什么。這些文人情懷,時時溫暖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