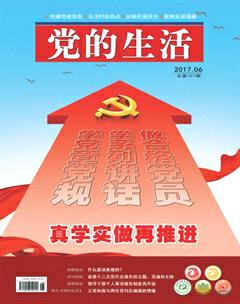為了那份重托
李長文
榆葉梅綻放清香的晨曦中,隨著此起彼伏的雞鳴聲,建設村醒來了。當許多村民家的煙囪升起裊裊炊煙時,街巷上有一群人正在清掃道路。
“李書記早啊!”
“起來了東子?”
掃街的隊伍中,一個身著迷彩服、足蹬解放鞋的中年人聽到過往村民與他打招呼,就直起腰回應一聲,或點下頭笑笑。
他叫李曉東,建設村黨支部書記。
正當不惑之年的李曉東從小生長在建設村。1992年初中畢業后,他外出打工,從建筑工地的水泥攪拌工到機器操作員,憑著一股踏實勁兒,贏得了企業老板的認可,成為獨當一面的項目經理,并且入了黨。再后來,他懷揣著夢想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披星戴月的打拼中,年收入幾十萬元。
“東子就是有本事,這才幾年啊,自己當了老板。”村里人閑聊的時候,常常把李曉東作為話題,嘆服,羨慕。
無論生意咋興隆,在李曉東心中,淡不了的是鄉情,抹不去的是鄉愁。在外創業的20年間,只要回村,他總要去一些老輩人的家里表示下心意;村里公共設施建設捉襟見肘的時候,他是“能拿錢就拿錢,能拿物就拿物”。他的企業在大慶市落戶后,建設村的村民始終是公司用工的首選。
在村民眼中,發達了的“李老板”始終是那個憨厚樸實的“東子”。然而,“東子”每每看到村里的貧窮與落后,一股淡淡的憂愁往往“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2013年年底,建設村“兩委”班子因嚴重內耗難以為繼。一天,老人們湊到一起說起建設村未來,長吁短嘆中,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建議:“這些年,曉東發達了都不忘幫家鄉人,能不能把他請回來當支書?”
大伙兒都說這個主意不錯,可又覺得不太現實——人家在外邊干得那么好,能愿意回來接這么個爛攤子?幾經商量,他們決定試試,并把“請諸葛”的任務交給了曾經在李曉東的公司上班多年的黨慶胡。
“東子,村里人都想讓你回去帶著大家致富呢!”見到李曉東,黨慶胡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是受托而來,“看看村里的破敗樣,大伙兒說也只有你能挑起這個擔子。”接著,老人掏出一封讓李曉東感動至今的聯名信——希望他能回來帶領全村人走出困境。信的末尾,是十幾個紅彤彤的手印。
面對這份信賴,李曉東不知說什么才好;面對這份期待,李曉東感到從未有過的糾結;面對這份感動,李曉東活心了。
家人一致反對。妻子敲警鐘:“醒醒你的書記夢吧!”
父母則擔憂:“這建設村的窮根兒,你得拔到啥時候是個頭兒啊!”
鄉親們的堅持,鎮黨委的信任,點燃了李曉東建設家鄉的夢想。他苦口婆心地說服家人,毅然決定:回村!
2014年1月,帶著全村人的期盼、建設美好家園的夢想,“李老板”成了“李書記”。
然而,即便做好了迎接各種困難的心理準備,但真正走馬上任后,一個個令人頭疼的麻煩事,就像一場場猝不及防的暴風雨,迎頭澆來。
第一個難題是,如何收回被村民無償耕種的機動地。
嘩啦!辦公室的窗戶玻璃碎了一地。熟睡中的李曉東被驚醒,翻了個身看了看,又躺下了。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驚嚇了,從宣布收回被村民無償耕種的機動地那天起,辦公室的玻璃就碎了一茬又一茬。
“先把你舅的地收回來再說!”有人直戳李曉東的軟肋——舅舅是李曉東在建設村唯一的至親。
那一夜,李曉東幾乎沒合眼。這燙手的“山芋”既然接了,就得吃下。
早上起來,他來到舅舅家,尚未進屋,舅舅的冷言冷語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無奈,李曉東扔下500元錢,說:“舅,機動地今天就得收回來,這些錢權當外甥給你的補貼吧。”說完,他轉身出了舅舅家。
剛走到地頭,好幾個村民就將他團團圍住,你一言我一語,火藥味十足。就在這時,李曉東的舅舅趕來了,大老遠就喊了一嗓子:“東子,我的地你處理吧!”
李曉東愣住了,眼圈紅了;圍他的人不說話了,紛紛散去。
隨即,1000畝違規地全部收回。經過重新發包,兩年共36萬元的承包款填補了建設村的虧空。
村民們對這個離村多年的“東子”真正刮目相看了。
建設村的歷史欠賬太多了,而千難萬難,出行是第一難。
2014年入夏后的第一場大雨倏然而至,把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走的村民都逼到了村委會辦公室門前的那條甬道——村里唯一的硬化路。外出剛回村的李曉東見此情景,忙招呼大伙兒進辦公室避雨。推開門的一瞬間,只見幾名村干部正有說有笑地打著麻將,李曉東的氣不打一處來,快步上前一把掀翻了麻將桌。
村干部們傻眼了,村民們看呆了。凝重的氣氛一直持續到天放晴,村民們悄悄議論:“曉東真是個茬子。”“村路這回有戲了。”
村民們沒猜錯——李曉東決心修村路。
修路當然是民心所盼,但村里一分錢都拿不出來。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讓村干部們手足無措。李曉東只好硬著頭皮、厚著臉皮到縣直有關部門去求援、去“磨叨”,幾經努力,終于爭取到200萬元資金。
修路那段時間,李曉東整天一套迷彩服,一雙膠鞋,與筑路工人們一道頂著烈日施工。村干部加入進來了,黨員們行動起來了。當一條條平整的路面鋪就,竣工那天,村民們開心得歡呼雀躍,放起了鞭炮慶賀。
路修完了,村干部、黨員們也變了樣——每月的義務勞動,他們沖在前邊;每天早上清掃街道,村干部、黨員也成了“建設村一景”。
啃掉“硬骨頭”,讓村民和黨員看到了李曉東的意志和能力,渙散多年的心漸漸向村黨支部靠了過來,村“兩委”重新贏得了百姓的信任與支持。
隨著多年沒人敢碰的機動地難題得以化解,多年望洋興嘆的行路難問題得以解決,李曉東心中的夢想也一點兒點兒變大。
單一的種植結構,是沒有資源稟賦的建設村實現致富必須突破的一個瓶頸。那么,改種啥?誰來改?對于離土離鄉務工經商已經20多年的李曉東來說,真是個嶄新的難題。
正當李曉東一籌莫展時,黨員李忠玉、朱長友和出面請李曉東回村的黨慶胡老人聚攏到他身邊。“你為村里做了這么多實事兒,我們得幫你多分擔分擔。”幾個人表態:愿意拿出近百畝地,做調整種植結構的試驗田。
李曉東的心一下子敞亮了,帶領他們到縣有關部門請教農技人員,到大慶市有關部門咨詢農業專家。經過反復調研論證,2015年,建設村種了百畝雜糧試驗田。當年秋收一細算賬,每畝雜糧比玉米多收入300余元。2016年,看出門道的村民將3000畝土地改種了雜糧。那年,玉米價格大幅下降,而建設村卻因大面積種植雜糧減少了損失,增加了收入。
為了讓鄉親們的糧賣得好,李曉東以招商引資的名義請朋友到村里投資。不到一年,收儲點的糧倉建起來了,李曉東卻向前來投資的朋友提起了條件:收建設村的糧食,得比別的收儲點兒價格高。
看著已經完成的基建,朋友大呼“上當”:“這小子,把我們給忽悠了!”而建設村村民的心里卻樂開了花。
種植結構調整有了進展,李曉東又有了新的擔憂:如果都種雜糧,就又陷入了結構單一的怪圈。怎么打破這個怪圈呢?李曉東經過調研提出:利用尼爾基水庫資源,推動全村的旱改水工程,打造“農家樂”,發展生豬養殖,推廣棚室蔬菜……
2016年10月17日,一天到晚不停忙碌的李曉東病倒了。住院的日子里,李曉東終于有空想想與家人有關的事了:2015年父親去世時,自己不在身邊,那份歉疚與遺憾總是縈繞心頭;自己的身體不好,妻子希望他借機趕快回城。他也在問自己:如今建設村已經有了點兒模樣,是不是可以抽身了?
就在李曉東糾結時,村民們推選代表,帶著大伙兒集起的10萬元錢,來到李曉東的病房。
“我們給你開工資,你不能走。”
“你要是不干了,旱改水還繼續嗎?”
李曉東謝絕了鄉親們給的“工資”,但那些期盼的眼神和當初請回自己的聯名信一樣,觸動著他的內心。
出院之后,李曉東又踏上了建設村的圓夢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