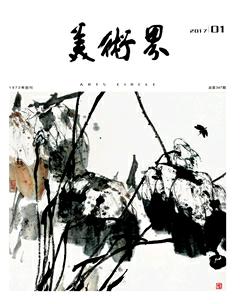深入認(rèn)識并理解中國畫的本質(zhì)和自律性
只有堅(jiān)持正確的文化立場,才可能正確地認(rèn)識和理解中國畫。中國畫是以中國文化和哲學(xué)為基礎(chǔ),西畫是自然科學(xué)為基礎(chǔ),由于基礎(chǔ)不同,兩者在藝術(shù)精神、造型觀念、風(fēng)格特征、觀察方法、表現(xiàn)法則、繪畫語言等方面產(chǎn)生很大差異性。要想學(xué)好中國畫,就必須深入認(rèn)識和理解中國畫的學(xué)理本質(zhì)和它自身內(nèi)在的規(guī)律性。我從以下幾方面試做分析:
一、中國畫的“中國精神”和“寫意精神”
中國畫在中國人心目中占據(jù)著崇高的地位,它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和哲理文思內(nèi)涵,不僅是純技術(shù)的表現(xiàn),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體現(xiàn)。因而與中國民族精神的三大支柱“儒、釋、道”文化樹人、治藝相一致。這樣的民族文化精神決定了中國畫必然既不拘于客觀物象,也不限于個體世界,而是在“技進(jìn)乎道”“技道統(tǒng)一”中,以大道至簡的筆墨表現(xiàn)形式完成主體精神的高揚(yáng)和自由馳騁。因此,中國畫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寫意精神,寫意精神不僅是中國畫的精神,也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這種精神是跟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形從意”“法從意”藝術(shù)法則、尊重個體生命和自然生命的哲學(xué)精神相統(tǒng)一。
寫意精神是中國畫的核心精神,中國畫不管是工筆還是沒骨、小寫意、大寫意等畫法,其本質(zhì)都是“寫意”的,寫的是由自然物象到畫面意象的象內(nèi)、象外之意和畫家主體的心中之意。中國畫的寫意精神之所以能在繪畫語言“筆墨結(jié)構(gòu)”形式中得到具體體現(xiàn),除了得力于詩畫融通的意象境界外,主要來源之一是“書畫同源”的藝術(shù)觀念,具有書寫和瀉意性的線條、墨法為中國畫寫意精神的體現(xiàn)提供了神奇的表現(xiàn)手段。
近一百多年來,在改良主義以西畫改造中國畫觀念的影響下,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受到很大的消蝕和破壞,當(dāng)前有相當(dāng)多的中國畫作品表現(xiàn)出嚴(yán)重的制作化、工藝化、素描化傾向,長此以往,中國畫的文化基因和藝術(shù)精神必然會變異,真正的中國畫也可能會從地球上消失!(當(dāng)然相信不會消失,因我們相信中國畫的民族性和強(qiáng)大深遠(yuǎn)的生命力。)所以我們要深入理解和領(lǐng)悟中國畫的寫意精神,守住中國畫的文化精神底線。
二、中國畫的“意象造型觀”
在造型藝術(shù)中,全世界的繪畫分兩大類:以中國畫為代表的東方繪畫和以油畫為代表的西方繪畫。兩類各異,潘天壽先生說:“東方繪畫之基礎(chǔ),在哲理;西方繪畫之基礎(chǔ),在科學(xué);根本處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極則。”因此,中西繪畫的極則主要表現(xiàn)在造型觀的絕然不同。科學(xué)思想決定了西畫的寫實(shí)造型觀念,決定了它在斷裂式變革中卻始終不離其根——寫實(shí)性;便決定了它對客體寫實(shí)素描的造型手段,而且是在其藝術(shù)體系中占主導(dǎo)地位并具有獨(dú)立訓(xùn)練的意義和可能。中國畫傳統(tǒng)中從不使用“造型”和“素描”這兩個詞,因“造型”不能從意象的意匠中獨(dú)立出來,它只能作為一個要素包涵在中國畫體系“技”“道”合一的法統(tǒng)之中。因此,關(guān)于中國繪畫“意象造型”的理論體系和畫學(xué)、畫技均在中國畫的整個道統(tǒng)之中。從《周易》的“象”、老子的“氣”“道”“象”、孔子的“繪事后素”、《淮南子》的“神貴于形”、謝赫的“六法論”、顧愷之的“以形寫神”的傳神論、蘇東坡的“始知真放本精微”和“常形”“常理”論一語道破寫意神髓,到現(xiàn)代的齊白石的“似與不似”,黃賓虹的“不似致似”,等等,絕妙地闡述了中國畫“意象造型”觀的深邃之理。中國繪畫秉持這種“觀念”和規(guī)律,實(shí)踐了幾千年,攀登到了世界“造型”藝術(shù)的審美最高峰,讓國內(nèi)外外行人望洋興嘆。
20世紀(jì)以來,中國畫教育“以西畫改造中國畫”之風(fēng)盛行,以寫實(shí)造型觀代替中國畫意象觀,即以西方素描代替了中國畫“技”“道”合一的基本功力訓(xùn)練;在寫實(shí)狀物能力上雖有裨益,但卻丟失了獨(dú)有的筆墨語言的審美含量和表現(xiàn)力,已有偏離中國意象藝術(shù)軌道的傾向。加上文化語境逐漸變遷等因素,造成了中國畫傳承的空前危機(jī)。其問題的要害在于:在幾十年的教學(xué)中,造型觀念、造型方法被西畫代替的同時(shí),將素描造型訓(xùn)練與中國畫的筆墨表現(xiàn)之道嚴(yán)重分離,致使心手不能相應(yīng),顧此失彼,導(dǎo)致了不少人拿毛筆、用水墨畫素描的后果。
中國畫自身的生命力及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yùn),決定著它可持續(xù)自律發(fā)展的無限性和融納百川的可能性。至于中西繪畫之爭,當(dāng)下亦可休矣!過去的一百年中,“改造”與“反改造”的教訓(xùn)及中國畫應(yīng)對的自醒、自律發(fā)展的經(jīng)驗(yàn)亦足矣!如能冷靜思考認(rèn)真總結(jié),遵照潘天壽先生提出的“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論,明確文化立場,“兩端深入”(潘公凱);不論是西畫的民族化,還是中西融合、“以西潤中”(薛永年)或傳統(tǒng)出新,在世界文化藝術(shù)的互補(bǔ)互用中,保持人類文化文明的高度多元,只要堅(jiān)持本體藝術(shù)之道,并深明“技”必從“道”之理,做好互用因素的藝術(shù)語言轉(zhuǎn)化。在這個前提下,不管是“中西融合”“以西潤中”“以中國畫改造西畫”抑或是傳統(tǒng)出新,都是可行的,合理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出現(xiàn)中華藝術(shù)多元繁榮的新局面。
三、中國畫的“筆墨結(jié)構(gòu)”
中國畫筆墨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元素是中國書畫的“一筆”功夫。中國書畫最基本的“一筆”中包涵著非常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審美意蘊(yùn),有獨(dú)立的審美價(jià)值,是典型的“中國功夫”。中國書畫的“一筆”,講究要有筆法,有了筆法,意自法生,自然就有了“筆意”,中國畫“千狀萬態(tài),筆簡而意足”(歐陽修)。中國畫的一點(diǎn)一線、一筆一墨除了有其獨(dú)立的審美價(jià)值外,還有很高的狀物功能。筆法、筆意已為中國畫的意象狀物能力奠定了基礎(chǔ),足以神明地將法、意、形統(tǒng)一于“技”“道”合一的法則之中,成為獨(dú)特的意象造型體系的構(gòu)成因素。由于筆法、筆意通神、通道、通造化,物形、物態(tài)、物神必在其中。筆法的嚴(yán)正來自哲思、物理,用筆有神、妙、奇、巧之功技,意境深邃,氣韻在胸,為意象立,“心隨筆運(yùn)”“取象不惑”“隱跡立形,備儀不俗”。這也是中國畫“不似致似”(黃賓虹)的法理。中國畫在一筆一墨中、一點(diǎn)一線的筆法筆意的基礎(chǔ)上,要寫出具體物象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神情氣度和形、質(zhì)、動的必要因素,這就是中國畫的藝術(shù)觀及“造型”觀。一筆一墨形態(tài)中的文化內(nèi)涵,即為中國畫的哲思文理之道。所以,中國畫從境界到藝術(shù)語言的一筆一墨皆蘊(yùn)含著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和中國畫的意象精神,一筆一墨皆是學(xué)問修養(yǎng),此為中國畫之獨(dú)到,其他畫種未涉足之領(lǐng)域。另外,從一筆一墨中可以看到畫家的個性、胸襟。說起個性,人人都有,但將個性融入自己的藝術(shù)之中,在一筆一墨中表現(xiàn)出來是極難的事情,個性既要鮮明、本真,格調(diào)高雅,不要故作姿態(tài),并能將它寓于民族性、現(xiàn)代性和本體藝術(shù)的特征之中,方可成功;獲得個性與藝匠的融通,達(dá)到出神入化之境。正是中國畫意象和寫意中強(qiáng)調(diào)的“內(nèi)美”特質(zhì),是世界繪畫的審美極致,體現(xiàn)了它的民族性、獨(dú)特性和現(xiàn)代意義的世界性。
什么是“筆墨結(jié)構(gòu)”?有了最高質(zhì)量和最大含量的“一筆”,以形態(tài)豐富各異的一筆一墨為因子,通過它在特定環(huán)境和畫面的題材、主題、造境、章法、布局等中的銜接、對比、轉(zhuǎn)換與滲透及筆墨的復(fù)加、沖、破與黑白、虛實(shí)的合成有機(jī)的排列組合,形成一定的韻律和節(jié)奏,構(gòu)成完美的“意象造型”,包括空間在內(nèi)的虛實(shí)境界,加上題跋鈐印,從而表現(xiàn)出具有一定審美意義的生命運(yùn)動與畫家藝匠、氣質(zhì)鮮明個性及藝術(shù)品格的完整畫“體”——畫面從局部到整體,從形象到空間的整體筆墨結(jié)構(gòu)。對創(chuàng)作而言,是審美主題的物化,同時(shí)也成為欣賞者汲取中國畫作品內(nèi)在精神的物質(zhì)媒介,亦為鑒定、批評作品真贗高低的首要因素。所謂“筆墨結(jié)構(gòu)”,其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理法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表現(xiàn)物象結(jié)構(gòu),依據(jù)物理的形、質(zhì)、動概括出來的點(diǎn)、線形態(tài)在自然生長規(guī)律(即常形常理)的制約下進(jìn)行組合;二是筆法、筆意在運(yùn)動間與表現(xiàn)畫體意象統(tǒng)一中的銜接、對比、轉(zhuǎn)換、滲透和行氣的節(jié)奏韻律,并與主題精神結(jié)合形成的筆墨組合形式(依據(jù)中國審美對自然和技法的超越)。以上兩個方面的結(jié)構(gòu)特征在形與神、理與法、技與道的高度結(jié)合完美統(tǒng)一下,形成了中國畫極為豐富、極高表現(xiàn)力的筆墨結(jié)構(gòu)乃至藝術(shù)程式。
說起“程式”,中國藝術(shù)多具程式。中國畫、戲曲、詩詞包括許多民間技藝,中國人玩什么都玩得很精,均有高度程式。我認(rèn)為凡藝術(shù)發(fā)展到一定高度才形成程式,程式是法之根,代表著藝術(shù)體系、規(guī)律的成熟與完善,代表著這一藝術(shù)的高級性和經(jīng)典性。我們從事中國畫的學(xué)習(xí)與創(chuàng)作就必須通過程式去尋找藝術(shù)規(guī)律,既由“度物得道”,再“度法思道”,又由“道”進(jìn)“技”,“技”“道”統(tǒng)一。
四、中國畫的“黑白韜略”和“開合戰(zhàn)略”

在中國畫的筆墨結(jié)構(gòu)中,有完成意象形象的筆墨點(diǎn)線組合,更有表現(xiàn)整體布局的黑白、空間、虛實(shí)、呼應(yīng)成章的集團(tuán)式筆墨組合結(jié)構(gòu)。運(yùn)筆運(yùn)墨時(shí)筆筆的起收方向與動態(tài)必須依照畫面氣脈主線起、承、轉(zhuǎn)、合的戰(zhàn)略部署去排列組構(gòu),即可完成畫面內(nèi)外整體格局,使其真體內(nèi)充并溢于畫外。這正是創(chuàng)作欣賞中國畫的最終意旨。中國畫的“黑白韜略”來自于傳統(tǒng)哲學(xué)的陰陽、黑白觀念,老子的“知白守黑”,成為畫中布黑用白的法則,因此發(fā)展了中國繪畫的多種對比關(guān)系。黑白就成了中國畫審美主體之一。畫畫在畫什么?可以說“畫黑白”。在黑白對比、黑白塑形中,空白本身就有形,并分虛實(shí),同時(shí)又決定著畫體的捭闔造型,其中空白的實(shí)虛也是關(guān)鍵,實(shí)空白決定氣象的形體分割,即大小分合;虛空白決定形體的虛實(shí)、空靈、厚度和豐富性。同時(shí),空白還關(guān)系到畫內(nèi)畫外氣量的吞吐,從而滿足我們對畫體的氣格與審美需求。
中國畫的不寫實(shí),意象表現(xiàn)中往往講“畫意不畫形”“畫氣不畫形”“舍形而悅影”“形神兼?zhèn)洹钡取.嬛行巍⑸瘛⒁狻馊诋嫛绑w”之中,“體”又重在氣、勢、力凝聚而成的氣勢線,在畫內(nèi)外跌宕、起伏的起、承、轉(zhuǎn)、合的大小開合的關(guān)系之中。因此,中國畫極重視的氣韻、氣骨、氣格及神逸之境的呈現(xiàn),完全依賴畫家如老將搴旗,胸有成竹地布施黑白、開合戰(zhàn)署中揮運(yùn)筆墨結(jié)構(gòu)軍團(tuán)去完成畫體藝術(shù)表現(xiàn)。
在以上所提的幾點(diǎn)中,“筆墨結(jié)構(gòu)”觀念是理解和學(xué)習(xí)中國畫的認(rèn)識論和方法論,把握了這一點(diǎn),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國畫的本質(zhì)。中國畫的這些特質(zhì)和內(nèi)在規(guī)律都是由其文化哲學(xué)根基所決定的,同時(shí)這些特質(zhì)也決定了中國畫教學(xué)和傳承必須與此相一致;在這些基本精神和本質(zhì)規(guī)律的指導(dǎo)下開展臨摹、寫生和創(chuàng)作“三位一體”的教學(xué)活動就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不但會收效甚微,甚至?xí)限@北轍。擴(kuò)展開來說,中國畫的鑒賞、鑒定、傳播交流等活動都應(yīng)以此觀念為指導(dǎo)。
(本文由賀文龍博士據(jù)2016年10月電視臺《書畫頻道》舉辦的《張立辰中國寫意畫高級研修班》系列講座授課記錄整理并節(jié)選以上內(nèi)容,經(jīng)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