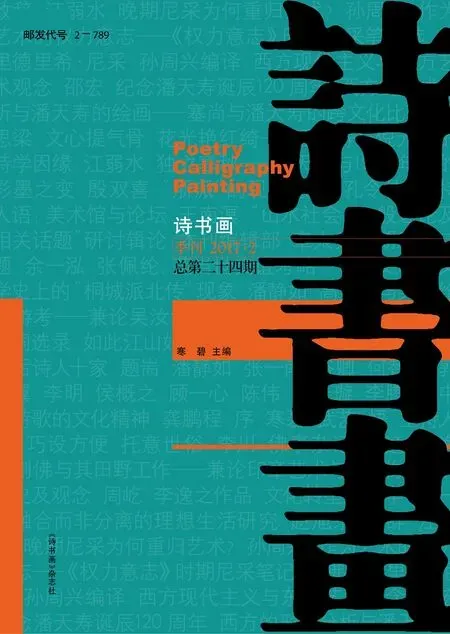晚期尼采為何重歸藝術?※
孫周興
晚期尼采為何重歸藝術?※
孫周興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學通常被分為早、中、晚三期。一般認為,早期尼采重視藝術,主張一種“悲劇形而上學”;中期尼采變了腔調,棄藝術而倚重于科學;晚期尼采致力于營造他的“哲學主樓”,形成了一種“權力意志的形而上學”。這種看法略顯粗糙,但大致不差。不過,我們的問題在于:在晚期的大量著述中,特別是在他的筆記遺稿中,尼采何以又重新大談藝術,標榜“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
或者我們干脆問:晚期尼采何以重歸藝術?

尼采
早期尼采受音樂大師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影響和激勵,在《悲劇的誕生》(1872年)一書中形成了關于希臘藝術文化的系統分析,并且把希臘悲劇藝術標舉為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藝術的典范樣式。這時的尼采與瓦格納可謂情投意合,兩人都懷著通過藝術重建神話—重新激活神話—的共同旨趣。瓦格納的戲劇以北歐神話(古日耳曼神話)為題材;而尼采這本《悲劇的誕生》則是以“悲劇時代”的古希臘文化為主題的—這無疑是尼采比瓦格納高明的地方,古日耳曼神話畢竟局限,僅限于德意志民族,而古希臘神話則是全歐洲文明的原點和本源。雖然尼采反對以溫克爾曼為代表的歐洲古典學者們對古希臘藝術和文化的理解和規定,但我們看到,他最后為我們端出來的也無非是一個“樂園模式”,即“樂園—失樂園—復樂園”三步曲方案:悲劇代表著希臘藝術和文化的完美狀態,即酒神狄奧尼索斯元素與日神阿波羅元素的二元性結合;自歐里庇德斯和蘇格拉底開始了希臘悲劇文化的衰落和科學樂觀主義(理論科學)的興起;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通過藝術挽救頹敗文化的重任,而瓦格納大師已經為“先行者”了。
在《悲劇的誕生》第三節中,尼采首先借助于酒神之師昔勒尼的故事,提出一個叔本華式的生命哲學的難題:人生短暫,人生悲苦,人何以活下去?①參看尼采《悲劇的誕生》,中譯本,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頁。這個故事的大意是:相傳昔勒尼知道人世間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某國王抓住昔勒尼,問他人世間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昔勒尼說:是不要出生。國王又問:那次好的事情是什么?昔勒尼答道:快快死掉。剩下的只有一種最不妙的可能性:活著。尼采認為,人類各種文化形式都是在解答一個問題:人何以承認悲苦人生?通過對古希臘三種基本文化類型(即藝術文化、悲劇文化、理論文化)的討論,尼采建立了一個基本的對立,即酒神狄奧尼索斯與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對立。這就是說,尼采此時主要反對的是蘇格拉底理論文化,即科學樂觀主義的哲學和科學傳統。反“理論人”是此時尼采哲學的主題。尼采相信,唯有悲劇藝術能解生命哲學的難題,因為唯有悲劇藝術才能直面此在的原始苦難,確證生命本體的根本統一。原始的“苦”與原始的“樂”是一體的—把痛苦當作快樂來感受,這是悲劇給予我們的形而上學慰藉。似乎在尼采看來,其他文化樣式要么騙人要么傷人,但悲劇至少能讓人直面痛苦和苦中作樂。
但好景不長。中期尼采疏離了瓦格納,轉而反對瓦格納式的藝術宗教理想。特別當尼采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收到瓦格納晚期作品《帕西法爾》劇本時,尼采對這位曾經的偶像已經徹底絕望了。在中期重要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年)中,尼采一反《悲劇的誕生》時期的藝術理想,斷然放棄了他前期所謂的“作為真正形而上學活動的藝術”的觀點,轉而認為藝術是“無法觸動世界本身的本質”的,甚至于指責他所酷愛的音樂藝術。尼采居然寫道:“就本身來說,沒有一種音樂是深刻的和富有意義的,它并不觸及‘意志’和‘物自體’。”②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175頁。尼采把矛頭直指瓦格納及其音樂,這就難怪瓦格納夫人柯西瑪憤怒了。尼采此時對于藝術(音樂)的貶抑態度與其說是學理上的,倒不如說更是情緒上的,意氣用事的成份居多。隨后幾年經常被學界認為是尼采的“實證階段”。一八八二年,尼采出版了《快樂的科學》一書。
中期尼采相對疏遠了藝術,不再鼓吹藝術的形而上學性,也不再以藝術對抗科學,但這并不意味著尼采直接倒向了科學,充其量,他此時主張的是藝術與科學的“雙腦制”。尼采開始從宗教和道德批判(實即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加以深化。反“宗教人”和反“道德人”成了此時尼采的心頭大事。尼采做的清算策略依然是生命哲學的:形而上學的“另一個世界”導致頹廢即生命的弱化,所以要返回感性生命,要從靈魂返回身體,從天國返回大地—由此形成他的“超人”理想。
自晚期代表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1883-1885年)開始,尼采開啟了他的哲思的最后一個階段,即所謂《權力意志》時期。通過密集的寫作和大量的筆記,尼采試圖構造一個以“權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輪回”為基本概念的形而上學體系。在不久前的《快樂的科學》結尾處,尼采已經對《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的生命哲學命題—即如何承受悲苦人生的問題—做了一次轉換。尼采的問法是:“對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這樣一個問題:‘你還想要它,還要無數次嗎?’這個問題作為最大的重負壓在你的行動上面!”①尼采《快樂的科學》,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3卷,第570頁。這一節題為“最大的重負”(第341節),屬《快樂的科學》第四卷。現在,“苦難”問題被轉換為無聊而不斷重復生命的“意義”問題。尼采試圖以“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學說來加以解答。
與此同時,晚期尼采調整和改變了姿態。尤其在其《權力意志》時期的筆記中,尼采花了大量筆墨重提藝術和美學問題,以積極肯定的姿態重新審理前期《悲劇的誕生》一書的立場、問題和觀點,重又賦予藝術以一種特別重要的地位,重新采納了《悲劇的誕生》時期關于藝術的基本主張,即:藝術可為人生此在(Dasein)作審美辯護,或如我們所謂“通過藝術獲得解放”。
在一八八八年春夏做的一則筆記中,尼采對《悲劇的誕生》做了如下兩點總結:其一,《悲劇的誕生》是以另一種信仰為背景去信仰藝術,那就是:“憑真理生活是不可能的;‘求真理的意志’已經是一個蛻化的征兆……”;其二,《悲劇的誕生》含有“一個特別陰郁和令人不快的想法”,即:“藝術是非道德的:—藝術并不像真理那樣,是由哲學家的妖精即德性激發出來的。”②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6[40];參看中譯本,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259頁,版本下同。這兩點,簡而言之就是藝術的非真理性和藝術的非道德性,是尼采晚期對于前期《悲劇的誕生》中的藝術觀的再確認。
在同一則筆記中,尼采還進一步說:“真理是丑的:我們擁有藝術,是為了我們不因真理而招致毀滅。”③同上。這話已成名言,把藝術與真理直接地對立起來了。所謂“真理是丑的”,背后的話無疑就是“藝術是美的”,而“美與丑”對應于“強與弱”—尼采的意思是說:強壯者才可能是美的,虛弱者能美么?尼采因此就把自己此時已經形成的“權力意志”命題審美化了,把“權力意志”與藝術和審美緊緊聯系起來了:“所有丑都使人虛弱,使人悲傷:它使人想起衰落、危險和昏聵無能。人們可以用測力計來測量丑的印跡。凡在人受到壓抑處,就有某種丑發揮作用。權力感,權力意志—它隨著美而高揚,隨著丑而跌落。”④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6[40];參看中譯本,第1258頁。美等于“強壯”而丑等于“虛弱”,尼采這種生命哲學的邏輯未免簡單了些,把我們通常所謂的“陰柔之美”完全排除掉了。
尼采也把“丑”稱為“藝術的否定”:“丑,即藝術的對立面,為藝術所排除的東西,藝術的否定—只要衰退、生命之赤貧、昏聵無能、解體、腐敗遠遠地被引發,這時候,審美的人都會以其否定(Nein)來作出反應/丑發揮令人沮喪的作用,它是一種沮喪的表現。它消減力量,使人貧乏,令人壓抑……”⑤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119];參看中譯本,第1027頁。在《權力意志》時期的另一則筆記中,尼采把藝術界定為反對禁欲和虛無主義的“反運動”,把藝術之“美化”稱為“一種提高了的力的一個結果”、“一種勝利意志的表達”,而“丑”則意味著“某個類型的頹廢”,是“力的衰退”和“意志的衰退”。
尼采接著寫道:“人們稱為陶醉的快樂狀態,準確地講,乃是一種高度的權力感……/空間感覺和時間感覺已經變化了:異常迢遠之物被一覽無馀,幾乎是可感知的了/視野的擴展,涵攝更大的數量和廣度/器官的精細化,使之能夠感知大量極其細微的和轉瞬即逝的東西/預見、理解力,對于最輕微的幫助、對于一切暗示,此乃‘聰明的’感性……/強壯作為肌肉的支配感,作為柔韌性和運動欲,作為舞蹈,作為輕快和急板/強壯作為對強壯之證明的欲望,作為精彩表演、冒險、無所畏懼、漠然處之的本色……/生命中所有這些高貴的因素相互激勵;其中每一個因素的圖象世界和表象世界都足以啟發出其他的因素……”⑥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117];參看中譯本,第1023-1025頁。尼采這段筆記具有札記的性質,讀來未免有點雜亂,但其中的基本意思還是可以了解和掌握的。這是對作為權力感的美感的各個面相的描寫。以意大利學者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看法,尼采在這里表述的恰好是亞里士多德關于作為“凈化/陶冶/渲泄”(Katharsis)的藝術的觀點的反面。①吉安尼·瓦蒂莫《弗里德里希·尼采導論》,克勞斯·拉爾曼(Klaus Laermann)德譯本,斯圖加斯,1992年,第93頁,版本下同。尼采一直反對美學中的道德主義原則,在他看來,悲劇性與道德沒有任何原始的關聯。“誰要是在道德上欣賞悲劇,他就還得提高幾個檔次”。參看尼采《1880-1882年遺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9卷,12[102],第594頁。在《權力意志》時期的筆記中,尼采也明言:“我曾再三指出亞里士多德的一大誤解,因為他認為自己在兩種沮喪的情緒即恐懼和憐憫中找到了悲劇性情緒”。(《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5[10];參看中譯本,第1153頁)。在尼采那里,藝術并不是用來緩解和平息情緒的,也不是用來渲泄不良情緒的,甚至也不是用來陶冶情操、提升道德境界的,而是旨在彰顯力量,感受權力。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的“凈化/陶冶/渲泄”(Katharsis)概念本身傳達了對于藝術的道德主義要求,這種古典美學的要求源遠流長,而在尼采看來恰恰是藝術的主要反對目標,即禁欲和虛無主義。因為藝術的“非道德性”,自稱為“非道德論者”的尼采最后仍舊倒向了藝術,重歸“藝術形而上學”。
尼采進一步強調了藝術與身體和感性生命力的關聯,特別是把藝術與性(性欲、生育)聯系起來了。以尼采的說法,“春天、舞蹈、音樂,一切都是性競爭”。“藝術家們,如果他們有點用處的話,就是具有強壯的氣質(包括身體上的強壯)、精力過盛、力大如牛、感覺豐富。要是沒有性系統的某種亢奮,那就無法設想拉斐爾了……音樂創作也還是一種生育;貞潔只是藝術家的節約:—而且無論如何,即便在藝術家那里,多產能力也是隨生殖力而終止的……”②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117];參看中譯本,第1023-1025頁。這就難怪后來的性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如此鐘愛尼采了(弗洛伊德于1908年為尼采開了世界上第一個尼采研討會)。
除此之外,上面這段話中還有兩個要素是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其一是作為生命激發/激動之結果的感受力之強化(作為陶醉的快樂狀態/審美狀態、高度的權力感),其二是作為這種提高了的激發/激動狀態之結果的美的觀念。第一點導致了“傳達手段的充溢”,“審美狀態具有十分豐富的傳達手段,同時帶有一種對刺激和信號的極端敏感性。它是生命體之間的可傳達性和可傳染性的頂峰,—它是語言的源泉”。③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119];參看中譯本,第1027頁。尼采在這則筆記本中接著寫道:“語言的發源地即在于此:聲調語言,同樣也包括體態語言和眼神語言。更為豐沛的現象往往在開端:我們文化人的能力是從更為豐沛的能力中削減而來的。然而,即便在今天,人們依然借助于肌肉來聽,甚至依然借助于肌肉來閱讀。”第二點則告訴我們,為何尼采會成為“偉大的風格”的主張者和追隨者。④參看吉安尼·瓦蒂莫《弗里德里希·尼采導論》,第93頁。

尼采手稿“永恒輪回”(1881年8月)

尼采手稿《反基督》(1888年9月)
尼采這里的“風格”概念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體概念,甚至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美學概念。在一八八八年春季的一則題為“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音樂’—以及偉大的風格”的筆記中,尼采寫道:衡量一位藝術家是否偉大,并不是根據他所激起的“美好情感”之類的女人氣的東西,而是要根據藝術家接近于“偉大的風格”(或譯“大風格”)的程度,是要看藝術家創造“偉大的風格”的能力如何。
什么是“偉大的風格”呢?按尼采的說法,“偉大的風格與偉大的激情有下述共同點,即:都鄙棄賣弄;都忘了勸服;都要發號施令;它們都意愿……控制人們那種混亂無序;迫使這種混亂無序成為形式;成就形式方面的必然性:邏輯的、簡單的、明確的、變成數學;變成規律—:在這里,這就是偉大的抱負和野心。……所有藝術都有此類追求偉大的風格的野心家……”①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61];參看中譯本,第969頁。在更早些時候的一則筆記中(1887年11月至1888年3月),尼采更直接地指出:“偉大的風格乃‘權力意志’本身的表現。”②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1[138];參看中譯本,第740頁。可見尼采所謂“偉大的風格”或者“大風格”,其實說的還是“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大風格”和“大氣派”,是權力意志的顯示和實現。
在這個時期的尼采眼里,所謂“偉大的風格”肯定還與“酒神頌歌”(Dithyrambus)相關。在概述自己的風格技巧時,尼采曾說過:“用符號、也包括符號的節奏,來傳達一種狀態,一種激情的內在緊張—此乃任何風格的意義。”③尼采《瞧,這個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04頁;參看中譯本,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86頁。尼采并且認為,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具有這種風格,特別是第二部的“夜歌”一節,諸如“我是光明:呵,但愿我是黑夜!”這樣的詩意歌唱,就是“酒神頌歌”的語言。④參看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4卷,第137頁;參看中譯本,第133頁。

尼采手稿《瞧,這個人》
正因為尼采把藝術與感性生命力關聯起來了,所以我們也才能理解,特別是從《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始,尼采構造出一種“生理學美學”(physiologische ?sthetik),強調美感的生理-欲望-身體基礎①尼采對“身體”問題的關注開啟了20世紀的身體哲學,但強調美感的生理-身體基礎,恐怕無法避免“審美種族主義”的問題。,主張藝術的力量感和權力意志屬性,在此意義上表現出重新肯定《悲劇的誕生》時期的藝術形而上學的傾向,而其中核心元素依然是狄奧尼索斯精神。于此是不是也呈現出一種思想運動的輪回?
我們的問題是:晚期尼采為何要重歸藝術?我想我們已經獲得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對晚期尼采來說,生命(存在)的本質是權力意志,是求權力/強力的意志,而作為人類創造性活動的藝術正是這種生命本質的基本實現方式,因此尼采勢必要轉向關于“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的思索。不止于此。晚期尼采的哲思高峰在于“相同者的永恒輪回”學說,而此學說的要旨就在于生命的創造性,同樣具有藝術哲學的歸指。
尼采對“永恒輪回”之說做過多維度的論證,我們在此無法展開②參看孫周興《未來哲學序曲:尼采與后形而上學》,第216頁以下。。我們只端出他的一個比較有趣的議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三部“幻覺與謎團”一節中,尼采曾經對自己的“永恒輪回”思想做了一個與時間性的證明,大意是:當有人從“瞬間”這個點往后走,有人從“瞬間”這個點往前走,他們倆到底會相遇嗎?③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4卷,第199頁以下;中譯本,第248頁以下。尼采說,如果我們同意“所有筆直者都是騙人的”,那么,他們是必定會相遇相交的。這就是意味著:如果所有筆直(直線)都是騙人的,那么,“相同者”(das Gleiche)必將復返,必將輪回—這個“相同者”不是“A是A”意義上的“同一者”,“相同者”永遠只是異中之同,是包含差異的。
尼采以此來反對傳統哲學的線性時間觀(即后來海德格爾所批判的“現在時間觀”),得出了“永恒在瞬間中”這樣一個全新的實存哲學結論。“永恒輪回學說中最沉重和最本真的東西就是:永恒在瞬間中存在,瞬間不是稍縱即逝的現在,不是對一個旁觀者來說僅僅倏忽而過的一剎那,而是將來與過去的碰撞。在這種碰撞中,瞬間得以達到自身。瞬間決定著一切如何輪回。”④海德格爾《尼采》上卷,斯圖加特,1998年,第278頁;中譯本,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27頁,版本下同。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闡明的以“當下/當前”決斷、不斷“重演”為核心的三維時間性思想,是與尼采的“永恒輪回”思想相貫通的。海德格爾也坦承這種聯系:“相同者的永恒輪回中的永恒性是尼采要求我們思考的;這種永恒性的時間的時間性乃是人置身其中的時間性。首先是人而且—就我們所知—只有人才置身于這種時間性中,因為人在向將來展開、保存曾在之際塑造和承受著當前。”⑤海德格爾《尼采》上卷,第318-319頁;中譯本,第376頁。
尼采的永恒輪回學說只有在實存論或實存哲學路線上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釋。尼采貌似高超空洞的“永恒輪回”之說,實質上卻是指向個體此在(生命)的當下存在。尼采仿佛是想“教誨”我們:你應當如此這般地生活在每個瞬間中,并且相信每個瞬間都是永恒的,是永恒輪回的。⑥關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輪回”思想,可參看孫周興《未來哲學序曲:尼采與后形而上學》,第212頁以下。
個體此在當下瞬間的時機性決斷原是一種創造,每一個瞬間都是一個創造性的“時機”,即希臘人所謂的“契機”(Kairos)。尼采在一則筆記中自問自答:“我不想要生活重復。我如何承受生活?去創造。什么使我經受住這景象?對肯定生命的超人的洞察。我已嘗試了對生命本身的肯定—啊!”⑦參看尼采《1882-1884年遺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0卷,4[81],第137頁。尼采在這里使用的“去創造/創造著”(Scha ff end)是一個現在分詞,強調當下正在進行之中。至此,晚期尼采的幾個核心思想,即“權力意志”、“相同者的永恒輪回”與“超人”,已經達到了統一,統一于個體此在(生命)的基于時機性決斷的創造性活動。
我們看到,晚期尼采意在建設自己的哲學大廈或哲學主樓,形成了以“權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輪回”為核心的形而上學,雖然終于未竟全工,但這種哲學的基本構件都已經擺出來了。此時尼采以“你還想要它,還要無數次嗎?”這樣一個行動的決斷問題,重新表達了生命哲學的難題。而“相同者的永恒輪回”思想不但為權力意志學說贏得了一個可能在邏輯上自洽的解釋,而且以直面當下、化瞬間為永恒的創造性活動為個體此在的意義問題開辟了一個實存哲學的解決之道,從而達到了尼采生命哲學的極點。這時候我們方得以理解,晚期尼采為何重歸藝術,思考“作為權力意志的藝術”。
尼采有言:“藝術本質上是對人生此在的肯定、祝福、神化……”⑧尼采《權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47];參看中譯本,第961頁。而尼采所謂“相同者的永恒輪回”,所謂“永恒在瞬間中存在”,也無非是想告訴我們:只有創造性的生活才是值得一過的。

酒神(古希臘)
※ 本文系作者為《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權力意志〉時期尼采筆記選》所做的引論,據其《未來哲學序曲—尼采與后形而上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本下同)第三編第三章第四節“作為藝術的權力意志”增刪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