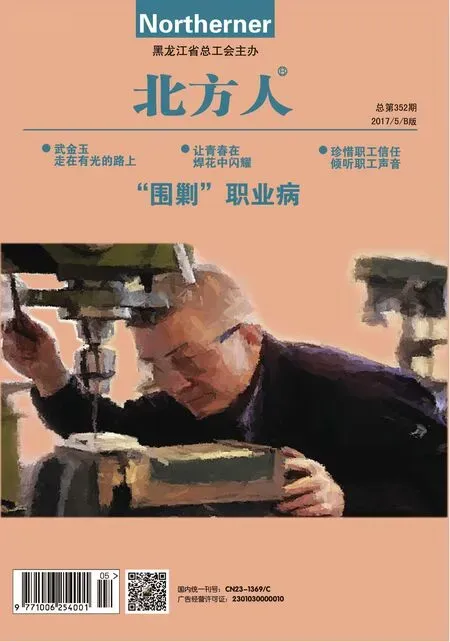最后一封情書
文/王世虎
最后一封情書
文/王世虎

人的年紀(jì)一大,身體就由不得自己了,就像“六月的天孩子的臉”一樣,說(shuō)變就變。爺爺便是這樣,上個(gè)月還笑呵呵的、一向硬朗的爺爺,就在我們不知所措之時(shí),悄然無(wú)聲地離我們而去了。
這件事,受傷害最大的當(dāng)然是奶奶,以至于爺爺?shù)膯适露嫁k完一個(gè)月了,她的精神狀態(tài)都不能恢復(fù)過(guò)來(lái)。奶奶本就是個(gè)健忘的人,爺爺走了之后,記憶更是差得不行,有時(shí)剛站起來(lái),便不曉得自己想做什么了。獨(dú)處的時(shí)候,她就一個(gè)人在那里喃喃自語(yǔ):“這個(gè)死老頭子,怎么就狠心走了呢?他答應(yīng)我的事還沒(méi)辦完呢……”
父親和母親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好多次勸慰奶奶,人死不能復(fù)生,我們都很傷心,讓她想開(kāi)一些。帶高考畢業(yè)班的父親不僅在百忙之中擠出幾天假帶奶奶出去散心,還請(qǐng)了許多老友來(lái)家里陪她聊天,以減輕她內(nèi)心的悲痛。可奶奶卻對(duì)這一切都無(wú)動(dòng)于衷,滿臉漠然。
“清明節(jié)”這天,像往常一樣,把奶奶扶到陽(yáng)臺(tái)后,母親照例開(kāi)始打掃衛(wèi)生。打掃奶奶臥室的時(shí)候,由于不小心碰掉了水杯,母親俯身去揀,冷不防發(fā)現(xiàn)書柜的下面有一封信。可能是不小心滑進(jìn)去的吧,母親好奇地把信拾起來(lái),上面竟署名奶奶收。
母親忙把信拿給奶奶,看見(jiàn)信,“沉默寡言”了一個(gè)多月的奶奶“倏”地站了起來(lái),用滿是老繭的雙手接過(guò)信,顫抖地打開(kāi)。瞬間,便淚流滿面。
“媽,您、您這是怎么了?”母親嚇得大叫。聽(tīng)見(jiàn)母親的叫聲,全家人都跑了過(guò)來(lái)。
“他,他沒(méi)有忘記對(duì)我的承諾啊。”奶奶激動(dòng)地說(shuō)。
“媽,您說(shuō)誰(shuí)啊?”父親問(wèn)。
“老頭子,不,你爸啊!他沒(méi)有忘記給我寫最后一封情書!”奶奶說(shuō)。
“情書?”我們一愣。
父親把奶奶扶到沙發(fā)上,讓她不要急,慢慢說(shuō)。于是,奶奶動(dòng)情地向我們講述了她和爺爺之間不為人知的愛(ài)情小秘密。
原來(lái),雖然出生在舊社會(huì),可爺爺和奶奶卻是私下里自由戀愛(ài)結(jié)婚的。為了這份感情,奶奶等了去參軍的爺爺近五年。五年啊,難耐相思的年輕人便開(kāi)始了頻繁的鴻雁傳書。奶奶要求爺爺每個(gè)月都要給她寫一封情書作為補(bǔ)償,深愛(ài)著奶奶的爺爺很守信,堅(jiān)持每個(gè)月寫一封情書寄回去。
后來(lái),爺爺復(fù)員回家,和奶奶結(jié)了婚。婚后的奶奶骨子里仍愛(ài)浪漫,就“死皮賴臉”地要求爺爺像以前一樣每個(gè)月給她寫一封情書。慢慢地,爺爺從不愿意給奶奶寫情書變成了把寫情書當(dāng)成了一種生活習(xí)慣。
一次,去參加一個(gè)老友的追悼會(huì),看到家屬哭得那么傷心,奶奶感傷地說(shuō):“老頭子,如果哪天我先走了,你可怎么辦啊?”爺爺嗔怪道:“你個(gè)傻老太婆,凈瞎說(shuō)!我還要給你寫情書呢,一直寫到死的那天。”那一刻,奶奶把這句話牢牢記在了心里。哪知,上個(gè)月,爺爺卻突然走了……
說(shuō)完,奶奶費(fèi)力地從床底下搬出了一個(gè)大皮箱子。打開(kāi)箱蓋,我們都驚呆了——里面整整齊齊地?cái)[放著奶奶珍藏了大半生的情書,從爺爺參軍時(shí)一直到現(xiàn)在的。奶奶小心翼翼地扶摸著那些信,老淚縱橫地說(shuō):“每當(dāng)我看見(jiàn)這些信啊,仿佛老頭子就還在我身邊。”
父親,母親,還有我都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
花開(kāi)有花落的時(shí)候,草榮有草枯的季節(jié),但在爺爺和奶奶平凡而又真摯的愛(ài)情中,我明白了,愛(ài)不變,真正的愛(ài)是不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