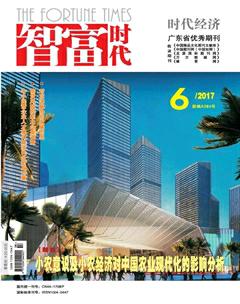淺析《我們》中的肖像描寫
王昕
(黑龍江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摘 要】本文將從特點分析、推動情節發展和揭示人物命運、表達作者思想的三個方面來對《我們》中的肖像描寫進行分析。
【關鍵詞】《我們》;肖像描寫;力與熵;“洞穴喻”
一、《我們》中的肖像描寫特點
《我們》雖然是一篇長篇小說,但是由于整個敘事都圍繞著主人公“我”即大一統號的設計師,數學家Д-503的視角展開的,所以書中主要的人物并不多,按照出場順序即Д-503、О-90、R-13、I-330、S先生、Ю小姐、醫生先生,次要人物比如看守古宅的老太太,以及一統號的第二設計師磁盤先生等等,最后還有一位在書中只出場了一次,卻有著絕對重要地位的“大恩主”。
作者對于各個人物都進行了肖像描寫,縱觀整部作品,不難發現這部分肖像描寫的特點:簡短并且高度概括。扎米亞京都沒有選擇對人物像素描一樣精準的刻畫,他在筆下為我們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更像是抽象畫,寥寥幾筆勾勒出人物最具有特點并令人深刻的部分,甚至在接下來的行文中以這些典型的特點去代替人物的數字代號。故事是以主人公“我”的第一人稱展開敘事的,這種簡潔并概括的肖像描寫方式符合主人公Д-503的數學家這一身份的抽象思維,另一方面,這樣“留白”的肖像描寫方式也留給了讀者想象的空間,足以去填滿這一形象,使得人物形象更為生動可親。
例如主人公Д-503在文中反復出現的毛茸茸的手臂和并不像“希臘式”鼻子那樣高挺的鼻子,我們完全可以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個相貌并不十分英俊的數學家形象。關于О-90的肖像描寫都圍繞著她的名字O展開——她有著圓鼓鼓的藍色的眼睛,圓潤的臉龐和豐滿的身材,還有她那帶有標志性的粉紅色的帶著肉褶的小拳頭,這一切都使她看起來帶有一股孩子氣般大的天真,盡管小說并沒有對О-90的言行多加以刻畫,但一個生動的不諳世事的有如鄰家女孩一般的形象就躍然紙上了。
對于女主人公I-330的刻畫則是完全相反的,與她有關的一切肖像描寫都像她的名字一樣,像一把出鞘的劍一樣銳利非常。她有著一口潔白而銳利的牙齒,經常挑起的太陽穴旁的眉尾和鼻子形成了一個倒三角,而鼻子和兩條法令紋則形成了一個正三角,這兩個三角形又如在她的臉上劃出了一個字母X——這是一個嘲諷的表情。盡管作者并沒有對女主人公進行過多的性格上描寫,但是不難想象出這是一個倔強并且難以接近,帶有十足神秘感和致命吸引力的女人。
同樣,作為詩人的R-13給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黑人般厚厚的嘴唇和潔白的牙齒,S-4711跟他的名字一樣,有著豎曲線一樣的身材和一對招風耳,關于醫生的肖像描寫都圍繞著單薄這一特點展開,他整個人就像是躺在手術臺上的剪刀片一樣。看守古宅的老太太有著帶著微微絨毛和充滿這周的嘴,Ю小姐那下垂的兩頰上的皮膚所讓人聯想到的令人不快的魚鰓,第二工程師的臉龐則變成了一個精致的白瓷盤,就連五官也像足了瓷盤上的紋樣……
這其中,對于大恩主的描寫使最為特別的,作者也描寫了他有如鐵柱一般的雙手,但最后,一開始仿佛被迷霧覆蓋的臉龐顯露出來——那是一個有著蘇格拉底一樣禿頭的男人。只有大恩主的面貌是通過對另一個人的聯想來完成的,甚至細致的描寫的在禿頭上汗珠,這樣的前后對比的描寫更突出作者對于大恩主這個只出場一次,卻貫穿了全文的人物的重要性的暗示。
二、《我們》中肖像描寫與人物關系、命運及情節發展的聯系
《我們》當中的人物肖像描寫除了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表達了主人公“我”對人物的看法,以及與各個人物的關系,同時揭示了人物個人命運以及情節的發展。
正如主人公自己所說的那樣,一切都是簡單的、規矩的、有限的,就像一個圓圈那樣。透過主人公對于О-90的描畫,最后他說出他對О-90正如古代人對自己子女一樣的態度的時候就不顯得突兀而怪異了。
在O-90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第一次對她的外貌進行了描寫:“可愛的O,我總覺得她長得像她的名字O,她的身高比母性標準矮十公分,所以整個形體也顯得圓滾滾的,她的嘴也像一個粉紅的O,總是張大著聆聽我說的每一句話。此外她的手上還鼓著一道肉呼呼的肉褶,像孩子的手。”O的形象似乎總是與粉紅色還有肉呼呼的詞匯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反復提到的她那充滿肉褶的小手更是能讓我們聯想到新生的嬰孩。就在這段肖像描寫后,在他們談論起機械與舞蹈后,主人公感嘆這一切都妙極了,O-90卻說“是的,妙極了,春天來了。” i
這里對于O-90肖似嬰兒的描寫,一方面揭示了主人公對O-90的態度,暗示了O-90對于主人公的愛慕必然沒有回應的結局,最后由主人公看清了他對O-90的態度更像是古代人父母對于子女的態度,而不是戀人之間的愛情。另一方面,也暗示了O-90最后孕育新并逃出圍墻的結局。除了在O-90第一次出場時提到春天,隨后在她隨后與主人公的見面中也有這樣一段描寫:“我十分熟悉她的雙手和乳胸,還有她的身體——都變圓了,制服緊繃在身上,仿佛她的身軀馬上就會撐破薄薄的衣衫來見陽光和光明,我不由得想到春天綠色的叢林,那里幼芽也這樣頑強地想頂出地面來,為的是快些抽枝、綻葉和開花。”ii圓形是沒有盡頭的,它可以象征著無盡的黑暗,但顯然在O-90身上它限時的是另外一種意思:生命的循環帶來的希望。
與代表O-90的是圓形,代表I-330的是三角形,顯然三角形這個圖形在本文中也寓意深刻。三角形往往被我們認為是最穩固的形狀,“反正,我、他和O——我們構成了個三角形,雖然不是等腰三角形,但反正是個三角形,我們,如果用我們祖先的語言來說,我們是個家庭。有時能在這里休息一下,把自己關進這簡單的、牢靠的三角形內躲避外部的一切,哪怕時間不夠,也足夠令人欣慰。”iii在此處,主人公特意強調了他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等腰三角形”,這暗示著三人關系的破裂,在接下來主人公與R-13的對話當中,R-13直接問道“是哪第四位插入我們的三角”iv,也直接證實了這一點。
顯然I所代表的三角形并不代表某種穩定的關系,而是與她那尖利的牙齒和像利劍的名字一樣,像她的出現迅速使主人、O-90、R-13看似穩固的關系瞬間瓦解一樣,代表著某種銳利的,未知的,猝不及防并不可避免的改變。這種改變有時甚至看起來并不與I-330直接相關的,卻都直接作用在了主人公和他周圍的人的身上。像在從診所返回的路上,診所和主人公的家還有古宅這三點之間,主人公看似遵循醫囑沒有走斜線回家,而是決定走直線到古宅去一趟,暗示了他內心的變化。再比如在演講廳里,放孩子的桌子、O-90和主人公這三點之間連成的線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投影,隱隱預示著最后主人公與O-90之后命運的突變。
這些三角形所代表的變化仿佛都與作者看似不經意間描寫的對I-330進行肖像描寫時在她眉宇間出現的三角形毫無相關,但卻又隱隱相互聯系,暗示了人物之間的關系與之后的情節發展。
三、《我們》中肖像描寫所蘊含的作者思想
《我們》的肖像描寫與其人物一樣,經常以對立成對的形式出現。作者通過對0-90和I-330的肖像描寫,對兩個人物進行了一凡對比。除了上文中提到的O-90所代表的圓形與I-330所代表的三角形的對比,在文中還對這兩者的眼睛和嘴唇進行了對比:O-90的眼睛是空洞的“我可以暢行無阻地長驅直入,因因為里面空空如也,也就是說,那里不相干的、不應有的東西一概沒有。”v而I-330則是這樣描寫的:“我眼前是兩扇黑幽幽的窗戶,里面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種生活。我只看到有火光,是那里一個“壁爐”的熊熊爐火……”vi,O-90的嘴唇是粉嫩嫩肉嘟嘟的,而I-330的嘴則像是用刀刃劃開的,仿佛能流下甜蜜的血。
這兩者的對比之中,正是蘊含了作者想要表達了另一沖思想:即力與熵。作者借著I-330闡釋了這一種思想:“一種力量導致舒適的平靜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種導致平衡的破壞,使事物永遠處于無窮盡的苦痛的運動之中。”這也就闡釋了為何在《我們》中的事物總是成對的出現:天才詩人與R-13、“蒜頭”鼻子與“希臘式”的鼻子、墻內與墻外、自由蠻荒與數字精確、直線與曲線、理性與感性、靈魂與驅殼、機械與幻想、靡菲與基督……這些都是力與熵這兩種力量在書中的具體投射。
同樣,在主人公的身上也存在著這兩種對量的對立沖突,而這種沖突對立我們而已直觀的從他對主人公前后的肖像描寫中清晰的感受到。一方面這種沖突是體現在他對待O-90與I-330的態度之中的,在主人公的事業去描寫O-90的時候,通過肖像描寫,我們知道他關注的她充滿肉褶的孩子一樣的小手,而當她注視I-330的時候,他的視線卻總是集中在她的胸乳上——這與理性所代表的克制不同,無疑是帶有強烈的吸引力,具有性暗示的意味。
另一方面,這兩種力量的碰撞也體現在主人公對自我的重新認識上。書中由于是以主人公的視角來進行描寫,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對他的外貌進行描寫,第一次提到主人公的外貌是他才意識到自己擁有著一雙原始人的一般毛絨絨的雙手,有著并不是很完美的“蒜頭”鼻子,他開始懷疑曾經對R-13、O-90這種家庭定義的認同,直至他重新審視自己:“我成了玻璃人,我看到自身的內部。出現了兩個我。一個是過去的Д-503,號碼Д-503,另一個……以前他只從軀殼里悄悄探出兩只毛茸茸的手,可是現在整個人都爬出來了,外面的軀殼裂縫了,馬上就會變得七零八落……那時候會怎么樣呢?”然后主人公站在了鏡子前,有生以來第一次審視自己,看他兩道濃黑的眉毛,看眉宇之間的褶皺,淺灰色的眼睛……
主人公終于從“我們”當中認出了自己。
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主人公終于與一直以來在《我們》世界中占有絕對至高無上地位的“大恩主”會面了。書中對于大恩主的描寫寥寥無幾,他的面容現實仿佛被迷霧籠罩,一開始只能看到如鐵鑄一般的雙手,終于在談話結束后,露出了他的面容——一個像蘇格拉底一般有著禿頭的人。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曾經提出“洞穴喻”的概念,后世人多對“洞穴喻”做出這樣的闡釋:“洞穴之中的世界相應于可感世界,而洞穴外面的世界則比作理智世界。可是原文可作許多不同的解釋。柏拉圖明確聲稱囚徒與我們相像,即是說他們代表人類的狀態;而囚徒被拉出洞穴的過程則類似于通過教育而獲得啟蒙的過程。我們可以把上升之途和對上面事物的觀照解釋成是靈魂上升到理智世界的過程。”vii
作者在的肖像描寫將大恩主與蘇格拉底聯系起來,一方面揭示了文章另一對力與熵的具體表現,即感性世界與理性世界的對立,另一方面正如蘇格拉底的悲劇下場一樣,也昭示了大恩主讓人們摒棄靈魂和思想以達到絕對理性統治的極端做法也必將失敗。雖然結局中描寫了男主角接受了手術,摘除了靈魂,但力與熵這一對相互對立,但也相互依存的力量,依然會存在于每一個人身上。或許我們每個人都與投射在洞穴之上的影子都十分相似,卻又不盡相同。正如男主毛茸茸的手臂,O-90比平常女性矮一些的身高……,正是這些細小的不同,讓我們脫離了“我們”,變成了一個個鮮活的個體。
O-90最終帶著自己的未出生的孩子去了墻外生活,力與熵這一對力量也將延續——就像普羅米修斯的火種一樣。
【參考文獻】
[1] 葉·扎米亞京.我們.顧亞玲等譯[M].作家出版社,1998-3.
[2]趙敦華.西方哲學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注釋:
i 葉·扎米亞京/我們/.顧亞玲等譯[M].作家出版社,1998-3.p6
ii 葉·扎米亞京/我們.顧亞玲等譯[M].作家出版社,1998-3.p161
iii 同上,p44
iv 同上,p61
v 葉·扎米亞京.我們.顧亞玲等譯[M].作家出版社,1998-3.p36
vi 同上,p29
vii 趙敦華.西方哲學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