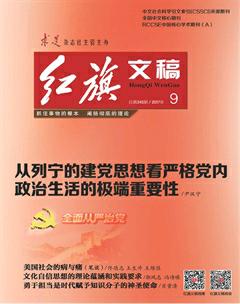為豐富和發展宏觀調控理論貢獻中國智慧
龐明川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日趨復雜的經濟形勢和前所未有的宏觀調控難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不斷創新宏觀調控思路,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僅準確定位了宏觀調控的政策邊界、大大拓展了宏觀調控的內涵和外延,而且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結構性特色,構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結構性調控新范式。這些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彌補了西方主流理論僅包含以需求管理為特征的總量調控的局限,為豐富和發展宏觀調控理論貢獻了中國經驗和智慧。
一、準確定位宏觀調控的政策邊界
改革開放以來,行政主導經濟的慣性思維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管理經驗的匱乏,直接導致了我國宏觀管理中長期存在宏觀調控的常態化和泛化現象。這一現象不僅造成在認識上出現“調控依賴癥”“宏觀調控是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以及宏觀調控“萬能論”等偏差,而且在實踐中經常性地出現將許多“微觀”問題宏觀化,將宏觀調控的任務和手段擴大化、夸大化等問題,在帶來一定程度的體制扭曲的同時,也造成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干預和政府職能的錯位與越位。因此,如何準確定位宏觀調控的政策邊界、地位和作用,就成為我國宏觀管理中的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了一系列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這些論述不僅將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準確地定位了宏觀調控的政策邊界。
第一,盡管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職能不同,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由于宏觀調控實質上是政府對市場的某種干預,因此,宏觀調控要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作為基本出發點,將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建立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第二,在政府的職能和作用中,宏觀調控不僅位居五大職能之首,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觀調控的職能。因此,一方面宏觀調控不能包辦一切,越俎代庖,尤其是要與屬于微觀范疇的市場管理與規制劃清邊界;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觀調控的職責,地方政府則應履行好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因而如何加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責和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這兩個方面顯得尤為重要。
第三,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這不僅闡釋了宏觀調控具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特征,而且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這就為宏觀調控指明了方向。
二、大力拓展宏觀調控的內涵和外延
發達國家的宏觀調控范式是以凱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為典型特征的。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宏觀調控不僅被嚴格限定在總量的范疇,而且強調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擴張與收縮來進行需求管理。
與此不同的是,中國宏觀管理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第一,調控的內容既包括總量調控,還包括結構性調控,長期存在“雙軌并行”的現象。第二,調控的目標不僅關注西方宏觀調控中的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大目標,而且增加了結構調整的目標,還根據中國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特點先后增加了房地產價格、土地、糧食安全、節能減排等目標,形成了兼具長短期目標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第三,調控政策不僅高度重視西方宏觀調控中慣常使用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而且注重發揮國家戰略與規劃、產業政策、價格政策、區域政策、土地政策、貿易政策、環境政策等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第四,調控手段既注重間接調控,也包含直接調控,在注重發揮經濟手段作用的同時,還注重發揮行政、法律等手段的輔助作用和協同效應。第五,調控的重點注重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結合,短期措施和中長期措施并重。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政府又相繼實施了“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等創新性宏觀調控方式,提出了“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思路,進一步拓展了宏觀調控的內涵和外延。主要體現在:
第一,在調控內容上,“區間調控”與“定向調控”的結合體現出“總量+結構”調控并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明“需求+供給”的有機結合。
第二,在調控目標上,《決定》提出,“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僅延續了總量調控與結構調控“雙軌并行”的經驗,還增加了“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等內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更加注重擴大就業、穩定物價、調整結構、提高效益、防控風險、保護環境”。不僅首次將擴大就業列為目標,而且在“總量+結構”目標之外還增加了提高效益、防控風險和保護環境等目標。
第三,在政策體系上,《決定》提出“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推進宏觀調控目標制定和政策手段運用機制化,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價格等政策手段協調配合,提高相機抉擇水平,增強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十三五規劃建議》和《十三五規劃綱要》則提出“完善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為主,產業政策、區域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價格政策協調配合的政策體系,增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性。”
第四,在政策工具上,在發揮結構性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相繼推出包括定向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定向再貸款,抵押補充貸款(PSL)、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以及中長期融資債券、PPP等貨幣政策工具,并充分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
第五,在調控方式上,由“強刺激”轉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轉向“定向調控”、由“遵循規則”轉向“相機調控”、由“大水漫灌”轉向“精準滴灌”、由“急剎車”改為“點剎”,并注重適時適度的微調預調,提高了調控政策的針對性與靈活性。
三、進一步凸顯結構性調控的特色
長期以來,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一直是中國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宏觀調控明顯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宏觀調控。這種區別就體現在中國的宏觀調控在堅持總量調控的同時長期堅持了符合自己國情特點的結構性調控。特別是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總量調控與結構性調控相結合使得中國經濟率先復蘇,與西方宏觀調控的效果形成鮮明反差,并引起了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有學者指出,正是由于宏觀政策只關注總量調控而忽視了結構調控,才導致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因此,單純關注總量的宏觀調控是不夠的,還需要關注經濟中的結構性變量和結構性調控措施,而關注結構恰恰與中國宏觀調控的實踐不謀而合。
結合中國宏觀調控的長期實踐可以看出,結構性調控具有緊縮性調控與擴張性調控相結合、需求結構調控與供給結構調控相結合以及政策工具多樣、調控手段多重等特點。
首先,從調控性質上看,結構性調控也分為緊縮性與擴張性兩種類型。在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2003—2007年五次緊縮性調控中,主要的結構性緊縮措施包括:嚴格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控制消費需求的增長、壓縮信貸規模、實現貸款限額管理、實行價格管理、壓縮財政支出結構中的行政管理費支出等;在1987—1991年的宏觀調控中,開始了運用結構性財政貨幣政策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強信貸調節等;2003—2007年“有保有壓”的宏觀調控中對有可能導致經濟過熱、資源耗費嚴重的“兩高一資”行業的重點收縮更是體現了結構性收縮的特點。在1998—2002年、2008—2009年和2010—2014年三次擴張性調控中,主要的結構性擴張措施包括:運用結構性財政政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結構性減稅、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向中西部等轉移支付、保障和改進民生、支持科技創新與節能減排、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等;貨幣政策如取消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調整對個人消費信貸政策、支農再貼現和再貸款以及窗口指導、兩次定向降準等措施等;注重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
其次,從調控內容上看,結構性調控既有對需求結構的調控,也有對供給結構的調控。其中,對需求結構的調控體現在緊縮性調控中的壓縮投資與消費需求,擴張性調控中的擴大內需、鼓勵出口等;對供給結構的調控體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展鄉鎮企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城市推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中小企業與非公有制經濟、政府機構改革,新世紀以來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農村稅費改革、要素市場改革以及近年來的簡政放權、降低稅負、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鼓勵創新創業等。
再次,從政策工具上看,結構性調控具有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幾乎所有的宏觀政策都可以作為結構性調控的政策工具使用,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經濟計劃、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價格政策、貿易政策、區域政策甚至糧食政策等。雖然西方主流理論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作為總量調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中的結構性調控功能與貨幣政策中的定向降準、定向再貸款等,明顯屬于結構性調控的范疇。其他如經濟計劃、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價格政策等都體現為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政策選擇,往往通過鼓勵和限制等措施來實現不同的結構調整目標。
最后,從調控方式上看,結構性調控綜合使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綜合使用直接調控與間接調控兩種方式。在這里,不能簡單地認為與間接調控相對應的是總量調控,而結構性調控對應直接調控和行政手段。事實上,新常態以來以結構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為代表的間接調控手段在結構性調控中得到了大量的運用。
可以說,以結構性調控為特色的宏觀調控不僅在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常態以來的經濟運行中也發揮了良好的調控效果。盡管當前中國遭遇三期疊加效應,經濟進入速度換擋、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的新常態階段,但增速依然處于世界前列,增量依舊龐大。從趨勢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實現了兩個層次上的重大突破:在總量與結構的關系上,不僅注重總量調控,而且更加注重結構性調控;在結構調控方面,不僅注重需求結構調控,而且提出要加強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控,形成了“總量+結構”與“需求+供給”兩大組合,與宏觀經濟運行的機理高度契合。這種結構性調控范式不僅彌補了西方主流理論僅包含總量調控的缺陷,豐富和發展了宏觀調控理論的內涵,而且,結構性調控政策的推出也豐富和發展了宏觀調控的政策框架體系。
(作者: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狄英娜 李民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