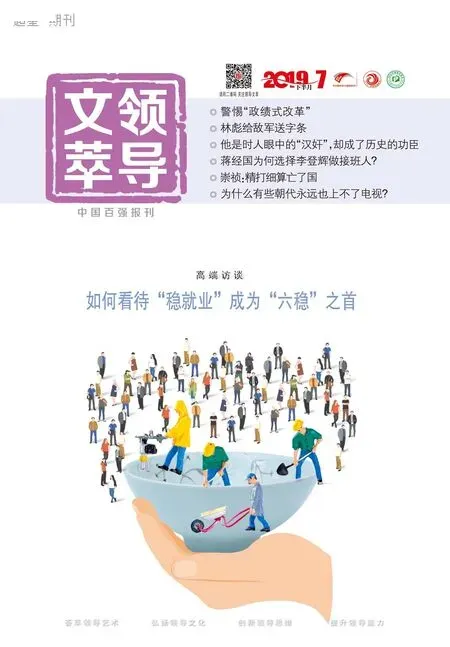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國力
唐世平
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使一些人認定以美國為基石的現有國際秩序面臨空前挑戰,甚至已近崩潰。在這樣的判斷下,國內外都有人呼吁中國“領導”對未來國際秩序的塑造。
基于對國際秩序變遷的研究,筆者認為,中國要對這種呼吁保持謹慎。首先,這是因為塑造國際秩序的努力不僅要付出可觀成本,還要承擔失敗風險。國際人士可以隨意鼓動,但不會承擔這種成本和風險。
其次,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國力,而中國離這樣的國力還有較大距離。塑造國際秩序也需大部分主要大國支持,而中國離獲得這樣的國際支持同樣有較大距離。
因此,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需要明確拒絕擔負起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領導者”角色。我們能做的是在某些特定領域,通過聯合其他國家,推動一些就現有國際秩序的有限改進或改革。
美國塑造國際秩序的漫長軌跡
法國大革命以降,國際社會只發生了一次和平的國際秩序塑造,那就是美國在二戰后的經歷。這一秩序在冷戰后得到強化并基本擴展到全球。過去一個多世紀,所有試圖通過非和平手段重塑國際秩序的努力都遭重創,無論拿破侖的法國,還是德意志帝國、“軸心國”或二戰后的蘇聯。
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美國自19世紀中葉到二戰這近一個世紀的成長軌跡,就會發現,其實美國并不是一個急于塑造和維持國際秩序的國家。
1895年的美國已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經濟規模達到英國的1.5倍之多,不過人均GDP仍略低于英國。此時的美國并未追求塑造國際秩序。相反,美國依舊專注于經營美洲,鞏固美國在整個美洲的地區霸權,直到在1904年—1906年間迫使英國承認“門羅綱領”,將其在美洲的存在全部和平地“移交”美國。
1916年,美國的經濟規模更是超過整個大英帝國。一戰結束后,盡管彼時的英國和法國已遭重創,但仍拒絕美國過多介入歐洲事務。最終,英法主導了《凡爾賽和約》談判和一戰后國際秩序的走向。而在大西洋對岸,美國國內對塑造國際秩序的意愿也不堅定。威爾遜總統無法獲得足夠國內支持來塑造國際秩序,最后美國連自己發起的“國聯”都沒加入。
因此,很大程度上說,二戰之后美國對國際秩序的主導地位,并不是美國主動爭取來的,而是歐洲哀求美國的結果。經過二戰,歐洲一片焦土。而美國在1945年的國力是空前的:不僅總體經濟規模超過了英法蘇德總和,而且人均GDP也遙遙領先其他國家。不夸張地說,二戰后,英法和其他歐洲國家別無選擇,只能懇求并服從美國來主導戰后國際秩序。而這個時候,美國國內也基本形成了介入世界事務的共識。
根據以上簡單回顧,我們大致可以說,僅是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并不足以讓一個國家去塑造國際秩序。最低的國力要求,恐怕也是這個國家的經濟規模大于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三大經濟體之和。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中國經濟規模必須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或至少是美國和日本經濟規模的總和才行。但即便是最樂觀的估計,中國與這樣的經濟規模至少也還有三四十年的距離。不僅如此,這個國家還必須是技術絕對領先的國家。在這個指標上,中國同樣至少還有幾十年的距離。總之,我們現在還無力塑造國際秩序。
中國如何作為
那么,就國際秩序而言,是否中國就應毫無作為呢?也不是。這背后仍是一個戰略計算問題,而其中最關鍵的是明確我們自己的核心指導原則。
首先,《孫子兵法》告誡我們:“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國家間的競爭就像下棋,最后看實力和誰犯錯少。如果家底比別人薄,犯錯比別人還多,結局可想而知。因此,我們不能一時興起就追求“領導權”或“引領權”,更不能因為別人起哄讓我們干就干。
其次,國內的改革和發展永遠是第一位的,因為沒有超強國力,其他一切都是空談。而只要我們把中國治理好了,中國肯定會有一定的國際影響力。因此,最后還是那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或者“發展還是硬道理”。
再者,針對中國的特殊國情,即便在整體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這兩項指標上都達到最低要求,中國要去塑造國際秩序,恐怕也還需要解決以下兩個突出挑戰:國家統一和“經營東亞”。
兩岸統一有助于中國崛起,更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同時,塑造國際秩序通常是“先地區,后全球”,因此我們也不能回避“經營東亞”這一挑戰。而要經營好東亞,中國又必須成為該地區“不可替代的國家”,對本地區的核心熱點問題都有我們的處理方式和決心。我們需要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可以是不完備的,也是可以商量和集思廣益的,但我們必須提供。
當然,我們也確實可以做一些具體事情。在那些對國力的要求不是特別高,且制度化和內化程度都比較低的領域,我們可以聯合其他國家以推動一些有限的變革。這需要建立在深入扎實的研究之上。
(摘自《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