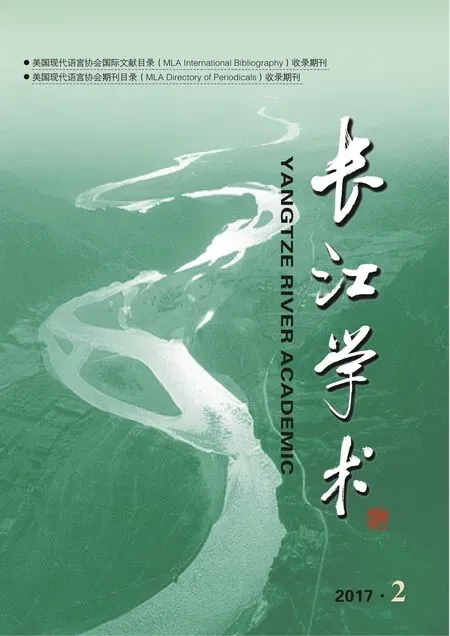西方哲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紅樓夢評論》
〔美〕涂經詒著 鄧明靜譯
(1.羅格斯大學,美國 新澤西州;2.湖北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2)
西方哲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紅樓夢評論》
〔美〕涂經詒著 鄧明靜譯
(1.羅格斯大學,美國 新澤西州;2.湖北大學,湖北 武漢 430062)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將西方哲學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開拓之作,其巧妙運用了叔本華的藝術理論來研究中國名著《紅樓夢》,從深度和廣度上論述了《紅樓夢》的精神內涵、美學價值、倫理價值以及悲劇意識。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從生活之本質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紅樓夢》的哲學基礎,認為《紅樓夢》極度體現了人生的苦痛以及人不斷追尋解脫之道,極具厭世解脫之精神,是一部舉世矚目的悲劇,完美展現了叔本華所謂的第三種類型的悲劇,因而被視作為“悲劇中的悲劇”,是“壯美文學”的代表,其美學價值與倫理價值密切相關。寫于一百一十多年前的《紅樓夢評論》在當時既倡導了一種研究《紅樓夢》的新方式,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示范。
紅樓夢評論 王國維 西方哲學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像很多其他學科分支一樣,其發展軌跡受到了西方的影響。從嚴復(1854—1921)譯介英國哲學開始,各種西方學說流派在中國找到了自己的聽眾。因此,運用西方哲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也就非常流行了。
在引進西方學說的眾多先驅者中,王國維(1877—1927)或許比其他人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展的貢獻更大。他的《紅樓夢評論》是學習德國意志哲學的直接成果,巧妙地運用了叔本華的藝術理論來研究中國名著《紅樓夢》。它從深度和廣度上論述了《紅樓夢》的精神內涵、美學價值、倫理價值以及悲劇意識。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并未將注意力放在現代學者認為值得關注的《紅樓夢》的重要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上。因而就連研究《紅樓夢》最有名的現代學者吳世昌先生也遺憾地未曾提及王國維這本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吳世昌先生遺漏《紅樓夢評論》很可能源于他的主要興趣在于文本批評而不是小說的文學批評。《紅樓夢評論》成于 1904年,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和胡適的文章《紅樓夢考證》的發表還早了十多年。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對于小說作者被忽視深表遺憾,他督促自己的學生去研究作者的生平和小說不同版本的成書時間。盡管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胡適的研究可能受到了王國維那本書的啟發,不過也沒有證據表明相反的情況就是真實的。不同于蔡元培的“猜謎”和胡適的文本探索,《紅樓夢評論》代表了一種用哲學思維去研究《紅樓夢》。就像王國維在“自序”中提及的那樣,他的《紅樓夢》解讀主要基于叔本華的哲學。
對王國維來說,《紅樓夢》不僅提出了叔本華在《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中提及的問題,同時也找到了問題的答案。王國維首先問道:“生活之本質為何?”追隨叔本華的思想,他提出生活的本質無他,只有作為意志行為的欲望而已。人性貪婪,欲望源于得不到滿足,而欲望得不到滿足的狀態即是苦痛。滿足一個欲望,則此欲望才能終止。然而,得不到滿足的欲望永遠多于得到滿足的欲望;同時,當一個欲望被滿足后,其他的欲望又會隨之而起。因此,終極的滿足是不可能的。王國維進一步論道,即使所有的欲望都被滿足了,再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去追求了,那么倦怠的情緒就會隨之而來。倦怠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苦痛,因為它使生活變成了負擔。因而,人生實如鐘擺,來回搖擺于苦痛和倦怠之間。
可以驅散人之苦痛與倦厭者,一般謂之曰“快樂”。但是在追尋快樂的過程中,人除了承受固有的苦痛之外,還必須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這反過來說也是一種苦痛。而且經歷過快樂之后,人對苦痛的感覺會變得更加敏感。常見苦痛不屈服于快樂,未見快樂不先之或繼之以苦痛。同時,人類的苦痛隨著文明的進步而增加。文明的程度愈高,人擁有的欲望愈多,他感覺到的苦痛也就愈強烈。王國維總結道,既然人的欲望不會越出生命本體,那么人生的本質就是苦痛,而欲望、生活和苦痛實際上只是一回事。
在所有的欲望中飲食之欲和男女之欲最為強烈。實際上男女之欲比飲食之欲更為強烈,因為前者在繁殖后代的生理需求的驅使下可以達到生命的永恒延續,而后者僅僅只能滿足此生的需求。“因而男女之欲是無盡的、形而上的,而飲食之欲是有限的、形而下的。”進一步來說,既然苦痛的程度與生活欲望的強度成比例,那么男女之欲所致的苦痛顯然要遠遠大于飲食之欲所致的苦痛。尋找引發和治愈男女之欲所致的苦痛顯然已經成為人類的當務之急。王國維指出,例如裒伽爾(1747—1794)就曾在他的詩歌中明確了這一問題: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學,既深且躋。
粲粲生物,罔不匹儔,各嚙厥齒,而相厥攸。
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
嗟汝哲人,淵淵其知。相彼百昌,奚而熙熙?
愿言哲人,詔余其故。自何時始,來自何處?
如果裒伽爾沒有在西方找到問題的答案,那么他應該試試在東方尋找答案。按照王國維的說法,《紅樓夢》體現了人生的苦痛,尤其是男女之欲的苦痛,都僅僅是人自己造成的,因此釋放苦痛的關鍵也就需要人自己去尋找。
在小說的開頭有一個關于寶玉來歷的神話解釋:
卻說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后,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骼不凡,豐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于掌上,笑道……“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
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后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
在王國維看來,這一段話體現了生活之欲先于人生而存在,而人生實際上只不過是生活之欲的表現或物化。同時,人之由天真無邪的天堂墮落到充滿苦痛的人世,就是其意志自由的罪過所致。對于那塊已經獲得靈性的頑石來說,這的確是不幸的;無論如何,如果那頑石安于他的命運留在那太虛幻境中,它也許就可以避免經歷人間的諸多苦痛。相反,它卻嘗試通過哀怨和不以為然堅持它到人間的愿望,從而開始了寶玉和其表妹黛玉的悲劇愛情,以及小說中其他的很多故事。
從人世的苦痛中解脫出來的關鍵必須要被人自己找到,這從敘述寶玉與和尚對話的片段中可以體現出來:
“弟子請問師傅,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
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你那玉是從那里來的?”
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和尚笑道:“你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
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
那句“……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的確意味著寶玉并沒有意識到他的人生是他意志自由的罪過所致。但是當那和尚一問他那玉,他立即意識到他在人世的不幸生活是他自己向往人世之念的后果,且他自己無法拒絕。因此,他想返還那塊象征著生活之欲的玉給那僧人,并開始朝著從人生苦痛中解脫出來的路徑邁進。
王國維說:“解脫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因為他已經知道生活不能避免苦痛,所能依靠的是解除生活之欲。在完成這一過程的終極階段,出世者的軀體雖存,但其心已經猶如死灰。另一方面,一個尚未解除自己生活之欲的人反而選擇自殺,這并不能被視作獲得了解脫,因為他只是不滿意現在的生活狀況,而追求來生有更好的命運。他對生活的欲望如原來一樣保留了下來,且會重現于來生,這樣苦海之流將無窮無盡。因此,王國維并不認為金釧之墮井、司棋之觸墻、尤三姐之自刎是真正的解脫。她們自殺僅僅是因為不能在此生實現她們的欲望。王國維注意到,“此書中真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
盡管自殺在平常看來并不是真正的解脫,但王國維在另一處論道:“茍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王國維這最后的聲明非常有意思,它不僅表明了王國維和叔本華在對待自殺的態度上的差別,而且也為王國維本人的自殺提供了一條線索。像王國維這樣極其欽佩叔本華哲學思想的人也會自殺,這對大多數人來說是另一個謎,要知道在叔本華的哲學中自殺是被譴責的愚蠢行為。一些人甚至因為他聲稱研究叔本華哲學而嘲笑他言行前后矛盾。但是他與叔本華理論中關于自殺的輕微但非常重要的分歧仍然未被關注。閱讀上述引文可知,假如王國維在自殺之前就已經放棄了他的生活欲望,那么我們可以斷定他的自殺在他的哲學中是說得通的。
王國維進一步注意到解脫之道有兩種:一是觀察他人的苦痛和思考世上的苦痛,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經歷苦痛。然而只有非常之人能通過前一種方式實現解脫;對于常人而言,解脫只能在他自己經歷苦痛的過程中去實現,而不是通過認知或者思考他人的苦痛來實現。那些非常之人由于擁有非凡才智,已經洞觀了宇宙人生的本質,無需親身經歷苦痛也能知道生活與苦痛不可分割,因而終結其生活的欲望并獲得解脫。但常人解脫的過程則是不同的,常人的生活欲望通常會因得不到滿足而愈加強烈,又因愈加強烈而愈加得不到滿足,重復這種循環則會陷于更大的長久的絕望中,其最終才會領悟到人生的真相而去尋求解脫。通過觀他人之苦痛獲得解脫可被稱為“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平和的也”,而通過親身經歷苦痛獲得解脫則被稱為“人類的也,詩歌的也,壯美的也”。惜春、紫鵑的解脫屬于前者,寶玉的解脫屬于后者。“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為賈寶玉者也。”
討論了《紅樓夢》的哲學基礎之后,王國維繼續探討了它的美學價值。他注意到中國人的精神通常被描述為世俗的和樂觀的,這種精神在中國文學中很常見。例如,在戲曲和小說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情節,即始于悲傷終于歡樂,始于離別終于團圓,始于困頓終于好運。他宣稱:“故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但前者(《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因為在厭世和解脫的強調上,《紅樓夢》顯然與中國人的精神希冀相背離了,“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
王國維深受叔本華悲劇理論的影響,在他看來,《紅樓夢》是一部舉世矚目的悲劇。在叔本華的美學理論中,悲劇因其影響力巨大和成就難以企及被視為文學藝術的頂峰。對悲劇而言,巨大的不幸是其唯一必不可少的關鍵性因素。叔本華基于悲劇呈現的方式將其歸為三種類型。其一,悲劇可能會通過極惡之人極其所能地制造不幸而發生。其二,悲劇可能會通過盲目的命運,即際遇和錯誤而發生。其三,人物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導致不幸。普通人物在沒有特殊事件或境遇的情況下做平常的事情,也可能因為人際關系明知故犯地致使他人遭受巨大傷害。按照叔本華的觀念,第三種類型的悲劇比另外兩類悲劇的悲劇感更濃,因為它體現了由普通人的性格和行為而非稀見事件或際遇引發的巨大不幸。因而蕓蕓眾生皆與此密切相關。第三種類型的悲劇也最難被創作出來,因為它必須由最少的起因產生最大的感染力,且其主要應通過人物的立場來實現。王國維認為《紅樓夢》就恰好屬于這類悲劇。
我們來看看寶黛愛情的悲慘結局是怎樣形成的。寶玉的祖母(賈母)喜愛薛寶釵的溫婉而不喜歡黛玉的孤僻,且由于深受命定的“金”(寶釵的象征)“玉”(寶玉的象征)良緣之迷信觀念的影響,她認為如果寶玉與寶釵結婚,寶玉的病就會痊癒。寶玉的母親王夫人與寶釵的母親是親姐妹,因此在決定寶玉的婚配對象時,她自然會喜愛寶釵多于黛玉,因為黛玉的母親只是她的小姑子。寶玉的嫂子王熙鳳深受賈母和王夫人的喜愛,她忌憚黛玉的才華,且擔心如果黛玉嫁給寶玉,那她在賈府的地位就會被黛玉蓋過。因此盡管她看到了寶玉和黛玉之間深深的愛情,但當討論寶玉和寶釵成婚的提議時,她沒有提出異議。同樣,作為合理選擇成為寶玉第一個妾的襲人,也因黛玉無意中說的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感到不安,她害怕如果黛玉成了她的上頭人,那尤二姐、香菱這樣妾的命運會降臨到她身上,因而她對寶玉與寶釵成婚的提議表現出了更大的熱情。最終,盡管寶玉深愛著黛玉,但作為一個孝順的兒子,傳統道德要求他不能違背祖母和母親的意愿。結果,“金玉以之合,木(林黛玉的別名)石以之離”。這出悲劇里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卷入其中么?沒有。其不幸皆由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和通常之境遇造成。從這個角度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此外,王國維沿襲康德和叔本華提出兩大美學品質:優美和壯美。“茍一物焉,與吾人無利害之關系,而吾人之觀之也,不觀其關系,而但觀其物,而謂此物曰優美”,且我們擁有的那種心態就是優美。而壯美的美學品質就是從中人們能意識到不利于己的事件和對象,并通常會產生敬畏感。但通過意志的自由超越,人們能夠在超然忘我的情境下觀照這些事件和對象。事實上,優美和壯美都能讓人暫時從生活的欲望中解放出來,使之進入到一種“純粹之知識”的狀態。然而一些與優美和壯美相左的藝術,則不僅不會減少或熄滅人的欲望,反而會加劇人的欲望。對于這類藝術,王國維杜撰了“眩惑”這一術語,并堅持認為色情文學之類的眩惑文學沒有任何美學價值。
《紅樓夢》當然不是那類眩惑文學,作者在小說開頭就申明了這一點:
至于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欲寫出自己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紅樓夢》無意成為作者明確憎惡的淫穢文學或一個常見情節的愛情故事。那么,《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是什么?既然它是“悲劇中之悲劇”,那么其表現的壯美也就多于優美了。王國維將描述寶玉和黛玉最后一次相見的片段視為“壯美文學”的代表:
[聽了傻大姐說寶玉娶寶釵的話,]林黛玉感覺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似的,兩只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腳下愈加軟了。走得慢,且又迷迷癡癡,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里走起來。
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里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
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
紫鵑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攙著她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里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
“你做什么來的?”
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里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
黛玉笑著說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么往這里走呢?”
紫鵑見她心里迷惑,便知黛玉定是聽見那丫頭什么話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里怕她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里雖如此想,卻也不敢違拗,只得攙她進去。
那黛玉卻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里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兒玩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里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
“姑娘,屋里坐罷。”
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么?”
襲人不知底里,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后和她努嘴,指著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見寶玉在那里坐著,也不起來讓座,只瞅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瞅著寶玉笑。兩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
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么病了?”
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
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人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和寶玉一樣,因悄和紫鵑說道:
“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
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便來同著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仍舊瞅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
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
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
在這個發展的段落中,悲劇效果通過黛玉和寶玉之間的寥寥數語和對黛玉非凡英勇力量的出色描述強烈地傳達出來了。盡管沒有哭泣、嗚咽和通常的情緒化,黛玉和寶玉的痛苦還是被讀者深切體會到了。
美學價值和倫理價值的一致性已經成為西方哲學最喜歡表現的主題之一。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悲劇被看作是一種宣泄,因為其有凈化心靈和使人精神崇高的效果。因此,藝術的目的從根本上說也是倫理學上的目的。同樣地,在叔本華的哲學體系中,悲劇,尤其是第三種類型的悲劇被視為詩歌藝術的頂點,因為其通常代表了生活可怕的一面,暗示了世界的本質和存在,因而能引導人們去尋求解脫。因此,藝術的終極目標和倫理學上的終極目標合二為一了。循著這一思路,王國維指出《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其倫理價值有關:
《紅樓夢》者,悲劇中之悲劇也。其美學上之價值,即存乎此。然使無倫理學上之價值以繼之,則其于美術上之價值,尚未可知也。今使為寶玉者,于黛玉既死之后,或感憤而自殺,或放廢以終其身,則雖謂此書一無價值可也。
如前所述,常人尋求解脫的路徑即在生活中經歷苦痛。但苦痛本身沒有固有的價值,其價值純粹在于它是人們實現精神解脫的物質媒介。面臨極大的苦痛時,人不會為了結束苦痛去自殺或尋求虛幻的感官愉悅來欺騙自己。真正的解脫是禁欲,其次是放棄生的欲望。《紅樓夢》的精神顯然在于解脫,因此“《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
最后,王國維提出了通過禁欲達到解脫是否足以被視作倫理最高境界的問題。王國維承認,從通常之道德的角度來看,其不是最高境界。例如,寶玉的情況按照世俗傳統,他大概會因為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被看作罪人。王國維注意到通常之道德對社會秩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其價值必須被承認。但是,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是有一個合理的根據,還是僅僅出于盲目的行動而別無意義?如果世界和人生的存在有一個合理的根據,那么通常之道德應該被視作絕對之道德。但王國維認為,從各方面來看,世界和人生的存在都僅僅是人類遠祖所犯偶然性錯誤的后果。這一觀點可從哲學家的暝想、詩人的悲歌和古代諸國的民間故事及神話傳說中得到印證。《紅樓夢》開頭關于寶玉來歷的神話故事也能使人想到同樣的宗教信條。既然生命的真相是人類遠祖犯錯的后果,則只要世界上仍然有一個人沒有獲得解脫,那么祖先的罪過就無法彌補。用通常之道德的標準來衡量,寶玉會因不忠不孝而被譴責;但是從超脫的角度來看,他定會被看作是嘗試通過不再從生物學上繁殖新生命來糾正祖先所犯錯誤的人。他明白祖先的過錯,不忍重復這種錯誤而加重其罪過。從這個角度來看,寶玉定會被認為是真正的孝順。他(寶玉)所說的“一子出家,七祖升天”,意味著他的孝道不同于通常之道德所謂的孝道。
至此,王國維已經成功運用叔本華的哲學來闡釋小說《紅樓夢》了。然而他天生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在運用叔本華哲學的過程中,他也感知到了其不同。一般而言,過去存在著兩種針對叔本華解脫理論的異議。第一,如果像生活一樣尋求物化是意志的本質,像叔本華主張的那樣,那么說拒絕生活意志似乎就暗示了意志的自相矛盾。第二,如果意志是自在之物,世界形而上的規則和存在是一個整體,那么當其他事物沒有同步時,個人通過拒絕生活意志獲得解脫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事實上,叔本華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些困難并試圖通過求助于神話傳說來解決它們,如提倡“前世的經歷”和“神的轉世”④。王國維并不認為這些宗教神話能解決問題,他提倡世界之解脫必須在邏輯上優先于個人之解脫。因此王國維總結道:“解脫之足以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與否,實存于解脫之可能與否。”
王國維論述的另一點也值得關注。盡管通過禁欲尋求解脫可能不是倫理學上的最高境界,但它至少是一種理想境界。功利主義的倫理理想是尋求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但在王國維看來,這種理想被實現的可能性值得懷疑。他強調生活存在兩面,即度與量,這兩者實際上互為反比例。
當世上有太多的生命時,其度一定會變到最低限度,因為世上的資源和范圍有限。終極解決方案要么是限制世上的生命之量,要么是維持生命之最低標準。在這兩者的任何一種情況下,功利主義道德理想和禁欲主義道德理想的不同都似乎只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王國維用《紅樓夢評論》創造了中國文學批評的開拓之作。《紅樓夢評論》寫在一百一十多年前,當時西方文學批評在中國仍然是聞所未聞,因而我們不得不佩服王國維吸納西方觀點闡述中國文學作品的非凡能力。王國維的著作可能是現存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著作中資歷最老的,它倡導了一種研究《紅樓夢》的新方式,與此同時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示范。
Western Philosoph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gloumeng PingLun
〔US〕Ching-I TuTrans.Deng Mingjing
(1.Rutgers University,New Jersey,USA;2.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Hubei,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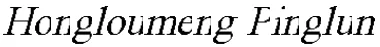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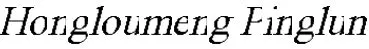
責任編輯:陳水云
涂經詒(1935—),男,湖北黃梅人,美籍華裔漢學家,1966年畢業于華盛頓大學東亞系,獲博士學位,現為美國羅格斯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及孔子學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文學與文論研究。
鄧明靜(1988—),女,湖北安陸人,湖北大學《當代繼續教育》編輯部編輯,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