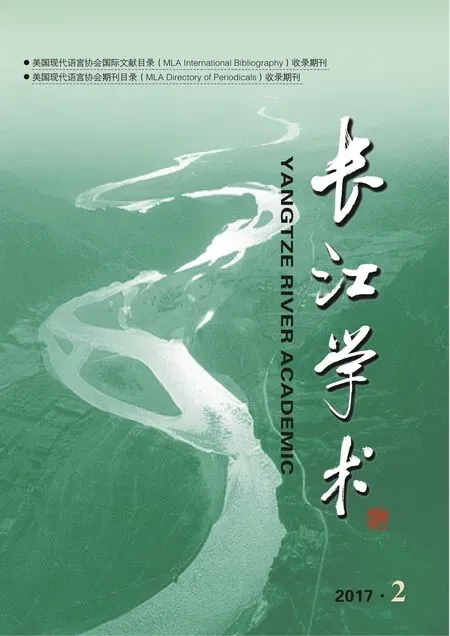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與文學(xué)的絕對
〔美〕徐平著 郭蔚臻譯 張箭飛審譯
(1.紐約市大學(xué)白如鶴分校 現(xiàn)代語言與比較文學(xué)系,美國;2.3.武漢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與文學(xué)的絕對
〔美〕徐平著 郭蔚臻譯 張箭飛審譯
(1.紐約市大學(xué)白如鶴分校 現(xiàn)代語言與比較文學(xué)系,美國;2.3.武漢大學(xué) 文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引證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雅典娜神殿斷片》及其他著述,本文試圖反駁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將“文學(xué)的絕對性”等同于“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的斷言,進而指出這兩位作者不但全然忽視了施萊格爾思想中的矛盾沖突的意義,而且暴露出他們對不矛盾律邏輯的堅守,而這一邏輯正是整個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的特征,也是施萊格爾和早期德國浪漫主義所攻擊的對象。
施萊格爾 雅典娜神殿 文學(xué) 絕對 浪漫主義 拉庫·拉巴爾特 南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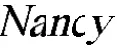
本文的主要目的:質(zhì)疑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所定義的“文學(xué)絕對(the liter aryabsolute)”的概念。通過閱讀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我想說明,施萊格爾的寫作具有一種張力,這種張力不會允許這種簡單鑒別:“文學(xué)的絕對性”和“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這兩個術(shù)語都統(tǒng)攝在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文學(xué)的絕對”的名義之下。同時,我也想指出,這種簡單鑒別不僅忽視了“張力”在施萊格爾思想中的重要性,而且暴露出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仍然深陷于不矛盾律邏輯(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之中,這正好是整個西方哲學(xué)傳統(tǒng)的特征,恰恰遭到施萊格爾和早期德國浪漫主義的全面挑戰(zhàn)。
一
什么是“文學(xué)的絕對”呢?正如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在前言中指出的那樣,“文學(xué)的絕對”指的是“浪漫主義思想不僅關(guān)涉文學(xué)的絕對性,而且關(guān)涉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換言之,遵循德國浪漫主義傳統(tǒng),這就意味著指浪漫主義思想不僅關(guān)涉文學(xué)的理念,而且關(guān)涉作為理念(dieidee)的文學(xué)。對于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來說,“文學(xué)的絕對”指的就是文學(xué)作為體裁(literature as the genre)這一概念,“一個或許在今天不可定義的概念,但卻是浪漫主義者曾經(jīng)竭力定義的概念。”至于“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類似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知識(absolute knowledge)”,用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話來說,“(絕對知識)之所以絕對,與其說是因為它是無限的知識,不如說是因為它是在知其所知的同時仍能自知的知識,這種知識因而構(gòu)成知識的真正的無限性,和其體系。”
顯然,根據(jù)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分析,定義文學(xué)作為體裁的概念——浪漫派這一嘗試其實就是一種確立文學(xué)作為絕對知識的意志。換言之,對浪漫派而言,“文學(xué)的絕對性”等同于“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也即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謂之的“文學(xué)的絕對”。“文學(xué)的絕對性與其說是詩(詩的現(xiàn)代概念是由《雅典娜神殿》斷章116所發(fā)明的),不如說是詩藝(poiesy),按照詞源學(xué)說法,而浪漫派總是求助于詞源學(xué)。所謂詩藝,就是生產(chǎn)。絕對地說,“文學(xué)體裁”這一思想所涉及的與其說是文學(xué)之物的生產(chǎn),不如說就是生產(chǎn)。浪漫派詩歌力圖深入詩藝的本質(zhì),也即,文學(xué)之物從自身產(chǎn)生出生產(chǎn)的真相(the literary thing produces the truth of production in itself),接踵而至的就是:詩藝生產(chǎn)以及詩藝自動生產(chǎn)(autopoiesy)的真實——這一點顯而易見。如果說,自動生產(chǎn)確實造就了終極實例(ultimate instance)和思辨絕對性(the speculative absolute)的終結(jié)——黑格爾很快就要論證:它其實徹底顛覆了浪漫主義,那么,可以說,浪漫主義思想所論及的不僅是文學(xué)的絕對性,而且是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簡言之),浪漫主義就是文學(xué)的絕對的開端。”
“文學(xué)的絕對”之概念,可稱作“文學(xué)的絕對性”,也即“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毫無疑問地構(gòu)成了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整本書的基礎(chǔ)。這讓他們能夠斷言:德國唯心主義始終保持著“浪漫主義的哲學(xué)視野”;文學(xué)的現(xiàn)代概念,從它誕生之時就“受控于”哲學(xué);浪漫主義依舊寄居于“體系——主觀(system-subject)”之內(nèi);就浪漫派而言,無法生產(chǎn)“絕對的作品”,這種失敗意味著“文學(xué)絕對的絕對消解”。總之,它允許“文學(xué)絕對的某一顯著優(yōu)點”存在,根據(jù)這本書的譯者所說:
因此,文學(xué)絕對的顯著優(yōu)點,其一即為,它提出并執(zhí)著于文學(xué)問題,諸如此類。正如作者的分析所表明,文學(xué),一如人們通常理解,浪漫主義的且現(xiàn)代性的文學(xué)概念,文學(xué)作為合法化和體制化的學(xué)科對象,完全是對某種哲學(xué)“危機”的回應(yīng)。人們接受的文學(xué)概念,換言之,也就是假定在諸多方面文學(xué)都是異于或者外在于哲學(xué)的(因此就可以永遠哀嘆:文學(xué)從外面突侵哲學(xué),或者“理論”侵入文學(xué)難題),其實哲學(xué)卻無時不刻貫穿于其中。當文學(xué)做出最全面的真實姿勢時,也正是它最大程度依賴哲學(xué)之時。
我并非有意低估文學(xué)絕對對于我們重新反思關(guān)乎文學(xué)與哲學(xué)所有問題的重要性,這也是近些年來在文學(xué)理論領(lǐng)域所探討的核心問題,但是我想要質(zhì)疑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認為理所當然的“文學(xué)絕對”概念的基礎(chǔ)。說得更明確一些,對我而言,文學(xué)的絕對似乎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作為絕對的文學(xué)”。然而,在試圖定義文學(xué)的概念的過程中,浪漫派的確有著將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與其說文學(xué)自身是絕對的,倒不如說文學(xué)是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換言之,將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與文學(xué)是一種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關(guān)系。在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這里,這種張力關(guān)系卻因鑒別“文學(xué)的絕對”和“文學(xué)作為絕對”而消解。這樣一來,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不但無法公正地對待浪漫派,而且也不能夠欣賞浪漫派的佯謬立場(paradoxical positions)——而后者正是籍此挑戰(zhàn)哲學(xué)思維的傳統(tǒng)方式。
二
這種張力關(guān)系在施萊格爾作品中顯而易見。
不用說,在施萊格爾作品中,將文學(xué)(或藝術(shù),或詩)絕對化的傾向俯拾即是。在他的《斷片集》中,他談?wù)摰搅恕皡f(xié)作詩(sympoetry)”、“先驗的詩”,他宣稱“詩和哲學(xué)應(yīng)該合二為一”;“哲學(xué)所止,詩之所始”;“藝術(shù)作品折射宇宙的另一面——unednlicheEinheit”。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在他《斷片集》第350條中,施萊格爾說道:“無詩歌即無現(xiàn)實。任憑感覺具備,無幻想則無外在世界,同理,即使感覺具備,無心緒則無鬼神世界。誰如果只有感覺力,他看不到人,而僅僅看到人性:只有心緒這根魔杖可召來萬物”。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同樣在施萊格爾那里,我們也可以清楚地感覺,文學(xué)并沒有如此絕對,而是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一種表現(xiàn)不可表現(xiàn)(the unrepresentable)的間接方式;一種表現(xiàn)思辨概念(speculativeconcepts)無法表現(xiàn)的間接方式。在這個意義上,絕對不是詩,也不是哲學(xué),而是遠遠超過二者的某物,施萊格爾稱作是“神圣(divine)”的東西。在第419條中,施萊格爾說,“神圣,就是源自于愛,升入至純至臻,高于任何詩歌和哲學(xué)。有一種寧靜的神圣,沒有英雄和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所具有那種毀滅性力量(crushing power),只要神圣,就會完善,偉大便是完美。”需要注意的是,對于施萊格爾,浪漫主義詩歌,一如教養(yǎng)(Buildung)和寓言,是欲成而未成的完美。甚至第116條,即使文學(xué)的絕對化達到峰值,我們依然可以讀到如下語句:“浪漫詩還在變化中;它永遠只在變化,永遠不會完結(jié),這正是浪漫詩的真正本質(zhì)。浪漫詩不會被任何一種理論徹底闡明,只有預(yù)言式的批評才敢冒險刻畫它的理論。”
顯然,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可以鑒別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所提出的“文學(xué)的絕對”和“作為絕對的文學(xué)”,那就是:在施萊格爾那里,施萊格爾沒有意識到在文學(xué)與絕對的關(guān)系層面,文學(xué)自有局限,所以試圖將文學(xué)絕對化,但他意識到文學(xué)不過是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如果將他的這個意識納入考慮,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鑒別就是不合理的。
從上面的討論,已經(jīng)可以清晰地看出施萊格爾的這種意識非常強烈。在這里,我想補充另一個片段,施萊格爾用一種確鑿無疑的語言表述:“詩歌,只是隱含著無限性,并不產(chǎn)生明確的概念,除了直覺之外。它(無限性)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豐富,是理念的混沌——詩歌力求表現(xiàn)這種混沌并將其融合為美好的整體。”
傾向于將文學(xué)絕對化與意識到文學(xué)是一種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這二者之間具有一種張力關(guān)系。現(xiàn)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這種張力關(guān)系?首先,不能忘記,對施萊格爾來說,文學(xué)應(yīng)該成為自己的理論,同時,它也是文學(xué)本身,正如他在斷片集第238條中說的那樣:“詩應(yīng)該描寫自身,總是同時既是詩又是詩之詩。”因此,如果理論(也就是文學(xué)本身)試圖定義“文學(xué)的絕對”,它是不可能“窮盡(exhaust)”詩的,正如在前面引文中施萊格爾指出的那樣,那么,同樣的理論怎么可能表現(xiàn)絕對?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文學(xué)是自身的理論,那么文學(xué)怎么可能表現(xiàn)同樣的絕對呢(the same absolute)?看起來,通過將文學(xué)絕對化(同時視文學(xué)為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施萊格爾事實上已表明表現(xiàn)絕對的完全不可能性。再換個角度來說,通過認定文學(xué)是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并揭示文學(xué)無法界定自己的理念及自己的絕對,施萊格爾得以削弱表現(xiàn)絕對這一可能性,而絕對是不可能用任何一種概念性語言表達清楚的。
我所指出的是,在施萊格爾作品中存在著清晰可辨的雙重姿態(tài)。通過將文學(xué)絕對化,施萊格爾毫無疑問站到哲學(xué)的對面。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通過認識文學(xué)自身的局限性,比如,將文學(xué)與哲學(xué)相提并論乃至認為文學(xué)應(yīng)當成為自身的理論,他同樣背靠著哲學(xué)。換言之,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先是直接地,然后是間接地削弱了思考傳統(tǒng)哲學(xué)特征的慣常方式(the conventional way of thinking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事實上,張力的兩極彼此矛盾,這代表著對具有概念性思考和表現(xiàn)性思考之哲學(xué)的雙重否定。正如Seyan指出的那樣:“在諾瓦利斯和施萊格爾那里,重提表現(xiàn)的難題,既非是想象力的非功利性實踐,也非完成哲學(xué)未竟事業(yè)的雄心勃勃和自我放任的嘗試。想象不可想象的意愿標畫出的路徑將浪漫主義引向新的疆域,在那里,現(xiàn)有知識形式的基礎(chǔ)受到激烈的挑戰(zhàn)。”
三
在施萊格爾作品中,這種張力絕非偶然出現(xiàn)。恰恰相反,它因“矛盾的理念”顯得更加突出,而矛盾恰好是施萊格爾思想的中心。“一切都在自我否定Alles widerspricht sich,”施萊格爾曾說,不僅現(xiàn)實如此,意識亦如此。這就是為什么施萊格爾反復(fù)在強調(diào)“兩種沖突的力”,“在自我創(chuàng)造(self-creation)和自我解構(gòu)(self-destruction)中不停地搖擺。”諾瓦利斯斷片集《花粉》(Blutenstaub)收錄了一則施萊格爾的斷片,他說:“一個人如果癡迷于絕對,無法擺脫這種癡迷,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斷自我沖突,與對立的極端事物并合。沖突注定不可避免,唯一可保持的選擇或是假定忍受這種命運,或是承認尚有自由行動的可能而將這種命運變成高貴的必然。”
同樣的矛盾概念也解釋了為何施萊格爾反復(fù)提到了反諷(irony)、機智(wit)、無序(chaos)、反論證(antithesis)。事實上,“斷片”這一概念就反映出矛盾概念的特征。
在斷片第121條,施萊格爾說:“一個理念也即完善到反諷境界的概念,就是絕對反論證的一個絕對綜合(an absolute synthesis of absolute synthesis),是兩種沖突思想之間不斷自我創(chuàng)造的置換。”在一些斷片中,他賦予機智如此特征:“化學(xué)的(chemical)”、“斷片的天才(fragmentarygenius)”、“受限精神的爆炸(an explosion of confined spirit)”、“聯(lián)合機智的無序(achaosofcombinativewit)。”在此,機智與理性之間的對比已經(jīng)很明顯了。正如Peter Firchow所說,“機智不是理性:理性是機械性和實驗性的;機智一觸即發(fā),并且來源于靈感。”
至于斷片本身,施萊格爾把它稱作“精神的自然形式”,并把它作為傳達他的理念的主要載體。在斷片集第22條中,他說:
一個構(gòu)想就是一個正在發(fā)展著的客觀的主觀萌芽。一個完美構(gòu)想一定既是完全主觀的,同時完全客觀的,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活生生的個體。究其起源,它是完完全全是主觀和原創(chuàng)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有可能成立;就其特性而言,它又是完完全全客觀的、自然的、道德必然的。對可稱為未來斷片之構(gòu)思的感覺,與對過去斷片的感覺,這兩種感覺只在方向上有所區(qū)別。前者是漸進的,后者是遞減的。本質(zhì)在于能將客體理想化,同時又能使其現(xiàn)實化:完善客體并部分地在自身里體現(xiàn)出它們。既然那些與理想和現(xiàn)實相合相分的事物就是超驗性,或許可以說,對于斷片及構(gòu)思的意識,乃是歷史精神的超驗性元素。
很清楚,根據(jù)施萊格爾所言,斷片的特征,恰恰是隱匿在佯謬之中破壞連貫性和哲學(xué)的不矛盾邏輯特征。正如Seyan所說,“斷片否定了連續(xù)表現(xiàn)的哲學(xué)(philosophical postulate)并給此種理念基礎(chǔ)造成裂痕。這一瓦解姿態(tài)恰恰扮演著佯謬的角色,糾纏著哲學(xué)不放。”在此,Seyan意指的“佯謬”來自施萊格爾的一篇文章“萊辛文章的結(jié)尾”,“就哲學(xué)生活的佯謬而言,或許沒有什么比那些彎曲的線條更美的象征了。憑借顯而易見的連續(xù)性和規(guī)則性,它們卻永遠只能表現(xiàn)為片段,因為它們的中心存在于無限。”耐人深思的是,正如Seyan指出的那樣,諾瓦利斯同樣也談?wù)摰搅恕皬澢木€條”,并且將它稱為“自然對于規(guī)則的勝利。”
現(xiàn)在很清楚,矛盾概念在施萊格爾的思想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我想表明的是,施萊格爾思想中顯著可見的矛盾概念已經(jīng)是邏輯不矛盾律(也即傳統(tǒng)哲學(xué)之特質(zhì))的持續(xù)顛覆,它的目標,用施萊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對最高知識做無果的追尋”(這個強調(diào)是施萊格爾的)。正如Manfred Frank指出的那樣:“事實上,它是對人性的復(fù)雜性、不確定性、不連貫性、以及矛盾性的發(fā)現(xiàn)。通過這一切它與那樂觀的傳統(tǒng)之間劃上了明確的分界線,不管這傳統(tǒng)是敬神的還是形而上學(xué)的。”以矛盾概念理解,將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和對文學(xué)自身局限的認識,這二者之間的張力看上去像是施萊格爾的游戲策略,從一開始他就以此對抗作為哲學(xué)之特征的不矛盾邏輯。換言之,通過在矛盾的兩極之間的“搖擺不定”,這種張力才能對其邏輯完全異于矛盾概念的哲學(xué)形勢我稱之為的雙重否定(doublenegation)。
四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著作,應(yīng)該注意到的是,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遮蔽張力以便彰顯“文學(xué)的絕對性”和“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的區(qū)別,此舉也并非偶然。畢竟,正如他們明確宣稱的那樣,他們的目的是要“對浪漫主義進行恰如其分的哲學(xué)研究”,“以哲學(xué)的方法解讀這些(浪漫主義)文本”。
如果我的理解無誤,這就是他們?yōu)楹蜗胍獏^(qū)分“文學(xué)的絕對性”和“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的原因。因為唯獨通過這種區(qū)分,他們才得以宣稱浪漫主義由哲學(xué)所控制,也即浪漫定義文學(xué)概念的企圖是確立文學(xué)作為絕對知識的意志。結(jié)果,他們根本不會把存在于浪漫主義之中,特別是施萊格爾之中的張力納入考慮,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整體上摧毀他們的構(gòu)想。總之,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整個構(gòu)想的邏輯就是建立在無視這種張力的基礎(chǔ)之上的。
因此,在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的眼中,浪漫主義的特征僅僅是把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而我則認為,其特征是:認識到文學(xué)與其說是絕對的不如說是一種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這個認識卻被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看做是:并沒有抓住浪漫主義的本質(zhì)和目的。
顯然,在《文學(xué)的絕對》一書中,爭論沿著這條線索展開,它始于區(qū)別“文學(xué)的絕對”和“文學(xué)作為絕對”,最后以失敗于定義浪漫主義的“文學(xué)的絕對”而告終。換言之,始于論證浪漫主義和哲學(xué)同一性,終于顯示浪漫主義乃哲學(xué)的失敗(former’s philosophical failure)。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其實探討的是浪漫主義不可能回答“什么是文學(xué)?”這一問題:
浪漫派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甚至對此含混不清,或者把一切夾雜在這個問題之中——浪漫派的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可能性顯然說明,它的問題實際上純粹是言之無物,徒有“浪漫派”或“文學(xué)”(還有“詩”、“文學(xué)創(chuàng)作”、“藝術(shù)”、“宗教”等等)的虛名,只要觸及到這種難以劃分和難以確定的東西就無限退縮,(幾乎)接受所有的名稱,卻又不能容忍其中的任何一個:那是一種不可命名、沒有輪廓、沒有形狀的東西——說到底,它“什么都不是”。浪漫派(文學(xué))就是沒有本質(zhì),甚至不存在于其非本質(zhì)性之中的那種東西。
這種不可能性被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看成是浪漫主義無法避免的失敗,但這也可以被看作只是基礎(chǔ)的失敗——“文學(xué)絕對”建立在既是“文學(xué)的絕對”又是“作為絕對的文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這一基礎(chǔ)是失敗的,而只有在這樣的基礎(chǔ)之上浪漫主義才能成為哲學(xué)構(gòu)想。隨之而來的是,只有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才有理由宣告“什么是文學(xué)”的問題是空洞的,文學(xué)的浪漫主義概念是不明晰、不確定、不可名之物,也即無形、無狀、甚至無物。然而,如果我們把施萊格爾作品中存在的鮮明的張力關(guān)系納入考慮范疇的話,我們會說,不明晰與不確定恰好是施萊格爾想要展現(xiàn)出來的文學(xué)特質(zhì)。正是因為表現(xiàn)絕對的不可能性,所以當我們屢屢嘗試去定義文學(xué)的時候,必須再三地顛覆之前的定義。“浪漫主義與生俱來的不可能性”,的確如此,但與其說這是浪漫主義的失敗,我更愿意說,恰恰相反,這才是浪漫主義的要義所在。
這一理解同樣適用于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所指責的浪漫主義夸張和歧義。論及夸張或夸張化,他們說,“這里的夸張,就是,詩的夸張,是從有機隱喻的字面化發(fā)展而來。或者更確切地說,既然藝術(shù)作品的有機性或者整首詩遠遠超過(或不止)一個隱喻——詩的夸張化,或詩的消解,是工具的理念或者工具作為一種理念而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至于“歧義”,他們寫道:
我們再三重申:斷片、宗教、小說、批評都以各自的方式重構(gòu)文學(xué)和文字的體裁:類(Guttung)、物種、特殊性本身的特殊生成,相同成分混合的自主生成。自發(fā)生殖(也譯作自然發(fā)生),即那個時代所謂的偶然發(fā)生(generatio aequivoca),它本身具有兩種含義,它在任何情況下自我生成。鑒于這個事實,體裁中的每個體裁都以各自的方式同時肯定生殖的歧義,aequivoca的歧義:物種也相當于含糊不清和沒有個性的混合。甚至在消解的有機進程中,某種東西始終在抵抗或逃離:比如謝林的消融(Auflosung)中的某種東西始終在抵抗黑格爾的揚棄,施萊格爾小說的某種東西始終在逃離謝林的消融。
在此,這種譴責也是基于對“文學(xué)的絕對性”和“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的鑒別之上的。顯然,因為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將浪漫主義視為確立文學(xué)作為絕對知識的意志,最終他們賦予浪漫主義“夸張”和“歧義”的特征,但卻無法定義絕對知識本身。換言之,如果一個人事先預(yù)設(shè)了“文學(xué)的絕對性”等同于“作為絕對性的文學(xué)”,那么浪漫主義當然應(yīng)該被看作是完全的夸張和歧義。但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樣,在施萊格爾那里,將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已經(jīng)被對于文學(xué)與絕對關(guān)系的局限性的認識所傾覆。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把文學(xué)夸張化的姿態(tài)其實是想要展示表現(xiàn)絕對的不可能性。如果這樣理解,所謂的帶有“模棱兩可的混雜”的“歧義”應(yīng)該被視為是浪漫主義的一個優(yōu)點,因為只有哲學(xué)產(chǎn)生不矛盾的邏輯以及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所說的“辨識性”。
最后,我想截取《文學(xué)的絕對》中的一個片段,它可以被當作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想要挪用于(appropriate)施萊格爾,反而被施萊格爾所挪用:
可以理解,在這些條件下,文學(xué)或詩,“浪漫體裁”其實始終被人當作對文學(xué)本身的某種超越來追求,這至少印證了這種東西確實存在。實際上,這無異于指責《談詩》不能帶來他許諾的觀念。這樣的絕對化或無限化的過程在任何意義上都超過了作為這種完成的一般理論(或哲學(xué))的潛能。這種“自主”運動——自主構(gòu)造、自主組織、自主分解等等——如果人們能夠這樣說的話,相對其自身來說永遠是無節(jié)制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如《斷片集》第116條指出的那樣:“浪漫詩還在變化中;它永遠只在變化,永遠不會完結(jié),這正是浪漫詩的真正本質(zhì)。浪漫詩不會被任何一種理論徹底闡明,只有預(yù)言式的批評才敢冒險刻畫它的理想。”
在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從斷片集中引用了同樣的片段,我認為這是一種標志:施萊格爾清晰地認識到文學(xué)在關(guān)系到絕對層面上存在局限。但這一片段卻被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用來支持他們的論點:文學(xué)在與自身的關(guān)系上始終是過度的且無法定義自身。然而,即便我們接受了他們的論點,依然存在一個有待質(zhì)疑的問題:他們的論點和引用的片段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換句話說,什么叫做“這個說法,在《雅典娜神殿》斷片集第116條中也提到了”?如果這意味著施萊格爾在這個片段中已經(jīng)認識到了文學(xué)的超越性,那么結(jié)論將會是:施萊格爾已經(jīng)意識到了文學(xué)本身不是絕對,而是表現(xiàn)絕對的間接方式。顯然,恰恰是因為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不承認這種認識,他們扭曲了這一片段傳遞的信息,取而代之用一些模棱兩可的詞組諸如“也(too)”“從某種意義上來說(in a certainsense)”等等來混淆視聽。但施萊格爾的信息如此明晰無誤以致于他們最后的引用暴露出他們論點的問題所在。
如果浪漫主義真的僅僅是試圖建立文學(xué)作為絕對知識,真的存在想要將文學(xué)絕對化的傾向,那么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所說的關(guān)于浪漫主義的一切都是成立的。但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忘了問:為什么我們要將浪漫主義首先看作是一項哲學(xué)構(gòu)想呢?事實上,他們所堅持的假設(shè)本身有待于在已有資料的基礎(chǔ)上加以論證。在這個意義上,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在《德意志唯心主義最早的系統(tǒng)綱領(lǐng)》中僅僅指出浪漫主義和哲學(xué)唯心主義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不夠的。同樣的,通過說“施萊格爾兄弟注定去繼承家族傳統(tǒng)的批評事業(yè);他們首先是一個哲學(xué)家和理論家,而不是詩人”道出施萊格爾兄弟的“家族傳統(tǒng)”是毫無意義甚至荒謬的。
這里,關(guān)鍵之處不在于,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是哲學(xué)家,所以他們從哲學(xué)的立場上來對待這個論題是理所應(yīng)當?shù)摹U嬲匾氖牵ㄟ^哲學(xué)立場來反思浪漫主義,他們自己也成為哲學(xué)不矛盾邏輯的犧牲品,而浪漫派恰為最先反叛這一邏輯群體之一。結(jié)果,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傾向于完全無視浪漫主義中存在的張力,或者被迫將這一張力視為浪漫主義不完全性的標志。哲學(xué)從來沒學(xué)會寄身于張力或矛盾之中,它的任務(wù)就是將所有一切轉(zhuǎn)化成一個邏輯的連貫的整體。就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情形而論,他們通過確立“文學(xué)的絕對”和“作為絕對的文學(xué)”之區(qū)別創(chuàng)造一個邏輯的連貫的整體。事實上,這個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整體是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為浪漫主義創(chuàng)造的一個體系。在這一體系里,如果按照他們的方式思考,我所說的張力注定會被當做是內(nèi)在于浪漫主義的難題。很明顯,通過區(qū)分“文學(xué)的絕對”和“作為絕對的文學(xué)”,拉庫·拉巴爾特和南希不僅遮蔽了張力本身,還從總體上消解了施萊格爾和浪漫主義思考的能動方式。在此,我們可以設(shè)想一下,真正被哲學(xué)所控制的既不是文學(xué)也不是浪漫主義,而是“文學(xué)的絕對”的作者和《文學(xué)的絕對》。
Friedrich Schlegel and“The Literary Absolute”
〔US〕Xu PingTrans.Guo WeizhenProofread.Zhang Jianfei
(1.Dept.of Modern Languag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Baruch College of CUNY,US;2.3.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Drawing on Friedrich Schlegel’s Athenaeum Fragments and other writing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tradict Lacour-Labarthe and Nancy’s assertion that“the absolute of literature”is tantamount to“l(fā)iterature as the absolute”,and to point out that the authors not only ign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sion in Schlegel’s thinking,but also betrayed their adherence to the 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tir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challenged by none other than Schlegel and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at large.
Schlegel;Athenaeum;Literature;Absolute;Romanticism;Lacour-Labarthe;Nancy
責任編輯:汪樹東
徐 平(1957—),紐約市大學(xué)白如鶴分校現(xiàn)代語言與比較文學(xué)系終身教授。
郭蔚臻(1991—),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張箭飛(1963—),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比較文學(xué)與世界文學(xué)專業(yè)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