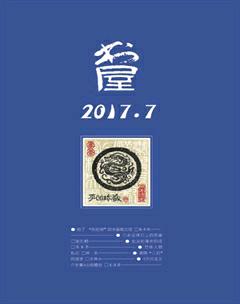復古的面相
朱光明
前、后七子是明代具有重要影響的文人群體,在弘治至萬歷的百余年間掀起一股復古浪潮,深深地影響著中國近世文學,乃至中華文化的走向。無論在民族心理的塑造,還是文學創作上,前、后七子都是中國歷史演進中不可缺失的一環。他們帶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是“復古”,不但有著完善的復古理論,而且有著豐富的創作實踐。然而,自晚明以來,隨著反擬古聲浪的高漲,前后七子不斷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時至今日,對前后七子的認識與評價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鄭利華先生的《前后七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對前、后七子文人群形成、崛興、衰亡各個階段的重要環節進行了重新審視,提出了不少新見解,辨析精微,論述深辟,為明代文學的研究朝著縱深方向推進提供了一種良好的學術范式。
談起前七子的復古運動,若不細加究察,我們很容易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一標簽所蒙蔽,這一口號的不合理之處,已有論者予以指出。然而前七子的復古宗尚系統是怎樣的,以及具體的層次與內在脈絡,關涉一代詩史的走向與風貌,亦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大關目,值得深入探討。鄭利華先生爬梳大量文獻,認真梳理前七子復古理念之開展,探究其復古的緒次與文學內蘊,最后得出結論:在詩歌的宗尚方面,李、何諸子追宗《詩經》、漢魏古詩和盛唐詩歌,雖與他們重視從這些具有“第一義”的詩歌中尋求養料的文學期望有關,或者是出于借助經典文本增強復古感召力的策略考量,還與他們注重詩歌的基本性質與審美特性有關,即“更加注重詩歌作為一種特殊文體的抒情特性,包括在此基礎上充分強調詩人情感體驗和表現的真實性,以及極力主張以有效和恰切的詩歌藝術表現手段來傳達詩人內在的情感”;在文章的取法上,李、何諸子對先秦、兩漢古文神醉心許,主要看重其樸質、切實、精簡的特點,而這些恰是后世之文所缺乏的,可作為學習的楷模。然而鄭著卻沒有止步于此,而是細細地辨察其中的針對性傾向,即諸子對執文壇牛耳之人壓制古文詞創作之士的不滿而表現出高度重視古文詞的態度,同時對明前期館閣文士鼓揚唐、宋韓、歐諸家導致文章流弊泛濫而進行的反撥。毫無疑問,這一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作為明確以繼承前七子復古大業而自命的后七子,在對待前七子復古思想方面,雖總體保持一致,然而具體層面,可謂是承繼中有新變。兩者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雅、俗的態度。前七子強調詩歌之“真”,對“真詩”的追求促使他們格外看重民間的“真詩”,而不惜貶抑文人士子的詩作,在某種程度上有“黜雅入俗”的味道。而后七子則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詩學立場,即“崇雅抑俗”。對于此一美學問題,鄭利華先生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體現在后七子諸成員身上這種崇雅抑俗的詩歌審美訴求,不可不謂折射著文人士大夫以雅正為尚的傳統意識,烙上了與之相關聯的根深蒂固的審美印記,由此其置雅與俗于對立緊張的關系之中,誠不足怪”。僅僅從這個角度,恐怕是不夠的,鄭著還進一步考察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演變脈絡,將上述問題置于詩史中觀照,并聯系后七子的創作實踐,指出后七子的這種審美訴求,是“與他們反宋、元詩歌日常化與淺俗化傾向的用意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而這一意向的呈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對詩歌這一特殊文體獨立品格的認知,以及由此所激發的強化相關藝術經營的意識”。只有對前、后七子對待雅、俗的具體態度以及傳統詩學的這一審美概念的相互關系進行詳細考察,才能深刻地認識復古的面相。
新變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對詩文本體藝術的高度重視,即“強調言辭修飾高度的藝術化和純美化”。后七子集團不但有立足于“詩之為詩”本位上進行創作的豐富實踐,而且有著較為系統的理論著作,如《詩家直說》、《藝苑巵言》、《詩藪》等。對此,鄭著深入細致地探察了后七子關于法度的闡論、復古習法的徑路與境界等方面,對后七子具體文學理念的審美訴求進行了精當的審視,品評允當。如在探討后七子復古習法的徑路和境界方面,鄭著從“積學”與“精思”、“擬議成變”與“悟以見心”、“因意見法”與“不法而法”三個維度來考察,既能抓住前七子、后七子兩者的共同傾向論述,又注意從二者的具體差異處入手辨析相關概念,找到分歧的癥結所在,同時較為全面地分析、審視二者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內在關系,最終揭開前、后七子復古的神秘面紗,讓人準確認識其復古情狀和審美內涵。
除此之外,《前后七子研究》一書的價值,并不局限于作者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見解,讓我們打破了對于復古的固有認識,還在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意義,即注重從人文生態、文人心態和作品形態三大主要方面入手,全面考察這兩大密切相關、影響明代文學走向的文人群體。在縷述成化、弘治之際學術與文學風尚及其變異的人文生態環境下,前七子是如何結盟,如何卷入政治漩渦,復古活動的倡起及文學熱潮的跌落,甚至中原與關中故里交游圈及活動重心的確立,同樣,在正德、嘉靖之際文壇格局的延續與衍變的大背景之下,后七子集團的形成、離京轉遷后的交往、濟南與吳中營壘的構筑和后期以王世貞為中心文學陣營的建立,在本書中都有著精彩的論述。從鄭著精簡的文字表述中可以看到一個文學集團的形成、發展演變的過程,灌注的是作者的生命關懷,將對前、后七子的理解和闡論置于更深廣的歷史脈絡中,無形中讓此書具有一種巨大的思想張力。在文人心態的把握方面,無論是對前七子從內在之性到時世之勢、政治情勢變易中的心態轉向以及寄心丘壑與順適其志的審視,還是對后七子寓志于仕路藝途之始的表現以及在進退之間徘徊的探討,皆能抓住其個性和心態,將文學理念的開展與七子心態的變化聯系起來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心態的變化也促使七子文學觀念出現一定的修正,文學觀念也可以說是七子心態的投射。諸子曲折幽微的心靈世界,在此書中得到了鮮活的呈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本《前后七子研究》就是一部精彩生動的士人心跡史。同時,鄭著亦十分注重對文學作品形態的分析,尤其是對詩歌文本的語言結構,投入了較多的心力進行闡述,向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的七子文學創作實態。對文本形態的高度關注與透辟論述,傳達著以文學為本位的書寫理念,而思想形態與語言形態的交織互融,尤其是冷峭謹嚴的行文風格中,無時無刻不在傳達著作者的識見。書后所附的《前后七子文學年表》則在歷時性的層次向我們呈現了前、后七子文學集團百余年的變遷,與前面的共時性的論述相互補充,相得益彰。
鄭利華先生接觸前、后七子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對此一領域投入了極大的心力和時間,先后撰寫了《王世貞年譜》、《王世貞研究》等著作,以自己的學術實績把前、后七子研究不斷推向新的高度。同時,于復古運動研究的傳統路徑中開創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學術研究范式,即人文生態、文人心態與作品形態相結合,把文學觀念的發生、展開放在動態的史程中審視,從而走向深細的學術研究,這或許是先生的思想關懷和創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