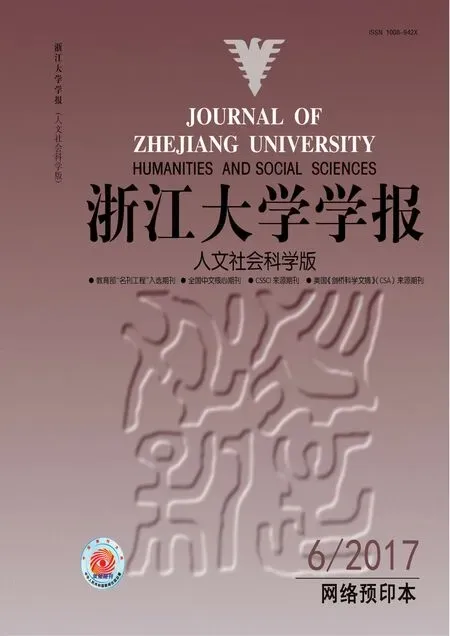論股權多重轉讓中善意取得規則的修正適用
吳勇敏 張桂龍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
論股權多重轉讓中善意取得規則的修正適用
吳勇敏 張桂龍
(浙江大學 光華法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08)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第1款規定“一股二賣”糾紛應參照適用善意取得規則。但股權與物權變動模式相去甚遠,股權登記對抗主義與善意取得制度亦抵牾頗多,股權多重轉讓參照適用善意取得規則將面臨適用上的窘境。為增進法律體系的和諧并促進股權登記、鼓勵誠信,第27條的修正適用需在登記對抗主義的前提下尋求先買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利益均衡點。由于我國現階段股權外觀效力的缺陷,股權多重轉讓中更需注重對先買人利益的保護,并妥當刻畫先買人的可歸責性標準與第三人的“善意”標準。可歸責性標準可以在個案中具體衡量,第三人“善意”標準可以從承擔有限的調查義務逐步過渡到善意推定,再到登記對抗主義,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對登記對抗的制度異化和干擾。
股權多重轉讓; 登記對抗主義; 善意取得; 修正適用
一、 問題之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以下簡稱《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將善意取得制度引入股權領域,其中,第25條、第27條分別規定了“隱名出資”、“一股二賣”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第106條處理。然而,學界對股權能否適用善意取得規則卻仍存爭議。贊成者認為,特定情形下會發生股權善意取得*比如股權連環讓與中的前手交易被認定無效或被撤銷,或者擅自處分共有股權的情形。參見郭富青《論股權善意取得的依據與法律適用》,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12頁。,而股權的真實權利歸屬與股東登記外觀的偏差,是產生權利外觀并成就善意取得的原因[1]41。股權善意取得制度體現了商法外觀主義對利益平衡的優勢,確保了在無權處分問題上法律技術的一貫性[2]47。批評者認為,股權變動異于物權變動[3-4],股權工商登記也無法承載權利外觀功能[3,5],而且股權二重讓與中,后受讓人的替代既無法理基礎,也無現實可能性*一股二賣中,前受讓人已經記載于股東名冊,公司無法為后受讓人辦理變更程序,否則有違誠實信用原則。整個過程中,后受讓人都保持善意不知情的情形,在實踐中極為少見。參見王涌《股權如何善意取得?——關于〈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8條的疑問》,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第32-33頁。,有限責任公司的人合性亦是其制度羈絆*對交易安全的一味追求與有限公司的人合性存在價值沖突,參見陳彥晶《有限責任公司股權善意取得質疑》,載《青海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第113頁。。另有部分學者則主張修正化適用,認為股權善意取得規則應在信賴責任框架下引入類型化的可歸責性要件,以彌補股權外觀可信賴度的不足[6],或者將各方風險和注意義務的分配納入考量范圍[7]。
為厘清股權善意取得的制度機理,應對紛繁復雜的司法實踐,重新審視股權善意取得理論尤為必要。具體而言,股權變動的法律定位、時間節點及其效力,股權善意取得參照適用《物權法》第106條的正當性,股權善意取得的理論依據和具體適用等核心問題亟待澄清。本文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第1款為中心,探討股權多重讓與中善意取得規則的機理。
二、股權參照物權善意取得規則的適用困境
(一) 股權變動的特殊性
1.股權變動模式的學說之爭
關于股權變動模式,學界可謂歧見紛呈。有觀點認為,股權轉讓合同僅產生履行義務,而非股權的當然變動,股東名冊是股權變動的生效要件,而工商登記具有對抗效力[8]313,這也是股東名冊立法功能和地位的體現[9]。另有觀點認為,股權轉讓采意思主義,股權轉讓合同一經生效,股權即被繼受取得。有關股權變更記載、登記的手續均不是股權轉讓的生效要件[10-12]。亦有學者認為,純粹債權形式主義和意思主義均有缺陷,應將公司受通知與認可程序嵌入意思主義的框架中,即股權變動于公司認可之時*關于純粹債權形式主義和意思主義的缺陷以及修正意思主義的體系,參見李建偉《有限責任公司股權變動模式研究——以公司受通知與認可的程序構建為中心》,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第19-29頁。。
2.股權變動遵循“公司確認+登記對抗”模式
依據《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45條,股權轉讓與債權轉讓并稱為權利轉讓,均可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然而,股權變動究竟是納入債權還是物權的參照體系予以適用仍然不甚清晰,這也是上述分歧的關鍵所在:第一種觀點以物權變動的視角來審視股權,后兩種觀點則立足于債權變動的視角。因此,求解股權變動模式及時間節點,首先在于確定股權轉讓的權利參照體系。本文認為,物權變動的比照解釋并不合理,有學者甚至批評《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為“物權式”的立法,使股權成為物權的延伸[13];相形之下,以債權為股權變動的權利參照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股權表現出相對權的性質,與債權的部分品格相契合,而與物權的絕對權性質捍格不入。股東是公司的成員,系與公司之間合同的相對方[14]265-266。股東權是股東地位上的權能和義務的集合體[15]204。股東地位隨股權轉讓而轉移[16]254,原股東的法律地位被受讓人完全承繼而退出其與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
其次,股權變動在程序上亦截然不同于物權變動,而表現出與債權轉讓相似的特性。股權變動涉及出讓人、受讓人、公司、其他股東等多個主體,需經歷股東同意、股東優先購買、通知公司辦理股東名冊記載、工商登記等多道程序,這與物權人一般可以依其意思而徑直處分其所有物的模式有相當大的差異,而股權轉讓中的通知程序則與債權轉讓程序相似。
本文認為,雖然股權變動表現出意思主義的特征,但與債權轉讓又有所差異,以通知和確認程序為核心的修正意思主義的解釋路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80條,未經通知的債權轉讓對債務人不發生效力。但依據反對解釋,未經通知,受讓人亦可對債務人外的第三人發生債權讓與效力[17]73。據此,當事人僅依意思表示就可取得債權,讓與通知僅具有對抗效力。然而,股權轉讓經通知后并不意味著受讓人可以當然取得股權:辦理股東名冊記載所涉及的公司確認程序是公司法上的重要議題,公司在某些情況下說明正當理由后可拒絕辦理股東名冊的記載[18]233-235。因此,公司確認程序的完成才能表征股東與公司之間法律關系的開始。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第32條第3款,工商登記是股權變動的外部對抗要件,據此,股權變動可以簡單概括成“公司確認變動+登記對抗”模式。可見,股權與債權和物權的變動模式旨趣不同,參照物權善意取得規則將面臨適用上的窘境。
(二) 善意時點判斷上的無所適從
根據以上分析,股權轉讓并非沿著物權變動的路徑,而大體上是債權讓與的軌道,這使《物權法》第106條的參照適用缺乏理據,而且有一種錯誤的導向,似乎把股權變動引導到類似物權變動的交付或登記的路徑上去。然而,若依《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參照適用《物權法》第106條的邏輯,無法回避的問題是:股權善意取得應參照動產或特殊動產的“交付”規則,抑或不動產的“登記”規則?從而便有“交付”的解釋路徑和“登記”的解釋路徑的探討。
1.“交付”解釋路徑的缺陷
股份有限公司無記名股票可適用動產善意取得的交付規則[10]261,有學者甚至認為善意取得僅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16]225。然而,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而言,何謂交付?有學者論稱:股東名冊變更登記時,即為股權交付、股東身份轉移之時[8]313。然而,此種觀點有待商榷。
首先,經股東名冊變更登記后的股權欠缺絕對對抗力,與善意取得的最終權利狀態不符*依《物權法》第106條第1款第3項,善意取得時點系于動產或不動產的交付或登記時,依《物權法》第6條,交付或登記是動產或不動產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因而《物權法》第106條善意取得的一般性前提是,若經交付或登記,動產和不動產物權已經發生絕對變動,足以對抗任何人。。德國法以股東名冊為權利外觀基礎確立股權善意取得制度[19]161-166,從而保障了股東名冊上所記載權利的效力。然而,依我國《公司法》第32條第3款,未經工商登記之股權“無法獲得公司法排他性的保護”[11]15,無法達到善意取得后的穩固權利狀態,股東名冊和通知也無法承載權利外觀功能。
其次,股權的邏輯起點不同于動產和特殊動產,不能簡單參照交付規則。基于現有特殊動產物權變動模式的考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20條明確了奉行登記對抗主義的特殊動產以交付為善意取得時點*該司法解釋的理由在于,現有特殊動產以交付為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因此善意取得時點同樣應以物權變動時點為準,登記僅是對抗要件。參見杜萬華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第一庭編著《最高人民法院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理解與適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54頁。。姑且不論該規定的合理性,特殊動產所遵循的“交付生效+登記對抗”變動規則與股權的“告知生效”變動規則有所不同,特殊動產多重讓與規則亦不能適用[17]。事實上,股權無須交付或登記,股權的變動以股權轉讓合同的受讓人或股權繼承中的繼承人在股權轉讓合同生效或繼承發生后,向公司發出股權業已變動的告知通知為生效條件。當然,此處所稱的“告知公司即發生股權變動”是以股權轉讓或股權繼承符合法律規定或章程規定的程序和條件為前提的。股東名冊或工商登記變更均是公司在得知股權變動后向新的股東履行的一項法定義務而已。無論公司在收到股權變動的告知通知后是否履行這項義務,都不影響股權變動效力的實現。股東名冊、工商登記等系股權變動的對抗要件,這與動產交付生效的規則亦相去甚遠。
2.“登記”解釋路徑的疏漏
有學者認為股權善意取得要求股權已經登記[2,11],然而若依不動產登記規則予以參照適用,則會陷入適用前提上的悖論。
首先,股權與不動產物權在變動時點和變動規則上有所差異。依《公司法》第32條第3款第2句以及《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3條,工商登記系股權變動的對抗要件,股權變動于工商登記變更之前。“用物權變動理論去套股權的善意取得似有草率,二者的前提條件——登記的公信力基礎也不一樣”[7]140。《物權法》第106條中登記的規則是以登記生效主義為前提的,而股權變動則是基于登記對抗主義,僅能對抗公司交易相對人等,并不能對抗股權的第二受讓人,因為股權的登記僅作為公司登記事項。
其次,經工商登記的股權并不具有不動產登記那樣的絕對效力。《公司法》第32條的邏輯前提是“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法效果是“不得對抗第三人”。由此可推出的唯一等價逆否命題是:可對抗第三人的股權必定經過登記或變更登記,而不可反面解釋為“經登記或變更登記的股權一定具有對抗效力”。試舉一例,于“一股二賣”情形,若第一受讓人已記載于股東名冊,而第二受讓人基于虛假材料進行工商登記,此時第一受讓人仍可基于股權轉讓協議、股東名冊記載等事實提起異議,請求變更登記。此時,經登記的第二受讓人則不具有對抗第一受讓人的效力。實際上,登記對抗主義下的登記,并非賦予自己取得物權的權利,而僅是具有否定他人物權變動的權利[20]96。
三、 股權登記對抗主義與善意取得的制度沖突
(一) 轉讓人并非無權處分
善意取得的前提系無權處分,股權多重轉讓中是否涉及無權處分,則有三類代表性的觀點。肯定意見認為,股權多重轉讓如同債權多重轉讓,后一轉讓在法教義學上構成無權處分[5]。此外,根據《公司法》第73條的表述,股權在辦理公司登記前已經發生變動,造成股權真實歸屬和外觀的分離,從而使無權處分成其可能[1,11]。否定意見認為,依《公司法》第32條第3款,未登記的股權對第三人而言視為不存在,股權的第二次轉讓系有權處分[12]。亦有基于適用角度的折中觀點,認為登記對抗與善意取得規范可以發生競合*如尹田認為,受讓人既可主張登記名義人為有權處分,亦可主張登記名義人系無權處分而適用善意取得規則。參見尹田《物權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頁。。為求解上述理論爭議,需從登記對抗主義的法律構成中尋求答案。
登記對抗要件主義旨在解決意思主義結構下物權多重轉讓中的權利歸屬問題,是對無權利法理這一近代法前提的突破*參見[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Ⅱ:物權法》,王茵譯,渠濤審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不再標注版本),第50頁。無權利法理即羅馬法諺云“任何人不得向他人轉讓大于自己本身所擁有的權利”(Nemo plus juris ad alium transferee potest, quam ipse habet)。。日本法關于登記對抗的具體法律構成歷經百年爭鳴,涌現出無權處分和有權處分這兩類構成理論*有權處分構成理論如債權效果說、相對無效說、不完全物權變動說;無權處分構成理論如相反事實主張說、公信力說。參見[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Ⅱ:物權法》,第51-52頁。。前者的代表性觀點認為,出賣人因第一次轉讓而成為無權利人,因信賴出賣人名下的登記且善意無過失的第二買受人可以取得所有權[21]52。后者的代表性觀點認為,無權處分論忽視了二重買賣中兩個受讓人居于平等地位,均可對世主張絕對性的消除妨害等請求權,但相互之間不得主張所有權,唯有先登記者取得完整所有權,登記對抗的意義便在于此[22]33-34。日本判例中逐漸形成了背信惡意者排除理論[21]62,從而使得以善意為基礎的無權處分的法律構成日漸式微。
我國司法實踐中擅長運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對登記對抗制度則疏于適用[20],《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也是直接建立在善意取得的制度框架上,卻忽略了登記對抗主義與善意取得的制度性差異。登記對抗主義旨在賦予第三人否定物權變動的權利,而非有權利取得的效果[20],其前提是從相對無權利人處取得權利;而善意取得是法律規定的從絕對無權利人處直接取得權利的制度*相對無權利的登記名義人至少曾經具有權利,而絕對無權利的登記名義人自始便缺乏真實權利對應關系。參見郭志京《也論中國物權法上的登記對抗主義》,載《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3頁。。登記對抗主義處理的多是怠于登記的效果問題,而不動產善意取得涉及的常見情形卻是登記錯誤下的真實權利關系不對應問題[23]。多重轉讓中的登記名義人具備處分權,系登記對抗主義下的必然邏輯推演[24]。據此而言,在同樣遵循登記對抗主義的股權多重讓與情形下,轉讓人亦難謂無權處分,否則有悖于登記對抗主義和善意取得的制度機理。
(二) 第三人范圍不同
在《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出臺前,《公司法》第32條第3款即賦予了股權工商登記的對抗效力。多數觀點認為條文中的“第三人”應指善意第三人,不包括惡意和重大過失的第三人,公司內部股東以及已經對變更事項知情的人[8]。這一觀點鮮有異議*反對者的觀點參見施天濤《公司法論(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頁。。
然而,登記對抗主義并不排斥知情的第三人,知情并不一定惡意,否則正當競爭將無從談起[20]。因為“知道”無關倫理上的善惡,而且公信力說論及的“惡意者”實質上無異于通說和判例確立的“背信惡意者”[22]35-36。日本不動產登記采形式審查,難以排除不正當第三人,因此立法上對第三人做出兩項例外規定*即“以詐欺或脅迫妨礙登記申請的第三人”(日本《不動產登記法》第4條)和“有為他人進行登記申請之義務者”(日本《不動產登記法》第5條),參見[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Ⅱ:物權法》,第54頁。。另外,還可援引誠實信用原則排除背信惡意第三人[22]49-50。
此外,從我國立法體系的前后觀照而言,“善意第三人”和“第三人”的語意是嚴格區分的*《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中多處出現“第三人”,均未冠以“善意”;《物權法》中出現的“善意第三人”是有特定含義的,其與《物權法》第106條確立的善意第三人的主客觀標準相關聯,涉及特殊動產、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浮動抵押領域。,“善意取得”和“善意地取得”亦是涇渭分明:如前者必須以有償法律行為前提,并符合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股權的多重受讓人理論上可能“善意取得”股權;而后者可以包含贈予、繼承、拍賣等情形,破產債權人、扣押債權人等則可能基于“善意地取得”股權而非“善意取得”股權。
綜上,登記對抗主義較善意取得制度下的第三人范圍更為廣泛,不僅涵蓋“善意第三人”,而且囊括了“知情的第三人”和“善意的第三人”等。而且,這種第三人范圍的設計還有激勵商事登記的制度性功能。正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臺灣地區有關規定*臺灣地區有關規定為:“公司設立登記后,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和相關判例亦未有善意惡意之別,旨在促使公司辦理登記,貫徹登記效力[25]74。
(三) 股權外觀可信賴度不足
善意取得制度立基于權利外觀理論,權利外觀的可信賴性是其制度運行的前提。然而,對于股權外觀的可信賴度問題,理論和實務上卻莫衷一是。
圖書館在圖書的借閱及歸還讀者圖書就已經是大工程。近年來,一方面由于職工職稱評聘要求科研必須是高水平的高質量的文章,所以科研是熱門話題;另一方面大學生科技創新課題啟動,兩者都給圖書館帶來大量數據,這些數據的產生為大數據技術到來做足了前期準備工作。
部分學者認為,股權工商登記無法成為善意取得的權利外觀,因為工商登記簿缺乏公信力,其所公示者并非必然指向股權歸屬關系,亦缺乏為應對登記錯誤而設立的救濟程序等[5]。但實務部門是認可股權工商登記的公信力的*如《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的起草部門就認可登記簿的公信力,參見劉曉燕《規范審理公司設立、出資、股權確認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答記者問》, 2011年2月16日,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1/02/id/441068.shtml, 2017年2月6日。代表性案例見“四川京龍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等與深圳市合眾萬家房地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等股權確認糾紛上訴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終字第29號判決,法寶引證碼CLI.C.1783274。另有實務觀點認為,股權工商登記涉及法律的強制規定和公權力的干預,其法律效果體現為登記事項的推定真實狀態以及對善意第三人的保護,參見江必新、何東林等《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裁判規則理解與適用·公司卷》,(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47-448頁。,并力求審查的審慎性*如反復比對原始檔案、嚴格核查簽名真偽等,參見傅燕萍《辦理股權變更登記應審慎審查》,載《中國工商報》2009年12月8日,第3版。,而非僅流于證據效力。比較法上的經驗也表明登記對抗主義下的登記簿具有合理信賴度[26]。另有觀點認同股權工商登記的部分可信賴度:雖然股權工商登記的可信賴性供給存在缺陷,但股權工商登記是法定的強制事項,進而激勵人們進行公示,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登記權利的名實統一[6]。
本文以為,股權工商登記雖然具有一定的可信賴度,但與善意取得制度下的可信賴性仍有差異。首先,有限的形式審查難以保障股權外觀的真實性,實踐中虛假股權糾紛大量涌現。從《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等可以看出,我國對股權并不進行實質審查,不僅股權工商登記的正確性難以保障,股東名冊的真實性亦難以保證。縱有配套規定力圖保障股權登記的真實性,但我國缺乏像德國那樣的股權審查制度*在德國法上,股東名冊須儲存于商事登記法院,并由公司執行人或公證人制作與呈交,真實權利人可提出異議登記。股東名冊具有股東資格證明作用和權利外觀功能。參見張雙根《德國法上股權善意取得制度之評析》,載《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2期,第161-166頁。,而且股權工商登記和股東名冊的雙重公示還會造成權利外觀上的混亂*表現為任一公示形式難有充分的外觀效果,兩者的結合也無法發揮功效。參見楊祥《有限公司“一股二賣”善意取得之質疑——對〈公司法解釋三〉第27條適用的限縮》,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82-83頁。,進一步削弱了股權工商登記的可信賴度。實踐中,股權登記被偽造的案例層出不窮,“崔海龍案”*參見“崔海龍、俞成林與無錫市榮耀置業有限公司、燕飛、黃坤生、杜偉、李躍明、孫建源、王國強、蔣德斌、尤春偉、忻健股權轉讓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終字第1號判決,法寶引證碼CLI.C.2454398。即是典型著例,就連實務界人士也坦承我國公司登記制度上的缺陷導致了股權登記上的混亂局面*如我國法律未要求股權轉讓須進行公證,也不要求各方現場簽字等,導致股東身份的真實性存疑。參見“崔海龍、俞成林與無錫市榮耀置業有限公司、燕飛等四人以及孫建源等五人股權轉讓糾紛上訴案”,法寶引證碼CLI.C.330017。。其次,登記對抗主義體現為一種交易規則,而非以可信賴性為前提。縱觀我國《物權法》,登記對抗主義的物權變動模式集中在登記制度不完善的領域中*如特殊動產、土地承包經營權、地役權、浮動抵押等領域。。登記對抗主義正是登記缺乏公信力時有限維護交易安全的一種規則,其所謂的推定乃消極推定,而非登記的權利真實,第三人基于法律擬制的規則行事,而非出于對登記簿的真實信賴[20]。股權工商登記作為商事登記,著眼于公司的對外關系,并不彰顯股權的變動。
四、 股權多重轉讓參照適用善意取得規則的路徑修正
我國現行法一直對善意取得存在“制度性偏愛”,并試圖尋求其與登記對抗的制度融合: 《物權法》規定了登記對抗下的第三人范圍限于善意第三人,《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20條更明確將此處的善意第三人和善意取得制度相聯系,《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亦是這種法律邏輯的延伸*有學者認為,由于《公司法》第32條第3款未對登記對抗下的第三人范圍做出進一步限定,構成法律漏洞,司法解釋便類推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填補。參見戴孟勇《民法解釋學在大陸的實務應用——一個對照觀察》,見張雙根、田士永、朱慶育等主編《中德私法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頁。。這也體現了我國法律應對第三人和股東不誠信行為的一貫思維,即從法感情上排斥惡意第三人,并強調善意第三人的調查義務[20]。但多重讓與中善意的后買受人并非基于善意取得而取得所有權,登記對抗制度本身就蘊含著所有權的效力,多重讓與中的權利取得規則需排除善意取得的異化干擾[27]。不僅如此,司法解釋的這一制度異化亦不符合法律效力位階,同樣也有悖于司法解釋不能創設法律的原則,因此,股權的多重讓與仍然應在登記對抗的制度路徑上進行解釋。
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善意取得制度全無意義,善意取得制度本身也蘊含著對利益分配的考量。立法的目的就在于調節社會利益、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以協調社會正常秩序,并最終凝結為法律制度中的具體利益[28]56-58。股權多重轉讓中的權利取得規則設計,既要注重制度的邏輯演繹,也需在不同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就具體利益格局而言,多重買受人的主觀狀態、注意程度等均可成為影響利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善意取得制度在這方面有許多制度性嘗試。從制度利益上看,登記對抗主義旨在通過賦予第三人否定權以激勵股權登記,并導致競爭性交易的發生;而善意取得意在保障交易安全,通過強化調查義務以保護真實權利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競爭性交易和登記的積極性[20]。激勵登記和鼓勵誠信都是重要的立法目標,登記對抗和善意取得制度對此各有側重。如果全然遵循善意取得的制度路徑,促進登記的立法目標便會被打破;若不加限制地貫徹登記對抗主義,虛假和惡意交易便會盛行。
因此,在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不變的情形下,不能盲目地倚重某一制度來處理股權多重轉讓中買受人的權利取得問題,而應注重法律制度的邏輯推演并尋求制度借鑒和利益衡量的空間。具體而言,在制度邏輯上應以登記對抗主義為法律適用的主線,以“有權處分”為制度基點;但同時在利益衡量層面上又需要擴展善意取得制度的應用空間,注重先買人可歸責性、第三人主觀狀態和注意標準的考量。這樣的考慮既能符合各方利益,也能契合立法目的,對鼓勵股權登記、遏制惡意交易也大有裨益。
(一) 先買人可歸責性
多重讓與中先買人的利益被多國立法和司法實踐所認可*如美國和法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參見吳一鳴《論“單純知情”對雙重買賣效力之影響——物上權利之對抗力來源》,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2期,第111-112頁;再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10條。,而先買人的失權須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比如善意取得。傳統善意取得的制度缺陷在于對真實權利人可歸責性的忽視[2,7],這在我國立法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德國立法經歷修訂,真實權利人的可歸責性已經成為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構成要件。基于可信賴程度的差異,同樣作為善意取得的權利外觀載體的土地登記簿、商事登記簿、股東名冊的外觀效力依次遞減,真實權利人可歸責性的標準和受讓人善意的標準則逐級遞增[3]。在德國公司法上,當登記錯誤可歸責于真實股東,或登記錯誤不可歸責于真實股東時,經過3年期限,不知情第三人可以善意取得股權[7]135。從德國法上可以看出,權利外觀效力越弱,第三人取得最終權利的構成要件越復雜,真實權利人越難失權。依此邏輯,我國股權外觀的可信賴度較德國更低,因此更需要注重刻畫真實權利人可歸責性的標準。
(二) 第三人的主觀狀態和注意標準
善意取得制度與第三人的主觀狀態和注意標準相關聯,又因動產和不動產的區分而在適用上有所差別,股權多重轉讓中的善意標準引起了學者的熱烈討論。有學者認為,登記對抗下適用善意取得應弱化善意要件并進行善意推定,由第三人證明其惡意[20]。而主張適用股權善意取得的學者認為,明知和重大過失均為惡意[9],應基于工商登記進行善意推定[11]。另有觀點認為,考慮到信息獲取成本的差異性和商事外觀主義理念,股權對內轉讓中的善意應指不知且無一般過失,股權對外轉讓中的善意應指不知或無重大過失,未查詢工商登記視為重大過失[12]。
本文認為,在立法不變的前提下,我國在處理股權善意取得問題時可以從賦予第三人有限的調查義務逐步過渡到善意推定,再到完全的登記對抗制度,逐步消解善意取得對登記對抗的制度異化和干擾。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第1款的主要目的在于應對司法實踐中大量的不誠信股權交易,通過僅賦予善意第三人否定權而將明知的第三人排除在外,雖然危及交易安全,但大幅抑制了交易的進行[20]。另外,由于登記規則本身具有風險提示和減輕調查義務的作用,現階段善意的標準應以調查義務的有限性為前提,如工商登記的查詢和有限的公司內部調查即達到了認定善意的注意標準。
然而,從長遠來看,促進股權登記、貫徹登記效力也是矢志不渝的立法目標。何況《公司法》的效力層級高于《公司法司法解釋三》,在登記對抗主義和善意取得存在制度沖突的前提下,原則上應傾向于登記對抗制度的一體化適用。因此,為彌合登記對抗和善意取得的制度裂痕,應對善意做擴大化解釋以契合登記對抗的制度內涵。
依《物權法司法解釋一》第18條,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必須貫穿交易的始終,但本文認為在參照適用的股權領域,則應區分初始知情、嗣后知情、完全不知情三種情形。股權外觀效力上的缺陷使我國法在現階段更需關注真實權利人的失權問題,而第三人的主觀狀態深刻影響著權利的最終歸屬。日本法和法國法上,登記對抗下的第三人主觀范圍經歷了從無限制到限制的發展軌跡*日本法上是背信惡意者排除說,法國法上是惡意者排除說。參見郭志京《也論中國物權法上的登記對抗主義》,載《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頁。,美國法和法國法上多重讓與中后受讓人的單純明知會構成妨礙權利取得*美國和法國通過修法將“知情”作為權利取得的重要考量因素,參見吳一鳴《論“單純知情”對雙重買賣效力之影響——物上權利之對抗力來源》,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2期,第112頁。。我國《合同法》第52條關于惡意串通的規定是合同無效的情形,股權領域惡意串通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鑒于股權外觀效力的缺陷和對真實權利人的保護需要,初始知情或重大過失不知情的第三人不應取得最終權利;而嗣后知情或者完全不知情的第三人應被推定為善意,但并非基于善意取得而是依據登記對抗規則而取得權利。隨著股權登記制度的完善,摒棄善意取得因素的登記對抗制度應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是登記對抗制度的應有之義。
綜上,股權登記對抗主義與善意取得制度捍格不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7條將善意取得制度引入股權多重讓與領域,尤顯疏漏之余,徒生司法實踐的困境。該條文的修正化適用需在股權登記對抗主義的前提下開展,并綜合考量先買人的可歸責性與第三人的主觀狀態和注意程度,如此,法律體系方能一以貫之。如此衡量的意義在于,既能實現激勵股權登記并貫徹股權登記效力的長期立法目標,又通過為第三人取得權利設置難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股權的多重讓與,從而保護股權外觀效力缺陷狀態下的善良先買人。
[1] 胡曉靜: 《股權轉讓中的股東資格確認——基于股權權屬與股東資格的區分》,《當代法學》2016年第2期,第36-44頁。[Hu Xiaojing,″The Identity of Shareholders in Share Transfer: A Distinction Based on the Equity Ownership and Shareholder Eligibility,″ContemporaryLawReview, No.2(2016), pp.36-44.]
[2] 朱曉娟、姚籃: 《論中國有限公司股權善意取得的一般結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第45-55頁。[Zhu Xiaojuan & Yao Lan,″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ies in China,″Journalof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SocialSciencesEdition), No.5(2013), pp.45-55.]
[3] 余佳楠: 《我國有限公司股權善意取得制度的缺陷與建構——基于權利外觀原理的視角》,《清華法學》2015年第4期,第109-124頁。[Yu Jia’nan,″The Deficiencies and Construction of Equity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Limited Companies in China:A ′Rechtsschein′ Perspective,″TsinghuaUniversityLawJournal, No.4(2015), pp.109-124.]
[4] 王涌: 《股權如何善意取得?——關于〈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8條的疑問》,《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2期,第30-34頁。[Wang Yong,″How Could Equity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Be Acquired in Good Faith?——A Query about Article 28 of the Thir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CompanyLaw,″JinanJournal(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No.12(2012), pp.30-34.]
[5] 張雙根: 《股權善意取得之質疑——基于解釋論的分析》,《法學家》2016年第1期,第131-147頁。[Zhang Shuanggen,″A Critiqu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Equity: An Explanatory Approach,″TheJurist, No.1(2016), pp.131-147.]
[6] 石一峰: 《非權利人轉讓股權的處置規則》,《法商研究》2016年第1期,第95-105頁。[Shi Yifeng,″Disposition Rules of Non Obligee’s Transfer of Shares,″StudiesinLawandBusiness, No.1(2016), pp.95-105.]
[7] 張笑滔: 《股權善意取得之修正——以〈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為例》,《政法論壇》2013年第6期,第130-143頁。[Zhang Xiaotao,″The Correc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Stock Right,″Tribun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No.6(2013), pp.130-143.]
[8] 劉俊海: 《現代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Liu Junhai,ModernCorporationLaw, Beijing: Law Press, 2008.]
[9] 楊祥: 《有限責任公司“一股二賣”善意取得之質疑——對〈公司法解釋三〉第27條適用的限縮》,《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74-88頁。[Yang Xiang,″Quest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Equities Being Sold Twice′,″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Law, No.3(2015), pp.74-88.]
[10] 李建偉: 《公司法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Li Jianwei,CorporationLaw(2ndEd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郭富青: 《論股權善意取得的依據與法律適用》,《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7-16頁。[Guo Fuqing,″On the Basis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to Equity and Its Legal Application,″JournalofGansuPoliticalScienceandLawInstitute, No.4(2013), pp.7-16.]
[12] 姚明斌: 《有限公司股權善意取得的法律構成》,《政治與法律》2012年第8期,第82-93頁。[Yao Mingbin,″Legal Constitution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Corporation Equity,″PoliticalScienceandLaw, No.8(2012), pp.82-93.]
[13] 鄧峰: 《物權式的股東間糾紛解決方案——〈公司法〉司法解釋(三)評析》,《法律科學》2015年第1期,第178-189頁。[Deng Feng,″A Continental Property Right Perspective on Shareholder’s Dispute in China: Also Comments o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Ⅲ ofCorporateAct,″ScienceofLaw, No.1(2015), pp.178-189.]
[14] A.Dignam & S.H.Goo,Hicks&Goo’sCases&MaterialsonCompanyLaw(7th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 [韓]李哲松: 《韓國公司法》,吳日煥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C.S.Lee,CorporationLawofSouthKorea, trans. by Wu Rihuan,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0.]
[16] 施天濤: 《公司法論(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Shi Tiantao,CorporationLaw(2ndEdition), Beijing: Law Press, 2006.]
[17] 周江洪: 《特殊動產多重買賣之法理——〈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10條評析》,《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第72-81頁。[Zhou Jianghong,″Legal Theory of Multiple Transaction for Special Movable Properties: Commenting on Article 10 of 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ContractofSalesby Supreme People’s Court,″JournalofSoochow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ScienceEdition), No.4(2013), pp.72-81.]
[18] D.French, S.Mayson & C.Ryan,Mayson,French&RyanonCompanyLaw(29th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 張雙根: 《德國法上股權善意取得制度之評析》,《環球法律評論》2014年第2期,第156-176頁。[Zhang Shuanggen,″Analysis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Shares in German Law,″GlobalLawReview, No.2(2014), pp.156-176.]
[20] 郭志京: 《也論中國物權法上的登記對抗主義》,《比較法研究》2014年第3期,第95-113頁。[Guo Zhijing,″Also on th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in Chinese Real Right Law,″JournalofComparativeLaw, No.3(2014), pp.95-113.]
[21] [日]近江幸治: 《民法講義Ⅱ:物權法》,王茵譯,渠濤審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Koji Omi,CivilLawLectureNotesⅡ:PropertyLaw, trans. by Wang Yin, Rev. by Qu Ta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 [日]鈴木祿彌: 《物權的變動與對抗》,渠濤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Rokuya Suzuki,AlterationandConfrontationofRealRight, trans. by Qu Tao,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99.]
[23] 程嘯: 《論不動產善意取得之構成要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106條釋義》,《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74-84頁。[Cheng Xiao,″On the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the System of Real Estate Acquired in Good Faith: Interpretation on the Article 106 ofPropertyRightsLawofPRC,″StudiesinLawandBusiness, No.5(2010), pp.74-84.]
[24] 冉克平: 《論機動車等特殊動產物權的變動——兼析法釋〔2012〕8號第10條的得與失》,《法學評論》2015年第4期,第153-162頁。[Ran Keping,″On Change of Right over Motor Vehicle and Other Special Movables,″LawReview, No.4(2015), pp.153-162.]
[25] 梁宇賢: 《公司法論(修訂六版)》,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Liang Yuxian,CorporationLaw(6thEdition), Taipei: Sanmin Book Co., Ltd., 2006.]
[26] 龍俊: 《中國物權法上的登記對抗主義》,《法學研究》2012年第5期,第136-153頁。[Long Jun,″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in Chinese Real Right Law,″ChineseJournalofLaw, No.5(2012), pp.136-153.]
[27] 李宗錄: 《登記對抗主義下多重所有權變動論》,《法學論壇》2015年第6期,第141-148頁。[Li Zonglu,″The Theory of Multiple Ownership Changes under Registration Antagonism,″LegalForum, No.6(2015), pp.141-148.]
[28] 梁上上: 《利益的層次結構與利益衡量的展開——兼評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論》,《法學研究》2002年第1期,第52-65頁。[Liang Shangshang,″Stratified Structure of Interest and the Unfolding of Interest Measurement,″ChineseJournalofLaw, No.1(2002), pp.52-65.]
Modified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Wu Yongmin Zhang Guilong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China)
According to Paragraph 1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 the people’s court shall refer to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when handling the disputes over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However, this application would create unnecessary troubles. Moreover, equity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conflicts with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many ways.
First of all, applying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which typically is applicable in the field of real property, to the field of equity transactions may face difficulties. Article 32 of theCompanyLawconstitutes the legal basis for changes in equity interests, according to which, changes in equity interests follow the rule model of ″the company’s approval +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Thi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hanges in the real property ownership. In addition, the abuse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the field of equity changes might lead to confusion of third party in terms of ascertaining the time node.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equity changes, neither referring to the delivery of movable property nor the registration of real property can be logically consistent. In addition, 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rules.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hinges upon the theory of right appearance, aiming to safeguard transaction security. The premise of the applic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s ex right disposition,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as well as trustworthiness of right appearance. However, equity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acts more as a trading rule, aiming to promote equity registration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ness of registration. Accordingly, the nominal registrant who transfers the equity in multiple transactions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the equity, and consequently the third party does not need to be bona fide during the transaction. Additionally, under Chinese law, equity register and stock ledger are not reliable enough in terms of right appearance, and thus does not fulfill the premis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In views of all the conflicts listed above, Paragraph 1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essentially violates Article 32 ofCompanyLaw, and also does not follow the hierarchy of the legal effe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harmony of legal system , promote equity registration as well as deter transactions in bad faith, modified leg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7 ofJudicialInterpretationⅢofCompanyLawshall focus on the intrinsic logic of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 of first transferee and the third party.
Specifically, from systemic logic perspective,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should be the main thread in legal application; while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weighing specific interests, considering the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as well as duty of care. Under German law, the effects of right appearance have inverse correlation with both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and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Due to the drawbacks of the appearance of equity under Chinese law, which leads to relatively lower trustworthiness, the interest of first transferee deserves more protection in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In this sense, the criteria of the first transferee’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third party’s subjective state should be adjusted properly. Given the institutional and habitual preference for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assessment of the criteria of the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may be carried out in several separate stages. Nevertheless,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shall be the center. Specifically, the criteria of good faith may be improved gradually from the third party’s limited investigation obligation, to the presumption of good faith, and finally the absolute legal application of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rule, and thus reduce the interferenc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rule progressively.
multiple equity transactions; registration confrontation doctrine;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equity; modified application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2.064
2017-02-06
1.吳勇敏(http://orcid.org/0000-0002-3865-4216),男,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經濟法學研究; 2.張桂龍(http://orcid.org/0000-0002-1371-4665),男,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民商法學研究。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7-06-09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