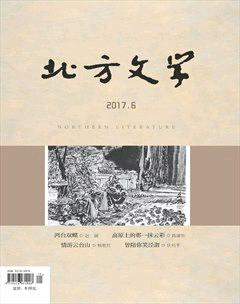新時期女性文學中的母親形象的構建
劉媛媛
摘要:女性文學是人類精神文化的一座不可忽視的豐碑,大量觸目驚心的反傳統的母親形象,賦予了母親角色以新的理解。女性文學中的母親形象使我們看到,母親不僅是慈愛的圣潔的奉獻者,同時也是可悲的父權制的犧牲品,甚至是可憎的“同謀者”。隨著時代的變遷,許多女性作家開始覺醒。她們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母親形象。通過女性文學的發展歷程來反映女性意識中的母親形象由圣化到俗化的過程。
關鍵詞:女性文學;母親形象;女性意識
“女性主義”的概念最早來源自于西方的女權運動,它與女權主義,男女平等主義等多種釋義,一樣都泛指主張性別平等。女權主義思想是人類在追求自由、平等歷程中必然產生的一個產物,是女性對自我認識的覺醒與發展。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創作的兩次博興與西方女權運動和女權主義文化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五四時期反封建和個性主義的宏偉壯闊的革命樂章,婦女解放的呼聲僅僅是其中的一個聲部;新時期思想解放和人道主義的時代強音,主權意識的張揚也不過是點綴其間的低吟而已。
一、傳統語境中的母親形象
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兩千多年的男性為本位的宗法社會中,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宗法社會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觀念,就是男子被看作是傳宗接代的繼承者,婦女則是成就男子社會成就的輔助者,在人格上她們沒有自主權,對于自身存在的女性意識更是認識的少之又少。
在傳統的倫理道德中,母親的基本職能是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務。中國人對母親的敬重也來源于此。但是對母親的尊重這種代代相傳,根深蒂固的習俗,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母親的價值判評上,而且也形成了“賢妻良母”這樣的一個古典的審美文化范疇,母親身上的道德完美性得到強化。人們將母親的犧牲、奉獻、隱忍精神推崇到極致,常被看作是“義”的化身,但這種“義”帶有一種愚性。這些母親多是一種喪失主體性的存在,她們是忘我的、非理性的,忽略個性與個體的自我價值,超越本能欲望沖動完美而神圣的,因此在這個時代她們是被看作依附于男性,她們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理想,成為成就男人們社會地位的一道輔助工具。
在傳統社會中,男性不僅可以三妻四妾,甚至眠花宿柳也無任何道德壓力,卻嚴格規定女性的決對從一而終、守節明志。反之,就會認為不貞。傳統社會對女性有種種限制。社會壓力,自身的認知也使得很多女性甘愿守節。宋代的程朱理學尤其是推崇婦女的貞操節烈。“餓死是小,失節事大”[2]扼殺了無數女性的青春與幸福。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女人沒有選擇自己婚姻的自由,她們也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人生軌跡,只能服從父母和丈夫,做一個十足的附庸品。
從古至今,母親受到無數的贊揚。在一般意義上說,母性是女人具備的最基本的特征。其具體內容大抵包括女人的善良品格、對長輩的孝道、對家庭的勤勞、相夫教子、賢惠與貞潔等層面。
母親這一字眼在一定意義上占據了一個女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但卻只是一個女人人生意義中的很小的一部分。歷來作家們大都只關注到母親作為一個女人的特定的稱謂,而把母親與崇高、博愛、溫柔、賢良等光輝的贊譽相關聯。有依據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時代背景將母親塑造成不同的側面。如魯迅、柔石、蕭紅等革命作家為表現婦女所受的封建神權、夫權和男權社會的壓迫,塑造了一系列苦難愚昧不幸但善良、慈愛的母親形象;艾青筆下的大堰河更是集中了所有母親的溫柔慈愛的品格,也受盡了天下苦楚的母親形象。在封建社會的教義中人們要求把女性塑造成幼從父,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形象。母親是圣母的化身,家庭,丈夫,孩子是他生活的全部,她不能有自己追求自由的權利。
和歷代的女性文學家相比,現代女作家無疑是幸運的,她們在一個反叛傳統的偉大時代,五四運動推動的人們對自我的覺醒。作家們第一次爭得了在創作中言說女性婚戀自由的話語權。因此在這個時候,出現許多不同的新女性形象。在個性解放和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下,現代女作家首先把話語的批判鋒芒對準造成幾千年婦女痛苦不幸的罪惡淵源——封建禮教和包辦婚姻。
二、覺醒的一代對傳統母親形象的質疑
五四以來,隨著先進思想的傳播、女式學堂的不斷興起,涌現出了一大批新女性。她們不認同傳統的相夫教子、生兒育女、孝敬公婆的道德倫理觀念。她們的價值取向在于追求美麗愛情、張揚獨特個性。一些新覺醒的人開始選擇了積極自強、自求進步。一些孀居的年輕女性,在失去家庭丈夫的依靠,也開始逃離了家族的束縛限制后,勇敢的走向更加廣曠的的空間,去實現自身的價值。
提到母親,人們聯想到的便是愛心、圣潔,是兒女躲避風雨的溫暖港灣。這也是中國傳統的母親形象。比如,在以冰心為首的一批女作家眼里,母愛是真正的皈依,是可靠的真善美。然而,在張愛玲的小說中,母親光輝美好的形象幻滅了。她說“金發的圣母不過是個俏奶媽,當眾喂了一千余年的奶。”這一說法卻也是大膽新奇,也是對傳統母親形象觀念的大顛覆。但人只有了解了人生的真相,我們才能重新站在世俗的現實人生中去探求人生的真諦。誠然,張愛玲把母性的荒涼與暗角揭示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她推翻了傳統的母親身上的桎梏,解放了母親作為人的天性。而這一點,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了傳統文化對于母親人格的束縛于罹難,以全新,大膽的筆觸對封建思想作出了回擊,這對于母親文學的發展而言,是十分難得可貴的。
母親走下神壇,在現實生活中被完全世俗化。她們雖不乏對兒女的疼愛,但絕非神圣、純潔,而是或糊涂、或自私、或卑瑣、或病態、或兼而有之,后者往往淹沒了前者。
縱觀五四女作家筆下的母親形象,她們一方面是慈愛母親的化身,是子女們感情與心理上尋找庇佑的對象,另一方面卻由于所處的時代的沖擊和社會的影響,成為父權制度的直接承載者。而母親這一獨特形象,在此時所處的社會地位并不能為兒女所接受,覺醒的兒女開始對被壓迫的母親形象大膽提出質疑與批判。她們要想自身走出母親的生活模式,并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唯一的方式就是和叛逆之子組成新的家庭,這種以建立在愛情上的新家庭,也是她們對抗封建家庭攻擊的一個政治堡壘。對于一份來之不易的自由戀愛,五四青年們誓死捍衛,于是就有了《隔絕》中的女主人公的竭力高喊:“生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女性作家由此開始了對母親的生活狀態的思考與質疑,這種追問與質疑的目的,無疑是對母性生活自由與獨立人格的熱切期待,她們渴望母親能夠在家庭與社會中重新享有平等的生存環境和話語權利。這與傳統社會對母親真實的定位在本質上并不沖突。可以說,在與現存秩序的不斷抗爭過程中,她們發現母親不但是封建父權專制的犧牲品,也是封建父權的間接幫兇。于是,她們在塑造母親、歌頌母愛的同時,也重新跳出傳統,發現了母親的不完美之處,開始對母親的復雜角色屬性進行了重新分析,定義,批判和質疑。首先她們以一個女性的視角對母親的“女奴”地位進行了觀照,毫無遮掩的揭露了母親在其日常生存與生活中所受到的種種壓迫,也即是母親所受的舊倫理的制約與其自身主體人格的缺失與束縛。在眾多作家筆下,母親勤勞隱忍,且時刻堅守自己所背負的男權思想。母愛從一開始就攜帶著母親的權威,同時也把這樣的痛苦直接施加在女兒的身上,主導女兒的婚姻同時也造就了女兒人生的不幸。母親再一次成為了封建父權專制的同謀者。作者針對于母親的這一定位,表達出了自己滿心的懷疑和不滿。
凌叔華在她的一系列小說中,表達了對忍讓癡心的母親形象的深刻反思與審視。但她筆下的人物正像魯迅所說的,她的作品描寫的是“世態的一角”。她的作品告訴我們,一切除了叛逆、弒父、追尋母親之外,這個時代的女性生活還有如此多隱秘不被人熟知的的、封建腐朽的的、可悲可鄙的方面。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撕掉了母親身上被男人們所強行掛上的裝飾品。用她犀利蒼涼的筆觸寫出了女人生命的掙扎和遭受的迫害。黃七巧是現代文學中母親形象的內心欲望與精神世界最為張揚也最為深刻的一個。她本性并非是惡, 然而她終究由一個無辜的受害者,逃不出女性命運的藩籬,轉而變成了害人者,這無疑體現了對母性乃至人性裂變的深刻拋示,也體現了這類母親深深的生命痛楚。
女性出走在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中雖然并不鮮見,但其身份往往定位于“新女性”而較少缺少母親身份的出走者。同時,五四啟蒙文學中的女性出走所反抗的對象也往往是傳統舊家庭。在此背景下,《寒夜》中的主人公曾樹生具有“新女性”與“母親”的雙從身份,她所克服的對象也包含了新舊兩種不同的家庭秩序,這樣一個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的很遠的任務體現了女性的不斷覺醒。她既是一個言行反悖于傳統的受氣小媳婦的兒媳形象,又是一個心靈深處充滿反抗風暴,卻絲毫不弱于其他異態母親形象的人物。作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她敢于追求個性解放和社會理想,曾希望依靠自己的最大努力來為社會奉獻自己的全部力量。因此,她像當年的眾多新女性一樣,勇敢的逃離家庭,轉而從事了教育專業,成為一名職業新女性。創辦鄉村化和家庭化的學堂成為了她和汪文宣的共同理想。她不但找到了事業上的同事,也找到了生活中的如意伴侶。在家庭中,她為了追求真愛而不選擇形式,依然和汪文宣同居,面對婆婆的無理指責,她昂然回擊并我行我素。她認同的是自由平等的新式家庭關系,而不是汪母所遵從的封建家庭倫理道德。當婚姻失去愛的基礎的時候,她毅然決然的與汪文宣解除婚姻關系,從這一點而言,她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母親,而是一個帶有叛逆色彩的母親形象。
參考文獻:
[1]孔子.論語.陽貨[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2]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N].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劉傳霞.被建構的女性[N].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