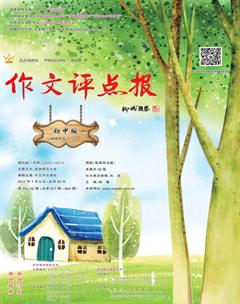馮其庸:國學大師的西域情懷
2017-08-11 23:51:24
作文評點報·初中版 2017年26期
2014年春天,隨著中央領導的慰問,馮其庸這位國學大師,再次成為了世人關注的熱點。馮其庸生于無錫,成長在“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水鄉,卻對西域的情感格外深厚。80高齡時,他十闖新疆,三登帕米爾高原,兩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整整繞塔里木盆地走了一圈。途經巴音布魯克高時,夜里的氣溫零下幾十度,別人都縮在屋里取暖酣睡,馮先生卻夜半獨出,到院子里欣賞冰峰羅列的月下雪景,體會蘇東坡“困眠一榻香凝帳,夢繞千巖冷逼身”的詩境,差點沒把自己凍成高山上的一尊雕像。
盡管吃盡苦頭,西域之行卻給了馮其庸新的學術生命。他早年學畫,耽于花卉。西域之行,拓寬了他的胸襟,題材也側重于祖國的山川大地。四次進入西部大沙漠、兩次險越天山形成的《瀚海劫塵》攝影集,以深厚的歷史內涵,展示了祖國西部古文化的燦爛,也為他贏得了著名攝影藝術家的頭銜。他兩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繪畫展,最為奪神攝魄的亮點,便是他獨創的重彩西部山水。馮先生堅信,聞名世界的西域學,必將和敦煌學一樣,產生巨大的飛躍。更值得驕傲的是,他踩著時代的鼓點,提出的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創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建議,也得到了中央的批準。
【多維解讀】
1.藝無止境。人到黃昏,該是享福的時候。馮老卻不同,越到晚年,對藝術的追求越是執著。這種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精神,正是大師的與眾不同。
2.注重實踐。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僅是治學的真經,在馮其庸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沒有數次邊疆之行,也許就沒有先生如今的高度。
【適用話題】
文化、實踐、熱愛、追求、光彩、胸懷、高度、標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