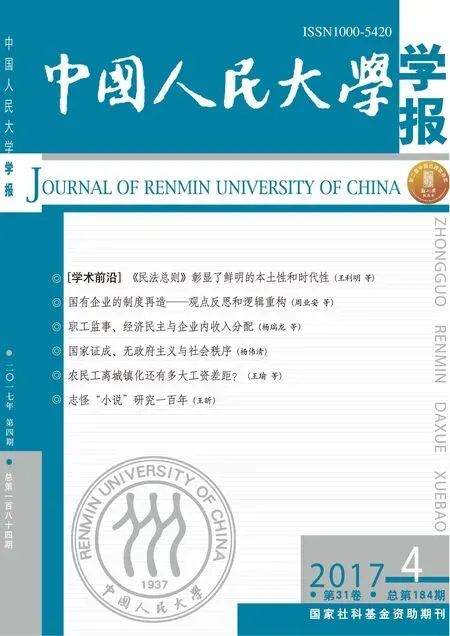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與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楊菊華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與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
楊菊華
城鎮與鄉村、本土與外來的區隔構成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加上附著于其上的外溢特征,使得國內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既面臨國際移民融合的共性問題,也面臨中國式的融合困境。其中,鄉—城流動人口相較于城—城流動人口,更是多重弱勢身份交疊,融入進程更為坎坷,融合前景更不確定。總量巨大的流動人口與流入地主流人群和制度安排之間的斷裂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也是新型城鎮化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中必須掃除的重大障礙。突破戶籍墻、結構墻和理念墻,跨越人為設置的各類邊界,推動群體關系從隔離到嵌入,是新型城鎮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它既是社會融合的本質特性,也是實現社會融合的根本途徑。
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社會融入;戶籍制度“雙二屬性”;新型城鎮化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總數超過2.45億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8%。流動成為流動者及受其影響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改變個體生存和發展狀況的同時也帶來了深刻的人口、經濟和社會變化,主要表現在:改變了中國人口的地域分布狀況,成為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情景下國內人口區域變動的主導要素;改變了地域之間人口的年齡結構和老齡化程度,以及地區之間的性別結構和通婚模式,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區域發展的一個核心要素。
隨著流動模式的改變,許多流動人口“并不流動”,從計劃返鄉轉向渴望融入流入地社會。為此,中央政府反復強調,必須從維護最廣大民眾根本利益的高度出發,落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推動流動人口的融入進程,提升新型城鎮化質量,實現“共享”發展。作為“十三五”時期政府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之一,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要旨和重要檢驗標尺,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成為一個具有全程性、全局性和現實緊迫性的重大戰略議題。
社會融合是指通過個體之間、群體之間、文化之間互相接觸、競爭、沖突、適應[1],流動人口逐步實現經濟整合、社會互動、文化交融和心理認同的過程,也是一個制度排斥逐漸減弱和人群機會差異逐漸消弭的過程,其間,宗教文化、資本稟賦、職場能力、制度因素等都是重要的影響要素。[2]對國內流動人口而言,“戶籍墻”[3]是制約融合進程的本源性障礙,文化要素和自身主觀因素也會阻礙流動人口的融合[4]。戶籍制度改革的滯后性,制度和觀念的不包容性依舊是融合進程中的“堅鐵”[5],導致流動人口缺乏實現融合的財力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權利資本,進而使得他們(主要是指農民工)面臨“被邊緣化”和“自邊緣化”[6]的雙重困境。無形的隔離墻(即文化和理念的排斥)和有形的隔離墻(即制度有意或無意的制約)[7]使得流動人口的融合路徑狹窄,最終能實現融合、成為真正“本地人”者少之又少。
現有研究對流動人口戶籍制度中的“城—鄉”屬性有較為豐富的論述,但僅有極少數研究關注到其“內—外”屬性。流動人口也是一個高度分化的群體,內部分化嚴重,表現為:不僅有“農民工”,還有大量的隨遷家屬;不僅有鄉—城流動人口,還有約四分之一的城—城流動人口,故戶籍制度的“內—外”屬性對流動人口而言同樣重要。那么,戶籍制度城—鄉、內—外“雙二屬性”如何影響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目前以居住證制度為載體和抓手的戶籍制度改革可否破解流動人口融合過程中的障礙,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步伐?怎樣有效突破融合進程中的“三堵墻”?凡此皆為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推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進程、提高其融合水平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本文的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剖析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及其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帶來的排斥效應;其次,探析戶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狀況,重點論述戶籍制度改革存在的問題及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合進程的影響,并提出突破區隔、跨越并立、共享機會和共有權利、實現人群嵌入的途徑,探尋推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突破口;最后,對融合困境隱含的潛在的社會風險提出初步思考。近年來西方國家頻發的移民惡性事件表明,社會的融合傳遞著成功經驗,而斷裂則引發失敗教訓。流動人口若長期無法融入流入地社會,可能會進一步激化社會分化,引發社會矛盾,激發或加劇他們的“失范”行為,形成社會沖突與動蕩的隱患,危及社會和諧與穩定。故此,關于戶籍制度、結構排斥及其衍生制度阻礙流動人口的融合進程的途徑和機制等諸多問題,亟須政府、社會和學界高度關注。
二、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與“雙重排斥效應”
社會融合本源性的要義是,少數族裔文化與主流文化的交融匯合,這也是國際移民融合研究的核心內涵。作為一個多元一統的國度,中國以漢民族為主,國內多數流動人口并無太大的語言障礙和宗教隔閡,但卻面臨因制度隔離帶來的獨特的融合困境。
(一)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思路和模式是,將農村作為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勞動力蓄水池,勞動者游走于城與鄉之間,漂泊在東中西部地域之間,需時便取用,不需時便閑置,這種“兩棲化”模式使得流入地社會無須為流動人口提供平等的福利和服務待遇。這種現象又與地區分割密切聯系在一起。地區公共資源的配置主要依據身份關系,不同身份之人對應著有差別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盡管在市場化過程中,就業制度對外來人口的排斥大大減弱,但一些流入地依舊遵循“先城鎮、后農村,先本地、后外地”的用工原則,在就業崗位上對流動人口進行限制。流動人口主要在體制外就業,集中在次級勞動力市場,難以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進而被排斥在社會保障和住房保障制度之外,導致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在居住條件等方面產生隔閡,阻礙二者的互動與接納。
戶籍制度是中國特色“流動人口”產生的制度根源。戶籍制度不僅具有社會普遍關心的單純的城—鄉“二元”屬性,而且具有“雙二元”屬性,即既有“城鎮—鄉村”的戶籍類型,也有“本地—外來”的戶籍地點。[8]戶籍制度基于人口管理的目標對個人信息進行登記本身并無不可,但基于戶籍的身份制度卻超過了把人區分為“是誰”、“從哪里來”、“與他人是何關系”的普通范疇,成為資源配置、服務享有和福利可得的標尺。作為具有極強張力的制度,戶籍帶來的影響輻射到人們經濟生產和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造成城市與農村的斷裂,市民與農民的鴻溝,本地與外來的隔離。換言之,在戶籍制度的規范中,人不僅被標記為城里人、農村人,而且被標記為某個具體地點的城里人或農村人,使人一生下來就被賦予了四種有差別的身份(見圖1)。當這種身份區隔與人口流動結合在一起時,就形成了四類具有等級高低之分的人群,一個國家有“四個社會”。與之對應的分別是本地城鎮戶籍人口、本地農村戶籍人口、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

圖1 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
可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9]一樣,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對現地的四類人群進行的等級劃分,使之形成核心—半核心—半邊緣—邊緣的群體構架(見圖2)。其中,鄉—城流動人口與現地戶籍農民和城—城流動人口在身份上存在交叉,或同為農村人口,或同為外來人口;城—城流動人口與鄉—城流動人口和現地城鎮市民在身份上也有所交集,或同為外來人口,或同為城鎮居民。

圖2 戶籍制度的“雙二屬性”與人群等級劃分
戶籍制度的雙重屬性不僅將本地城鎮戶籍市民和鄉—城流動人口完全隔離開來,也將本地農村人口與外來農村人口隔離開來(盡管他們擁有相同的戶籍類型),還將外來城鎮人口與本地城鎮市民隔離開來(雖然他們擁有同樣的戶籍類型)。在流入地資源和福利享有方面,本地城鎮戶籍居民坐擁作為本地人和城市人的雙重利益。相對于城—城流動人口,他們具有作為本地人的優勢;對于本地農村人,他們又是城市人。本地城鎮戶籍是他們對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享有的“入場券”,并使他們成為現地公共資源和社會服務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
現地的農業戶籍人口雖不在城市公共管理體制之內,但城市的擴張和發展也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實際利益,并可能一夜之間成為當地的“新富人群”。這種優勢資源的獲取對外來人口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學歷高素質強的城—城流動人口亦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城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的關系更為復雜。有時,城—城流動人口處于半邊緣地位;有時,本地農村戶籍人口處于半邊緣地位,二者在資源的可及和享用方面相互交錯,互有優劣。但凡涉及稀缺公共資源的分配,城—城流動人口就位居弱勢,處于半邊緣地位。而當市場力量更強(即個體稟賦因素能發揮更大作用)時,城—城流動人口作為城里人的優勢才可能顯現出來,地位超過本地農村人,處于半核心地位。可見,在承擔著多種制度帶給他們的不確定風險時,城—城流動人口也獲得一定的向上流動機會。
可見,“雙二屬性”所帶來的排斥既針對農村人,也針對來自其他城市的外來人。在“雙二屬性”的作用下,改變了生活場域和職業的(鄉—城)流動人口被排斥在現地體制之外,游走于城市體系與農村體系、體制內與體制外、正規市場與非正規市場、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之間,在生活地域、工作職業與社會網絡等方面與現地戶籍人口處于區隔甚至割裂狀態。[10]
(二)城鄉差分與基于戶籍類型的排斥
城—鄉、內—外的“雙二屬性”帶來“農村人效應”和“外來人效應”,對流動人口或形成單一的“外地人排斥”效應,或形成“外地人”和“農村人”的“雙重排斥”效應。
鄉—城流動人口居于金字塔的底端,既屬于空間形態上的外來人口,也屬于制度安排上的農村人口,同時由于自身資本缺失的局限(而這也與戶籍有關),與其他人群難有交集。雖與本地農村人口擁有相同戶籍,但他們卻多了“外來人”的標簽;雖與城—城流動人口擁有相同的流動身份,但他們卻多了“鄉下人”或“農民工”的標簽,是多重弱勢身份交疊、最邊緣化的一類人群。
因此,戶籍制度的排斥首先是針對鄉—城流動人口的,而這一排斥的根源首先在于戶籍性質(即類型),而當前社會主要關注農民工也是出于這樣的考慮。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在子女教育方面,城—城流動兒童的在園比例顯著高于鄉—城流動兒童;在流動人口整體受到排斥的情況下,鄉—城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受到的排斥更為明顯:與城—城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相比,很多人只能選擇私立學校,甚至少量群體只能選擇打工子弟幼兒園;在收入方面,在業鄉—城流動人口的月收入不僅低于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還比城—城流動人口約低900元;鄉—城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擁有住房的比例僅有7.65%,比城—城流動人口低16個百分點;在社會保障水平方面,鄉—城流動人口各類保險的參與比例均不及本地市民的一半,只有8.4%的鄉—城流動人口擁有住房公積金,僅略超過城—城流動人口(30.2%)的1/4。
可見,對鄉—城流動人口而言,基于戶籍制度的“雙重排斥”不僅使他們難以平等享受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的成果,而且也限制了其他方面的融合,表現為:他們與本地人口除了業務往來外,多數沒有發生真正的接觸和互動;作為弱勢群體,他們很難對現地文化帶來積極的貢獻;作為受到排斥的外來人口,他們也難以對現地產生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三)內外之別與基于戶籍地點的排斥
基于戶籍地點的排斥,不僅限于本地—外來的簡單區分,還可從跨省、省內跨市和市內跨縣這一行政區劃維度進行細致的分析。
如圖3所示,結構性排斥隨著人口流動跨越區域的擴大而愈發彰顯。若以行政縣(市、區)界作為界定流動人口地域標識的話,則相較于省內跨市流動人口而言,市內跨縣的流動人口可享受到當地更優質的公共資源和更多樣的社會服務;進而,相較于跨省流動人口而言,省內跨市的流動人口又可享受當地相對更多樣和更優質的公共資源與服務。

圖3 “內外之別”與公共資源和社會服務的配置
從教育方面來看,若孩子在省內流動,面臨的各級各類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的障礙不大,但一旦跨省,情況就發生了質的變化:越是優質教育資源較多之地,學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對外地考生設置的準入門檻往往也越高。從求職就業的門檻來看,一些地方(如北京)對于單位招收外地戶籍畢業生有明確規定,即每招收一個外地戶籍生,就必須搭配一個本地戶籍生,反之卻不然。從社會保障制度來看,社會保險的轉移支付往往以地級市為界分,市內流動者在保障接續上面臨的障礙較小,而跨市,尤其是跨省,則會帶來極大不便,甚至難以執行和落實。如果說從高保障地區向低保障地區的轉移有較大可能性的話,那么,從低保障水平地區向高保障水平地區的轉移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極其困難的。正因為如此,若不考慮資源稟賦等個體差異的話,流動人口在現地所能享受的(優質)福利和服務隨著按行政制度劃分的戶籍地點與居住地點差距的加大而呈現出漏斗式的減少。
即便稟賦極高且具有高度正向選擇性的城—城流動人口,也未能擺脫外地戶籍給他們在現地生活帶來的障礙和流入地社會的結構性排斥。他們大多是從中西部城市來到東部發達城市,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渴望體面工作、有尊嚴地生活,希望通過隱忍和自身努力來實現夢想。的確,較高且超過本地市民平均水平的人力資本積淀可以給他們帶來更高的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但是,雖然生存境遇好于鄉—城流動人口,但制度的不認同帶來的政治、經濟、公共服務與福利、社會網絡等方面的排斥,加上政治資本和組織資本獲得途徑的堵塞,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舊被擠壓在流入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尤其是難以正常獲取必須憑本地戶口才能享受的權利和資源。在吸引了大量來自其他城市和鄉村的流動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和大城市,本地農村戶籍的“含金量”甚至超過外地城市戶口。戶籍制度的“內—外之別”,以及顯性或隱性的地方保護政策和措施的普遍存在,構成城—城流動人口實現融入的最大制度障礙。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多個調查數據的分析結果都表明,盡管城—城流動人口的工資性收入高于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但通過勞動合同和工作時間測量的勞動保護、通過職業類型透視出來的社會聲望、通過社會保障折射出來的社會保護、通過住房體現出的生存尊嚴等都反映出,城—城流動人口在人力資本更高的情況下,亦未被等同對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流入地學習、工作和生活了多年,但一紙“外地”戶籍卻將其排斥在外,具有較高的邊緣化風險。
三、突破邊界、實現嵌入是社會融合的根本途徑
個體差異和群體差異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但是,因制度設計不合理所帶來的資源壟斷和不公平的利益競爭,由此形成的個體之間和群體之間機會的不公,以及因機會不公所導致的個人發展能力之差別卻是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實現融合的本源性障礙。因此,推動流動人口的融合進程,首先必須破解戶籍制度這面“玻璃幕墻”[11]。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橫亙在農民與市民之間,阻隔在本地人口與外來人群之間。為此,許多學者提出,需要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以社區為依托、互動為根本,加強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12];重視流動人口的自然性和干預性融合,鼓勵其主動參與雙向融合,推動其漸進性和多維度融合[13];充分考慮流動人口內部結構的復雜性,提供匹配流動人口不同亞群體的制度安排、城市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14];等等。過去幾年中,部分大城市為實現人口管理目標,逐漸推行居住證制度。2014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也正式公布。但是筆者認為,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制約流動人口實現融合的制度障礙。
(一)戶籍制度改革的現狀
近年,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15],制度本身及其外延經歷了由表及里的變化,從暫住證到居住證、從計劃分配到積分落戶,旨在打通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地區到東部地區的道路,破解戶籍這面“玻璃幕墻”。在國家層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要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下稱《規劃》)提出:“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選擇,因地制宜、分步推進,存量優先、帶動增量的原則,以農業轉移人口為重點,兼顧高校和職業技術院校畢業生、城鎮間異地就業人員和城區城郊農業人口,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2016年1月1日頒布的《居住證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規定,在全國推行居住證制度,并以居住證為載體,各地必須積極創造條件,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向常住人口全覆蓋,逐步提高居住證持有人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打通居住證持有人通過積分等方式落戶的通道。
同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建立健全‘人地錢’掛鉤政策。居住證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蓋未落戶的城鎮常住人口,使他們依法享有居住地義務教育、就業、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 推進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條件的外來人口逐步納入公租房供應范圍”。
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居住證制度是我國戶籍制度改革邁向深水區的重要步驟,表明了政府推動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推進新型城鎮化的信念和決心。
(二)戶籍制度改革并未發揮應有效應
由于戶籍制度改革涉及稀缺優質資源的再分配,所以也是外來人和本地人等多個利益集團多方博弈的過程。在博弈的過程中,外來人口處于絕對的弱勢,也使得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存在四大相互關聯的問題,延宕了流動人口的融入進程。
一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戶指標緊縮、大門緊閉。《規劃》的戶籍改革原則是:“以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等為前置條件,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城區人口50萬~100萬的城市落戶限制,合理放開城區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條例》幾乎完全延續了這一原則,規定持證后在大城市落戶仍有限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特大城市落戶標準最嚴苛,需根據當地綜合承載力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以穩定就業和住所、參加社保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指標。因省會城市或東部發達地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基本都超過這個下限,僅此一項,就將絕大多數流動人口排斥在(特)大城市門外。目前的這種頂層制度設計透視出的是對流動人口赤裸裸的拒入。對不同級別的城市設置略有差異的落戶標準可以理解,但時下這種“一刀切式”的大門緊鎖政策和機械性的做法,不留空間和余地,違背了人口流動的自然法則,具有倒退性和掠奪性的特點。更重要的是,敞開還是關閉大門是政策理念和價值導向的外化,而這種理念會直接作用于制度墻和結構墻的高聳或消融,帶來一系列的衍生效果。
二是小城市(鎮)戶籍制度改革收效甚微。戶口即利益,超(特)大城市的戶籍更是綁定了流動人口的利益。小城市(鎮)、中西部地區的大城市的戶籍管理較為寬松,通過購房或積分形式即可入戶,但這些城市的優質文教衛生資源較少,勞動力市場不夠發達和規范,經濟上難以形成規模效應,人們對未來的發展前景不樂觀,且在短期內,這種差距很難發生徹底扭轉。這種狀況對本地人,尤其是青年人缺乏吸引力,連本地人都留不住,更不用說吸引外來人口了。
相反,一個城市的經濟越發達,就越可能為流動人口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更高的收入水平、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發揮自己潛能并得到認可的機會,也就更可能成為流動人口大量聚集之地,成為面臨嚴峻融入問題的地區。大城市對入戶申請者的就業背景、就業時間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提出較高的要求,而鄉—城流動人口群體幾乎達不到這個條件,所以除中小城市外,落戶政策與鄉—城流動人口關系甚微,即積分落戶制實際上是將占到全部流動人口四分之三的底層流動人口排斥在外。城市越大,落戶越難。中小城市若能提供較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則有利于這些地方聚集人口。
三是地方改革有名無實的多,戶籍改革“去福利化”的少。首先,地方政府進行的戶籍制度改革多是將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統稱為“居民”,對戶口所附著的福利和服務并未有實質性的變革。其次,各地落戶積分的條目很多,但多向高端人群傾斜,教育水平和社會保險繳納在積分中的權重很高,具有很強的傾斜性,所以幾乎將大部分城—城流動人口和絕大部分鄉—城流動人口拒之門外。事實上,在(超、特)大城市,積分落戶政策不僅浮于表面,甚或淪為政府管人控人的“政策工具”,成為顯性排斥政策的隱性替代品。[16]
差別化的落戶政策驅動不同城市設置不同的落戶標準,而這種政策為流動人口設置閘門和分流裝置,給不同城市不同的開放程度,以及接納流動人口的自由,進而使得積分落戶制“雷聲大、雨點小”,本質上還是服務于人口控制。的確,一些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和人口調控的目標是,“控制人口,不控制人才”,而另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則是“既控制人口,也控制人才”,這就直接影響到積分落戶政策的實施。特(超)大城市通過表面的戶籍制度改革,樹立“作為”形象,擺出“政治上正確”的姿態,但實際上卻如“蜻蜓點水”、流于形式,遠未實現“去福利化”。無論是積分落戶,還是其他形式的戶籍制度改革,對流動人口的平等覆蓋依舊大多停留在理念層面。各地出臺的更為具象的積分落戶政策,可能也是順應中央精神而不得不為的應付之策,其本質依舊是要維護現地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17],或在不觸動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對流動人口略加“施舍”。實踐經驗表明,不是從暫住證變為居住證,甚至也不是戶口變了,標示農民身份的土地沒有了,一切區隔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了。如果說20年前,通過地域流動還有可能實現社會流動的話,那么時下,這樣的可能性不僅沒有增大,反而更為狹小,本地人在理所當然地享受流動人口的付出時,卻強制地將流動人口拒絕在公共福祉的大門之外。
四是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一定的“有效維持不平等”性質。流動人口目前可享受的福利多為邊緣性福利,并未真正觸動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再分配,且“梯次漸進式”福利享受機制更可能成為外來人口享受進一步福利的玻璃天花板。以隨遷子女的義務教育為例。出生人口數量的減少,降低了適齡兒童的就學人數;一些資源較豐厚且較優質的公立學校可吸納更多學生就讀,而地理位置較差且質量較低的公立學校可能面臨關、停、并、轉的風險。為保證學校存續,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不得不轉向流動兒童。從某種意義上看,不是學校給流動兒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而是流動兒童為部分公立學校提供了生存的機會。而在流入人口集中的特大城市,流動兒童大多只能就讀于質量較差、本地孩子淘汰下來的幼兒園、小學或中學,高考也受限制。更有甚者,隨遷子女的教育也成為人口調控的重要手段。比如,2014年北京市規定,流動人口子女入學須數證俱全:身份證、出生證、戶口簿、暫住證(或居住證)、務工證、住房合同、借讀證等證件的原件及復印件;具體操作中約需提交20余種證件及幾十種稅票、明細、單據文件,并需街道、教委、工商、稅務、城建、公安等多個部門的層層審核,一處不清,則前功盡棄;自有住房而無暫住證者,孩子不能上學;社保居住不同區者,孩子不能上學……同年,北京市教委發布十五條,嚴令各校不得接收無正式學籍的學生;2015年實行電子學籍卡,通過限制非京籍學生,減少低端人口流入或將他們驅趕出去。這就使得流動人口,尤其是鄉—城流動人口僅有四種選擇:或把子女留在老家,成為留守兒童的一分子;或不能適齡上學;或將孩子送入一個本地孩子不愿上的公立學校或辦學條件(尤其是軟件)較差的私立學校,接受質量較低的教育;或干脆讓年齡稍大的孩子輟學在家或過早地進入勞動力市場。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優質教育的途徑被阻斷,既未實現相對公平,更談不上絕對公平,不僅使得(鄉—城)流動人口自身的生存發展空間十分逼仄,也阻隔了后代的融合前景,還不利于“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
制度難破及因此而起的代際傳承是我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和新型城鎮化步履維艱的主要原因。推動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和新型城鎮化發展,必須從社會和諧的整體角度出發,突破城市利益、本地人群體利益的限制,扭轉已有戶籍制度改革浮于表面和形式的狀況,從根本上破除影響各層次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障礙,賦予他們平等的市民權利。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推動新型城鎮化的發展。
(三)破除制度、結構和理念三堵墻,實現機會均等
長期以來,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均通過戶籍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城與鄉、內與外的區隔性的管理體制,造成了本地城鎮戶籍人口、本地農業戶籍人口、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四類群體之間的割裂,阻礙了流動人口的融合進程和新型城鎮化的步伐。推進流動人口的融合進程,必須打破區隔,實現嵌入式融合*就好像將各面顏色相同但相互隔離的魔方,轉化為一個不同顏色相互交錯、并存林立的錦磚或馬賽克,進而形成片與片之間互相嵌入的多彩拼圖。。
在戶籍制度的基礎上,流動人口社會融合主要面臨制度墻、結構墻和理念墻(或稱“邊界”)的阻礙。制度墻主要是指戶籍及其附屬制度,前者對人群進行標記,而后者則通過各項福利和服務將不同人群隔離開來;同時,人群的身份不同,隔離墻有厚有薄,隔離度有深有淺。結構墻同樣來源于戶籍制度,也與地方經濟、社會、文化構成密不可分;制度墻越厚重,結構墻也會越堅固。理念墻則是在制度墻和結構墻共同作用下產生的人群之間的互動認知心態的偏差;與具象的制度和結構墻相比,理念墻也更為隱蔽。
要破解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困局,必須沖破三堵“墻”,跨越由此形成的區隔邊界,推動不同人群之間的關系實現從魔方狀態向錦磚狀態的轉變,最終實現嵌入式發展。錦磚模式是指打破制度墻和結構墻帶來的人群區隔,推動族群和人群之間的互動;拼圖模式則是在拆除制度墻和隔離墻的基礎上,進一步消除理念墻的區隔,實現人群之間的嵌入交往,真正實現心與心的溝通、文化與文化的交融。
具體來說,一方面,只有制度和結構的“長堅之鐵”真正消融,理念墻才能真正拆除;另一方面,理念墻的消融,也會使制度墻和結構墻失去依托。對于理念墻,本地人在墻內,流動人口在墻外,二者的相互對立態度或彼此的漠視共同架起這面高墻,因此,此墻的摧毀也需要墻內和墻外之人的共同努力。美國社會學家Milton Gordon提出人群融合的七個階段,其中的兩個階段是本地人對移民的接納態度和行為,表明社會融合是本地與外來雙方的適應與接納過程,既需要流動人口本身的主動性和融入意愿,也需要流入地人群的包容和接納。[18]只有流動人口做出積極的融入努力,只有本地市民消除對流動人口的偏見,只有消除結構性障礙、制度性歧視、政策性排斥,流動人口才能適應、融入流入地社會中,才能實現社會的良性整合,促進新型城鎮化的健康發展。
此外,流動人口的融合能力對于融合進程和結果也至關重要,包括人力資本的提升,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有效建構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對此做進一步的闡釋。
四、余論:謹防社會階層的固化風險
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社會,特別是流入地政府對待流動人口的態度一直處于變動之中,從最初把他們視為“盲流”,到視為勞動力,再到視為有家有口的“人”,中間經歷了較為曲折的過程。這兩(三)代流動人口在出血流汗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同時,始終未能擺脫與主流社會相隔離、缺乏有尊嚴生活和較少向上流動希望的弱勢地位。在個體層面,雖然由于先賦要素、融入的努力程度、偶然的機會運氣等千差萬別,使得每個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機遇會有所不同,融合的軌跡起點和終點也有先有后,但是,社會融合既需要流動人口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流入地居民的包容與接納,更需要國家層面和地區層面公共政策的制度性安排。在融合這條路上,流動人口擁有與本地市民均等的機會和公平的權利,既是融合的前提條件,更是社會公正中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如前所言,實際情況是,人口的地域流動制約雖多已消除,但流動人口面臨的很多切實的障礙卻未消解,討薪、維權、子女上學、社會保障、居住隔離等諸多問題都困擾著他們,高質量的組織參與和政治權利等對他們來說更是遙不可及,一些資源豐富之地設置極高的準入門檻,對他們的進入實行管制——高端人才可進,低端人口嚴控。哪怕是高端人才(如高科技領域的城—城流動人口),也只能以外來人身份在特(超)大城市生活。除少數人外,積分落戶遙不可及,戶籍及其附著制度的“長堅之鐵”依舊將他們排斥于現地社會之外,向上流動機會受阻,社會融合進程步履維艱。
如果說第一代流動人口流動的目的是給后輩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并在自己老去后返回家鄉的話,那么,很多在城市出生、成長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動人口則與城市的聯系極為緊密。然而,目前社會上“勞力吸納、福利拒入”的制度、態度和行為,使得多數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動人口依舊只能重蹈父輩的流動軌跡,夢想難圓。媒體曾通過一雙鞋子來描述農民工的代際輪回。一如時下的新生代一樣,20世紀80和90年代,年輕、意氣風發、滿懷勇氣和理想、對未來充滿期許的進城農民,與這個城市唯一的聯系,就是他腳上的那雙在彼時廉價、平常但需用現金購買的“回力牌”球鞋,那也是他們生活于城市的見證,是現代性和城市人的標志。如今,老一代農民工雖然還穿著“回力牌”球鞋,但他們與城市的關系并未發生本質變化。而“農二代”、“農三代”等稱呼,也很好地詮釋了父輩經歷的延續和社會階層的代際傳遞。新一代的流動人口雖穿著與城市同齡人類似的球鞋,但他們與現地的關聯一如前輩,疏離甚至斷裂。幾代人有的只是因歲月變遷和時間流逝帶來的生活閱歷之別和時代之烙印,而難有社會地位的上升。
社會學理論告訴我們,社會分層具有固化性和代際傳遞性:父母或家庭的社會階層地位越高,子女獲得更高或保持已有社會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社會階層越低,子女也越難以擺脫既有的社會階層地位。雖然中國社會的變革激活了競爭機制,個人的能力稟賦可以在社會流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子承父業”的代際傳承模式,但在權利支配模式未變、群體利益結構穩定的情景下,社會地位的固化與傳承依舊凸顯。時下,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動人口雖有融入意愿并付出融入努力,但結果卻一如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樣,懷著把巨石推上山的夢想,但現實總是使其一次次滾落山下。生活在留有祖輩和父輩青春記憶和奮斗足跡的城市,子代和孫輩往往也只留下一個類似的“背影”。鄉—城流動人口作為現地社會的新底層代表,各種弱勢通過世代傳遞而傳續到子代甚至孫輩身上,“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流動兒童若不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將會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二代、三代鄉—城流動人口難以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難以獲得職業發展和職位升遷,難以收獲像樣的收入,難以得到穩定的社會保障,難以培育與本地市民進行真正交往互動的社會資本,沒有資格實現組織參與和政治參與,最終無法實現對現地社會的認同。如若出現這種情況,將會導致二代、三代鄉—城流動人口既脫嵌于傳統的“鄉土情結”(失去了傳統紐帶的支持網絡),也被流入地社會的制度安排所拋棄,生活于現地社會的制度圍墻之外,“無所皈依”。這不僅會導致他們在個體層面難以實現社會融入,群體層面難以實現社會融合,而且還存在部分流動人口向下流動的可能性。
這種現實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社會公平正義理念背道而馳,而且從長遠來看,缺乏改變底層命運的機會可能帶來嚴重的社會隱患。輕者形成負面的亞文化圈,犯下“自我救贖式”的失范行為,而失去改變自己貧困地位的機會所帶來的危害可能更大。人們被喚醒或自覺之后,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核心要素,一旦觸發,就會勢不可擋,引發難以掌控和極其嚴峻的社會后果。
因此,無論是出于對流動人口及其家庭成員福祉的關切,還是從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出發,政府和社會都必須真正關注流動人口的融合問題。推進該群體的社會融合,就是要突破前述的“三堵墻”,實現制度邊界、結構邊界、理念邊界的跨越與重構。無論哪一堵墻,要拆之、平之、融之、化之實非易事。這也提醒我們,社會融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甚至亦非一兩代人的努力就可實現,而是一個長期、艱難且復雜的過程。需要有長期性和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在理想目標上,有追求天下大同的氣魄和決心;在融合過程中,立足現實革故鼎新,通過福利政策的共享和個體的主觀努力,掃除融合道路上的諸多“堅鐵”,形成人群之間的良性互動。漸進式也好,矯枉過正式也罷,小打小鬧、蜻蜓點水式的改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只有革命性的變革,才能真正動搖“三堵墻”帶來的區隔,實現社會邊界的跨越。
[1] Park, R.“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28(6):881-893.
[2][13] 任遠、喬楠:《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過程、測量及影響因素》,載《人口研究》,2010(2)。
[3] 劉傳江、程建林:《雙重“戶籍墻”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載《經濟學家》,2009(10)。
[4] 莊士成、王莉:《社會融合困境與城鎮化“陷阱”: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載《經濟問題探索》,2014(11)。
[5][8] 楊菊華:《中國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15(2)。
[6][7][12][14] 楊菊華、王毅杰、劉傳江、陳友華、王謙等:《流動人口社會融合:“雙重戶籍墻”情景下何以可為?》,載《人口與發展》,2014(3)。
[9] Wallerstein, I.TheModernWorldSystem: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nth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0] 徐祖榮:《流動人口社會融入障礙分析》,載《黨政干部學刊》,2008(9)。
[11] 悅中山、李樹茁:《中國流動人口融合政策評估——基于均等化指數和落戶指數的分析》,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6(6)。
[15] 劉麗:《“居住證”能否讓人“四海為家”》,載《人民論壇》,2015(21)。
[16] 熊萬勝:《新戶籍制度改革與我國戶籍制度的功能轉型》,載《社會科學》,2015(2)。
[17] 彭希哲、趙德余、郭秀云:《戶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思考》,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3)。
[18] Gordon,Milton.AssimilationinAmericanLife:TheRoleofRace,Religion,andNationalOrigi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責任編輯 武京閩)
Double-Dual Property of Hukou System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Blueprint Urbanization in China
YANG Ju-hua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addition to similar issues that international migrants face,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encounter unique difficultie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due to the “double-dual property of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tructural and attitudinal barriers brought about by Hukou at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The multiple and overlapping disadvantages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render them to be more difficult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host society.Current Hukou reform, particularly the policy of “integral settled” (ji-fen-luo-hu) adopted in metropolis, becomes the new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means of social exclusion, although it seem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migrants to be integrated.We propose that overtur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and attitudinal walls, transforming the boundary and enhancing embedment across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and inevitable way to facilitat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Key words: internal migrants; 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double-dual property of the Hukou system; segregation
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13JZD024);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留守兒童與流動兒童發展狀況動態監測研究”(15AZD053)
楊菊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老年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