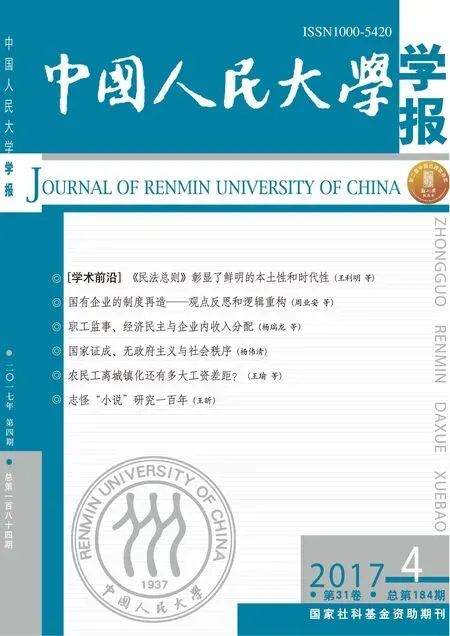四言詩演變的文體學考察
易聞曉
四言詩演變的文體學考察
易聞曉
《詩》四言簡質未舒,但以虛字襯貼、疊字形容、章句字詞重復間破板質,而且分章合樂適于言志的歌詠。賦在一章具有整體性和結構性的作用,比興則僅有暫時性和片段性的功能。《詩》四言與《書》四言散語實字并列及賦體四言散語一順鋪陳具有本質的區別,但漢代四言參合《詩·頌》和《書》語,愈顯典重。漢末以降文人創制已非分章合樂,或自抒懷抱,或受五言、駢體影響,工于屬對鍛煉,及唐人四言都從擬樂府而來,終乖《詩》體本調。
《詩》四言;分章合樂;《書》與賦四言;樂府與駢語
古人創作,首嚴體制之辨。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謂“論詩文當以文體為先”[1](P459),元佚名《文章歐冶序》謂“不知體制……失于文體,去道遠也”[2](P467),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謂“文章自有體裁,凡為某體,務須尋其本色,庶幾當行”[3](P21),都十分強調辨體之于詩的寫作的重要性。在中國詩史上,《詩》四言最早成為一體,它以體制的限定與散文四言相區別。漢以降四言之作既少,造語受到其他文體的影響。從文體學的角度考察四言詩及其演變,可以獲得確切的認識和重要的判斷。
一、《詩》四言與分章合樂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謂“四言優而婉”,且以“四言大雅之音也,其詩中之元氣乎”?又謂“風雅之道,衰自西京,絕于晉宋,所由來矣”[4](P1402),不僅準確把握了四言句式的特點,而且對于四言體詩的盛衰具有深切的洞察。《詩》主四言,故謂“正體”,要以“雅潤為本”[5](P67),或謂“典則雅淳”[6](P4)。四言以“大雅之音”而“最為平正”[7](P158),句式辭氣謂之“優而婉”,與“三言矯而掉”[8](P1402)比較,則謂“密而不促”[9](P571),但視五言、七言則亦當如胡應麟所謂“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10](P22)。四言以二雙音節成句而形成2-2節奏,按韻律構詞學之說[11](P1-2),則是兩個標準韻律詞的組合,它由于具有兩個音步而使聲氣舒緩平穩,所謂“平正”“典則”“不促”,都與聲氣節奏相關。但四言句短、節奏單一,四平八穩而缺乏變化,它的“簡質”“未舒”也是顯而易見。啟功先生提到《詩》之造語“缺頭短尾、脫榫硬接”的現象,這是因為“四字一句……實出無奈”[12](P4),可見四言簡質的局限,所以《詩》之造語有所謂“足四”現象,即通過四言句式的強制作用而使就范。
何丹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充分論證。“足四”的表現,一是“截短”,即把超過四言的長句截短為四言句,例如《詩·國風》首篇《周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二句在“語法”上并屬一句,后二句亦然,只為適合四字句式故為截短。鐘嶸《詩品序》謂“四言……每苦文繁而意少”[13](P23),即指句短而繁,五、七言一句可盡者,在《詩》中往往需要兩句才能表達。“足四”的另一表現是“拉長”,即把“語句字數不足四言者,使用特殊手段,使之成為四言句”,其特突者當是聯綿字的拆分,如《詩·周頌·有客》“有萋有且”,萋且,敬慎貌[14](P1740);《詩·曹風·侯人》“薈兮蔚兮”,薈蔚,云興貌[15](P474)。這種聯綿字拆分的作用,就是把雙音詞拉長而成為四音節即2-2節奏或韻律組合,以合四言[16](P19-23)。
按照誦讀節奏,四言必然就是2-2式,它的整齊劃一不能有所改變,所以節奏單一乃是四言句式的主要弊端,也是“簡質未舒”的表現。但是《詩》語的虛字襯貼和疊字、聯綿字運用卻起到舒緩聲氣的作用,可用清人冒春榮所謂“句中有讀”[17](P1580),即字的組合來分析其中多種不同的現象。從《詩》的造語結構上看,它尚未與散語區別為完全獨特的句法,在某種程度上未離散語。當然,《詩》以四言句押韻,就在體制的限定下形成《詩》的句法。《詩》四言的虛字襯貼,一類與散語語序和結構相同,如《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詩·陳風·月出》“月出皎兮”,很像散語主謂句的四言縮短,盡管誦讀還是2-2節奏或韻律的組合,但以前后二言字組結構不對稱間破兩個節奏排列的板滯,從句意和語氣的輕重上是前重后輕,打破了前后均等的平衡。這種類似于散語的句式變化形式是在主謂間加“之”,如《詩·衛風·氓》“桑之落矣”,“之”作為虛字襯貼不同于散語變成“名詞性詞組”,如《莊子·逍遙游》“風之積也不厚”[18](P4),而是為了湊足四言,同時使四言前一雙音節奏后字“虛化”,句尾的“矣”字更使整句失衡,舒緩聲氣,以破“簡質”。另一類虛字襯貼的情況,則純以虛字湊句,并無意義和語法的功能,僅資合于音節、適應歌唱而已。例如《詩·周南·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在此除了“采采芣苢”的重復,就是“薄言采之”的變化,實際上只是兩句合于音樂的反復迭唱。“薄言采之”四言一句之中,只有“采”字具有實義。“薄”為語助。毛傳:“薄,辭也。”[19](P51)“言”亦語助,或在句首如《詩·小雅·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或在句中如《邶風·泉水》“駕言出游,以寫我憂”,楊樹達《詞詮》卷七謂“助詞,無義”[20](P395)。《爾雅·釋詁下》謂“言,間也”[21](P37),間于句中,在《詩》四言則以語助湊句,間破聲氣。“之”為代字,虛用亦無義,并同語助湊句之用。那么“薄言采之”四字以當實義者,惟“采”一字而已。“采采”則“采”之疊用轉為形容。全詩僅“芣苢”名物為實,如散語為述,則僅“采芣苢”三字為足,但《詩》以虛字襯貼,疊字形容,語句重復,重章迭唱,敷衍一篇,實義為寡,唯以歌詠為功。在節奏的分析上,則“薄言采之”雖誦讀必取2-2式,但未形成二字并列的平衡結構,每個字都以單處,不與相鄰之字為侔,這當然有類散語,但更是由于湊句以合四言限制使然,反而在2-2的板滯節奏中造成多變的聲氣效果。
疊字又稱重言,《詩》中常用,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了《詩》四言2-2節奏模式的簡質板滯。《詩》用疊字在詩句前面者如上引《詩·周南·采苢》“采采芣苢”,又如《詩·邶風·谷風》“習習谷風”,疊字在后則如《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詩·小雅·出車》“春日遲遲”,并以名物之實與疊字形容之虛相合,或為主謂結構,或為偏正結構,使2-2節奏呈現不平衡的變化。上引陸時雍《詩鏡總論》所謂“四言優而婉”,與疊字及聯綿字的運用具有很大關系,由于疊用二字聲韻俱同而延長,起到延緩聲氣的作用,適與《詩》四言“言志”抒情、一唱三嘆相契。與疊字具有相似功效的是“疊語”,即兩個字組結構的重復,如《詩·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詩·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盡管誦讀節奏仍是2-2平半截分,但是疊語卻使語氣一順,不覺簡質板滯。
《詩》語多用疊字,一則由于何丹所謂“足二”原則,足二則以足四。疊字多仍單字之義,轉為形容。例如《詩·小雅·小宛》“溫溫恭人”,朱注“溫溫,和柔貌”[22](P94),其實“溫”本柔和義,重言足二,繼以足四,不言“溫恭人”,必言“溫溫”而足。又如《詩·王風·黍離》“中心搖搖”,“搖”本動作字,疊用作“搖搖”足二,義如單字而轉形容。二則《詩》四言整齊平正,節奏分明,適于重言之用,較雙聲疊韻,聲氣最為明暢,但少婉轉變化。三則《詩》以合樂之需。重言即是長言、緩言,適于歌唱合樂,聲音綿綿,以抒《詩》怨。例如《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依”“霏”疊字,本義仍之,然以雙音長言合樂,情韻悠長。四則《詩》以分章迭唱,各章字辭大略對應,重言亦必重出,或需變換增損,故用重言為多。但如雙聲疊韻,其字本少,變更為難,重言則單字長言而已。例如《詩·陳風·東門之楊》兩章,前章“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后章“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晳晳”。“牂牂”,木盛貌。朱注:“肺肺,猶牂牂也;晳晳,猶煌煌也。”[23](P55)。“肺肺”“晳晳”以應“牂牂”“煌煌”之對,必然再造重言,以使重章疊句,音韻回環,也是歌唱旋律回環的需要。
疊字是相同二字的疊用,所以聲韻完全相同。聯綿字中雙聲是聲母相同或相近而韻母不同,疊韻是聲母不同而韻相同或相近。關于雙聲字,一般認為是聲母相同,如1988年版《辭源》“雙聲疊韻”條云:“二字同聲母為雙聲,二字同韻母為疊韻”[24](P1907)。但實際上古人用為雙聲之例,也有聲母不完全相同而是相近者,若“凄愴”,賦如枚乘《七發》、陸機《文賦》見之;“憯惻”,見王粲《登樓賦》,“凄”“憯”并清母,“愴”“惻”并初母,然以清母、初母并齒音,聲母相近,故以雙聲用之為常。這是由于因聲造字,產生聲韻相同或相近而又義同或近的字系,作者臨文,但以聲韻相同或相近并字義相同或相近者臨時并用,久之習用,成為連綿[25]。“凄愴”“憯惻”乃是清母字系“憯、慘、凄、愀”、初母字系“愴、惻”的臨文選擇并用,而且這兩個字系也還產生“憯凄”(宋玉《九辯》《風賦》《髙唐賦》)、“慘凄”(嵇康《琴賦》)、“愴惻”(潘岳《寡婦賦》)、“愀愴”(嵇康《琴賦》)等組合,或聲母完全相同,或僅相近湊合,都可視為“雙聲”。至于疊韻,或韻母相同,或主要元音相同,都視同類為然,但“二字同韻母為疊韻”的定義則使人誤認韻母完全相同,其實所謂“疊韻”是兩字并用的韻母音韻聯系,這與句尾押韻同理,簡言之就是兩字的“押韻”,都是本于同韻部的并用。
詩用雙聲、疊韻不若疊字為多,至《離騷》則大量使用。《詩》用雙聲疊韻,大約見于《詩·周南·關雎》“窈窕”“參差”、《詩·周南·卷耳》“崔嵬”、《詩·召南·羔羊》“委蛇”、《詩·邶風·燕燕》“差池”、《詩·邶風·旄丘》“流離”、《詩·邶風·新臺》“燕婉”、《詩·豳風·鴟鸮》“漂搖”、《詩·豳風·七月》“觱發”“栗烈”、《詩·陳風·澤陂》“滂沱”、《詩·陳風·東門之枌》“婆娑”、《詩·小雅·四牡》“倭遲”等。雙聲、疊韻對于《詩》四言節奏單一導致的簡質板滯,具有與疊字一樣舒緩聲氣的功能。《詩》少雙聲疊韻,或以字組的聲韻系聯尚未發達,但也是由于雙聲、疊韻不如疊字用以足二、足四,單音重復,聲氣朗暢,肖吻上口。而且由于《詩》以分章迭唱,各章字詞大略對應,重言亦必重出,若多雙聲疊韻,其字本少,變更為難。
《詩》篇分章乃是適應重疊歌唱的需要,分章合樂是《詩》篇的重要特點,這不僅導致各章造語結構的對應和部分字詞的重復,從而在整體上產生音韻回環的效果,襯托言志的歌詠,而且也正好切合賦比興表現手法的應用,或者說賦比興原本就以《詩》四言和分章合樂的體制需要而產生。《詩》篇絕多分章合樂,只有《大雅》如《文王》《生民》敘事,連貫各章,是周人的史詩,整體上“敷陳其事”,即以敘事為篇,不是分章合樂的“言志”詠嘆。但在《國風》和《小雅》之什,大多數是在一章之內以賦為整體構架“敷陳其事”,一首詩的分章合樂造成每章句數結構和句式一致甚至語詞的基本重復,章與章之間的疊復打亂了一篇整體敘事的完整性,換言之,是依靠分章的重復詠嘆言志抒情,并不在于敘述一個完整的事件,往往違背事件的時間順序,本于情志的詠嘆顯得顛倒錯亂,事件被碎化為一個個細小的片段。例如《詩·小雅·采薇》,我們只看到“采薇……采薇”的重復動作,一邊想著嗟嘆著軍旅的艱辛,不僅是“不遑啟居”、“靡使歸聘”的幽怨,也有“王事靡盬,不遑啟處”的國家擔當、“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的軍人使命,甚至有“四牡業業”“一月三捷”的戰士自豪。又如極像敘事的《詩·豳風·七月》,它對于節序之事的敘述,卻是顛三倒四,旨在抒發農人一年勞苦的感慨,卻不是以此完整敘述一年的事情,可以說它展現上古農事生活的場景,卻不能稱為“史詩”。盡管如此,《詩》篇一章之內,即如上舉《詩·邶風·式微》四言句式在時間順序的排列,即其娓娓道來的詠嘆本身,卻必然是賦,賦擔當了一章整體性和結構性的職能,但全詩卻是詠嘆為主。
相對于賦在《詩》之一章的整體性和結構性功用,比、興在一章中卻是隨意性、暫時性和片段性的。比的情形如《詩·邶風·綠衣》首章“綠兮衣兮,綠衣黃里”,朱熹注謂“比也”,綠為間色,黃為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里,言皆失其所也”[26](P11)。這是援綠衣黃里之物,借以表達“失所”之意,后者為本,前者為末,惟意之所至,隨時遣用,用過即止。由于《詩》四言為短,往往兩句才得意思完整,尤其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多為前二句先言“他物”,后二句顯示“所詠之詞”。例如《詩·衛風·氓》“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興起“自我徂爾,三歲食貧”,以四言兩句形成一個相對自足的語意單位,即四言兩兩的排列形成一章,賦比興都以這種四言的排列生成,一章的四言排列往往就是賦的敷陳。例如《詩·衛風·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顯然是比,可是朱熹注謂“賦也”[27](P26),興的前后順序也處于一章敷陳的序列中,比興乃在賦的敷陳中實現,表明賦在一章中具有整體性和結構性的功能。
二、《書》、賦四言與漢代四言頌詩
《文鏡秘府論·定位》以四言“在用宜多,凡所結言,必據之為述”[28](P158),當然不獨指詩而言,散文、大賦和駢體亦多四言。《詩》語四言適合抒情和歌詠的需要而具有詩的造語特點。散語四言以《書》為代表,本質上是敘述的,其虛字的使用乃是散語結構的需要,而不是《詩》足二或足四的襯貼。《書》中疊字、連綿字罕見,而是實義字多、單用為常,實義單字的并列由于缺少虛字的襯貼和疊字、連綿字的聲氣調節而顯得簡古急迫、佶屈聱牙,這可以視為顧炎武《日知錄》所謂“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者”[29](P1809)的典型表現。語氣虛字的使用如《書·堯典》“曰若稽古”,固與《詩·周頌·噫嘻》“噫嘻成王”并示莊重,但《書》語在于史實的客觀敘述以顯典重,《詩》語則在深沉的情感以表崇仰。又如《書·堯典》“乃命羲和”,“乃”作為連詞的運用,不同于《詩·豳風·七月》“言私其豵”的“言”字只為發語湊句。當然《詩》語如《大雅·緜》亦有“乃召司空”“迺立皋門”之類,應該說《大雅》和《頌》的莊重頗有近于《書》語者,但“乃召司空”之類的造語多用于《詩》章首句,引起一章的描寫。《書》四言夾在雜言之中,并不存在所謂“四言體”的限制,四言與雜言都歸散語敘述對話之用,本質上屬于散語,因而并不需要“足二”和“足四”的湊合,而是將單字聚合,連用表意而已。如《書·無逸》略云: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30](P430-431)
《書》的敘述性散語特點就是文理一順,四言夾雜其中,僅當文理順序中的過程和片段。“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四語的遞進遵照文理的順序,因為散語沒有《詩》的篇章制約和合樂要求,并不需要過多考慮句式的長短和句數的多寡,只是依照文理順序進行一順的敘述,表現在標點上,則四言數句之間必以逗號,而不是像《詩》語那樣兩個四言為句。《詩》四言既為定式,篇章句數又有大致的制約,而且必須押韻合樂,因此《詩》四言大約兩句一意,即使號為“賦”者,也不能像散語一樣一順敘說。例如《詩·衛風·氓》中一章: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兩句一意一韻,接下另起,如此順推,兩句一意與接下兩句一意即兩韻之間,具有意義的間隔和停頓,或者說兩句之間實際上存在意義的“空白”,這是《詩》韻乃至篇幅、篇章制約使然,相對于散語一順的情形來說,這些“形式”的限定正是《詩》語之為《詩》語、《詩》之為《詩》的決定性因素。然而恰恰是《詩》語之間的意義空白引發讀者的聯想。實際上,《詩》語即使“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與散語的一順敘述具有體制的區別,即《書》中四言多句與《詩》中兩句一順的不同。不僅如此,而且《書》四言夾于雜言之中,“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四句逗號不可間斷,語意承前則以“昔在殷王中宗”領起,接后則至“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才得意完。
至于《書》語實義之字的組合排列,則如“治民祗懼”,“祗”義為敬,四字都有實義,但依文理排列,中無虛字襯貼,“祗懼”不用疊字或連綿,讀之“語急”不伸。《詩》語則如《周頌·雝》:“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疊字“肅肅”“穆穆”,并與“祗懼”義近,而前者作疊字、后者則無聲韻關聯,只是兩字并置,則《詩》語悠婉、《書》語佶屈[31](P46),誦讀可知。當然,《書》亦偶有如《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之類,但不主故常,而以簡古拙重為其造語本色。再如《洛誥》“伻來毖殷”,“伻來”為使者前來,“毖”亦慰勞,“殷”指營洛殷民,四字措實不虛,“毖殷”單字動賓結構,尤使語急。
《書》四言散語而外,賦四言亦可比照《詩》四言的特點。《離騷》為賦之祖,造語則以虛字連帶形成長句的復雜結構,并以句尾虛字強調抒情的感嘆。宋玉棄情賦物,則已舍棄《離騷》長句及其抒情的功能,轉而多用省煉的四字散語,用以鋪排名物,或堆砌形容。這種四字句之所以稱為散語,并非不入韻或不作偶對之謂,雖然賦語入韻而略有屬對,但關鍵在于四字句之間的語意連貫、一氣直下之勢。《高唐賦》四字句如“秋蘭茞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32](P266),這種四字句舍棄了《詩》四言虛字襯貼和《騷》語虛字連帶,只以四字為讀,直接呈現名物,無須句法成分的組合,形成縝密的鋪陳效果。如“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眾雀嗷嗷”[33](P266)之類。宋賦直開漢代大賦,造語隨之。四字形容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涌澎湃,滭弗宓汩,逼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橈,宛潬膠戾”,連綿形容,氣勢奔涌。名物呈現則如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山則”“其土則”“其石則”提挈四字之句,構成山、土、石、東、南、西、北、高、卑、上、下、高、低的廣闊空間和多維視角,例如“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眾物居之,不可勝圖”[34](P351),散語一順鋪陳,語勢一氣直下,名物紛至沓來,節奏震人心魄,句無長字,字無虛發,目不暇接,間不容發。當視“其山則”“其土則”領屬連串四字之語,以其一順鋪陳,語勢不斷,必為一句,不以分號或句號隔斷為然[35],這是漢大賦被稱為“散體大賦”造語的突出特點。究之賦四言的職能就是名物的一順鋪排和呈現,或是形容描寫的魚貫疊加,《詩》四言則是借助比興點逗的情感詠嘆,以及所謂“賦”法的物事影掠,加以分章合樂和句式“足四”的種種限制,必用虛字襯貼,聯綿字的使用也主要是為了舒緩聲氣,賦四言的連綿堆砌卻是指向鋪陳的目的。
但在漢代大賦中卻有四言系詩,并郊祀歌中四言體,內容為頌,大率《詩·頌》之余,而參以《書》語。此外尚有一些文人四言之制,總體上數量為少,表明《詩》的衰微,繼以漢樂府五言詩興起。漢代郊祀歌中《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諸篇,又《安世房中歌》中如第一章等,模擬《詩·頌》,可以視為《詩》四言在漢代的嗣響。《青陽》略云:“青陽開動,根荄以遂……枯槁復產,乃成厥命。眾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啿啿,惟春之褀。”[36](P1054-1055)《朱明》略云:“桐生茂豫,糜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37](P1055)虛字襯貼、疊字形容,優游不迫,但較國風篇什莊重整肅,更近《詩·頌》。而漢大賦序文和賦末系歌,亦以歌功頌德,造語參合《詩》《書》,古拙質重。班固《東都賦》末系《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白雉詩》五首。《明堂詩》云:
于昭明堂,明堂孔陽。圣皇宗嗣,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其誰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38](P40)
造語莊重質樸,顯系仿效《詩·頌》,多用實字,則近《書》語。大賦正文四言也有類于《詩·頌》者,如揚雄《河東賦》:“秦神下詟,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饗,五位時敘,絪缊玄黃,將紹厥后。”[39](P3536-3538)后四句有類《詩·頌》,但前段用字繁難,實字堆積,可見賦家造語習慣。大賦中校獵、祭祀、都城等題材本是國家社稷之事,賦以鋪陳夸飾,具有頌揚的本質傾向,是為“賦體頌用”[40],賦家以此為主導,而又記誦《詩》語,不覺寫之,有如己出。

于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42](P165)
《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晉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是時中興三十余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43](P1433)劉蒼所制,本于《詩·周頌·清廟》:
于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44](P1279)劉制功用同之,詞意亦然。前二句襲用《清廟》,“越序上帝”易為“對越在天”,“駿奔來寧”顯然是“駿奔走在廟”的改寫,當然歌頌的具體內容就只能本于光武丕業和漢臣“越序上帝”的時代觀念。但整體辭氣不若《清廟》優游不迫,而顯得莊雅厚重,頗類《書》語。《書》語如《康誥》“用保乂民”“用保康民”,散語直述,結構緊湊,與《詩》語多用虛字襯貼、辭氣優婉不同。劉蒼擬作“駿奔來寧”副之,《清廟》作“駿奔走在廟”,雖五言不資比較,但如減為“駿奔在廟”,“在廟”以虛字襯貼,辭氣就顯得優游不迫。劉作“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則淺白呆滯,語意平直,既無《詩》語虛字襯貼,也不若《書》語簡古嚴密。如作“既立三雍”“圖讖是章”,則語意高古,有類《詩》《書》。四言愈到后世,愈減虛字之用,雖如劉作本為樂舞命辭,卻似乎不諳辭以合樂的優婉不迫,這反映了四言句式演變的真實情形。
三、文人述志四言與五言、駢語影響
《詩》以“言志”,但《詩》篇作者既不可考,國風多出民間,或經口耳增損,而且采詩合樂,又或經過修改潤色,加以尊《詩》為經,通過經學的闡發,我們很難就《詩》篇作者意識進行確切解讀。而漢代郊祀歌并賦頌四言,系事為大,不在一己言志。但漢末仲長統有四言兩首,可以視為文人四言述志之作。《后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第一篇云: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云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45](P1644-1645)
這表明四言詩在漢代的新變:文人述志,不主抒情,轉而議論,不用比興,不再歌詠,只是賦的一直敷陳,故非分章合樂,不資虛字襯貼,而且詞意淺直,語帶戾氣,喪失優游和緩、“溫柔敦厚”的“詩人”之旨。詩中少用虛字而多用實義字構為屬對,如“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字字為對,音節鏗鏘,遂乏悠婉不迫之致;后首如“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詞意淺直而強為構對,適見傖父面目。此風實開六朝,但六朝四言詩屬對多運意象、故事,物我交融,類于五言詩與駢語構對,這是四言體的進一步演變。
西漢淮南王劉安作《八公操》[46](P852),頗類騷體,被稱“騷體四言詩”[47],又有霍去病《琴歌》,其實都是歌謠,雖或造語偶近于《詩》,但總體上與之不侔。明代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云:“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諷諫》《自劾》等篇,典則淳深,商、周之遺軌也;《黃鵠》《紫芝》《八公》等篇,瑰奇風藻,魏晉之前驅也。”[48](P8)《八公操》略云: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剩毛羽兮。超騰青云,蹈梁甫兮。
其辭托物見志,頗類《離騷》,但《騷》語是用虛字連帶的押韻散語,句式長短參差,其“兮”字的用法,或在前句末尾,后句不用。例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劉作“公將與予,剩毛羽兮”,語意似有不愜。比較屈辭《橘頌》四言而隔句用“兮”,其辭略云: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49](P153)
《橘頌》的四言句式可能開啟了一種傳統,漢人如劉向《九嘆·離世》云:
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當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愿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50](P288-289)
它的整篇詞意頗類屈原《九章·哀郢》,《九嘆》命篇也是仿效《九章》,這是沒有異議的。將劉安《八公操》置于這一傳統中考察,基本上可以斷為“騷體”。盡管騷體與《詩》并為四言,而《詩》《騷》并稱,現代也將《騷》及楚辭其他作品視為詩歌一類,但二者存在體制的本質區別,屈辭開啟宋賦,漢大賦與騷體并存,后人并稱辭賦,在名稱上彰顯了以《騷》為代表的屈辭與《詩》的體制之異。
漢代被后人視為四言詩的尚有霍去病《琴歌》,其辭略云:“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載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51](P882)《詩》篇造語有“兮”字者,如《邶風·擊鼓》后四句云:“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第三字押韻,且首句入韻,這是《詩》語押韻的特殊現象。又隔句用“兮”則如《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是亦隔句第三字押韻。第三章則換“兮”為“之”字,表明《詩》四言“兮”字的足四湊句作用。霍去病的《琴歌》從“兮”字湊句和押韻方式上都與《詩》相近,而且與劉作“公將與予,剩毛羽兮”的截分略感不愜相反,若作一語“麒麟來臻鳳凰翔兮”則顯冗長,分為“麒麟來臻,鳳凰翔兮”則語順。所以我們可以大致判斷霍作近《詩》、劉作近《騷》,但后者既然近《騷》,就不能稱之為詩,所謂“騷體四言詩”乃是無謂的假設。
漢魏曹操作四言《短歌行》《觀滄海》以為述志。前者直用《詩·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及《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語,其余自作語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則沖口所出,自抒懷抱,不加雕琢,亦不按音律,究歸徒歌而已,故前者命“歌”,后者亦然,不合樂則不需虛字襯貼,不需疊字連綿以舒聲氣,這是四言在漢魏之間的一大轉變。即使曹操二首“被之管弦”,由于詞句并非為合樂而配,效果也不會很好,那就是“乖樂”。鐘嶸《詩品》謂“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52] (P220),宋敖陶孫《詩評》謂“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53](P1031),蓋自辭氣言之,為得體要,但這一評價移于合樂,則已乖甚。
至操子曹植《朔風詩五章》[54](P173),一方面較其父歌行為合《詩》語,“仰彼朔風”“思彼蠻方”“豈忘爾貽”“豈云其誠”,由于虛字襯貼,頗有“優婉”的意態,而“昔我初遷”“今我旋止”則顯系祖于《詩·小雅·采薇》“昔我往矣”“今我來思”諸語。但另一方面,更為突出的是承接《古詩十九首》的文人意趣,以及已見整麗的造語,這與鐘嶸《詩品》所評其五言詩“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55](P56)具有相似性,也許是曹植善作五言的造語習慣不自覺用于四言。例如“愿騁代馬”“愿隨越鳥”自《詩》“愿言”翻出,若《詩·衛風·伯兮》“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但以去掉“言”的虛字襯貼,代之以“騁代馬”“隨越鳥”的動賓結構,遂見整練,卻失去了《詩》語的優婉。魏晉五言“愿言”尚用,如晉謝混《游西池詩》“逍遙越城肆,愿言屢經過”[56](P312),由于五言多一字而不顯拘迫,在“愿騁代馬”四言則只能減去“言”之虛字,便覺急促。“代馬”“越鳥”祖述《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57](P409),意態如之,然五言削足四言,不免拘迫。又“倏忽北徂”語意亦近《古詩十九首》“道路阻且長”,“四氣代謝”則是魏晉多少帶有玄言的感思,降及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58](P693)云云,人心之于物色的心物遇會,反映六朝文人的多愁善感。抑如“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的對舉,“懸景”造語的精整,“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別如”“脫若”的切對,以及“昔我初遷,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二四隔句的對舉與“朱華”“素雪”的切對,都反映文人詩琢句練字的明顯趨向。在曹植五言,練字琢句的顯露正是文人趨擬樂府而使五言詩出脫樂府民歌造語敷衍散緩、而逐漸成為文人自抒懷抱的案頭作品的關捩。所謂《詩》四言雖仍保留了它的基本形式,但是造語用字的切要之處,卻不免隨著時代人心發生變化,字句的細微雖然不易察覺,但卻是詩史演變所示最為切要的方面。
曹植四言意趣與造語用字受其本人五言詩創作的影響,較為典型地反映文人擬樂府過程中逐漸出脫樂府的趨向,而曹魏時嵇康四言詩如《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則受到駢文造語的影響。茲以第九首[59](P10)、第十四首[60](P15-16)為例略作討論。四言二句形成一個語意單位,在《詩》已然,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兩句相合,一意既完,接下又是兩句相合以完一意,如“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今”“昔”的對比,明顯分為兩個語意的單位。兩句相合的語意單位的疊加易于導致兩句之間的對舉,從而衍為屬對,《詩》語略見,但尚未著意構對,而是通過兩句一順和虛字連帶保持與散語的聯系,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散語的詩體規范化,卻不能稱之為屬對。但到嵇康的四言,則已在兩句一意的語意單位構為駢偶,這是受到文語駢化的影響,第九首首句“良馬既閑,麗服有暉”,“良馬”對“麗服”,虛字“既”對“有”,“閑”以形容對“暉”,“暉”輕用虛化,故可為對[61](P119-121),這是主謂結構為對。“左攬繁弱,右接忘歸”則是動賓結構為對。“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則以兩個主謂結構對舉兩個主謂結構,益見整飭縝密,間不容發,“躡景”以對“風馳”,尤為著力。第十四首“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息徒”對“秣馬”,“蘭圃”對“華山”,堪稱工切,同樣整飭縝密。“流磻平皋,垂綸長川”也是屬對工整。只是“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后二字不甚講求,反映屬對尚未務必精工的造作,而且“嘉彼釣叟”“郢人逝矣”的虛字襯貼多少保留《詩》語的散緩,但這已無關緊要,因為不是《詩》篇合樂重章疊句和悠游不迫的詠唱,而是文人緊扣一意的個人創制。字斟句酌的駢語營構,才是魏晉文人的詩心所在。及唐四言作者益少,為舉孫思邈、李賀、顧況所作以見大概。孫思邈《四言詩》完全成為整篇敘述說理的文字:
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爐烈火,烘焰翕赫。煙未及黔,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環,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62](P9717)
這已經不是《詩》篇重章迭唱的詠嘆,也已完全失去四言散緩敷衍的優婉韻致,兩句一韻的語句疊加率多構為屬對,以為鋪陳,如“煙未及黔,焰不假碧”“姹女氣索,嬰兒聲寂”,屬對勉強,作意顯露,以至聲氣不暢,節奏不振。而如“壁立幾多,馬馳一驛”,衍為數字為對的簡單湊合。又如“惡黜善遷,情回性易”的句中自對,以及“熠若火生,乍疑血滴”的散語緊縮,不可謂知《詩》四言作法,通篇只是一首敘議的歌訣,而不是詩。
再看李賀的四言詩《猛虎行》[63](P252),按詩題乃是歌行一體。唐代歌行由漢樂府經六朝文人擬作演化而來。《漢書·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64](P1755)所謂“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乃是漢樂府詩的本色,也是歌行體的特點。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65](P104)李賀詩寫猛虎,即是“緣事而發”,篇幅較近體四句或八句為長,確是“放情長言”“疏而不滯”,放情而篇幅為長,不限句數,不受近體絕句或律體四聯起承轉合的嚴格限定,順適抒寫,故謂“不滯”,這是唐人歌行的基本要義,李賀是詩如之。那么它以一順的即事抒情,當然已非《詩》四言的優婉和簡質未舒,因而也不需要《詩》篇重章疊句的詠唱,而是一氣呵成,抒發胸臆。最后引錄唐顧況的《囝》: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66](P2930)
此詩換韻為多,有如唐七言歌行,換韻而轉意。《詩》篇亦有換章轉韻者,但以詩語分章合樂、重章疊句,僅易一二字,且各章結構相同,因而保持通篇各章的基本協調。顧詩整篇用賦,一順敘述,與《詩》整篇詠嘆不同,除去“彼受其福”“及汝既生”等句以虛字襯貼略存《詩》語影跡而外,若“閩吏得之,乃絕其陽”“不從人言,果獲是苦”的白話直述,較諸《詩》語優婉和意蘊的含蓄即所謂“主文而譎諫”的“溫柔敦厚”之旨已落下乘。而且“心摧血下”“隔地絕天”的縝密結構也與《詩》語優婉散緩之致不類,顯露唐人琢句練字的普遍好尚。究之自曹魏以來,文人擬樂府逐漸出脫樂府本旨而發展為文人特有的創制,唐詩淵藪都在樂府,因而六朝以迄唐人四言雖仍《詩》語,然意態辭氣則從樂府而來,又以擬樂府最終出脫樂府一途,卒成文人作者抒情述志的個人創制,可是那種風雅頌的弦歌合唱已經是隔絕多代的遙遠余音了。
[1]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2] 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6][10][48]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8] 陸時雍:《詩鏡總論》,載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5][9][58]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7][28]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
[11] 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12] 啟功:《漢語現象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97。
[13] 曹旭:《詩品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14][15][19][44] 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版社,1999。
[16] 何丹:《詩經——四言體起源探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17]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載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8] 郭莊藩:《莊子集釋》,載《諸子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74。
[20] 楊樹達:《詞詮》,北京,中華書局,1978。
[21]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2][23][26][27] 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 《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5] 易聞曉:《賦用聯綿字字本位語用考述》,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2)。
[29]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0]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1] 韓愈:《進學解》,載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2][33][34][38][56][57]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35] 易聞曉:《“賦亡”:鋪陳的喪失》,載《文學評論》,2015(3)。
[36][37][39][41][64]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40] 易聞曉:《論漢代賦頌文體的交越互用》,載《文學評論》,2012(1)。
[42] 吳樹平:《東觀漢紀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43][45] 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46][51]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47] 程彥霞:《兩漢四言詩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49][50]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52][55] 曹旭:《詩品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53] 王世貞:《藝苑卮言》,載《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
[54]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59][60]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61] 易聞曉:《中國古代詩法綱要》,濟南,齊魯書社,2005。
[62][66]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63] 王琦等:《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65] 徐師曾:《文體明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責任編輯 張 靜)
A Stylistic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Four-character Poems
YI Wen-xi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The four-character verses of the “The Book of Songs” are simple yet implicitly conveyed, lined with functional words, reduplicated describing words and phrases to break the pattern, in addition, chapter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musical rhythm,making it suitable for expressing aspirations.Fuplays a holistic and structural role in the chapter , whereasXingmerely serves arbitrary, temporary and fragmented function. The concrete word blending of the four-character vers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four-character prose in “The Book of History” are essentially distinct from the elaboration of four-characterFu. But the four-characterHanFu, mixed with four-character of “Book of Songs,Hymn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carries more classic weight. Star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literary creations are no longer required to be in synchrony with misical rhythms, rather they are either self-expression of aspirations, or products influenced by five-character proses and parallel style. And all the four-character prose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their origins in the simulation ofYuefupeotry.
four-character vers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synchrony with musical rhythms; “The Book of History” and four-characterFu;Yuefuand parallel style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古代詩法理論的現代闡釋”(12BZW013)
易聞曉: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貴州 貴陽 5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