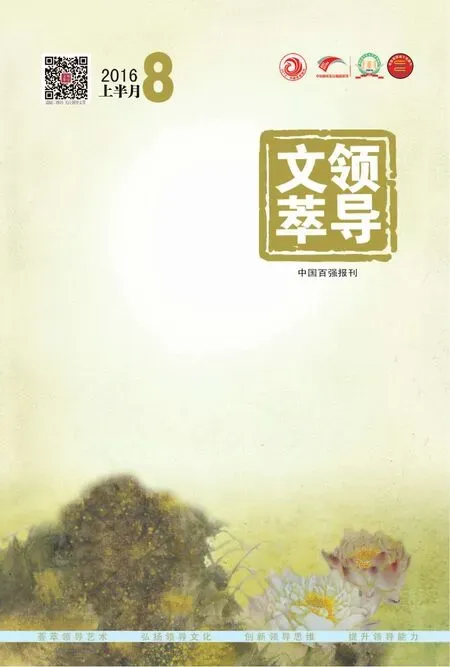中美經濟的共同挑戰
黃育川
緩解不平等、完善監管體系、重塑財政和金融體系、管理大企業帶來的風險和鼓勵創新是兩種發展模式都要應對的問題
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奇跡和美國金融危機后無比艱難的復蘇,引發了關于政府和市場角色的討論。
人們通常認為,美國市場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政府主導型的模式是兩個極端。多數觀察家認為,這兩種體系不僅在運作方式上有根本性的不同,而且面臨著不同的挑戰。但現實卻是,兩種體系需要應對的問題中,共同點很可能多于不同點。 第一個共同挑戰是緩解巨大的不平等。中國似乎并不比美國能更有效遏制不平等。目前兩國基尼系數均在0.45左右,但起作用的因素不同。在這兩個國家,有關系的“圈內人”比富有創造力的“圈外人”更受青睞。
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社會差距。美國中產階層工人的薪酬增長陷入了停滯。而中國因貿易帶動的沿海與內陸的收入差距已十分顯著。兩國都試圖通過加強外部監管和財政政策的調節來彌合這種差距,這又帶來扼殺創新的風險。美國經濟仍然需要通過擴大投資來提高生產率;中國則需要向價值鏈上端移動,以保持增長動能。
第二個共同挑戰是完善監管體系。在不完善的監管制度下,無論是政府提供的還是私人部門運作的公共服務,都存在脆弱性。中國薄弱的食品安全標準和曾發生的高鐵安全事故表明,分離監管和運營職責異常重要。而美國鼓勵私人部門提供公用事業的模式,則很容易造成抬高價格、限制消費者選擇的問題。
問題重重的監管體系下,中美兩國的金融體系都面臨極大風險。兼并提高了美國金融業的集中度,凸顯了“大而不能倒”的風險。中國銀行業由國企主導,過度的銀行貸款擴大了準財政赤字,增加隱性成本,助長了投機性房地產泡沫和高風險影子銀行業務。
第三個共同挑戰是重塑財政和金融體系。在使用金融和財政體系支持創新、提供更多公共服務方面,兩國均面臨挑戰。美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來有所上升,反映出面對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政府的壓力在增加,引發了各方對政府可承受能力的擔憂。中國政府控制著更多的社會資源,也承擔著各式各樣的職責,財政預算僅扮演極為有限的角色,其后果是:過度依賴銀行體系來完成本應由財政負擔的公共職能,亟需的社會和環境公共服務成為短板。
第四個共同挑戰是管理大型企業帶來的風險。大型公司很容易破壞監管策略,西方的“大而不能倒”與中國的“大而不能管”一樣致命。許多行業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大企業一方面能起到引領作用;另一方面也會抑制其他企業的發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綁架政府。美國的大銀行如此,中國的大型壟斷國企亦如是,后者由于政府近兩年倡導重組整合,正變得越來越龐大。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競爭,對投資者、銀行體系和中小型企業的保護,兩國經濟最終都會遭受重創。
第五個共同挑戰是鼓勵創新。傳統觀點認為,市場導向型的資本主義對鼓勵創新更為有效。不過,美國近年被認為喪失了不少創新活力,一大原因是政府未能扮演足夠支撐性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市場導向型資本主義的信仰,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對與創新相伴而來的風險的評估。美國的創新招牌或許并未褪色,但捍衛其過往的顯著優勢正變得越來越有挑戰。
對中國來說,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化,中國需要培育出更廣泛的行業。與私人部門相比,政府看起來并不適合推動此類努力。大型國有企業在國內固然占據支配性地位,但在國外尚未成為真正創新性實踐的引領者。如果國內回報依然很高,創新和冒險就缺乏動力。在國外,如果其資金成本仍然很低,政府仍然看起來擁有無限資源,它們在海外的投資很可能仍然回報寥寥。
(摘自《財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