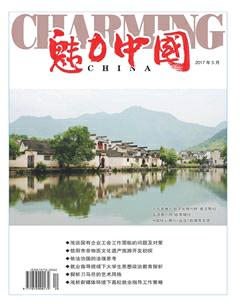社會轉型期城市居民信任的差序格局
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化嚴重。進而使得個體對不同對象的信任程度出現差異。再加上近幾年,社會矛盾和問題的突出,社會公信度的下降,導致中國的信任危機越發嚴重。本文依據上海的調查數據,從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方面來比較不同類型信任是否存在強弱差異,描繪出轉型期中國的信任的差序格局。研究結果顯示:居民的信任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和對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級差異,且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對制度的信任。
關鍵詞:社會變遷;人際信任;制度信任;差序格局
一、 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分工的細化以及社會流動的增加,原有的社會格局被打破,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環境的變化使得個體對不同的對象賦予不同程度的信任[1]。信任與社會結構、制度的變遷轉型存在著明確的互動關聯,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會結構和制度之中的一種功能化的社會機制[2]。因此,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正面臨著沖擊和挑戰。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原來單純的人際關系被改變,使人際間的信任趨于弱化,造成人際信任關系的解體。尤其近幾年,社會的公信度下降,甚至在以血緣為紐帶的特殊信任中也出現了危機,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殺熟”現象。目前,失信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問題。因此,研究中國的信任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費孝通提出,中國的人際關系呈現以個體為核心、由強至弱的 “差序格局”。他強調,人際交往在中國是 “攀關系、講交情”的。每個人的人際關系圈具有獨特性,以己為中心,按照交情深淺,由近至遠呈現強弱差異。由親疏遠近而形成的人際關系的 “差序格局”包括了另一層含義:這種按照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并確定圈內人員情況的關系格局實際上離不開個體對他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個體對他人越了解、越熟悉,彼此關系越緊密。
對于信任的劃分標準大致分為兩類:一是被分為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盧曼認為前者是產生于自然人之間的情感關系紐帶,常發生于首要群體和次要群體中,后者發生于抽象的關系中,依賴于制度環境(如法律、政治、經濟等相關制度)[3]。傳統社會中,信任通常靠兩人關系取得。但隨著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人們將逐漸依靠合約和公平的制度而形成信任。
第二類主要把人際信任分為兩種子類信任:一是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指個體對自己群內的或和自己有親密互動的他者所持有的積極性預期,后者常指個體對那些自己并不熟悉、群外的或者與自己不直接互動的他者所持有的積極性預期[4]。二是認知信任和情感信任[5]。前者是建立在知識和個體經歷基礎上的認知能力是其發生的主要依據。而個體和他者的情感關系主要影響了后者的發生。依據人際關系的類型,在首要群體關系(比如家庭)中的信任以情感信任為主,而次屬群體關系中(如同事)的信任則以認知信任為主。據此,本文以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這一劃分標準出發來研究中國的信任的差序格局。
二、 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在西方對信任的相關研究中,關注的問題集中在中國人“信任誰”和“何種信任”方面。普遍認為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的社會。韋伯認為,中國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緣共同體基礎上的,是建立在家族親戚或準親戚關系上的特殊信任。中國人彼此之間存在著普遍的不信任[6]。懷特利在研究華人企業中的信任行為時發現:在中國社會中,人們主要采用以交往經驗為基礎的,以及以個人特性為基礎的信任建構方式,很少采用以制度為基礎的方式。即人們主要根據他人由個人的誠信所積累的聲譽和他人與自己有無共同的既定關系來發展信任,而較少用制度化的手段[7]。福山認為信任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華人本身強烈地傾向于只信任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親屬以外的人”,他認為中國的一切社會組織都是建立在以血緣關系維系的家族基礎之上,因而對家族之外的其他人缺乏信任,這樣的社會是一種低信任度的社會[8]。
國內對于信任的研究多是在社會關系類型的視角下,探討信任結構以及本土模式。作為對西方這種特殊主義論的回應,梁漱溟指出,中國是一種倫理本位的社會,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有一種社會傾向性,這一點不同于西方社會的個人傾向性[9]。費孝通發現與西方社會關系呈現“團體格局”不同的是,中國人社會關系呈現“差序格局”的形態[10]。這些對信任的社會基礎的研究說明,中國與西方的文化特質、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等存在復雜的差異,因此二者的社會信任結構也是迥異的,信任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也存在差別。李偉民、梁玉成等提出,中國人的信任是一種基于具體交往對象的特殊信任。中國人不僅信任與自己具有血緣家族關系的人,而且也信任與自己具有親近密切交往關系的個人,中國人的信任中包含有以觀念信仰為基礎建立起的普遍信任[11]。
以差序格局為理論支持,有學者提出了信任的同心圈理論,即每個人以自己為中心,按自己與他人的信任關系的強弱程度劃出一個個圈子,圈子里的人被稱為自己人,圈子外的人則是外人,對自己人遠比對外人信任,對圈內人比對圈外人信任但圈子的范圍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有彈性。楊宜音等提出了關于自家人與外人相互轉化的關系信任的觀點,即圈內外的人會隨著交往的發展而互相轉化,隨著交往的深入,有些人可能被納入圈子而有些人則可能被剔除出去。
基于以上文獻綜述,發現當前關于中國人的信任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對于不同類型信任的強弱差異比較的研究比較少,僅有的也是通過對信任等級作百分比或者直接賦分合并求均值得出。從統計方法上,直接比較此類數據的做法有欠妥當,并無成熟的量表可資借鑒。據此,本文依據上海的調查數據,借鑒上述信任的分類標準,采取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作為劃分信任的主要變量。從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方面來比較不同類型信任是否存在強弱差異,描繪出轉型期中國的信任的差序格局。
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居民的人際信任仍按照“差序格局”由近而遠地減弱。在越是親近的小圈子里,日常交往的頻率較高,信任程度也較高。而隨著范圍的擴大,交往次數減少了,信任程度也大大降低。具有親疏遠近特征的關系包含不同數量和質量的信息,這種人際關系所承載的信息量的差異使得個體的信任出現強弱差異:個體與家人、鄰居、陌生人等自然人的關系親疏不同,意味著個體對與他們相關的信息的熟悉程度不同,個體對這些不同對象的信任也因而會有程度差異[12]。即個體的人際信任存在差序格局。因此,假設1: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存在強弱差異
與人際信任相對的是制度信任。在傳統社會,以個人、家庭或地緣等構建的社會團體,是分配社會資源的基本單位。在現代社會,由于科層組織的興起與擴散提供了另外一種資源分配方式,許多社會活動超出傳統人際架構的范圍。這種建立在 “非人際”關系上的社會現象,引致一種不以自然人為對象的信任逐漸成為現代社會運作的重要機制[13]。這種以組織及其代表為對象的信任被稱作 “制度信任”。個體之所以對制度產生信任,在于相信這些制度的承諾能夠實現[14]。而信任程度的差異,在于個體對制度承諾的相關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對這些承諾實現程度的判斷。因此,假設2:個體對制度的信任存在強弱差異
三、 數據與變量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源于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2011年在上海市進行的“上海市居民法律意識與行為”的調查。該調查采取多段隨機抽樣,共獲得有效問卷2240份。樣本的性別比、年齡段比與總體基本吻合。
(二)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是研究受訪者對社會的整體信任。在問卷中對應的問題是:“您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整體信任狀況是?”選項分為:大多數人是不可信任的、大多數人是可信任的、說不清。
(二)核心自變量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核心自變量主要有:
1、.自然人的信任。主要通過對問卷中十類群體的信任程度進行判斷(親密朋友、一般朋友、家人、直系親屬、其他親屬、鄰居、單位同事、單位領導、一般熟人、陌生人)。問卷中的問題為:“您對于下面這些群體的信任程度怎么樣?”信任狀況為五級定序變量。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說不清。我們將選項順序做了反方向調整,排除了“說不清”。比較信任差異時,把分析單位由通常的“受訪對象”轉換成“受訪對象—信任題項”。
2、.對制度的信任。選取包括對政府、法官、媒體、警察、居委干部這5類來測量對制度的信任。采用定序測量。問卷中的問題為:“您對于下面這些機構的信任程度怎么樣?”。選項為完全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說不清。我們將選項順序做了反方向調整,排除了“說不清”。比較信任差異時,把分析單位由通常的“受訪對象”轉換成“受訪對象—信任題項”。
(三)控制變量
1、.性別。將男性賦值為1,女性賦值為0
2、.年齡。將年齡出生年份轉為具體歲數,為一個定距變量。
3、.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專=3,大專=4,本科=5,研究生=6。設定為定序變量
4、.戶籍。本市戶口賦值為0,外來戶口賦值為1.
5、.政治面貌。黨員、共青團員賦值為1,其他的民主黨派人士、群眾統一賦值為0.
6、.單位。把受訪單位分為兩大類,黨政機關、國營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為國有單位,賦值為1。把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自雇經營和合伙經營為市場單位,賦值為0。
7、.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賦值為1,無宗教信仰賦值為0。
四、 數據分析
首先進行因子分析,然后將核心自變量加入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多變量分析。
本文通過將信任群體類型進行因子分析,由表2來呈現,列舉了對不同群體信任的得分。我們運用主成分法進行因子分析,其kmo值為0.755,達到顯著,因此可以進行因子分析。根據特征值和碎石圖,采用最大方差旋轉,最后降為四個公共因子。
表2:對不同群體信任的得分
家人間信任 朋友間信任 熟人間信任 社會信任
均值 5.36e-10 1.02e-09 -3.27e-10 1.79e-09
標準差 0.9851 0.9246 0.9943 0.8373
為了更準確地驗證本文的假設,建立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多變量分析。模型1是納入對自然人的信任自變量及其他控制變量。模型2是加入制度的信任自變量和控制變量。
表3:多元回歸分析模型
模型一 模型二
變量 自然人信任 制度信任
性別a -0.382* -0.152
(0.170) (0.192)
教育 0.186 0.217*
(0.0956) (0.106)
年齡 -0.00921 -0.00989
(0.00734) (0.00831)
戶籍b -0.633** -0.940***
(0.228) (0.254)
政治面貌 0.360 0.662*
(0.278) (0.327)
單位 -0.187 -0.243
(0.186) (0.214)
宗教信仰 0.646** 0.477
自然人信任c (0.215) (0.248)
對家人的信任 0.678***
(0.0784)
對朋友的信任 0.472***
(0.0730)
對熟人的信任 0.0891***
(0.0907)
制度信任d
對警察的信任
0.832***
(0.244)
對政府的信任 0.774***
(0.379)
對法官的信任 0.562***
(0.245)
對居委干部的信任 0.245***
(0.204)
常數 2.420*** 1.099
(0.542) (0.702)
R2 0.2124 0.1992
n 1,811 1,514
注:①括號前為原始系數,括號內為標準誤差。②*** p<.001;** p<.01; * p<.05(雙尾檢驗)③a.以“女性”為參照;b.以“農村戶口”為參照;c.以“社會信任”為參照;d.以“對媒體的信任”為參照.
從模型一來看: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自然人的信任均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且存在強弱差異,順序由強至弱為:家人、朋友、熟人、社會上陌生人。驗證了假設1.
從模型二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各項制度代表的信任均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即各項制度代表的信任也存在差序格局,存在強弱順序:警察、政府、法官、居委干部、媒體。這說明,在各項制度信任中,個體對媒體的信任最弱。其他各類制度信任相互差別雖然不大但仍都存在強弱差異。驗證了假設2。
從總體上來看,研究中的模型均通過檢定,模型sig均為0.000,說明本模型有效性較好。在模型中加入自然人信任、制度信任因素之后,模型的解釋力度有較明顯地上升。Pseudo R2 分別為0.1992、0.2124、0.2891,上升了0.0767。
五、 結論與討論
綜述可知,居民的信任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和對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級差異,且個體對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對制度的信任。
首先,自然人信任差序格局不僅存在,而且對家人的信任與對其他自然人的信任在程度上存在差異。這與前面學者的研究一致。我們所提取的四個因子,親屬間信任、朋友間信任、熟人間信任和社會信任,隨著關系強度的變化,表現出強弱高低的差序結構。即不同關系的交往對象之間存在著差序性的信任。這說明,個體與家人以外自然人的關系比較淡薄。隨著現代社會個體的人際關系網覆蓋越來越多家人以外的自然人,人際關系可能出現越來越明顯的矛盾和張力。
其次,信任的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各類制度的信任中。從分析結果來看,對警察的信任程度最高,對新聞媒體的信任最低。基于制度在當代社會運作具有重要的位置,并且會影響個人的福祉,而制度本身的工具性本質很容易成為個人操控其他人的工具。在民眾心中,形象不同,信任程度也不同,部分原因是與政府的表現和對制度相關信息的了解程度有關。為需要者提供公關服務的組織或政府會獲得民眾較高的信任。政府組織在大眾心中的信任程度更在政治和社會變遷上被視為有指標性的意義。總之,從各類制度的信任的差序結構的視角切入,可以解釋為什么非政府組織比政府組織獲得民眾較高的信任,非營利組織比營利組織獲得民眾較高的信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費孝通所指的差序格局,不僅是關系和結構上的差序,更是基于道德倫理上的情感意義上的差序。在現實交往中實際存在的情感決定著人們的信任狀況。情感是可以通過各種方式來營造和改變的。“做人情”的各種公關手段是中國人最擅長的事情[15]。總之,在中國處于迅速變遷中的城市社會,它的流動性決定了人際關系的不穩定性。人民的信任及影響因素也日趨復雜。這導致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信任狀態也不斷地變化,出現信任結構的動態的一面。因此,差序格局的信任結構隨著變化而適時調整。閻云翔也指出,情感也是影響人們態度和行動的重要因素,它并不能被利益計算所完全遮蔽[16]。
參考文獻:
[1]C.L.Scot I II, “Interpersonal Trust:A Comparison of Atitudi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Human Relations,vol.33,no.11,1980,pp.805-812.
[2]Luhmann, N . 1979,Trustand Power, Chichester : John Wiley & SonsLtd .
[3]N. Luhmann, Trust and Power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9.
[4]E.M.Uslaner and R.S.Conley, 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 "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31, no.4, 2003, pp.331-360.
[5]J.Lewis and A.Weigert, Trust as a Social Reality, "Social Forces, vol.63, no.4, 1985,pp.967-985.
[6]馬克思·韋伯.王容芬譯.儒教與道教 [M].商務印書館,1995 .
[7]Whitley,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usiness Systems in East Asia”, Organization Studies, 12(1).
[8]弗朗西斯·福山.彭志華譯.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M].海南出版社,2001 .
[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0—73
[10]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27.
[11]李偉民,梁玉成.特殊信任與普遍信任:中國人信任的結構與特征[J].社會學研究,
[12]A.Portes and J.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vol.98, no.6, 1993,pp.1320-1350.
[13]張苙蕓,譚康榮:《制度信任的趨勢與結構:“多重等級評量”的分析策略》,《臺灣社會學刊》2005年第35期.
[14]B.Barber,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 1983.
[15]黃光國 ,胡先縉. 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游戲[J]. 領導文萃,2005,07:162-166.
[16]徐業鑫.禮物與情感—讀《禮物的流動》及其他[J]. 新西部(理論版),2016,23:12+15.
作者簡介:
宋小尊(1992—),女,河南鄭州人,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警事社會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