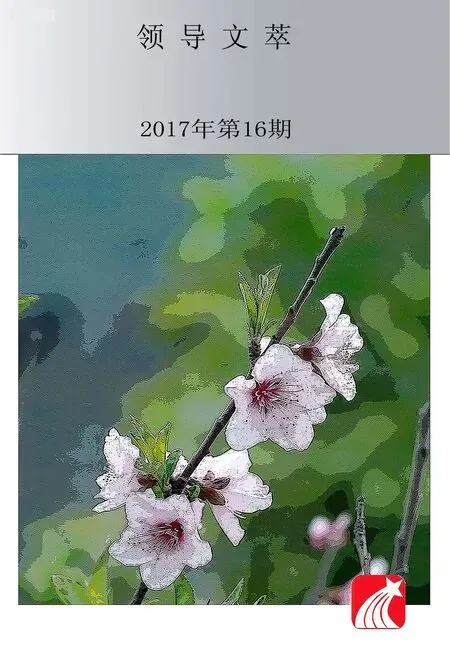宋之問(wèn)們的惡
高自發(fā)
大唐王朝是詩(shī)歌鼎盛期,群星璀璨,詩(shī)人“泛濫”,宋之問(wèn)似乎也就是一枚被群星湮滅的小星星。不過(guò),能和沈佺期并稱為“沈宋”,也不是浪得虛名,其詩(shī)自有他獨(dú)到之處。例如那首《渡漢江》:“嶺外音書(shū)絕,經(jīng)冬復(fù)歷春。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wèn)來(lái)人。”把游子歸家忐忑不安的心情寫得真是惟妙惟肖。
孰料,就是如此精于刻畫(huà)游子歸鄉(xiāng)的詩(shī)人,竟是個(gè)劣跡斑斑的人!宋之問(wèn)的外甥劉希夷曾寫過(guò)一首《代白頭翁》,詩(shī)中有兩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之問(wèn)特別喜歡——詩(shī)人自然都喜歡好句子,他們有人追求佳句甚至達(dá)到“吟安一個(gè)字,拈斷數(shù)莖須”的境界。宋之問(wèn)卻不是拈斷胡須、搜腸刮肚想好句子,而是直接討要。仗著老娘舅的身份,欲占有劉希夷這首詩(shī)。劉希夷起初答應(yīng),后又反悔,惱羞成怒的宋之問(wèn)令家奴用土袋將劉希夷活活壓死。此事史稱“因詩(shī)殺人”,北宋王讜所著《唐語(yǔ)林》有記載。
自從知道了宋之問(wèn)的惡(先不管真假),再讀《渡漢江》,便有了一種怪怪的感覺(jué)。“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wèn)來(lái)人”,體現(xiàn)的可是滿滿的善良!游子客居在外,家書(shū)斷絕,年復(fù)一年,自然思鄉(xiāng)情切,今欲近家門,由“切”轉(zhuǎn)“怯”,何哉?自然無(wú)外乎“怯”爹娘身體有恙,“怯”家庭有變故,越是“怯”急,越不敢問(wèn),只想快些進(jìn)家門。不是孝順父母、疼愛(ài)兒女、友愛(ài)他人的人,如何有如此細(xì)膩情感?換句話說(shuō),不是良善之輩,如何寫得如此好詩(shī)?然而做出如此有情有義之詩(shī)的人,卻因一句好詩(shī)殺死了自己的外甥,是歷史失實(shí),還是后人編造,抑或人心本就難測(cè)?
中國(guó)人向來(lái)推許“文如其人”。很多名家偉人著作等身,為人為文,都令人敬佩。但是也不乏“文不如其人”者,如宋之問(wèn)類。 小時(shí)候看電影,每當(dāng)人物一出場(chǎng),我們總喜歡問(wèn)大人:“好人壞人?”早些年的中國(guó)電影刻畫(huà)人物太呆板:壞人一律賊眉鼠眼,猥瑣不堪;好人一律英俊瀟灑,光明磊落。總而言之,善與惡寫在臉上,好人壞人一眼就能看出來(lái),這是特定時(shí)期的電影制作者的惡趣味。等到電影開(kāi)始往深了挖掘人性,好人也有壞脾氣,甚至也有一些無(wú)傷大雅的臭毛病,壞人竟然也有優(yōu)點(diǎn),諸如小賊竟然也孝順爹媽幫助過(guò)鄰里,讓我們大吃一驚,原來(lái)這才是實(shí)實(shí)在在的人!只是,每逢劇中人物一登場(chǎng)亮相,積久的習(xí)慣仍讓我們即使不在嘴上也會(huì)在心里問(wèn)一句:“好人壞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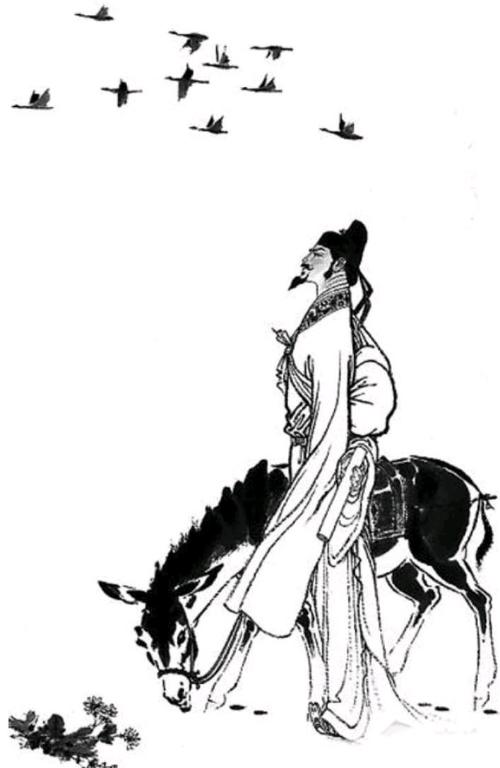
分不清善惡我們糾結(jié),分出了善惡我們還糾結(jié):好人做過(guò)的那些錯(cuò)事我們?cè)撛趺磳?duì)待?壞人曾經(jīng)有過(guò)的貢獻(xiàn)又該如何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不是黑白的,而是多彩的!愁腸百結(jié)之余還是想起了魯迅先生的“拿來(lái)主義”。你的詩(shī)文寫得好,那就毫不客氣地拿來(lái),誦讀涵詠,大快朵頤吸取詩(shī)文中的養(yǎng)料,絕不會(huì)因?yàn)樵?shī)人有過(guò)什么不端,就以為讀他的詩(shī)文是一種罪惡,索性不讀他的詩(shī);當(dāng)然,因?yàn)樵?shī)文美質(zhì)可口,就無(wú)原則地寬容作者,哪怕他是個(gè)殺人犯,就是昏蛋孱頭。文是文,人是人,必須一分為二地對(duì)待。
看電影《末日危途》,兒子問(wèn)爸爸:“我們是好人嗎?我們會(huì)一直做好人嗎?”在世界末日,他們父子二人到處流亡,占有了別人地窖里的生活用品,還殺死了想要他們性命的人……兒子迷茫了,但是他發(fā)自內(nèi)心的一問(wèn),卻給了我們解答:其實(shí)堅(jiān)持做個(gè)好人,才是最重要的!
(摘自《雜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