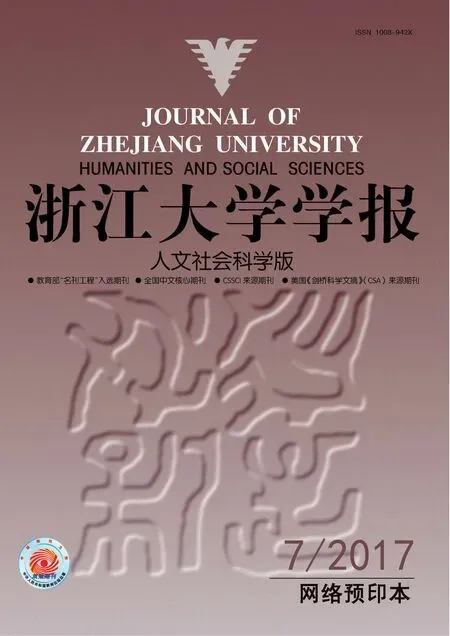觀念競合與國際體系的變遷
儲昭根
(浙江大學 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觀念競合與國際體系的變遷
儲昭根
(浙江大學 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觀念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在過去的四百多年里,國家主義和保守主義分別主導、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及維也納體系,而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雖然塑造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但主導該時期的卻是激進主義。直到雅爾塔體系時期,民族主義才終于打敗了帝國主義,自由主義則成功戰勝了極權主義。因此,國際體系確立的背后是觀念分配競合的結果,是主流觀念取向在競合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過程。觀念作為深層次因素,始終是影響、塑造國際體系的更新與變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觀念; 競合主義; 國際體系;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一、 引 言
正是“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1]12,哈耶克(F.A.von Hayek)如是說。觀念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信仰、習俗以及政治態度,它是根植于人們心中深層的精神的東西,在人們看待自己、他人以及世界其他事物的過程中給予了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思想觀念的力量在今天的世界中日益不容忽視,其在近代人類歷史的作用決不亞于科學技術的力量。”[2]18
通常認為,國際權力、國際政治之爭的核心就是國際秩序之爭。從表面上看,國際秩序是某一時段各個主要行為體間基于實力競合而形成,進而造就的一種國際格局。而更為深層次的,國際體系內的觀念分配才是決定國際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穩定的關鍵性變量[3]134。因此,國際體系確立的背后是觀念分配競合的結果,是主流觀念及價值取向在單元及系統層面“雙層競合”[4]76-93的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結果。
從單元層面看,外交決策者的觀念制約著國家對外政策的制訂。國家最高決策者的觀念不僅與其本人的價值觀息息相關,也同樣折射出特定國家的傳統、道德觀念、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國家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基本價值或政治觀念都必然受到國內政治及特定觀念氛圍的影響;另一方面,領導人之所以能被民眾所廣泛接受和認可,前提是他的言行能符合國家精神、體現本民族共同價值觀以及代表國家利益。“從決策過程來看,重要的是個人或群體如何認識環境,而不是環境到底是什么。”[5]9外界信息通常經由決策者的觀念和動機所構成的“透鏡”,經過有選擇地過濾和吸收后才有意義。
1993年,由朱迪斯·戈爾茨坦(Judith Goldstein)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主編的《觀念與外交政策》更是將觀念作為與物質性變量并列的因素,用以解釋國家的沖突與合作行為[6]11。他們從個體主義的視角出發,探討了觀念影響外交政策的內在機制,并將觀念分為三種形態:世界觀、原則化信念和因果信念[7]8。正是觀念的差異,影響了國家間的有效溝通,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偏見、誤會及錯誤認識。以羅伯特·杰維斯(Robert Jervis)為主要代表人物的國際政治認知學派進一步指出,國家決策者的錯誤知覺可以加劇國家之間的沖突,甚至導致國家之間的戰爭[8]。約瑟夫·奈(Joseph S.Nye)則把觀念、文化、價值觀和政策,以及在太多情況下被忽略的吸引力,即通過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結果的能力稱為軟權力。“如果一個國家代表著其他國家所期望信奉的價值觀念,則其領導潮流的成本就會降低。”[9]193,6
從系統層面,作為后起之秀的建構主義則認為觀念結構對國際關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建構主義堅持觀念本體論,強調觀念的重要意義,以及規范、價值對國家行為的塑造作用。建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觀念是無所不在的”,或者說幾乎是無所不在的[10]23。社會共有觀念建構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并使這種結構具有動力,國際體系是“觀念分配”的結果。觀念最重要、根本的作用是建構具有解釋能力的權力和利益。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及效用取決于由國家間的互動而產生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這三種無政府文化,哪一種占主導地位,這三種國際體系文化都是由自我和他者主體間的實踐活動形成的不同社會共有的觀念結構所分別建構的,且遞次進化,其分別對應為敵人、競爭對手和朋友這三種國家角色(身份)。簡言之,是朋友,還是對手或敵人,這一過程就是觀念分配及身份競合的結果。
除了建構主義,英國學派也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結構是觀念,而非物質。這從英國學派對其核心概念“國際社會”(或國家的體系)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最早提出“國際社會”概念的曼寧(Charles Manning)認為,國際社會不是一種經驗的存在物,而是一種觀念的實體[11]。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的“國際社會”是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他認為:“如果一群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從而組成一個社會,也就是說,這些國家認為它們之間的關系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制約,而且它們一起構建共同制度,那么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了。”[12]10-11也就是說,共同利益觀念,對共同價值、規則的認同以及行之有效的國際制度構成了國際社會的核心。規則、認同與制度本身是觀念性的形態,構成了英國學派明顯的理念主義特色的本體論[13]。
因此,從總體上看,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和國際政治的認知心理學派均認為國際政治結構根本上是一種觀念結構,也都承認觀念因素如理念、規范、價值、認同和文化在國際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而隨著建構主義的興起并成為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國際文化或曰共有觀念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觀念結構也就成為國際體系內部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14]4。但對于觀念建構國際體系的過程,無論是建構主義還是國際政治認知學派均語焉未詳,“建構主義者總體上主要關注觀念的作用,并未試圖描繪國際體系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的‘畫像’”[15]。
瑪莎·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在《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變化》一書中試圖用實證的方法來彌補建構主義的這種缺陷。作者通過武力索債、人道主義干涉、干涉與國際秩序三個案例,論證了過去四個世紀不同時期軍事干涉的變化是國際社會觀念演變的直接結果,以及國際社會共享的觀念如何塑造了武力的使用[16],但仍未完成觀念如何塑造并推動國際體系變遷這一研究任務。
為此,本文試圖從觀念或思想史的角度,探討觀念分配的競合如何影響、塑造國際體系的更新與變遷。自1648年現代國際關系開始以來,曾先后出現過四個國際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與此對應并占據主導地位的觀念是國家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以及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將此劃分為四個時期:國家主義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保守主義主導的維也納體系時期、激進主義主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交相輝映的雅爾塔體系時期。應該看到,任何一種體系的建立必然伴隨著一種主導性觀念(規范)的確立,但主導性觀念的產生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個周期,即興起、擴散/普及、內化[17],并最終確立其主導地位的競合過程。不過,主導性觀念一旦確立,便成為“集體持有的行為觀念”與“社會結構”,即國際規范[18],進而制約行為、建構身份、塑造利益,導致國際體系的變化。芬尼莫爾和斯金克(Kathryn Sikkink)特別強調:“觀念性國際體系結構中,觀念的變化和規范的變更是國際體系變革的主要動力。”[19]303正因如此,觀念分配的競合過程對這四大國際體系變遷的塑造及沖擊,可以說完全不亞于實力或權力對國際體系的作用及影響。
二、 國家主義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
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天主教教會的大一統神權觀念被打破,主導性觀念實現了從教權至上到國家主權至上,以國家主義代替神本主義的轉變。在這一時期逐步占據統治地位的觀念并不是以自由主義為特征的個人主義、科學主義或自然主義,甚至民族主義,而是國家主義,即一種強調國家利益至上、建設強大國家的意識與觀念[20]46。這種主導性觀念的轉變是通過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而最終確立的。
率先打破神本主義禁錮的是14世紀在意大利各城市興起,隨后擴展到西歐各國,并于16世紀在歐洲盛行的史稱“文藝復興”的運動。這是一場崇尚理性、關注世俗生活、要求把人從宗教和神權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并直接反映西歐各國正在形成中的資產階級要求的思想文化運動。
但丁在其名著《論世界帝國》(DeMonarchia)中指出,實現人的塵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但沒有國家統一作為保障,和平是不可設想的;而要實現國家統一,權力就必須集中到君主手里。這樣,他從人的塵世幸福這一人文主義的理想出發,首次明確地提出了國家必須統一、王權必須強化這一時代的重大命題。而尼科洛·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則首次摒棄了傳統的宗教道德觀,從“人性惡”的基點出發,提出了一套功利主義的國家理論,被譽為近代西方國家主義理論的創始人。他推崇共和政體,但又認為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只能依靠君主制來對抗羅馬教會和封建割據勢力。他主張以國家利益作為政治行為的唯一準則,為此,君主可以不擇手段;外交需要依靠實力,則無須用道義和諾言來約束自己。讓·博丹(Jean Bodin)是國家主權理論的創始人,他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主權概念,并在其代表作《共和國》中對國家主權下了一個定義:主權是“國家中最高的、絕對的、永遠位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權力”。繼而,他第一次用明確的語言表達“國家權力世俗化”,“擁有主權的人除了不朽的上帝之外,是無需向任何人負責的”[21]562。此外,他還首次對主權包含的立法、決定外交政策、任命官吏、要求國民效忠、行使最高司法裁判、赦免罪犯、鑄幣、規定度量衡和征稅等九大標志或權限,及其所具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轉讓、不受時效限制等特征,做了全面系統的論述,由此奠定了全部現代國家學說的理論基礎[22]547-548。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確立了國家主權“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原則,首次將國際關系作為政治學的思考對象。他通過區分古羅馬以個人和契約為基礎的萬民法和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法,使國際關系超越了習俗和慣例,具有了共同的準則,并首次提出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的主體,從而奠定了國際法的基礎。他的國際法理論對“三十年戰爭”所創立的以會議解決爭端的先例和第一個國際關系體系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國家主義意識思潮的興起更加速了民族君主國的出現。
文藝復興運動之后,宗教改革進一步促使歐洲沖破了中世紀的巨大束縛。而宗教改革的結果直接導致了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在戰爭中,新教—民族—主權國家和天主教—傳統皇帝之間的沖突本身就已經代表了兩種價值取向的斗爭,法國參戰并選擇皇帝對立面的立場,正是對傳統宗教認同觀念的致命打擊[23]92-93。而在新教一方,另一個最重要的國家瑞典,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卻為了反對德國皇帝和天主教而與紅衣主教黎塞留所領導的天主教大國法國結盟,這不由令人感到奇怪與費解:他們在國內以利劍對付異教徒,而在對外政策中卻不顧他們在國內所奉行的教派原則。黎塞留對其宗教信仰與政治行為的矛盾性是這樣解釋的:“人可不朽,救贖可待來日。國家不得永生,救贖唯有現下,否則萬劫不復。”這實際就是強調了國家至上的觀念。這一觀念在那個中世紀道德觀與宗教評判盛行的時代無疑是一首創,無怪乎基辛格將他稱為“現代國家制度之父”[24]47。“三十年戰爭”后,歐洲實現了從封建體制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轉變,破除了中世紀以來歐洲所形成的羅馬教皇神權政體下的世界主權論、教權至上論,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國家主義是這一復雜競合過程的最終贏家。
文藝復興運動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在歐洲開花結果。古典文明的復活為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的普及奠定了基礎。其中,人文主義精神影響了宗教改革,探索世界的精神成為近代科學革命的先導,對理性的注重則帶動了第二次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啟蒙運動的發展。
啟蒙思想家們從理性主義出發,以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啟示,以人的自然權利對抗封建主義的王權、神權和特權,反對蒙昧主義、專制主義和宗教迷信,呼吁建立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新制度,因而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為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歐洲和美洲的其他革命和改革做了充分的輿論及理論上的準備。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天賦人權和自然權利學說,在國家起源問題上,他們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和人民主權學說;在國家政體問題上,他們主張實行憲政民主,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并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系統地提出了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為未來的理想社會確立了一套成熟的政治藍圖。啟蒙運動激發了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參與意識。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及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均是啟蒙運動思想成果的結晶,實現了啟蒙基本理念的具體化與法律化。18世紀上半期,啟蒙思想在北美殖民地廣泛傳播,北美各地民主和民族意識日趨增強,進而導致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在法國大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以啟蒙思想為旗幟,推動了革命的深入。法國大革命確立了現代的革命概念,特別是“人民主權”的思想,在雅各賓派統治時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同時,由革命孕育出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治理念又被拿破侖的軍隊鐵蹄傳遍了整個歐洲,這些理念主導著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政治圖景[25]529。
三、 保守主義主導的維也納體系時期
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促進了自由主義在歐洲及北美的發展,影響和推動了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但隨著拿破侖在戰爭中失敗,大革命釋放出來的兩大顛覆性的力量——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受到了壓制。
拿破侖戰爭是當時歐洲新誕生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傳統的封建主義制度之間的斗爭,戰爭以前者的失敗而告終,歐洲舊專制體制得以復辟,保守主義一度甚囂塵上,整個歐洲的保守主義政府致力于在全歐維持舊秩序。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以法國大革命前的世界政治觀念為基礎,充當了維也納和會的設計師。而法國外長塔列朗靈活地提出了“正統主義”原則,滿足了各國封建主的“歐洲均勢”,代表了恢復歐洲舊制度的共同愿望,成為會議的旗幟。1815年6月9日,英、俄、奧、普、葡、法、瑞典七國簽署了《維也納會議最后議定書》,其內容主要有兩項:一是俄、英、普、奧四大國主宰的歐洲領土體系,二是歐洲封建“正統王朝”的政治統治體系。該議定書確立了均勢原則、正統主義和補償原則,并隨后在歐洲建立起一個遏制資本主義發展與革命、重建歐洲專制主義的維也納體系。因此,維也納體系是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經過激烈的競合,最終由保守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的體系。
維也納體系建立后,均勢和維持歐洲現狀是歐洲大國對外政策的主導思想,但列強在處理利益沖突的途徑、方式和手段上存在差異。大體上說,“把以俄國為代表的外交路線稱為‘保守主義’,把以英國為代表的外交路線稱為‘自由主義’”[26]87-91。保守主義體現為俄國、奧地利及普魯士三國以“基督教的信條”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君主聯盟——“神圣同盟”,強調維護君主政權的合法性及歐洲封建專制制度的正統性,正統秩序一旦被破壞,同盟國家就應像基督教民族大家庭成員那樣彼此幫助和相互支持,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與此相反,英國的島國特性、與“神圣同盟”各國迥異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以及工商實業方面利益的追求,使它在是否干涉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問題上往往與這三個保守君主國在立場、取向和實踐上存在不同,甚至產生嚴重的分歧。當然,在維持歐洲均勢和政治局勢穩定方面,英國又常常與三國有著類似的立場。同樣,盡管法國在維也納會議后恢復了波旁王朝的君主統治,但經過大革命的洗禮,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對封建勢力的勝利,建立了代議制機構,法國已無法倒退到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狀態中去了。法國在外交政策方面,與英國一起反對“神圣同盟”的集體干涉原則[24]113-114。因此,英國和法國遵從自由主義原則,它們反對“神圣同盟”對歐洲事務奉行的集體干涉的原則,不同意動輒派軍隊鎮壓歐洲的革命運動。在對待歐洲民族問題上,自由主義的態度與保守主義有很大的不同。這兩種主義在維也納體系內同時存在并起作用,它們之間的對立和原則分歧正是兩種觀念、兩種主義之間的競合。
不過,進入19世紀之后,封建主義的日趨沒落和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已是大勢所趨,并不是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兩個原則所能阻止的。盡管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啟蒙主義思想及其工業主義、大眾參與等觀念還是逐漸成為這一世紀的主導思想[27]173。新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因法國的革命劇變而誕生的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已經獲得了巨大的力量,不再被保守主義所限制。于是,在19世紀20-30年代引發了一系列起義和革命,周期性地震撼著歐洲,并形成1848年遍及全歐的革命運動[25]559-560。同時,啟蒙思想家的自然權利卻被演化成對利益的無限追求,尤其是在國際關系上,隨著歐美各國海外殖民擴張日益狂熱,國際關系中所奉行的原則也不再是正統主義,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23]93。
觀念的發展也與時代的主題遙相呼應。在19世紀轉折之時,從西方關于社會變化的討論中分裂、產生出了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世俗思想體系或意識形態。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視為是啟蒙主義流派的繼續;保守主義則是對啟蒙主義的一種反動。理論上,雖然三大意識形態共有一些假定,但在整體上,它們之間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天生就致力于消滅那些被保守主義視為社會靈魂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激進主義既攻擊舊制度的擁護者,也批判自我調適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以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對立面來定義自己的性質[27]167-168。但在政治實踐上,這些相互競爭的觀念之間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也從來沒有完全分開。尤其是在19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人們常常很難分辨激進主義在哪里結束,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又從哪里開始[27]154。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三大意識形態的追隨者們常常結成暫時性的同盟,共同利益可能促使其中的兩種意識形態結成同盟以反對第三種。總之,三種觀念之間相互競爭、相互滲透。
但是,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就像一顆炸彈震動了學術界,引發了一場激烈爭論并深刻地改變了自由主義、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三大意識形態。馬克思對現代社會也發起了尖銳的批判。他認為,現代社會的非人性生產方式使人類異化。馬克思主義倡導以一種現代性觀念即社會主義,取代另一種,即資本主義。
達爾文的觀念得到了其他理論家的進一步闡釋。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物種進化觀點實際發表在達爾文之前。不過受達爾文影響,他將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即適者生存)觀念應用于經濟社會,也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將達爾文主義當作一種歷史和政治學的新的普遍哲學。海克爾認為,人類的歷史必須根據人的生物本性來重新考察,它將表明,人類社會是由競爭法則所控制的,民族是必須為生存而斗爭的生命體。他把達爾文進化論引入德國,同時加以完善并進行了最熱情的歡迎和宣傳。兩年后,普魯士國王授予達爾文藍馬克斯勛章。達爾文主義為導致一戰的軍國主義提供了依據,甚至為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上的正當性。
四、 激進主義主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時期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形成、發展中,各種觀念間的競合出現了空前復雜的社會圖景。殖民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結合,便成了帝國主義;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便成了軍國主義;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則產生了燦爛一時的威爾遜式理想主義,并塑造、建構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不過,隨著激進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競合加劇,理想主義終歸失敗,民族主義進而與帝國主義結合,又產生了更瘋狂的法西斯主義。總體來看,這一時期被激進主義所主導。
激進主義最初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約瑟夫·奈認為:“民族主義的興起、對和平自滿情緒的滋長、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德國的政策等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國際體系靈活性的喪失,進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28]108挪威學者托布約爾·克努成認為,工業主義、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已經破壞了舊秩序,國家間的激烈對抗使歐洲充滿了緊張氣氛[27]206,奧地利皇儲弗蘭茨·斐迪南于1914年6月28日遭到暗殺只是打破了歐洲的政治僵局而已。
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開始逐步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此之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意識與民族主義的交織及宣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了德、法、俄等歐洲主要國家的內外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德國的泛日耳曼主義、法國的復仇主義、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及塞爾維亞人的大塞爾維亞計劃。這些形式各異的民族主義及其所掀起的種種運動,使本不平靜且充滿明爭暗斗的歐洲又增添了引發敵意與對抗的眾多危險因素。“民族主義力量在團結工人階級上比社會主義強大,在團結銀行家上比資本主義強大。在各個君主制國家之間,民族主義力量的確比家族關系還要強大。”[28]106
隨著歐洲事務的日趨緊張,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升級,歐洲各國紛紛在海外搶占殖民地,以便為本國海軍獲得港口和加煤站,甚至僅是國際聲望。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在重商主義時代表現為殖民主義;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后,壟斷代替自由競爭并占據統治地位,壟斷資本主義得以形成,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又表現為帝國主義,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導致列強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以及階級壓迫和民族奴役,加劇了全世界范圍內普通民眾的苦難,社會主義思潮作為激進的階級斗爭和階級革命理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激進主義。列寧的著名論斷是,帝國主義必然導致戰爭。
不過,從觀念競合視角看,此時的自由主義仍不能戰勝極端民族主義等所代表的激進主義,并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戰中的同盟國與協約國進行了四年的廝殺,如何結束這場戰爭也頗費腦筋。美國總統威爾遜敦促交戰各國接受“沒有勝利者的和平”。而俄國在發生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后,列寧公布了全部秘密條約,建議各國立即停戰,并締結“不割地不賠款”的和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列寧的倡議使威爾遜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動。為此,威爾遜總統于1918年1月8日在國會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威爾遜的建議包括公開地達成和平條約,以取代秘密外交,削減各國軍備,使其“能夠完成保衛國家安全之需”即可;以及民族自決,以便使“所有清晰表述出來的民族主義愿望都能夠得到最大滿足”。他還將一戰描述為一場人民戰爭,旨在反對“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它們是對自由的兩大威脅,只有通過創建民主政府才能夠消除,也只有“各民族的普遍聯合”才能夠保證“大國和小國同樣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威爾遜用理想主義代替了古典自由主義[25]697。自由貿易、民族自決和集體安全這些觀念被威爾遜包裝到國際聯盟新的制度設計中。阿莫斯·珀爾馬特認為,“在整個20世紀,民主和民族自決這兩個威爾遜的遺產主導著美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在某種程度上還在繼續”[29]134更進一步地看,蘇聯領導人列寧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自決”觀念則摧毀了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盛行的殖民主義,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雅爾塔體系及“冷戰”后國際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30]8-19。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歐洲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假定,驚人的破壞程度和將近1 000萬人的死亡完全改變了進步的觀念。戰后,革命的思想和民族自決的觀念滲入歐洲之外的世界,并在那里啟蒙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導致了中東、近東和遠東地區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運動的產生,及亞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戰后的經濟危機導致西方世界內部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當激進主義、擴張主義、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和好戰的社會主義在一戰后占據政治舞臺時,自由主義者的疏離感和孤立感大大加深了。不僅這些運動的內容,而且還有這些運動的思潮和氣質壓抑著自由主義者。”[31]397同時,俄國內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及其革命也奠定了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崛起的基礎。由于美國參議院未能批準《凡爾賽和約》并否決了威爾遜關于與英國和法國建立防御性聯盟的主張,俄國共產黨又退出世界事務轉而培育自己的社會主義體系,歐洲已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復興的德國迅速填補了美俄留下的政治真空。隨即而來的是法西斯在德國和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地方興起,進一步粉碎了自由主義的夢想和社會生活。激進主義再次成為壓倒性的社會思潮,到1939年,歐洲主要國家中只有兩個還保持著民主制度,即英國和法國。
五、 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交相輝映的雅爾塔體系時期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在威爾遜式理想主義的基礎上,但縱觀整個時期,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始終主導并貫穿其中。威爾遜總統試圖用自由主義加民族主義來阻止及解構激進主義,但終歸失敗。不過,到雅爾塔體系時期,一戰后喚醒的亞非拉民族主義終于打敗了帝國主義,且自由主義成功戰勝了極權主義。
法西斯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所代表的激進主義再次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充分顯示了現代戰爭的激烈與殘酷,因此,英法等國戰后出現了一種和平主義思潮,鼓吹不惜代價避免戰爭。而隨著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崛起,及1929年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發生,英、法等西方國家從防止德國的再起轉向綏靖德意等法西斯勢力。在綏靖不成功之后,又希望將法西斯禍水引向社會主義蘇聯。與英法的綏靖政策如出一轍,美國在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日益加劇之時,奉行了一種表面上不偏不倚的中立主義政策。所有這些均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為了打敗法西斯,美國與英國,包括戰時盟國蘇聯進行了一系列的觀念磨合與磋商。羅斯福于1941年1月6日在美國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匱乏自由和免除恐懼自由。羅斯福以非凡的勇氣與遠見,用“四大自由”鼓舞了公眾,為美國積極援助盟國和介入戰爭做了輿論上的準備。這是一份反抗法西斯、捍衛資產階級民主的決心書,同時又是一份建立美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的宣言書。他將自由和平等聯系起來,將政治自由和經濟公平聯系起來,將機會平等和收入上的保障聯系起來,將自由競爭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將個人自由和國家干涉聯系起來,從而使自由主義獲得了全新的生命。
隨著戰事的擴大,美、英迫切需要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同時,美國也擔心英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事先與其他歐洲國家就領土或戰后安排等重大問題達成秘密交易,撇開美國。為此,1941年8月9-13日,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大西洋上舉行了他們在二戰期間的首次首腦會晤,并簽署了一份戰爭目的和戰后和平目標的文件即《大西洋憲章》,并于1941年8月14日公布于世,得到了廣泛響應。憲章宣布了民族自治、領土完整、經濟國際主義、社會安全、縮減軍備以及國際合作等八個原則,并決心以此作為重建戰后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依據。不過,在推進自由貿易還是帝國特惠制,民族自決適用于全世界還是只適用于被法西斯奴役的地區,建立有效的國家組織還是創立普遍安全制度等方面,美英均存在意見沖突。《大西洋憲章》不像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那樣是美國單方面的政策宣示,而是美英共同簽署的一項聯合文件。盡管它沒有采取對雙方更具有約束力的條約形式,但它的重要意義和影響并不亞于一項條約的價值[32]。《大西洋憲章》不僅標志英、美兩國在反法西斯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也是后來《聯合國憲章》的基礎。1942年1月,蘇、美、英、中、澳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家宣言》,重申了《大西洋憲章》中的原則,促使國際反軸心國同盟的形成,在法律上為重建戰后世界奠定了原則基礎。任東來認為:“美國和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自然是盟國物質力量遠遠超過法西斯軸心國的結果,但是,盟國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和‘民族自決’這類進步觀念,以及滲透著這些觀念的《大西洋憲章》、《已解放的歐洲國家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等法律性文件,在鞏固反法西斯同盟、爭取民眾的廣泛支持方面,實在是功不可沒。”[2]18
對于戰后安排及構想,羅斯福在吸取國際聯盟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基于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和大國合作原則的戰后世界藍圖:第一,依照民族自決原則確定歐洲政治版圖,并決定殖民地的未來前途,反對英蘇劃分勢力范圍,且敦促歐洲各殖民國家在戰后實施非殖民化政策;第二,根據自由貿易原則組織國際經濟事務,建立開放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此即后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第三,在大國合作與大國一致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集體安全組織——聯合國,其中,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由五大國組成,負責國際穩定與和平。羅斯福戰后世界藍圖的三個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美國的政治抱負、經濟利益和安全關切,這個構想與威爾遜主義一脈相承,本質是自由國際主義的[33]87。為此,各大國在創建雅爾塔體系時,沒有急于求成,而是審慎、耐心地進行細致、紛繁的工作。戰時僅美國、英國、蘇聯“三巨頭”會晤就有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三次,其他級別的會晤更是頻繁。從1941年8月的《大西洋憲章》到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約》,雅爾塔體系的形成過程歷時整整10年。顯然,他們是吸取了上個體系的失敗教訓,因而表現得十分小心與謹慎。在經歷了威爾遜和國際聯盟的失敗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已不太相信單純一個國際組織的建立就能保證持久的和平。因此,羅斯福轉而尋求一種“大國警察制”,有別于國際聯盟時期“大國負責制”的集體安全。隨后,美蘇英中“四強”,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思想的提出和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確定,均反映了羅斯福的集體安全觀。
二戰結束后,固有的意識形態問題暴露出來并上升為主要矛盾。雅爾塔體系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來劃分美、蘇各自的勢力范圍,隨著美、蘇之間矛盾的加劇,美、蘇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演化成兩個陣營、兩種制度、兩種經濟之間的競爭,再演化成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意識形態與觀念的形同水火、勢不兩立成為美蘇“冷戰”與對抗的根本特征。
從歷史進程看,觀念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更為明顯。18世紀法國大革命早已成為歷史,但它提出的理想,即自由、平等和博愛,至今仍影響著世界;20世紀社會主義的理想一度改變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運,而且,至今還可以聽到它頑強的吶喊。試看今日之世界,某些獨裁國家也要追求民主的形式,甚至最可怕的恐怖主義集團也要說明自己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的目標[2]18。
民族自決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世界的影響相當明顯,且具有根本性。列寧、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分別提出民族自決思想,并用于其外交實踐,隨后民族自決成為“巴黎和會”的基本原則,并在一戰后完成了對歐洲版圖的大規模變更及重新劃分。再到1945年被寫入了《聯合國憲章》,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運動,直接導致了殖民體系的瓦解,使20世紀末殖民主義統治造成的民族問題在國際層面上基本得以消解,這一觀念影響并真實地改變了20世紀的世界版圖[30]8-19。正是通過民族自決這一理念,民族主義徹底戰勝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主義。世界范圍內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逐漸被民族國家的覺醒和進步所取代,許多國家重新獲得獨立,延續了幾個世紀的主要大國間的殖民競爭和對抗也由此落幕。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也在觀念競合中成長。文藝復興動搖了中世紀神本主義的經院哲學對人類精神的束縛,人文主義猶如一股清新的風,推動了宗教改革,亦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精神動力。伴隨著國家主義意識,人們從效忠教會轉向王權,由此誕生了近代君主國及民族主義。在文藝復興中復活的自由主義對君主專制主義進行了挑戰。隨著布丹的契約觀念得到約翰·洛克、亞當·斯密等的補充和完善,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由此奠定,人們逐漸由效忠君主轉向國家。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深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英、美、法等國家落地生花,古典自由主義在19世紀達到了巔峰。但是,代表保守、專制的勢力并不甘心落敗,在維也納體系中一度回光返照,取得了對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優勢。此后,自由主義與達爾文主義結合導致了帝國主義;德、意等國民族主義大旗反被保守主義奪去,保守主義勢力掌控了民族主義,并一度演變成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似乎失敗了,它無力阻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未能阻止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發生,同樣無力阻止1939年二戰的爆發。不過,一戰后,威爾遜給民族主義裝上了國際自由主義的內核——民族自決,拋棄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從保守主義、激進主義手中奪回民族主義的主導權,這是自由主義的一次重大修正。二戰中,羅斯福總統提出了“四大自由”,再次高舉一度消沉的自由主義旗幟,他大膽借鑒社會主義的優點與長處,以“新政”的名義,用改革的方法走出了危機,挽救了資本主義;通過把政治自由和經濟公平聯系起來,使自由主義再次獲得了全新的生命,實現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從而戰勝了納粹主義,進而奠定了打贏冷戰的基礎。自由主義在觀念競合中重放光芒。
也就是說,經過多個世紀的不同觀念的激烈競合,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成為最后的贏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自由主義在維也納體系時期內被俄、普、奧等主要大國視為威脅,直到20世紀后期才獲得政府的偏好,被廣泛視作最為和平的政府形式[16]114以及穩定當今國際局勢的最好保證。自由主義曾一度慘敗,但通過在不斷競合的過程中借鑒、吸收其他觀念精華,不斷實現自我調整,從而煥發出頑強的生命力。同樣,民族主義也曾步入歧途,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結合,直接導致推行這種政策的國家的毀滅,但民族主義轉而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結合,從而徹底改寫了20世紀的政治版圖。
六、 結 語
在本文行將結束之際,不得不探討20世紀社會主義的進程,這對中國有重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直指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病的新型社會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超越與創新。從競合的視角來說,社會主義不僅與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有競爭的一面,更有吸收、消化及合作的一面。而歷史的現實卻是社會主義多數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國家中發展、實踐起來的,挫折在所難免。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在與民族主義結合,完成了原來的革命使命、破壞了舊秩序之后,就必須轉向建設和改革的使命。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還應包括更為根本的現代制度建設;而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鄧小平曾高瞻遠矚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封建是一個長期的斗爭,比打倒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困難得多。”[34]353就當前而言,既然在過去的五百年中,自由主義已是最大贏家,但還遠遠不是福山所宣稱的“歷史的終結”*參見F.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福山在此書中樂觀地宣稱“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及對美好制度的探索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更高、更遠大的理想與社會形態,若能正確、全面地吸收自由主義的精華部分,必將煥發出強大的生命,成為塑造“冷戰”后正在形成的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性觀念,這也是觀念競合過程中的應有之義。因此,看清世界發展之大勢,才是我們研究國際體系變遷的真正意義所在。
此外,我們經常過度強調觀念之間的對立、對抗與競爭,而實際上,不同觀念之間還有保留、繼承與合作的一面。譬如,自由主義是針對封建主義、專制主義,民族主義是相對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事實上,自由主義、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都反對中世紀的教權至上的觀念,如今按自由主義建立起來的近代發達國家也都是政教分離;民族主義戰勝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但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帶來的全球體系、貿易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民族主義者并不反對,或者說是阻擋不住的。另外,主權的觀念盡管早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期便得以確立,并為以后各個時期所繼承,但對它的理解直到“冷戰”時期的世界政治中才達到最高點,主權得到了國家,特別是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極力捍衛,且實際上壓倒了包括人道主義在內的所有其他訴求[16]19。但20世紀90年代的人道主義干涉表明,以前不被接受的干涉方式正在合法化,人權訴求一定程度上壓倒了主權。人權保護已與安全聯結起來,并成為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35]712。這也表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在后“冷戰”、全球化時代已開始退潮。
進一步地看,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在冷戰后全球范圍內并行發展,曾是風光無限。但這一波自由化與全球化也導致全球層面嚴重的經濟與貧富分化,政治極化與社會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反全球化浪潮。反主流、反建制的全球化憤怒力量崛起與反撲,這將是決定未來數十年全球發展的最重要趨勢。應該看到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歐……全球風云突變,這一切均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后果。新自由主義危機直接導致了美國2016年大選成功地刮起了“桑德斯旋風”,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罕見地在自由主義大本營和堡壘的美國開始復興。這位來自佛蒙特這樣小州的參議員、立場超然獨立的“政治異類”,已崛起為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鑒于美國民主黨內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70%均是桑德斯的支持者,因此,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將福利社會主義的種子播灑在年輕的一代人心中,這同時折射出西方發達國家正在進行新一輪自我修復與調整,全球正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在尋找新的方向與突破。
最后,我們不能忽視觀念的局限性及唯觀念論。雖然從近五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看,人類一直不斷努力超越物質力量對人類的制約,但“無論我們是否愿意,物質力量的分配和組成在任何時間點上幫助劃定了可能的行動界限”[10]142。對觀念的這種局限,亞歷山大·溫特進一步形象地指出:“我們可以對這些因素置之不理,就像巴厘人沖向荷蘭人的機槍、波蘭騎兵沖向德國人的坦克一樣。但是這樣做我們自己是要付出代價的。激進建構主義提醒我們要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對待物質制約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物質力量此時此地怎樣制約我們這個同時存在的問題。”[10]142-143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20世紀初便一語中的:“直接影響人的行為的因素不是觀念,而是物質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觀念’造就的‘對世界的認識’卻往往像扳道工一樣起到確定方向的作用,決定著受利益動力驅動的行為運行的軌道。”[36]280
因此,從總體上看,觀念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得到檢驗和發展,才能變為與物質一樣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性觀念是不同觀念與權力相互競合的結果,而國際制度是主導性觀念或國際共識競合的結晶,同時制度的形成及其作用的發揮也取決于物質性權力和利益的博弈和回報。權力結構、制度結構與觀念結構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張力與合力,也就是它們內部亦有充分競合。這正是競合主義要義之所在——從國際進程看,國際關系總體表現為權力分配競合、制度分配競合及觀念分配競合的過程[4]50。不過,權力結構與制度結構只是國際體系的表層結構,觀念結構才是掩蓋于權力結構、制度結構之下更為根本的深層結構。更直接地說,權力結構與制度結構的背后是觀念結構,觀念的根本作用在于建構及定義具有解釋能力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在國際體系變遷過程中,觀念作為深層次因素,始終是影響、塑造國際體系更新與變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1] F.A.von Hayek,TheRoadtoSerfdom, London: G.Routledge & Sons, 1944.
[2]任東來: 《大國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傳統——以美國為例的討論》,《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4期,第16-22頁。[Ren Donglai,″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radition of Thought in the Rise of a Great Power: Taking U.S.A.as an Example,″StrategyandManagement, No.4(2004), pp.16-22.]
[3]門洪華: 《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國際政治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3-142頁。[Men Honghua,″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StudiesofInternationalPolitics, No.2(2004), pp.133-142.]
[4]儲昭根: 《跨層次理論整合:從雙層博弈到雙層競合》,《國際觀察》2016年第5期,第76-93頁。[Chu Zhaogen,″Cross-level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From Two-level Game to Two-level Coopetition,″InternationalReview, No.5(2016), pp.76-93.]
[5]M.L.Cottam, E.Mastors & T.Preston et al.,IntroductiontoPoliticalPsychology,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4.
[6]秦亞青: 《西方國際關系學:知識譜系與理論發展 》,《外交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第9-14頁。[Qin Yaqing,″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West: Genealog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JournalofForeignAffairsCollege, No.3(2003), pp.9-14.]
[7][美]朱迪斯·戈爾茨坦、羅伯特·O.基歐漢編: 《觀念與外交政策:信念、制度與政治變遷》,劉東國、于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J.Goldstein & R.O.Keohane(eds.),IdeasandForeignPolicy:Beliefs,Institutions,andPoliticalChange, trans. by Liu Dongguo & Yu Ju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8][美]羅伯特·杰維斯: 《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R.Jervis,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 trans. by Qin Yaqing,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3.]
[9][美]約瑟夫·S·奈: 《硬權力與軟權力》,門洪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J.S.Nye,HardPowerandSoftPower, trans. by Men Hong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美]亞歷山大·溫特: 《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A.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trans. by Qin Yaq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11]C.Manning,TheNatureofInternational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62.
[12][英]赫德利·布爾: 《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張小明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H.Bull,The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OrderinWorldPolitics, trans. by Zhang Xiaoming,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3.]
[13]方長平: 《英國學派與主流建構主義: 一種比較分析》,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12期,第34-38頁。[Fang Changping,″The English School and Mainstream Constructiv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WorldEconomicsandPolitics, No.12(2004), pp.34-38.]
[14]秦亞青: 《國際體系的延續與變革》,《外交評論》2010年第1期,第1-13頁。[Qin Yaqing,″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ForeignAffairsReview, No.1(2010), pp.1-13.]
[15][英]巴里·布贊: 《英國學派與世界歷史研究》,顏震譯,《史學集刊》2009年第1期 第3-16頁。[B.Buzan,″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by Yan Zhen,CollectedPapersofHistoryStudies, No.1(2009), pp.3-16.]
[16][美]瑪莎·芬尼莫爾: 《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變化》,袁正清、李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M.Finnemore,ThePurposeofIntervention:ChangingBeliefsabouttheUseofForce, trans. by Yuan Zhengqing & Li X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7]M.Finnemore & K.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2, No.4(1998), pp.887-917.
[18][美]瑪莎·費麗莫: 《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袁正清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頁。[M.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rans. by Yuan Zhengq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19][美]馬莎·芬尼莫爾、凱瑟琳·斯金克: 《國際規范的動力與政治變革》,見[美]彼得·卡贊斯坦、羅伯特·基歐漢、斯蒂芬·克拉斯納編: 《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秦亞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M.Finnemore & K.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P.J.Katzenstein, R.O.Keohane & S.D.Krasner(eds.),ExplorationandContestationintheStudyofWorldPolitics, trans. by Qin Yaqi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0]李濱: 《國際體系研究:歷史與現狀》,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Li B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System:HistoryandStatusQuo,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英]昆廷·斯金納: 《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段勝武、張云秋、修海濤等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Q.Skinner,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t, trans. by Duan Shengwu, Zhang Yunqiu & Xiu Haitao et al., Beijing: Qiushi Press, 1989.]
[22]馬克垚主編: 《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Ma Keyao(ed.),TheHistoryofWorldCivilization(Ⅰ),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23]高飛主編: 《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于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Gao Fei(ed.),GentlemanlyDiplomacyinaHarmoniousWorld:ChineseForeignPolicyandtheInternationalSystem,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11.]
[24]劉德斌主編: 《國際關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Liu Debin(ed.),AHist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25][美]杰克遜·J.斯皮瓦格爾: 《西方文明簡史(第4版)》下冊,董仲瑜、施展、韓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J.J.Spielvogel,WesternCivilization:ABriefHistory(4thEdition)(Ⅱ), trans. by Dong Zhongyu, Shi Zhan & Han Ji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陳樂民主編: 《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Chen Lemin(ed.),TheHistoryofWesternDiplomaticThoug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5.]
[27][挪威]托布約爾·克努成: 《國際關系理論史導論》,余萬里、何宗強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T.L.Knutsen,AHist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trans. by Yu Wanli & He Zongqiang,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28][美]約瑟夫·奈: 《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J.S.Nye,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Conflicts: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History, trans. by Zhang Xiaom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9]A.Perlmutter,MakingtheWorldSafeforDemocracy:ACenturyofWilsonianismandItsTotalitarianChallenger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30]儲昭根、于英紅: 《一戰后民族自決原則的公認與效應》,《世界民族》2007年第4期,第8-19頁。[Chu Zhaogen & Yu Yinghong,″The Recogni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Effec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WorldEthno-NationalStudies, No.4(2007), pp.8-19.]
[31][英]安東尼·阿巴拉斯特: 《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曹海軍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A.Arblaster,TheRiseandDeclineofWesternLiberalism, trans. by Cao Haijun et al.,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32]李鐵城、武冰: 《大西洋會議和大西洋憲章》,《世界歷史》1985年第9期,第56-57頁。[Li Tiecheng & Wu Bing,″The Atlantic Conference and Atlantic Charter,″WorldHistory, No.9(1985), pp.56-57.]
[33]李而炳主編: 《21世紀前期中國對外戰略的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版。[Li Erbing(ed.),TheChoiceofChina’sForeignStrategyintheEarly21stCentury,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2004.]
[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CCCPC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ed.),ACollectionofDengXiaoping(1949-1974)(Ⅰ),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35]M.N.Barnett & M.Finnemore,″The Politics, Power, and Patholog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3, No.4(1999), pp.699-732.
[36]M.Weber,″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 https://uk.sagepub.com/sites/default/files/upm-binaries/30619_182tg.pdf, 2016-03-29.
[37]儲昭根: 《競合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新探索》,《太平洋學報》2015年第8期,第43-52頁。[Chu Zhaogen,″Coopetitionism: A New Approach to the IR Theories,″PacificJournal, No.8(2015), pp.43-52.]
Ideas Coo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u Zhaogen
(Center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The coopetition theory holds that the overall IR process is an allocation process of power, institution and Ideas. If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 distribution, it acknowledges its role and import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gardless of IP Cognitive School of the unit level, th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FPA) or the mainstream IR theory—Constructivism and other schools on the system level. However, neither constructivism, the English school, nor Cognitive School can provide a clear language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rough ideas. Therefore, it has some special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in examining the validity of ideas on I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s or ideology history, and in discussing how the coopetition of the idea distribution influences and shapes th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istorical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1648, the coopetition of statism, conservatism, radicalism, na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other ideas, has successively become the dominant concept of four major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Westphalian system, the Vienna system, the Versailles system, and the Yalta system, all of which dominate the use of power and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 in the various periods. It’s also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n the main ideas become the dominant positions in the coopetition. As an integral factor, the idea is always an indispensable force to shape and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tatism was the first to become the dominant idea in Europe. After the Renaissance, Reformation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dominant European ideas transformed from church supremacy to the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 and sovereignty. Statism took the place of the theocentricism, and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was further confirm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The subsequent Enlightenment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and influenced and promoted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in Europe and America. But with the failure of Napoleon in war,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the two subversive forces releas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were then suppressed, and conservatism dominated the Vienna system period. However, conservatism could not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Extreme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militarism and radicalism directly l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overthrew the old order. 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human catastrophes and rebuild peace, U.S.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brought out idealism, which is literally a combination of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shaped and established the Versailles System. With the intensifying coopetition of radicalism and idealism, idealism failed. The combin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produced wild fascism and triggere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general, this period was dominated by radicalism. In World War Ⅱ, U.S.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learned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and put forward the ″Four Freedoms,″ once again raising the once depressed liberal flag. Until the Yalta system after World War Ⅱ, nationalism finally defeated imperialism, while liberalism succeeded over totalitarianism.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tide of statism and nationalism began to ebb in the era of post-cold war and globalization.
Moreover, socialism as a higher and lofty human ideal and social form will rejuvenate the strong youth and vitality if it can correctly and comprehensively absorb the essence of liberalism, and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ideas in shaping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The process of idea coopetition should be part of it. Therefore, correctly grasp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500 years and the future of mankind is essential for us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deas; coopetition;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sm; liberalism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6.03.293
2016-03-29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7-07-17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
儲昭根(http://orcid.org/0000-0002-6420-2328),男,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南海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管理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安全理論、美國全球戰略、非傳統安全與中國對外戰略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