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過云樓家書》的密碼
沈慧瑛
解讀《過云樓家書》的密碼
沈慧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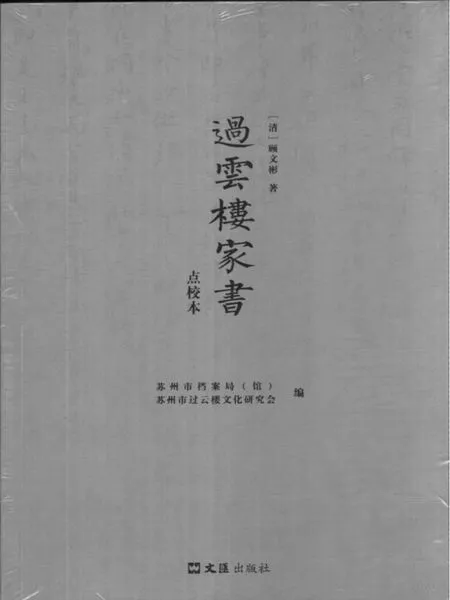
由蘇州市檔案局和蘇州市過云樓文化研究會點校的《過云樓家書》于2016年11月正式出版,此書收錄了顧文彬北上京城候缺及出任寧紹臺道期間寫給兒子顧承的書信527通,起止年代為同治九年(1870)三月至光緒元年(1875)四月。過云樓第一代主人顧文彬生活在沒有網絡的年代,唯有以“見字如面”的方式傳達有關牽掛家人、教育兒孫和買賣書畫的情感與信息。由于顧文彬時為寧紹臺道,故其家書中有不少涉及官場交往、處理政務、收繳關稅及海關邊防等內容,因此《過云樓家書》除研究官宦之家的家風家教、人情往來、民風習俗和過云樓收藏經過之外,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
一
蘇州過云樓因庋藏名家書畫、古籍善本而聞名海內外,前幾年又因《錦繡萬花谷》等珍本以2億余元的天價拍賣成功,再次引起社會轟動。過云樓收藏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要研究過云樓的歷史文化,自然離不開《過云樓日記》《過云樓家書》等第一手文獻資料,尤其是顧文彬與顧承的來往信函,更是詳細反映了他們收藏書畫碑拓、名人手札等精品的全過程。《過云樓家書》形成之期,正是過云樓藏品日漸豐厚之時,有關書畫的來源、價格、價值和鑒賞,以及買賣過程都有詳細記述。
買賣書畫是顧文彬父子信中討論最多的問題,幾乎占了家書絕大部分篇幅,由此可見書畫是顧文彬官宦生涯外的精神與物質支撐。顧文彬受其父顧春江的影響而喜愛書畫,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書畫不僅能陶冶情操,而且通過買賣還能獲利。一旦將書畫經營作為重要行當來做,那么掌握書畫市場的行情對藏家來說非常重要,以便用最合算的價格在最適當的時機買進賣出。顧文彬在京城候缺等待起復的十個月里,經常光顧博古齋、松竹齋、論古齋、德寶齋、潤鑒齋等古玩店鋪,及時將京城的書畫價目、流行情況等告知顧承,以便作好買賣的準備。除北京、杭州、寧波等地方外,上海也是他特別關注的重點,同治十年八月的家信中羅列了上海金蓮生、金蘭生、鄭朗亭、齊玉溪、樓氏等處書畫的情況,要求顧承一一尋訪。當時顧氏收藏書畫的名聲已傳播在外,因此那些做古董生意的人和朋友們經常會主動向他們父子兜售或介紹書畫,以至顧文彬在信中驕傲地對兒子說:“我與汝既具空群之目,復為登高之呼,各處尤物不脛而走。”同樣一件書畫,一旦賣家得知過云樓有意收藏,其價格必然上漲,故而顧文彬在書信中經常關照顧承購買書畫要“以速為妙”,“先搶到手,省得與人競爭。”當他得知上海齊玉溪要出售書畫時,立即致函顧承,說齊家佳物必多,“山樵、石谷兩冊,世間稀有,切勿交臂失之,更恐為捷足者得去,如肯脫手,亟須取歸。”顧文彬求物心切,但又怕別人得知他的想法后居奇待沽,便要求顧承想方設法,“先將物取歸,以杜他人奪取之路。”顧文彬先用自身的藝術修養來判斷書畫的優劣、真偽及其價值,又用商人的精明手段來獲得心愛之物。縱觀過云樓書畫買賣過程,實為斗智斗勇的過程。當然這是在確保真品的情況下才能如此行事。來之不易的藏品自然需要妥善保存,但又不能拒絕朋友們的觀賞要求,傷了感情,故顧文彬明確一般的書畫作品,吳云、李香嚴等朋輩可借去閱覽,但特別珍貴的只能到家中欣賞。在他看來,書畫既怕沾染油漬,又怕水運中出現危險,“一則油具之污可虞,二則據舷之奪可怕,皆當防備。”
有一段時間,顧承對書畫的興趣不如先前那么濃厚,顧文彬頗為傷感,勸導兒子:“書畫一道,汝已闌珊,我尚高興,汝何不從我之興,踴躍從事乎?”某種程度上,他們既是父子,更是書畫同道,父親的財力支撐與兒子的鼎力相助成就了過云樓的傳奇。他們經常在書信中分享鑒定書畫真偽之經驗,顧文彬一度認為對書畫真偽的評判憑第一感覺,在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信中向兒子介紹鑒賞書畫要訣:“我最佩服金蘭坡之言,曰以乍展閱時,一眼望去為準。此最初一念,所謂是非之公心也。及至反復審視,往往有搜尋出來之好處,然此已是轉念,未免有回護之意,而是非之公心淆矣。執此以論定書畫,十得八九。”隨著經驗與教訓的積累,憑第一印象斷定書畫真假的想法得以改變,而是認為“觀古人遺跡,必須虛心細審,若自執己見,一望便決其真偽,必有失眼之處”。顧承長期浸淫書畫,自言鑒定書畫“眼光如電,一閃便知真偽”。顧文彬借顧承曾看走眼沈石田作品為例,教育兒子要謙虛謹慎,必須心細如絲,才能萬無一失。鑒賞力也是書畫藝術修養達到一定高度才會具備,而虛心細心審看才能避免買到贗品或者錯過真跡。比如,顧文彬當初并不欣賞惲南田的一幅山水畫,畫上出有霉跡,畫面沒精氣神,過后發現這是惲南田仿黃公望“陡壑密林圖,山川渾厚,草木華滋,竟是出色之作,題字超逸,亦與芝山圖相埒,幾失交臂”。全面掌握書畫行情,及時做出準確判斷,講究談判技藝是顧氏父子得以將珍貴字畫一網打盡的主要原因。
顧文彬在《過云樓書畫記》中說“書畫之于人,子瞻氏目為煙云過眼者也”。任何個體在人類在歷史的長河中都是滄海一粟,何其渺小,書畫之物確如過眼煙云,然人與物相比,物是永恒的,而人才是物的過客而已。從大處講,顧文彬所言極是,書畫于人也是一場終究要散去的盛宴,然正是他對書畫的癡迷與渴求才有了江南名樓過云樓的崛起。顧氏父子拼眼力拼財力,四外搜羅書畫,且不斷將收藏的中下等書畫出售,“推陳出新,新得之物必皆上駟”,換言之,以贏利所得購買檔次更高的書畫珍品,使過云樓收藏精益求精。“紅塵四合,煙云相連”,緣于顧文彬的執著及其子孫們的努力,才打造出過云樓書畫王國,才使一個多世紀后蘇州博物館舉辦轟動書畫界的《煙云四合——顧氏收藏展》。而顧文彬留下的一部《過云樓家書》則揭秘了一件件書畫作品的前世今生及其與顧氏的緣分,從中也可以一窺顧氏父子高超的藝術修養、雄厚的財力保障、獨到的眼界、精明的經營頭腦和強烈的市場意識。
二
顧文彬除酷愛書畫藝術、擅長詩詞寫字之外,十分懂得生活與處理家事,私密性的家書如實反映他的思想與情感活動。對家人的溫情是《過云樓家書》的看點之一,顧文彬在書信中對家人噓寒問暖,細致呵護,嚴格教育,呈現他為人夫為人長輩的體貼、慈愛、嚴厲的多面性。
首先對妻妾有情有義。他的原配浦夫人病亡之時,顧文彬正在湖北任上,得知浦氏及兩個兒子過世的消息后,顧文彬難以接受。之后再未續弦,而是納妾侍候生活,以示對浦夫人的尊重。當年顧文彬進京做官時,浦夫人一路相陪,之后他重返京城舊居時,觸景生情,告訴顧承:“惟念及汝母與蟾仲夫婦,未免又生傷感。”浦夫人過世多年后,他又請人為其畫像,以志紀念。他先后納蔣氏(早亡)、張氏和浦氏為側室,由于擔心浦氏阻止他北上之舉,故同治九年三月初二黎明,“潛令張姬同行,托言兒輩送我登舟”,浦氏蒙在鼓里。但顧文彬心中放不下浦氏,再三叮囑顧承多加勸慰,并要兒孫多關心浦氏的身體,說“伊腹中素有結塊,大約肝氣所凝,倘或舉發,仍須延醫調治”。之后多封家信中提到浦氏的零花錢、傭人使用與日常起居生活等方面的安排,不得不說顧文彬是個多情周到的丈夫。張氏婚后七年沒有生育,望子心切,郁郁寡歡,顧文彬見此,主動提出將顧承的幼子作為張氏的嗣孫,讓她親自養育,解其憂愁。
其次對兒孫關愛有加。他與浦夫人、蔣氏、浦氏育有七子二女,除二子一女夭折,其余都長大成人。與浦夫人所生的長子、次子皆亡于咸豐十年,故對兒子顧承備加疼愛,在信中時時關心他的身體狀況,并對用藥提出建議。這種疼愛還延續到對家中產婦身體保養及哺乳育兒的具體指導上,全然是個充滿生活經驗的和藹可親的長者。在同治十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封家書中,關心顧承及其妻子朱氏,他說:“天氣炎炎,切勿出門,恐致受暑。汝媳分娩在即,諸須小心,從前產后多病,尤宜預防也。”之后又來信關照:“天氣酷暑,汝媳分娩在邇,務須格外小心,著涼固不可,觸暑尤不可也。”同治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三孫麟誥(顧文彬次子廷熙的次子,在家族行三,俗稱小三房)再次添丁,這個名為則忠的男嬰是顧文彬的第二個曾孫,他得知消息欣喜萬分,牽掛孫媳與曾孫的健康,在八月的家書中叮囑:“小三房產母、小孩諒俱平安,飲食寒暖,必須加意調護,乳如夠吃,以自哺為妙,若用乳嫗,安能如自家小心乎?”顧文彬這一支人丁單薄,其父育有兩子,長兄文榮幼殤,只有顧文彬承繼香火,而今兒子輩只剩下顧承一脈和年幼的八子顧煦,長子又沒有后嗣,人丁興旺是家族的希望所在,能夠四世同堂、后繼有人是顧文彬所夢寐以求的。
再次對孫女教育有方。顧文彬閱歷豐富,深諳處事之道和人情世故,當鐘愛的大孫女顧麟保(小名大麟)即將嫁給好友吳云之孫時,在同治十一年四月的家書交代顧承:“大麟出閣在即,我不能當面告誡,汝代為宜示。大麟素性尚為馴順,此后務當孝順重闈,敬事夫子,持躬宜儉,作事宜勤,謹慎為先,言笑勿茍,……其姑傳聞略有脾氣,尤須加意侍奉,切勿稍有違拗。況生我等閥閱之家,一切規矩禮貌,偶有失錯,便要受人指摘,被人談論,非同小戶人家子女,可以恕其無知也。兩家雖對衡望宇,無事不必時常歸寧,彼家新婦,只此一房,自應常依膝下也。此雖老生常談,而為婦之道實不外乎此。”看似嚴格而絮叨的訓示,實質上是顧文彬對孫女即將開啟新生活的切實關愛與指點。這段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有關為婦之道的“訓誡”今日看來仍有一定道理,如何孝敬長輩,如何勤儉持家,如何謹言慎行,如何增進家庭和睦,也是當下每個女性要學習與遵循的。顧文彬多次強調“家庭之間,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所謂家和萬事興,家風家教影響人的一生,也影響到家庭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
三
如果說對孫女的教育更多側重于婦德,那么對孫子輩的教育則著眼于“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之道了,孫子們是否有出息將涉及顧氏家族未來的發展走向。由于他長期在外做官,無法親自教導孫子輩,故經常在家書中隔空訓導一番,對他們提出具體要求。通讀家書,顧文彬對兒孫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要他們立志向上。所謂志即人生的目標,有了目標就有了前進的方向與動力。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當顧文彬得知孫子們結束考試后荒廢功課,沒有作文,嚴厲警告,說“肯用功否,全在自己立志,志愿上進,自然埋頭用功。志甘下達,自然游蕩虛度”。他認為一個人若一定要老師來監督,那么用功的程度亦是有限的,換言之,外因須通過內因才起作用,內因即是個人的志向,它決定人們的言行。顧文彬在信中要求孫子們即使老師沒來授課,也要“按期作文、作詩、寫字,終日安坐館中,不準在外游蕩,若不聽我言,荒唐如故,即作為不肖論”。
二要他們走科舉之路。他多次在家書中嚴正指出必須“以舉業為正宗”,“與其捐監,不如入泮,為正途也。”顧文彬命令顧承聘請品行端正的老師授業,認為“品行比學問更關緊要”,要求新請的業師吳培卿“嚴立課程,勿因學生年紀已大,從寬優待”,并指示顧承延師要送“聘敬”,辭師則要送“辭敬”,禮節周全,切不可忽略,對老師的尊重體現了顧文彬的重教與為人的理念。他認為一個人想要發達,須要預備發達的本領才行,故他以一個過來人的經驗總結讀書的最佳年齡在二十歲左右,這是一個人學習的黃金時代,過了這個年齡段,即使再勤奮努力,收效也不大,事倍功半,故他要求孫輩“趁此二三年中,埋頭用功,一氣呵成,始不負天付好時光也”。讀書寫字是最基本的功課,他對孫子們作文寫字提出具體規定,按期作文,大題小題“相間而做”,書課以“小楷為重,小楷為應制之要”,考試要用小楷書寫,是必須要學會寫好的技能,而“大字乃應酬之具”,練好小字關系自己科舉前途,寫大字是為別人助興而已,輕重懸殊已然清楚。至于讀什么文章,也作具體規定:“以聽雨軒所選天崇、國初兩種為主,時下墨卷只可略罩正宜書院課藝。校邠諸君與我同考時所刻一部,其中佳作甚多,買一部寄來,俟我選出數十篇,令孫輩讀之,必有進益。”曾在一封家書中接連提問題,諸如孫輩們誰學得最快、老師上課情形、能否按期作文、有無提高等等,關切之情躍然紙上。從讀書、作文、寫字、請師等各個方面提出詳細的規定和要求,目的希望孫輩一舉成名,獲得一官半職,提升顧氏的社會地位,增強家族實力。
三要他們“講究書畫”。顧文彬再三要顧承督促孫子們“舉業之暇”學習鑒賞書畫知識,不要蹉跎歲月,因為書畫是門大學問。顧文彬父子合力開創過云樓的書畫事業,而孫子則屬于守成者,較他們父子有福。所謂創業容易守成難,如果不懂書畫之道,那么孫子們則是有福不能享,更有可能敗掉辛苦打拼來的家業。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書畫知識,就有利于將來書畫事業的發揚光大,他直言不諱:“孫輩講究書畫必須認真,因保守與散去皆用得著。而我家積蓄,此項亦是大宗。否則我現在之極意搜羅皆成虛設矣。”對顧文彬來講,過云樓書畫收藏既有怡親養性的考慮,更有積累資本擴張財富的目的。除了他與顧承精通書畫鑒賞之外,孫輩們尚且缺少這方面的能力,故而“以此為慮”,經常詢問孫輩們研究書畫的進展,家書中經常出現“此事汝等視為緩圖,我卻視為急務也”“務與孫輩講究書畫,切勿視為緩圖”諸如此類的話。當他的想法與顧承產生分歧時,心里煩悶,略帶指責的口吻說:“孫輩講究書畫,我視為要圖,汝等皆視為迂圖。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我未如之何。以后收羅字畫,殊覺心灰興索耳。”責備的語氣中充滿了一個父親、祖父的委屈與無奈,屢次告誡顧承切不可因為孩子們對書畫知識“難于領會而置之”。早在同治九年三月,他就制定研習書畫的“章程”,要求顧承每月舉行六期講座,“按箱捱次將字畫每期取出十件,令四孫環侍,汝與講說,先論其人,次論其書法、畫理,再論其價值。四孫各立一冊,將所講十件詳記于冊,自書分執。行之一年,必皆成內行矣。此乃要事,切須依我行之。”當時麟祥、麟誥、麟軺、麟元四個孫子已經長大,分別為21歲、20歲、20歲、17歲,處于學習的大好時光,然顧文彬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付諸現實,致使他產生不滿情緒,時常在信中發泄一番。其實作為CEO的顧承身上的壓力與責任巨大,他既要掌管大家庭的日常事務,又要執行父親書畫買賣的指令,還得操心典當、收租等其他生意,之后又建造怡園和過云樓,故不可能將顧文彬這個董事長的每一個決策執行到位,父子之間的摩擦在所難免。苦口婆心地教育孫輩,無非希望他們光宗耀祖,希望他們成材,傳承過云樓的文脈與家族的事業。
《過云樓家書》內涵豐富,涉及家庭、社會、官場等方方面面,而書畫是家書中的關鍵詞,因此《過云樓家書》是顧文彬父子有關鑒賞書畫的談藝錄和書畫買賣的生意經,體現了顧氏極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和晚清書畫市場的走向,以及過云樓成為江南第一樓的過程。顧文彬處理家事、教育兒孫等方面的書信,則傳遞以和為貴、勤儉持家、立志上進、嚴禁賭博等思想,這種良好家風的倡導值得今人學習與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