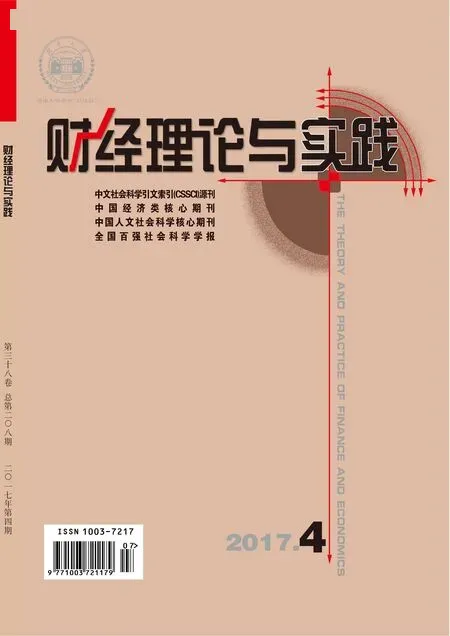公司戰略、大股東持股與財務欺詐
艾永芳,佟孟華,孫光林
(東北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5)*
·財務與會計·
公司戰略、大股東持股與財務欺詐
艾永芳,佟孟華,孫光林
(東北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 遼寧 大連 116025)*
以2001—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企業公司戰略定位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有顯著影響,公司戰略定位越激進,越可能導致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經過穩健性測試后,結果依然成立。進一步研究發現:提高大股東持股比例,可以增強大股東對管理者的“監督效用”,從而提升企業內部監督效率,進而抑制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
公司戰略;財務欺詐;大股東持股
一、引 言
關于上市公司財務欺詐的成因,美國現代內部審計之父Lawrence B.Sawyer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著名的舞弊三角理論,Albrecht和Chad(2004)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提出財務舞弊是由動機、機會和借口等三要素共同作用下產生的[1]。現有文獻大都以此為基礎研究財務欺詐問題。然而,從公司戰略角度研究財務欺詐的文獻并不多見。
已有研究認為,不同的公司戰略會影響企業的盈利模式、高管薪酬以及組織結構[2]。盈利模式與高管薪酬會影響高管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從而影響高管進行財務欺詐的動機[3-5]。另外,組織結構的不同會導致企業內部監督效率的差異,從而影響高管進行財務舞弊的機會[6,7]。如此,公司戰略與企業財務欺詐之間應該是存在著一種影響路徑,即公司戰略影響企業高管進行財務欺詐的動機和機會,進而影響財務欺詐發生的概率。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可以找到導致企業發生財務欺詐行為的內在原因。然而,我國很少有文獻將公司戰略與企業財務欺詐行為結合起來進行深入研究。
基于上述考慮,本文以2001—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了公司戰略定位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首先,相對于比較保守的防御型戰略,比較激進的進攻型戰略更容易發生財務欺詐;其次,大股東持股比例可以影響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的作用程度,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抑制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的影響。
二、文獻綜述及假設提出
(一)文獻綜述
現有關于財務欺詐成因的文獻分別從動機、機會和借口等三種因素入手進行研究。具體來講,企業進行財務造假的動機因素大體包括:快速增長[3]、以股票期權形式激勵高管[4,5]、 外部融資需要[6]、較差的業績表現[8]。企業進行財務造假的機會因素主要有:低效率的監督機制[6]、內部控制缺失[7]。更具體的,比如外部董事比例[9]、 獨立董事規模[10]、董事會規模和董事會持股比例[11]、 監事會規模[12]以及大股東持股[13,14]等。借口因素主要涉及到高管個人因素,比如高管的品德[15]以及高管對造假行為的態度[16]。然而,諸如高管的品德和高管的態度一般難以量化,現有研究大多用高管的背景特征來預測高管的行為,比如高管的學歷[17]、CEO的任職時間[18]、高管性別[19]以及高管年齡[20]。
縱觀上述研究,雖沒有以公司戰略為視角來研究財務欺詐成因的文獻,但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
(二)研究假設提出
Miles等(1978)按照企業對市場變化的反應速度將公司戰略分為進攻型、防御型和分析型[2]。進攻型對市場變化反應最快,防御型反應最慢,分析型介于二者之間,兼具二者的特點,所以分析起來并不方便。鑒于此,與其他研究一樣[21,22],本文將主要關注進攻型戰略和防御型戰略。
不同的公司戰略定位決定了不同的盈利模式、高管薪酬結構以及組織結構,從而導致企業高管進行財務欺詐的動機和機會也不同。因此,本文認為公司戰略會影響企業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率,即相對于比較保守的防御型戰略,比較激進的進攻型戰略更容易發生財務欺詐風險。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進攻型企業研發投入和營銷費用都非常高,同時產出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2],導致了該類企業的業績波動風險非常大[23]。同時,為了鼓勵高管創新和風險承擔,該類企業在高管薪酬結構安排上,與業績掛鉤的浮動薪酬占比較高,而固定工資較低[25]。較高的業績波動風險與較高的浮動薪酬比例造成進攻型企業的高管的貨幣性薪酬波動較大,很可能會因為企業業績不良而獲得非常低的報酬,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高管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從而催生了高管進行財務造假的動機。相對而言,由于采取防御型戰略的企業只在比較狹窄的領域生產經營,并采取漸進式的創新模式,因此該類企業的研發投入和營銷費用相對較少,而且產出也容易預測[2]。同時,在防御型企業的高管薪酬結構中,固定薪酬占比較高[25],因此,高管薪酬相對穩定,從而高管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沖突比較小,進而削弱了其進行財務造假的動機。由此可見,同防御型企業相比,進攻型企業的高管進行財務欺詐的動機更高,因此更容易發生財務造假現象。
其次,進攻型公司通過不斷創新立足于市場,這種戰略定位注定了該類企業的人員流動比較強,導致組織結構不穩定[2]。同時,為了適應企業在多個產品領域同時發展,進攻型企業的組織結構趨于分散化,因此,如何促使各個部門間的協調發展是這類公司面臨的首要問題。鑒于此,進攻型企業在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制定上均重視部門間的協調,而忽略了監督。與之相對應,防御型企業由于產品線比較單一,因此組織結構比較穩定,管理模式趨于集中化,協調機制也比較簡單[2],所以,其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更加注重監督效率。而低效率的監督機制[6]、內部控制缺失[7]等因素為高管隱瞞公司信息提供了機會,大大降低了企業信息的透明度,從而也為財務欺詐創造了條件。由此可以判斷,同防御型企業相比,進攻型企業更有可能發生財務欺詐風險。
通過以上理論分析,提出以下假設:
H1:激進的公司戰略發生財務欺詐的風險更大。
大股東持股作為企業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內部監督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有文獻證明,提高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可以增強大股東監督的主觀能動性。如,Grossman和Hart(1980)認為,比較集中的股權結構通過賦予大股東比較高的剩余索取權,提高其對管理者監督的主觀意識,從而可以緩解第一類代理問題[13]。Shleifer和Vishny(1986)指出,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動力去監督管理者的利己主義行為[14]。王化成等(2015)的研究認為,提高大股東持股比例可以激發其對管理者的“監督效應”,從而降低股東與管理者間的代理成本,進而抑制股價暴跌[25]。由此可見,較高的大股東持股比例可以激發大股東的監督作用,從而有效抑制管理者出于利己目的而進行的財務欺詐行為。那么,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否抑制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呢?為了回答此問題,提出以下假設:
H2:公司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抑制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及來源
選擇我國2001—2015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為研究樣本。之所以從2001年開始,是因為我國從1999年才開始披露公司員工人數相關數據,而員工波動率的計算需最近三年的數據。此外,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被標記為ST的上市公司、相關實證變量有數據缺失的觀察值、上市不滿三年的上市公司。經過以上篩選程序,獲得14321個“公司一年”度觀察值。除研發費用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外,其他所有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為了避免極端值造成的影響,對所有存在離群值的連續性變量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選擇
1.財務欺詐。參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6,27],將CSMAR數據庫違規類型中的“虛構利潤”“虛列資產”“推遲披露”“虛假陳述”“重大遺漏”等違規行為確定為上市公司財務欺詐樣本。通過構造虛擬變量的方式定義財務欺詐指標(Fdum)。當某公司某年度發生以上五項違規行為中的一項或多項,同時還被上海證券交易所、深證證券交易所、證監會或財政部等部門中的一個或多個認定為違規行為時,虛擬變量Fdum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此外,引入受罰程度指標Fdeg。借鑒郝玉貴和陳奇薇(2012)的做法[28],Fdeg的構造方法如下:根據CSMAR系統中的上市公司違規數據庫,若公司當年未因財務欺詐受罰,賦值為“0”;若僅有高管受罰而公司未受罰或公司受罰類型為“其他”, 賦值為“1”;若公司受罰類型為批評或譴責,賦值為“2”;若公司受罰類型為警告、 罰款或沒收違法所得,賦值為“3”。同時受到多種處罰的取最嚴重的受罰類型,一年內多次受罰采用受罰程度最嚴重的一次。
2.公司戰略。遵照Miles等 (1978)對公司戰略的劃分標準[2],借鑒Bentley等(2013)的研究[29],公司戰略變量的構建主要關注以下六個方面的特征: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員工人數與營業收入的比值、 營業收入的歷史增長率、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員工人數的波動性以及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
變量構建過程如下:(1)將上述六個變量取過去三年的移動平均值。(2)對于上述前五個變量,在每一個“年度—行業”樣本中從小到大平均分為5組,最小的賦值為1分,最大的賦值為5分;對于第六個變量,分組方式相反,即最小的賦值為5分,最大的賦值為1分。(3)對于每一個“公司一年度”樣本,將六個變量的分組得分相加,得到6~30分的度量變量——公司戰略(Strategy3)。較高取值的Strategy3意味著較為激進的戰略,而較低取值的Strategy3意味著較為保守的戰略。
出于穩健性考慮,還構造了另一個公司戰略變量Strategy5。構造方法是將上述操作步驟的第1步中的三年移動平均改為五年移動平均,然后重復第二、三步,便得到Strategy5。
3.控制變量。參照已有相關文獻的研究[25],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賬面市值比(BTM)、資產收益率(Roa)、資產負債率(Lev)、是否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n)。所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及度量
(三)檢驗模型的設定
1.假設H1的檢驗模型。采用模型(1)檢驗假設H1。

+YearDum+IndDum+ξi,t
(1)
其中,因變量Fraud,代表公司財務欺詐。本文用財務欺詐啞變量Fdum來度量;同時,用財務欺詐受罰程度Fdeg進行補充測試。當因變量為Fdum時,采用Logit模型進行估計;當因變量為Fdeg時,采用Oligit模型進行估計。解釋變量Strategy為公司戰略,本文分別用Strategy3和Strategy5進行度量。Control為控制變量集。Controlk代表第k個控制變量。同時還加入了年度啞變量和行業啞變量,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用。在模型(1)中,預期β1>0,即公司的戰略越激進,公司越容易發生財務欺詐行為。
2.假設H2的檢驗模型。本文將采用兩種方法檢驗假設H2。
(1)采用模型(2)對假設H2進行檢驗。
Fraudi,t=β0+β1Strategyi,t+β2First

(2)
其中,因變量與模型(1)相同。First為大股東持股比例。交互項First×Strategy度量了大股東持股比例和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的交互作用。若H2成立,則β2<0,即大股東持股有助于削弱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風險的影響。
(2)以全樣本中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的均值作為臨界點,大于均值的樣本代表股權集中組,取值為“1”;小于均值的代表股權分散組,取值為“0”。分別在股權集中組和股權分散組估計模型(1)。如果假設H2成立,那么股權集中組中,公司戰略的系數β1的估計值的顯著性應該弱于股權分散組。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2 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財務欺詐啞變量Fdum的均值為0.09,說明在備選樣本中有9.42%的樣本發生了財務違規,同時,該指標的標準差為0.29,說明該指標在樣本公司中存在較大差異。受懲罰程度指標Fdeg的均值為0.15,標準差為0.52,說明在所選樣本中其變異性也很大。兩個公司戰略指標Strategy3和Strategy5的均值分別為17.36和17.46,標準差分別為3.85和3.89,最小值為6,最大值為30。Pros和Defe的均值分別為0.0623和0.1017,說明樣本中進攻型企業和防御略企業的占比分別為6.23%和10.17%。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的均值為36.98%,與現有研究相差不大[26]。

表2 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
注:所有變量定義見表 1 。
(二)單變量分析
表3列出了單變量分析結果。結果顯示:隨著企業戰略定位激進程度的增加,兩個代表財務欺詐的變量均有顯著上升,表明公司戰略可以影響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即公司戰略越激進,公司越有可能發生財務欺詐,且程度越嚴重。

表3 變量的單變量分析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數值表示t 統計量。
(三)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4 報告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兩個財務欺詐指標與兩個公司戰略指標的相關系數均為正,都至少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激進的公司戰略確實可以加劇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符合假設H1的預期。此外,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與兩個財務欺詐指標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31和-0.032,且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大股東持股有抑制財務欺詐的作用,符合本文預期。其他指標的相關系數均在合理范圍內。

表4 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
(四)回歸分析
1.假設H1的檢驗。表5 報告了檢驗假設H1的回歸結果。首先,以財務欺詐啞變量Fdum和財務欺詐受罰程度Fdeg作為因變量,以公司戰略變量Strategy3為解釋變量。結果顯示,Strategy3的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其次,當以Strategy5作為解釋變量時,其系數依然顯著為正。以上回歸結果表明,公司戰略對企業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有顯著影響,公司戰略越激進,企業越可能發生財務欺詐行為。這與本文假設H1的預期一致。
2.對假設H2的檢驗結果
(1)交互項分析結果。表6 列出了對假設H2檢驗的交互項分析結果。結果顯示無論是以Fdum作為因變量,還是以Fdeg作為因變量,兩個交互項指標First×strategy3和First×strategy5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說明,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確實可以抑制公司戰略對企業財務欺詐發生率的影響,這正符合假設H2的預期。

表5 檢驗假設H1的回歸分析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顯著,括號內數值表示Z統計量,以下類同。

表6 假設H2檢驗結果(交互項分析)

表7 假設H2檢驗結果(股權集中度對比分析)
(2)基于股權集中度的分組回歸結果。表7 給出了針對假設H2的基于股權集中度的分組回歸結果。在股權集中組的四個回歸模型中,兩個代表公司戰略的變量Strategy3和Strategy5的系數均不顯著。而在股權分散組的四個回歸模型中,Strategy3和Strategy5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以上結果表明,當公司的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時,大股東對高管的監督作用,可以抑制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而當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時,大股東對高管的監督作用減弱,使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的促進作用得以顯現。這同樣也支持假設H2的預期。
五、穩健性檢驗
為提高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對上述結果進行檢驗。分別以啞變量Pros和Defe作為公司戰略的度量,并將二者引入到回歸模型中。其中,Pros代表進攻型戰略,Defe代表防御型戰略。回歸結果見表8 。首先,在全樣本中,當以Fdum作為因變量時,Pros的系數為正,并接近顯著;當以Fdeg為因變量時,Pros的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進攻型戰略會加劇企業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另外,無論以Fdum為因變量,還是以Fdeg為因變量,Defe的系數均在1%下顯著為負。這表明,采取防御型戰略的企業確實不易發生財務欺詐現象。總之,以上回歸結果與假設H1預期一致。其次,通過將股權集中組和股權分散組的回歸結果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在股權集中組中,Pros的系數雖為正,但并不顯著;在股權分散組中,Pros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說明,大股東持股比例較高的情況下,即便企業采取的公司戰略比較激進也不會顯著增加企業財務欺詐行為的發生率。此結果支持假設H2。此外,Defe的回歸系數在股權集中組和股權分散組之間并不存在顯著差異,并且無論以Fdum為因變量,還是以Fdeg為因變量,其系數值均顯著為負。該結果并不違背假設H2,因為Defe代表的防御型戰略無論從財務欺詐的動機方面考慮,還是從發生財務欺詐的機會方面考慮,均不易發生財務欺詐現象,所以大股東的治理作用不會對該類企業產生顯著影響。

表8 公司戰略不同測度方法下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限于篇幅,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未列出。
六、結論
以上以2001—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公司戰略對上市公司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司戰略對上市公司財務欺詐行為有顯著影響,企業采取的公司戰略越激進,越有可能發生財務欺詐行為,經過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然成立。同時,結合公司戰略影響財務欺詐行為的內在機理以及大股東在內部監督中的作用,本文探討了大股東持股在公司戰略對企業財務欺詐行為影響過程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提高大股東持股比例,可以更大限度地發揮大股東的監督作用,從而可以有效地削弱公司戰略對財務欺詐行為的影響。
[1] Albrecht,Chad O.Fraud examination & prevention[M].Thomson/South-Western,2004.
[2] Miles R E,Snow C C,Meyer A D.Organizational strategy,structure,and proc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1978,3(3):546-562.
[3] Bell T B,Carcello J V.A decision aid for assessing the likelihood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J].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00,19(1):169-184.
[4] Burns N,Kedia S.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on misreporting[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4,79(1):35-67.
[5] Efendi J,Srivastava A,Swanson E P.Why do corporate managers misstate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 role of option compensation and other factors[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7,85(3):667-708.
[6] Dechow P M,Sloan R G,Sweeney A P.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arnings manipulation:an analysis of firms subject to enforcement actions by the SEC[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6,13(1):1-36.
[7] Loebbecke J K,Eining M M,Willingham J J.Auditors’experience with material irregularities:frequency,nature and detectability[J].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1989,9(1):1-28.
[8] Rosner R L.Earnings manipulation in failing firm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3,20(2): 361-408.
[9] 韋琳,徐立文,劉佳.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的識別——基于三角形理論的實證研究[J].審計研究,2011(2):100-108.
[10] 陳國欣,呂占甲,何峰.財務報告舞弊識別的實證研究——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經驗數據[J].審計研究,2007(3):88-93.
[11] 楊清香,俞麟,陳娜.董事會特征與財務舞弊——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09(7):64-70.
[12] 吳革,葉陳剛.財務報告舞弊的特征指標研究: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審計研究,2008(6):34-41.
[13] Grossman S J,Hart O D.Take-over bids,the free rider problem,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11(1):42-64.
[14] Shleifer A,Vishny R W.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J].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1986,94(3):461-488.
[15] Hernandez J R,Groot T.How trust underpins auditor fraud risk assessments[R].Working paper,2007.
[16] Gillett P R,Uddin N.CFO intentions of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J].Accounting Horizons,2005,24(1):55-75.
[17] 李若山,祁新娥.對當前我國企業舞弊問題的實證調查[J].審計研究,2002(2):17-22.
[18] 楊薇,姚濤.公司治理與財務舞弊的關系——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2(5):24-30.
[19] 楊星.高管團隊背景特征、薪酬激勵與內部控制有效性[J].商業會計,2013(12):82-84.
[20] 盧馨,李慧敏,陳爍輝.高管背景特征與財務舞弊行為的研究——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5(6):58-68.
[21] Ittner C D,Rajan M V.The choice of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annual bonus contracts[J].Accounting Review,1997,72(2):231-255.
[22] 孫健,王百強,曹豐,劉向強.公司戰略影響盈余管理嗎?[J].管理世界,2016,270(3):160-169.
[23] Hambrick D C.Some tests of the effectiveness and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miles and snow’s strategic typ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3,26(1):5-26.
[24] Singh P,Agarwal N C.The effects of firm strategy on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J].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02,19(1): 42-56.
[25] 王化成,曹豐,葉康濤.監督還是掏空: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股價崩盤風險[J].管理世界,2015(2):45-57.
[26] 汪昌云,孫艷梅.代理沖突、公司治理和上市公司財務欺詐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0(7):130-143.
[27] 辛清泉,黃曼麗,易浩然.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與獨立董事監管處罰——基于獨立董事個體視角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3(5):131-143.
[28] 郝玉貴,陳奇薇.上市公司財務舞弊受罰強度與審計風險定價——基于中國證監會2006—2011年行政處罰案的研究[J].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7-12.
[29] Bentley K A,Omer T C,Sharp N Y.Business strategy,financial reporting irregularities,and audit effort[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3,30(2): 780-817.
(責任編輯:漆玲瓊)
Corporate Strategy,Major Shareholders and Financial Fraud
AI Yongfang,TONG Menghua,SUN Guanglin
(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Liaoning116025,China)
This paper us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1 to 2015 in China’s capital market as the sample,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financial fraud.It comes to the results as follows:firstly,the corporate strategy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inancial fraud; the more radical of corporate strategic positioning,the more likely the companies financial fraud occurs; furthermore,an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the result remains valid.Secondly,improving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strong shareholders c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effect” of major shareholders to managers,which will improve enterprise internal supervision efficiency,thereby inhibiting the impact of the corporate strategy on financial fraud.
corporate strategy;financial fraud;major shareholders
2016-12-1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4AZD089).
艾永芳(1984—),男,滿族,河北承德人,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實證金融與公司治理;佟孟華(1965—),女,吉林白城人,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數理金融與實證金融;孫光林(1988—),男,新疆伊犁人,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理金融與實證金融。
F270
A
1003-7217(2017)04-007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