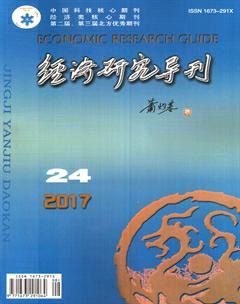碳足跡、人力資本與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
張頌心
摘 要:基于碳足跡的視角,通過對調查樣本區域內20個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及其低碳特征的比較分析,考察碳足跡強度、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影響強度及其作用方向,提出以碳足跡和人力資本投入的雙向耦合提升傳統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思路及對策。
關鍵詞:碳足跡;人力資本;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
中圖分類號:F2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24-0063-05
引言
商貿物流園區有別于傳統的工業園、生態工業園,其競爭力的來源一直廣為學界探討,主要包括三個維度:一是協同耦合的視角,認為商貿物流園區屬于其他類型工業園區的輔助配合模塊,其競爭力源于專業分工、生產性服務業嵌入制造業鏈條中帶來的增量收益(Dimond,2011);二是綠色經濟的外溢性視角,認為商貿物流園區本質上是加工與服務構成的商務社群,它們通過環境與資源管理合作,尋求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增加(Lowe、Moran,2000);三是精明增長的視角,認為商貿物流園區的存在,本質上是借助低碳經濟與人力資本的高效投入,通過改變生產函數性狀,實現投入—產出效率的最大化。
上述觀點各有其可取之處,從各類園區企業間的共生關系和基于園區清潔生產中心信息傳遞機制的效率的角度,本研究認為低碳經濟的低排放、低消耗、高產出是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直接體現,也是其有別于傳統工業園區的關鍵;而此過程中的資金、人力資源和企業家精神的投入,是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核心載體。本研究嘗試考察上述三者之間的關系,以DEA投入產出方法研究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關鍵來源。研究主體包含四個部分:一是對研究相關背景及其學術史的梳理,探查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來源,二是通過對調查樣本區域內53個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低碳特征及人力資本投入的測度,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同時分別考察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的引致因素;三是區分碳足跡強度與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影響途徑,包括不同強度的低碳投入與不同特征的人力資本投入之間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影響效果;四是與生態工業園進行比較研究,國外學者對工業園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在承認并接受生態工業園區的目標是在最小化(企業)的環境影響的同時提高其經濟效益;其方法主要通過對園區內的基礎設施和園區企業的綠色設計、清潔生產、污染預防、能源有效使用及企業內部和企業間物質、能量等要素的交換與利用,而商貿物流園在具備低碳效應的基礎上也存在著人力資本持續升值的潛在能力。
一、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低碳特征及人力資本投入的測度方法
本研究依據《中國園區黃頁》中相關招商引資和介紹信息,圍繞商貿園區、物流園區選取了揚州市江都區商貿物流園、廣西梧州市商貿物流園區、承德國際商貿物流園區等20個商貿物流園,確保其具備橫向可比性。按照研究框架,筆者建立了如下指標庫進行研究(見下頁表1)。
指標方案從發展能力、創新能力、市場開拓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等四個維度形成了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的完整認識,研究采取年鑒梳理、專家評分等方式,對涉及的園區上述指標進行了梳理和整合,按照AHP方法形成了總體認知。
在對商貿物流園區低碳特征的考察方面,本研究引入了碳足跡分析法。該方法近年來引入到低碳經濟、能源經濟領域,包括投出產出法、碳排放跟蹤法等不同手段。從經濟核算角度,采取WRI(世界資源研究所)的方法,將商貿物流園區的碳足跡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源于商貿物流園區在提供對外服務和日常運營運輸過程中的直接碳排放;第二層面是將上述直接能源排放向其上游延伸,即為獲得上述能源所耗費的各類資源能源的總和;第三層面將其拓展到工業部門低碳產業鏈中,即由于商貿物流園區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存在,所帶來的能源資源節約的經濟價值。
循環經濟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物質閉路循環和能量梯次使用為特征,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其目的是通過資源高效和循環利用,實現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護環境,實現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其基礎模型可描述如下(見下圖)。
在整個循環經濟基礎過程中,模型中的減量化(Reduce)原則是指,作為輸入端,旨在減少進行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物質數量,所以又叫減物質化。如在資源利用過程中常有資源開發地深加工、能源進行本地轉化和二次轉化等,就屬于循環經濟的起點。
再利用(Reuse)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倡導物質和能量盡可能“復用”,從而減少這個社會生產消費過程中的耗用量。常見如再利用、多次利用等工作,以及對貧礦的高效開發等。
再循環(Recycle)原則屬于輸出端,通過將廢棄物變成資源以減少最終處理量,這個過程與資源化的過程相適應,由消費者和生產者端通過購買用最大比例消費后再生資源制成品,使循環經濟實現閉路循環,從而減少成本支出。
本研究采取投入—產出復合的碳足跡分析方法,實施細節包括:
首先,設立碳足跡消耗減排矩陣,并計算商貿物流園區總產出情況:
X=(I+A+A×A+A×A×A+...)y=(I-A)-1y
其中,X為各商貿物流園區的實際產出情況,I表示各類能源物資的消耗矩陣,y表示最終需求,A×y為該部門的直接產出,A×A×y表示該部門的間接產出。
其次,根據上述闡明的三個層面,分別計算對應的碳足跡:
第一層面:bi=Ri(I)y=Riy
第二層面:bi=Ri(I+A)y
第三層面:bi=Rix=Ri(I-A)-1y
上述公式中,bi為碳足跡,Ri為CO2排放矩陣,該矩陣的對角線值表示商貿物流園區各類生產性服務業的單位產值CO2排放量。通過本研究中53個商貿物流園區樣本值的代入,就可以分層次的驗證其低碳特征和綠色效益。endprint
而在人力資本的形成和測度方面(見表2),主要包括人才發展相關指標,考察各園區人力資本形成的速率及其強度,作為商貿物流園區核心競爭力來源之一,高素質、能夠提供附加增值服務的人力資本,有助于占據產業鏈條上游,實現能級躍遷。
通過上述方式,將形成關于商貿物流園區碳足跡、人力資本與其競爭績效的測度方式,其中商貿物流園區碳足跡需要借助矩陣工具進行運算換算,其他借助SPSS可展開分析。
二、商貿物流園區碳足跡、人力資本與其競爭績效的耦合關聯
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分類考察了碳足跡強度、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影響強度及其作用方向。按照上述已有的數據,本研究采用DEA分析等方法研究三者之間的相對效率。CCR模型假設了規模報酬不變計算所得的效率稱為綜合技術效率,反映的是現有的投入對應于產出是否冗余。本研究旨在考察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影響的核心影響因素,因此采用投入—產出的一般均衡模型進行求解。以人力資本和碳足跡強度為投入量,以各園區競爭績效為產出量。利用CCR模型求解結果(見下頁表3)。
下頁表3中的影子價格是對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評價中,對于系統內碳足跡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等兩類資源輸入的反饋,其中碳足跡強度與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體現為:一是較低的碳足跡可能意味著較低的能耗,有助于通過降低交易費用、運輸距離的方式強化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二是較低的碳足跡可能意味著較少的商貿物流規模,可能不利于園區競爭力的提高。
在下頁表3中,若某項資源的影子價格小于0,表明該資源在系統內冗余,無法內生達成效率安排。從上述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商貿物流園區的競爭績效與其自身的碳足跡強度、人力資本投入高度相關,體現為:一是碳足跡強度并未成為影響其競爭力的制約因素,而是作為投入有效率產出的一部分,對于商貿、物流等不同類別的園區而言影響效果也存在著差異,對于物流園區有著更強的競爭力提升效果;二是人力資本豐度是影響我國目前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的重要指標,在本研究涉及的20個園區中,人力資本要素與碳足跡強度存在著耦合配比關系,即較高的人力資本存量與較低的碳排放強度之間往往能夠形成更有效率的產出強度。
三、碳足跡、人力資本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績效驅動效率
更進一步來說,按照下頁表3中不同園區類型,將其碳足跡強度劃分為高中低三組分別研究,考察碳足跡強度與人力資本投入對于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的影響途徑是否存在差異,即較低的碳足跡強度是否能夠顯著增強商貿物流園區的輻射能力;在園區發展特征減量化、循環化、低碳化的階段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何種因素。在對本研究涉及的園區按照碳足跡排放強度分組后,可以發現不同的碳足跡在控制了人力資本豐度及其他相關變量后仍體現為內在異質性,即碳足跡排放量已成為影響園區競爭績效的核心驅動因素(見下頁表4)。盡管其內在傳導機理存在兩種反向因果循環,但實證結果已表明,在較高的人力資本投入強度下,較低的碳足跡強度能夠顯著增強商貿物流園區的輻射能力。
此外,將涉及的園區按照碳足跡、人力資本豐度進行了兩兩分組,以表3中不同園區的中位數指標,按照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對碳足跡和人力資本豐度在不同園區的保有存量做了劃分,結論并不顯著,即二者不存在相互耦合或正向促進關系。這可能意味著在園區發展特征減量化、循環化、低碳化的階段中,競爭力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投入的質量而非數量性指標。
四、商貿物流園區提升競爭績效的建議
綜上所述,通過以碳足跡和人力資本投入的雙向耦合來提升傳統商貿物流園區的競爭力,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加強商貿物流園區的生態園區建設,最本質的就是要認清企業間的相互作用,以及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作用,通過二氧化碳吸收、材料交換和廢棄物統一處理,從而減少環境污染,達到減碳的目的。商貿物流園區,應該通過共生及層疊實現能量效率的最大化,園區內的成員之間要有業務上的互補性或者存在一定的供求關系。
其次,我國傳統商貿物流園區需要將低碳經濟作為長期發展方向,體現為采取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3R原則應用于園區運營和提升的各方面之中。如通過橫向的耦合,使生態產業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網狀結構,從而減少廢棄物的排放等;在園區內進行整合后,使得園區內產品的種類或者說服務的規模,對資源供應、市場需求以及外在環境的隨機波動具有較大的彈性,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當然,其促進作用體現為較低的碳足跡意味著較低的能耗,有助于通過降低交易費用、運輸距離的方式強化商貿物流園區競爭力,也意味著人力資本的加速形成。
再次,在園區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中,需要依托不同的發展稟賦與階段,包括在較低的人力資本集聚水平下,應當將人力要素集聚擺在首位,在此之后再提升能源資源集約效率,以達成最大化的競爭績效提升效果。
參考文獻:
[1] 戴亦欣.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的必要性和治理模式分析[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3).
[2] 王微,林劍藝,崔勝輝,吝濤.碳足跡分析方法研究綜述[J].環境科學與技術,2010,(7).
[3] 伏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際市場依存與制造業升級——基于我國長江經濟帶的實證分析[J].商業經濟研究,2015,(27).
[4] 胡永仕,王健.商貿物流園區:內涵、形成機理及投融資模式[J].中國水運,2010,(11).
[5] 張倩,王茂春.省際邊界縣建設商貿物流園區的研究與探討[J].現代商業,2015,(25).
[6] 伏虎.我國煤層氣清潔開發利用法規障礙及政策建議[J].中國國土資源經濟,2015,(1).
[7] 嚴先鋒.生產性服務業、制造業與農村服務業的聯動新探索[J].經濟研究參考,2014,(59).
[8] 王妍.商貿型物流園區運營績效評價研究[D].秦皇島:燕山大學,2014.
[9] 沈滿洪,高登奎.生態經濟學[M].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陳丹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