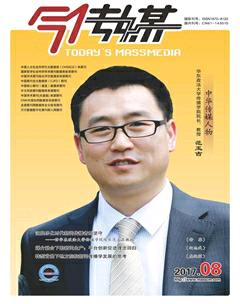大眾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問題探究
婁冠群
摘 要:現代社會進入一個不可控的風險社會,一系列科學技術與環境安全問題成為新聞傳播中的重點內容,新聞媒體在傳播風險信息時或由于一些失范行為造成許多新的風險,或放大風險加劇受眾的不安和恐懼心理,或將官方與民間兩個話語場域放置對立面激化社會矛盾。本文從媒介失范角度入手,淺析這些失范現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的可行性意見,以此減少媒體在傳播中造成的新的風險。
關鍵詞:風險傳播;風險社會;媒介倫理
中圖分類號: G20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08-0054-02
當今世界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政治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信息化程度越來越高,麥克盧漢預言的“地球村”成為現實。這種以科技為源頭具有不穩定與不確定性的現代風險,所產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系統性和擴散性。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階段,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都在發生深刻改變,同時也進入現代風險的高發期,毋庸置疑風險正成為當代社會的主要特征。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出版社的出版物NRC 在1989年將風險傳播定義為:“信息和觀點在個體、群體、機構之間相互影響的交換過程[1]。大眾媒介在建構風險的過程當中由于受控于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往往在傳播風險揭示事實的過程中帶有偏向。貝克肯定了大眾傳媒在傳播風險時起到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毫不懷疑大眾傳媒在建構風險傳遞風險時的欺騙性:一方面媒介將重新建構的風險社會進一步呈現在大眾面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知識和風險的不確定,加劇了受眾心理負擔和社會危機。
一、媒介在風險傳播中的失范表現
1.媒體跟風報道、密集性傳播風險信息。弗蘭克.富里迪在《恐懼》中表示,今日社會的恐懼是一個接一個,間隔時間短,目標范圍廣。受眾是風險的承受群體,大眾媒介是風險信息的控制群體。大眾傳媒作為有能力控制和降低風險的組織,在傳播風險信息的過程中有過度之嫌。新聞媒體在報道“校園暴力事件”或“校車安全事件”中,根據人民網-輿情頻道的盤點:2016年全年,全國僅經媒體報道的影響較大的校園暴力事件就有87起。媒體傾向于集中在某一時間段內對風險信息進行大量、集中報道。大眾媒體通過對風險信息進行解構和重構,原本旨在向社會大眾傳遞風險信息,但其用訴諸生存、生命恐懼的報道方式切中受眾的危機想象,這樣很難減弱人們對不確定性風險的感知,反而強化了對風險的恐懼造成受眾心理不適。
2.新媒體強調公眾立場極化批評場域。由于不同新聞媒體有不同新聞框架,所以大眾媒體對現實風險的呈現并不是完全客觀的“鏡子式”反映。如果媒體對風險信息的披露不全面、不平衡,會導致受眾無法正確判斷風險形勢造成受眾的理解誤區,這樣在傳播風險意義和信息時就產生了新的風險。“傳統媒體在風險故事中表現公共立場的35篇,表現政府立場的25篇”[2],通常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偏向以政府為代表的官方立場,而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更偏向普通受眾,他們要求民主參與、公開信息、參與政策制定和風險評估。新媒體相比傳統媒體滲透性更強、傳播范圍更廣,影響力更大,當新媒體的風險認知模型傾向展示公眾立場,而傳統媒體在傳達官方聲音比較刻板、機械,缺少有效回應方式時,就會引起公眾懷疑激化其抵觸心理,導致官方和民間的兩個話語場域溝通不暢。
3.媒體用弱勢群體的視覺形象放大風險。由于人們感知風險主要通過個人直接體驗和大眾媒介兩種渠道,當個人缺少直接體驗時媒體作為次級體驗就成為社會風險建構的重要部分。“持久的心理認同和態度是風險次級效應的重要表現方面。當一個事件定格成一個記憶點后,其帶來的風險體驗是持久的。情感波動、心理沖擊易在集體記憶中被觸發,從而增強個體的風險感知。[3]”無論是新媒體還是傳統媒體在傳達風險信息時都需要借助一些視覺形象來喚醒大眾的情感共鳴激起大眾的風險認知。媒體通常選擇借助老人、女性和兒童等弱勢群體的形象作風險信息載體,從而快速呈現風險并引發關注。2003年安徽阜陽的劣質奶粉事件,農村老人自殺等問題就是媒體將社會中隱匿的風險通過兒童、老人等形象具像化呈現出來,這種對弱勢群體不同程度的消費也放大強化了社會風險的程度。
4.報道偏向日常邏輯缺少科學性。在涉及科技安全和環境安全的風險傳播中,媒體偏向從公眾的日常邏輯出發,基于特定認知通路對信息進行選擇性理解和傳播,缺乏有效的科學知識傳播。“信任不平衡理論認為人們在進行風險判斷時,優先接受負面信息刺激,形成對風險技術的不信任態度。[4]”公眾在涉及自身生存倫理的問題上,傾向于優先接受媒體傳播的信息并形成認知成見,而不是尋找專業知識證據做出理性判斷。例如,2013年到2014年著名公眾人物崔永元和方舟子對轉基因食品問題展開激烈爭論,整個事件中許多科學家和科普人士明確批評了崔永元的觀點,但微博上的支持崔永元并質疑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的網友依然占多數。又如在各地爆發的“反px”項目的問題上,盡管專家盡力以科普的方式為px項目證明其建設的合理性和風險可控,但仍然激起群眾的抵觸情緒。風險傳播中科學推崇數據精確保持價值中立,而公眾反對技術的絕對權威主張開放多元。在科學技術發展與生命安全的博弈中,普通受眾比較科學家提供的科學事實,基于情感信任上更傾向基于在大眾傳媒傳播的信息上做判斷。
二、媒體風險傳播失范的原因
1.新聞報道行為不規范。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期,風險問題發生率高。一方面互聯網的無限放大和縱容極化場域,另一方面媒體對政府不作為等消極形象的塑造等,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人們對官方風險監管的信心。
大眾媒體在建構風險基于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迎合受眾需要,制造輿論聲勢影響正確的政策實施。長期報道行為不規范使受眾對媒體塑造的這種社會的“集體不負責任”的組織形象產生消極對抗,“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我們對社會中提供信息和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如果這兩大系統出現失衡,現代社會就有可能陷入高速緊張和突發性事件所帶來的混亂風險中。[5]”endprint
2.信息建構和呈現表現失衡。貝內特認為:“新聞報道中存在著四種影響受眾對新聞真正理解的信息問題,即個人化、戲劇化、碎片化和標準化。”大眾傳媒所建構的媒介環境在傳播信息過程中按照先后次序對特定的事物給予突出強調,改變議程設置的路徑。在一個商業化的媒介生態環境中,媒體在選擇新聞時不僅考慮事實因素,還要考慮新鮮、趣味等經濟因素。
在報道上的失衡會造成媒介生態失調、社會生態失調等一系列問題,過量、過度、娛樂性、偏向性的報道會也會導致公眾的認知偏向引起社會信任危機,加劇社會各階層之間矛盾。失衡報道還會剝奪受眾對信息的知情權,讓受眾在面臨風險時因缺乏對風險的完整認知,無法做出理性的正確的判斷,長此以往反而助長社會負面情緒。傳媒應該致力于平衡科學、利益機構和公眾之間的矛盾,減少個人對風險的不安和恐懼。
3.媒體科學知識不足。斯科特.拉什提醒:“始料不及的風險和危機將不再是工業社會的物質化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和危險,而是從信息領域、從生物科技領域、從通訊和軟件領域產生出的新的風險和危機。[6]”理性對話和科學知識在信息傳播中一直屬于稀缺資源,由于科學的安全性存在不同的解釋和局限性,所以即便一個被驗證的科學結果也不會被公眾視為絕對可信。不同媒體偏向不同解釋,大相徑庭的科學爭議往往混淆了受眾視聽,增加科學技術的不確定和公眾的心里不安甚至憤怒情緒。
在這里一方面網絡“噴子”利用社交媒體煽動民意,另一方面傳媒工作者自身缺乏一定的科學素養,在傳播風險信息時追求簡單不求甚解。在涉及科學的風險問題上,媒介工作者在科學知識的二次傳播中易造成信息變形,導致技術和民主對話不暢通。尤其是以社交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一味放大受眾的質疑聲,弱化專家、科學家對科學技術的解釋說明,削減以科學和政府主導的風險監管組織的意見,實際上這種媒介話語權的不平等,也阻礙了人們全面了解風險信息,影響人們對風險的理性判斷。
三、大眾傳媒的規范
風險傳播要彌合風險專家和公眾之間的知識差異,大眾媒體就要做好社會的瞭望臺。既要讓社會風險可知、可見、可控,又要消除受眾知識的不平衡和風險本身的不確定性。及時傳遞風險信息、有效解決風險問題,不僅需要健康的社會環境也需要健康的媒介環境。
一是媒體在傳遞風險時要堅持公開、及時、客觀、平衡的報道原則,確保多種信息渠道多種信息能夠相互制約相互印證,削減信息的不確定性減輕公眾面對風險時的心理不適。此外報道視角也要多元化,給各方公平發言的機會,客觀陳述無所偏向,幫助受眾全面認識風險問題做出正確判斷。
二是溝通政治信息、傳遞科學聲音時,媒體既要站在公眾立場提出意見,幫助公眾積極參與管理決策,形成健康的討論環境,也要站在政府和組織的立場,積極搭建第三方對話平臺,及時回應公眾的提問消除公眾質疑,做好政府和公眾之間溝通的橋梁保證信息透明渠道暢通。
三是媒介工作者和公眾都應該提高自身媒介素養和科學素養,增加科學知識學會理性發言。在涉及專業問題時,媒體工作者不能做簡單化碎片化處理,更不能將娛樂取悅大眾放在第一,要以審慎的態度對待科學問題。及時查閱相關資料、咨詢相關專家做好科學信息的二次傳播,盡量把復雜深奧的科學知識講清楚講完整講正確,減少在科學知識傳播中的信息變形,培養科學邏輯、教育說服公眾與科學技術共識結盟。
四是隨著互聯網的高速發展,信息的生產、傳播和獲取的成本都大大降低,更多的科學自媒體應該加入到風險傳播中,積極對社會大眾進行有效科普。公眾可以主動關注一些科普網站,比如果殼、知乎、松鼠科學會、機器之心等新媒體,同時傳統媒體、門戶網站等也可以和各大高校、中科院、社會院等相關科學機構、組織展開信息、知識上的合作,在風險問題上強強聯手積極發聲。
參考文獻:
[1] 喻國明,王威.危機管理中的風險傳播趨同效應分析[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
[2] 曾繁旭,戴佳,楊宇非.風險傳播中的專家與公眾 px事件中的風險故事競爭[J].新聞記者,2015(9).
[3] 周敏,王陽,何謙.風險傳播圖景中的童年 兒童影像的建構 再現政治與傳播倫理[J].國際新聞界,2016(12).
[4] 賈鶴鵬,范敬群,閆雋.風險傳播中知識、信任與價值的互動——以轉基因為例[J].當代傳播,2015(3).
[5] 杜建華.風險傳播悖論與平衡報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態視角的考察[J].當代傳播,2012(1).
[6] (英)斯科特.拉什.風險社會和風險文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4).
[責任編輯:思涵]endprint